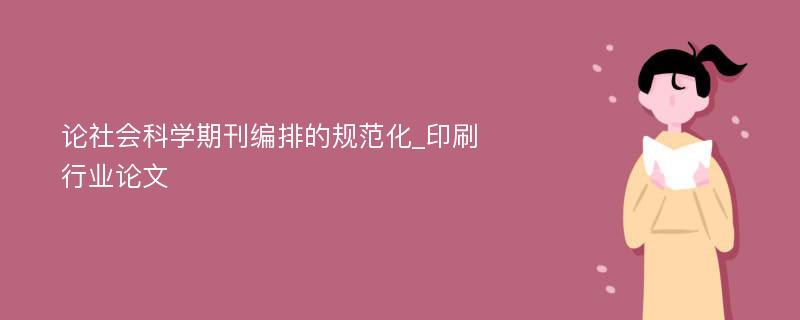
评“社科期刊编排规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4-0151-08
近几年来,在社会科学期刊界尤其是文科学报界,最大的热点话题恐怕就是所谓的“撰稿与编排规范化”了。一般认为社科期刊编排规范化最早可追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自然科学期刊编排规范化。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张积玉先生起草了《陕西省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试行稿),从而开“社科期刊编排规范化”的先河,后来他又受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后改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委托,起草了《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试行稿),于1990年6月由当时的研究会印发各会员单位“参考试行”。1994年,已是文科学报研究会核心成员的张积玉先生出版了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社科期刊撰稿与编辑规范十二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十二讲》),应该看到,在当时,张先生推荐给我们的仍然是一套比较尊重纸质期刊编排规律和编排传统,或者说与传统较为衔接的“社科期刊撰稿与编辑规范”。
然而到了1999年,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成化全文电子期刊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电子杂志社,将自己企业版的基于电子网络平台的“编排规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简称CAJ-CD规范),通过新闻出版署推荐给“入编的”印刷型(纸质)期刊。由于这套规范是基于电子网络平台而生成,就其功能而言完全是用来“检索和评价”的,其数据库属性显而易见,其与印刷型期刊的编排传统和实际可谓南辕北辙。而张积玉先生则作为这套光盘规范的三个起草人之一,显然是负责涉及人文社科方面的规范的制定。次年,他又作为惟一的起草人,在CAJ-CD规范的基础上制作完成了人文社科学报领域的“行业法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或“新规范”),并很快由教育部办公厅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并在学报界强力推行,从而将一种具有企业背景的“规范”以一种欠“规范”的、带有明显政府行为的方式强加给了文科学报以及许许多多为文科学报写稿的作者。
在展开充分的论述之前,笔者有必要申明的是,张积玉先生是我们敬重的文科学报界的前辈和领导,他对于学报界的贡献一直是我等晚学之辈所景仰不已的,他对于文科学报出路的思索以及对学术规范体系的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笔者所不赞同的是他主张的“编排规范化”。本文仅就“编排规范化”谈谈我们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希望在学报界一边倒的舆论和无奈里呐一声喊,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不当之处,敬请海涵和指正。
一
应该讲,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这样的电子杂志的诞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期刊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正如它所标榜的那样,它正是以其在“检索与评价”上的强大功能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从而赢得了市场。但是,当它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试图厘定一个让所有印刷型期刊遵从的所谓“行业标准”或“行业规范”的时候,那么它就犯了一个低级而又严肃的错误,因为它忽略了分属不同平台,有着不同本质特点的电子期刊与印刷型期刊的差异性。两者的差异性是这样的明显:首先,印刷型期刊是纸质期刊,而CAJ-CD是电子期刊;其次,印刷型期刊具有形式上的原创性,而CAJ-CD则更像一台巨型“刻录机”,不具有原创性;其三,虽然两者服务的对象都是读者,但印刷型期刊比CAJ-CD还多一个服务对象——作者;其四,CAJ-CD是数据库而印刷型期刊则不是;其五,CAJ-CD的主要功能是检索,而印刷型期刊则不以检索为目的。
因此,只从光盘企业的利益出发而借“行业标准”的名义向印刷型期刊以邻为壑地转嫁劳动环节,固然有利于本企业的发展,但从期刊发展的大局来看恐怕是不明智的行为。而印刷型期刊无条件地执行这套电子版平台的期刊规范,不惟违背印刷型期刊编排规律,有害于印刷型期刊文本表达的方式和深度,恐怕印刷型期刊编辑的从业良心和耐心也会面临考验。
事实上,由于这套规范脱离印刷型期刊以及人文社科的实际,钻研人文社科(尤其是钻研历史和古典文献)的学人们以及社科期刊的学术编辑在遭遇此规范的时候,表现更多的,是无奈和违心。以编辑为例,当遇到稿件发排涉及“编排规范”处理的时候,当手里拿的是一篇按照“论文写作的通则”(张积玉先生语)写就的质量优秀的所谓“不规范”稿件时,即使再优秀、再敬业的编辑在进行编辑加工时也会头痛不已。而由于这套规范掌握起来非常困难,不仅在整个学报界造成了诸多混乱,甚至于出现一本刊物由于编辑理解的不同,碰到的问题不同而表现五花八门的情况。这几年来的编辑实践已经证明,这套带有浓重的光盘版色彩的规范,危害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并且难以掩饰。也正因此,伴随着它的推行和实施,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它已不可避免地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和质疑。以《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美国研究》等为首的一大批学术期刊对这套规范进行的公开抵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它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注:期刊界与学术界对新规范的质疑和批评请参看如下文章:
姜朋:《注释体例大一统、学术规范及学术水准的提高——对〈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有关注释体例规定的思考》,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2001年11月18日;
姜朋:《再谈学术注释规范的若干问题——答周祥森先生》,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2001年12月17日;
任东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注释规范?——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批评》,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关于学术刊物注释规范的专题讨论”;
任东来:《学术期刊的注释标准——兼谈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预》,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关于学术刊物注释规范的专题讨论”;
任东来:《学术注释规范与国家权力——再与周祥森先生讨论》,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关于学术刊物注释规范的专题讨论”;
安拴虎 姜惠莉:《影响文科学报质量的几个因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张亦工:《关于〈历史研究〉的“引证标注方式”及相关问题》,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im.com,2001年12月22日;
任东来:《人文学科应对CAJ-CD规范说不——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批评》,《社会科学报》2002年3月21日;
汤啸天:《CAJ-CD如何偏离〈著作权法〉》,《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2日第5版;
傅丽英 陈曦 安拴虎:《社科期刊“编排规范”制定与实施中的误区》,《中国编辑》,2003年第5期。)。
二
在这里,让我们重点以修订后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为例,谈一谈我们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编排规范”有很多规范项。让我们从头到脚检点一下。
首先,关于“作者的署名”、“工作单位”、“作者简介”等条款有悖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关于作者的署名,我国《著作权法》里规定得很清楚,即作者有权署本名、代名、笔名、艺名、化名、假名,或者不署名、匿名。编辑必须尊重作者的任何署名方式,不能随意改动。然而奇怪的是,在张积玉先生《十二讲》中的“作者署名”一节中却对这一条只字未提,在张先生有关“编排规范”的诸多撰述中,虽没有明说署名要“实名化”,但任何人都能从中解读出他的主张,即署名只能用本名、要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自然,“作者简介”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规范项,其在文中的位置也基本固定:排在篇名页地脚“来稿时间”、“基金项目”之下。“作者简介”也已大体程式化:作者姓名(生年-),性别,籍贯,民族,职称,研究方向等。
其实,作者如何署名与作者作不作简介完全属于作者私权范围内的事情,是作者的权利和自由。作者有权采用任何署名方式,而期刊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尊重作者的选择,而有关作者的情况介绍完全可以根据作者的意愿或一并公开,或不公开,不必强求,更不能划一。我们完全不能以“该项目是文献计量评价机构特别需要的”(注:参见张积玉:《社会科学期刊规范化若干重要问题答疑》,《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第143页。)为理由,就生造规范项,逼使学术期刊去做有违作者个人意志以及《著作权法》的事情。即使公开,或详或略,尽可视情况而定;而其在文中的位置,也不必千篇一律,既可放在篇名页下,也可置于别处(如文末),完全毋庸程式化,更不必“克隆主义”地对待它。譬如《规范》中括号内作者生年之后的半个破折号就让人看着很不舒服,就好像还在期待着有哪一天再添上作者的“卒年”!因此,对于这一项,完全不必抱持“克隆主义”的态度,稍加变通总是应该的和起码的。
根据《规范》要求,在“作者”项下要用括号的方式添加作者具体单位(校系所)、地址(含省市)、邮政编码。只有一个作者时,括号内具体单位后面只加一个逗号,多作者且单位不同,括号内既要有逗号,又要有分号。在这里,我们以《十二讲》为例来加以说明。该书第42页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3~6岁儿童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熊易群1贾改莲2钟小锋1刘建君1
(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 西安 710062;2 陕西省教育学院教育系,西安 710061;第一作者,男,56岁,副教授)
这个例子几乎在每一个“规范化”了的学术刊物的“稿约”或“来稿须知”中部被反复征引。需要说明的是,新的规范版本为了方便计算机切分又在多作者间用逗号作了区隔。从这个例子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作者署名越来越多(“有些竟达10多人之多”——见《十二讲》第38页)的时代里,填充括号的复杂性快要超过高考中的“填充题”了,而且你还会对其在标点符号使用上对现有“国家标准”的莫名其妙的所谓“突破”(实为“违规”的代名词)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有关文前“摘要”、“关键词”等项的规定对于印刷型期刊自身来说属于无意义项,它不仅浪费版面,而且与正文形成重叠,是明显的“赘疣”,并且明显存在对国家标准的侵犯。
根据“新规范”的解释,“文前摘要也称同址文摘,它与原文同时发表。”(《十二讲》第44页)摘要按要求写成报道性摘要,字数也有规定:“在200~400字之间”。你甚至无权改用“提要”,因为据说“提要经常以书籍为主要对象”,而“摘要主要适用于学术性或技术性较强的论文或文章”(《十二讲》第46页)。写“摘要”“尽量不用‘我们’、‘笔者’、‘本文’等词作主语”(《十二讲》第49页)。
“编写好的摘要,需要作者和编辑共同努力,既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摘要写作的基本知识,更需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要像撰写论文、加工论文那样编写摘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学术论文文前摘要的质量。”(《十二讲》第53页)事实上,我们在编辑文稿过程中,经常碰到作者编写的五花八门的文摘,而这里面相当多的就是所谓的“不规范”文摘,而摘要“提要化”则是其中最突出现象。仅就摘要“提要化”这一现象,就十分耐人寻味,且不说曾经率先执行编排规范化的科技期刊目前绝大多数的文前摘要实际上都是“提要”(可以称之为“整体上的提要化”),即使文科学报的编辑也经常会碰到一篇文稿只能写成“提要”而无法写成摘要的情况。碰到这种情况时,编辑就显得很无奈、很无能,为了不碍于“形式上的规范”,往往只是简单地把摘要中出现的“我们”、“笔者”、“本文”等作主语的词抹去而不计其余,从而在实践上流于形式主义,而在工作态度上则呈现敷衍塞责等责任心遗失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试问,按照《规范》去“规范”地写摘要,哪一篇摘要不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又有哪一篇摘要不“像撰写论文、加工论文”那样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呢!“要像撰写论文、加工论文那样编写摘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作为一种要求固然必要,但它背后所隐含的问题也耐人寻味:与其说意在强调“摘要”的精品属性和创造性价值,毋宁说是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制作“摘要”的劳动成本太高昂了!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过于高昂的产品迟早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道理是一样的。至于每一篇文章为什么非得编写文前摘要,我们从该书中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原来文前摘要的“作用主要是:一,节省读者时间精力。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首先通过阅读篇幅短小的文摘,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然后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阅读全文。二是为文献检索作准备。有了文前摘要,编制文摘型检索工具就有了基础,有的可以直接使用,有的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加工,从而有利于计算机存贮。目前一般国家对文献的计算机存贮大多是输入摘要而不是全文,文前摘要为计算机输入创造了条件,为实现检索手段的现代化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十二讲》第44页)
这里所指的“作用”也可以看作是编写“文前摘要”的意义。既然起码有这么两条作用或意义,那么编写“文前摘要”看似就具备了充足的理由。然而除了第一条“节省读者时间精力”之外,后一条则与刊物本身毫不相干,属于搞文献检索和计算机数据库工作的范畴,刊物本身是没有义务提供这些服务的,须知越俎代庖是工作中的大忌。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文献计量评价机构特别需要”就为期刊生造功能,勒令其在文章发表时必须编写“别人”所特别需要的“文前摘要”。
在笔者看来,即便把第一条作为“文前摘要”存在的理由也殊难成立,因为“文前摘要”往往与正文具有某种重复性。按要求,“摘要是对‘一份文献内容的缩短的精确的表达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是对原文献的浓缩,其信息大致与原文等值”。这样一个“浓缩了的信息等值的”摘要在文前与文章一并发表,就好比一个人的头上又滋生出一个按比例尺“浓缩”了的“自我”,这在一般人看来分明是人身上的一块“赘肉”,是畸形,而在“规范派”(姑妄言之,不含贬义——作者)看来则是人身上不可或缺的部分。依照“规范派”的解释,别人在“读懂”这个人之前可以先“读懂”头上的小人,而这竟然就是小人存在的意义!
我们不妨揭示一下“摘要”的真正用途和“身份”:它属于图书情报工作者做文摘卡片的工作范畴,它对字数的要求正好是一张普通文摘卡片所能容纳的量度。坦白讲,读者阅读某篇文章,通常并不首先通过阅读“文前摘要”而获得信息,读者得到一篇社科论文,首先是看文章的题目和文章的开头,以及二级标题和文后的注释及参考文献表。并非如所说的那样,“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首先通过阅读篇幅短小的文摘,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然后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阅读全文。”尽管现在的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等都要求有“文前摘要”,但“摘要”的文献情报属性是不能不提的。
由此看来,属于搞文献检索和计算机数据库工作范畴内的“摘要”,硬性要求放在文前一并发表便显得有些荒谬了。笔者觉得,这种看上去早已习以为常、而问题又层出不穷的“文前摘要”现象,是不是值得反思一下它的“必要性”究竟有多大呢!
也许有人说文前摘要还是能够为读者阅读提供便利的。笔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一点。比如长篇文稿,为了导引读者阅读,及时将文章的主要论点和思路传递给读者,就有必要编写摘要或者提要,例如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篇幅一般在三四万字以上,这样的长篇大论没有一个“提要”性的东西作指引,是不可想像的。而对于中短篇幅的社科论文,甚至于三四千字的短文都无一例外地编写“摘要”,便失之于机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的主流学术期刊,对于篇幅一般都有一个限制性的要求,登载的文稿以中短篇幅的居多。总之,笔者主张在实践中,除了那些一两万字以上的长文可酌情编写文前摘要(或提要)以利于读者阅览之外,中短篇幅的文章根本没有必要附带文前摘要。但愿这个提法能够得到同行的赞同和响应。
再看“关键词”。“关键词是指那些出现在论文的题目、摘要或正文中,对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具有实质意义的词。”“社会科学论文标引关键词,首先是为了能够简要、明确的揭示论文的主题”,“其次,……也是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有关论文”。(《十二讲》第54~56页)至于关键词标引的数量也作了规定:以3~8个为宜。至于每个关键词中间如何间隔,旧版本说“相邻关键词之间空一字”(《十二讲》第54页),新版本又有了“进步”:以“分号”隔开,从而又一次为了计算机切分方便而“大胆突破”有关的国家标准。
学术论文为什么标引关键词?在这里,张先生给了两个答案:“首先是为了能够简要、明确的揭示论文的主题”,“其次,……也是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有关论文”。这两个答案中,第一个其实说的是“关键词”的功能,第二个答案,才是真正的原因。但是期刊刊载论文的同时并不负有“检索”的义务,那是文献情报工作者以及数据库工作者的业务内容,让别人替代自己的工作意味着剥削,因而是不公平的。反过来讲,编辑去搞检索乃至于搞“期刊评价”便是不务正业,便是代人受累或越俎代庖。
现实中,“摘要”编写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笔者并不完全的调查统计,现在声称全面执行规范的期刊中,能够真正按照《规范》写摘要的连一成都达不到,甚至包括相当大比例的所谓执行CAJ-CD规范的获奖期刊以及编辑出版学科内的一些所谓的“核心期刊”!他们要么将“摘要”写成实际意义上的“提要”,要么没有按照“摘要是对‘一份文献内容的缩短的精确的表达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是对原文献的浓缩,其信息大致与原文等值”的要求来写。正如张积玉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部分论文篇幅过短,有的甚至只是重复了标题中的信息量,不能充分反映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基本观点。二是摘要的内容不能概括、反映文章的主要信息、内容。三是与文章开头或结尾内容、文字重复。四是摘要的写法包括人称等不符合规范要求。”(注:参见张积玉:《社会科学期刊规范化若干重要问题答疑》,《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第144页。)至于关键词的标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关键词“不关键”的情况比比皆是,所谓“以选准、选全为原则”往往沦为一句空话。错标、漏标、非专指标引、过度标引是经常出现的错误(《十二讲》第61页)。至于分号在此处的大胆运用,与其说是对有关国家标准的“大胆突破”,毋宁说是对现有国家标准的违背。
这样就形成了形式上看似执行了《规范》,实际上则处处达不到《规范》要求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几年来,参与制定“新规范”以及推动社科期刊编排规范化的人士对于“新规范”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光盘版编辑部不下数十次地举办CAJ-CD规范培训班,在推行规范的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权力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影子。现在的学报编辑,手边新旧版本的《规范》、CAJ-CD规范和《十二讲》已经成了“编辑必备”。按说,《规范》规定得不能说不详细,《十二讲》不能说解析得不透辟,可为什么连“摘要”的编写都成了问题呢?
不外乎两条原因:不是时下的编辑们(甚至包括作者)太笨,就是《规范》制定得不近情理。笔者确信是后者的原因——由于规范制定得不近情理,大家在具体操作中很难中规中矩,作者乃至编辑们只好知难而退,追求形式,将就凑合了。
现在将笔者的观点作一小结:文前摘要和关键词各“规范项”有利于电子期刊以及文献工作者的检索、统计和评价,但对于印刷型期刊自身来说却意义不大,它不仅浪费版面,而且与正文形成重叠,是明显的“赘疣”。至于接下来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以及文后“参考文献类型标识”等,则更非印刷型期刊所需要,而彻头彻尾地属于文献情报工作以及数据库(例如光盘版)的作业范畴了。
第三,关于摘要和关键词等的“英译”的规定,不仅荒唐,而且也存在对国家标准的侵犯。根据“新规范”,摘要和关键词(包括文题等)要译成英文。然而这样做的必要性究竟有多大却很值得思考,除了把这种“英译”行为看作是出于传教情结的一厢情愿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外国人想了解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动向,自然有他们的方法和途径,而我们大可不必自作多情,急洋人之所急、想洋人之所想,越俎代庖地惟英译是务。国内期刊这种英译的做法不一定就能换来什么好报,相反,倒有助于增添外国人的骄气,愈发地对我们轻蔑和不屑。因为“英译”的做法简直有点像急于外嫁的妇人居然连花轿都自备停妥一样荒唐。退一步讲,即使向国外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一篇不落地作介绍,因为这样做非惟机械实属不智。坦白地讲,我国学术刊物的学术含量一般还很不高,即便是那些代表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刊物,也并非篇篇精粹,更不用说那些在学术质量上粗放式经营的、低层次重复建设的、存在着严重的关系稿以及文字垃圾问题的所谓学术刊物(比如相当数量的学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能引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所登载的文章一篇不落地对外介绍。
因此,关于“英译”的问题,完全可以作如下变通,即每一期可拣选一组较为重要的文章对外介绍,而不必逐篇都作介绍。这样,作为外国人,他从“英文摘要”所得到的信息或许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那些他不需要的,我们正好没有向他们作介绍,这样既省了将“家丑”丢到国外去,同时也省了版面和人力。而且那种在翻译过程中“弄洋文,出洋相”的事情也会减少许多。——如果给这种“介绍”寻找一个代名词的话,笔者宁愿称之为“恰到好处的对外介绍”。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作者姓名的翻译中,该规范也存在着对既有国家标准的侵犯。关于这一点,袁正明与苏春梅在《编辑学报》2002年第6期发表的“应尽快制定《中国人名书写及汉语拼音拼写规则》国家标准”一文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原来根据《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之规定: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笔名、别名等,按姓名写法处理。然而,无论是光盘版的CAJ-CD数据规范,还是《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为我们提供的却是另一版本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规范:
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字(写),复姓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字(写),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氏与名均不缩写。
示例:
ZHANG Ying(张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于2000年1月18日颁发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据说这一条又是经国家语委认可了的!——我们现在知道,CAJ-CD数据规范中凡是有悖于(或曰“突破”)国家规范的地方,据说都已“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认可”(注: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而且从国家语委缄默的态度来看,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相信,国家语委作为国家语言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维护着国家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却在私下里为一家光盘企业给众多印刷型期刊制定“家法”的行为大开绿灯!因为在遵行国家标准问题上,是不应该存在“特区”的。
第四,关于“注释”和“参考文献”著录的规定违背社科期刊的传统和编排规律,存在大面积对国家标准侵犯的现象。
这也是我们谈论的重点,也是争议最大、最为大家所关心的一点。由于“新规范”罔顾我国社会科学论文的行文传统和实际,结构性地偏离我国既有的社会科学书刊注释和参考文献著录的通行规则,一意孤行,从而引发期刊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成为争论的焦点。
问题首先是由“新规范”对“注释”和“参考文献”所作的非传统诠释所引发的。
依照我国既有的社会科学书刊注释和参考文献著录的通行规则,“注释亦称注解。是对文章中语汇、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其实注释客观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为解释补充性注释,简称“释注”;二是引文出处注,简称“引注”。就连张积玉先生的《十二讲》一书,也是沿袭的这种解释,那时的张先生还经常提及“社会科学文献通行的规则”以及“社科出版物的传统规格形式”,对于“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解释仍然不弃传统,并且捍卫把参考文献与注释相区别的社科传统。在《十二讲》中,他把“注释”分为三类:篇名注、作者注和文稿收到日期注;引文出处注;解释补充性注释。他在第151-152页说:
参考文献也称参考书目,通常置于文末,包括了全文注释中所征引的一切资料,是论文制作中所参考的范围与深度的重要标志。参考文献在形式上与引文出处注释大致相似,但两者的性质功能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注释是对某一论点、某一资料所作的征引,提供论文论证作依据,必须标明资料的确实出处;而参考文献是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全文注释征引资料的来源,无须注明具体出处——页码章节等。其次,注释根据论文写作的需要可对一份文献多次引用,而参考文献仅在文末作一次注明。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及次序基本与注释相同,不同处仅在于:1.参考文献一般在文内不编序号,仅在文末按其重要程度或参考内容的先后顺序编码排列。2.参考文献不注页码,必要时可注明所参考的论著的册(卷)、章,或起止页。
他在第11页还说:
自然科学期刊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者多,而社会科学期刊则以注释为多,注释中常常包含参考文献。社会科学论文中所谓的注释,除少数是补充说明的内容外,大多数是注明文献出处,因此对社会科学期刊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规范要求与处理上应同自然科学期刊有所不同。
他还在同书第160~161页强调说:
如前所述,本文则根据目前社科文献的通则把参考文献与注释区别开来:参考文献仅对论文著作从整(体)上做了参考的文献资料按先后顺序加以排列置于文末,在正文中并不标出连续序码。有人指出,社科期刊混淆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我们认为恰恰是社科期刊区分了这两者。
说实话,对于张先生当时的精彩论断我们由衷地表示钦佩。那时的张先生仍不失坚持基本原则,主动捍卫社科期刊编排的传统和“特性”。然而遗憾的是,不久后他就受聘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规范化工作组成员,成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的起草人之一。也许是角色的转换影响了立场,进而影响了观点,总之,此后的张先生已经将坚持了多年的“社科文献的通则”抛诸脑后,成了电子版—光盘版“规范”在社科期刊界的代言人和领航者,直至他负责起草《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将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贴上印刷型社科期刊的标签。大家知道,从那以后,它成了文科学报界“没有话语权”的编辑们只能简单尊奉的“行规”,直到现在,这个颇受争议的行业标准在文科学报界仍然享有不容批评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新规范”对“注释”和“参考文献”都作了哪些曲解和非传统诠释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注释”的“引注”功能割裂出来,划并到“参考文献”中。“注释”和“参考文献”在“规范”的名义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兼并重组,“注释”遭到人为肢解,仅保留了“释注”一项功能:“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而“参考文献”一改“仅对论文著作从整(体)上做了参考的文献资料按先后顺序加以排列置于文末,在正文中并不标出连续序码”的传统,赋予其“引注”的功能。虽然CAJ-CD光盘规范只是笼统说“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所参考的文献书目,一般集中列表于文末”,但从“14.4文后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中提供给我们的格式和示例来看,参考文献已经完全替代了引注的功能。
这样,经过声称“与国际接轨”、“与光盘版接轨”后的参考文献,就夹杂进了一些中西结合、土洋结合的标点符号和代码,最终变成了一个中不中、西不西、土不土、洋不洋的“参考文献四不像”。它不仅大规模地“突破”国家标准(注:譬如“新规范”关于“文献类型标识”的规定,明显有悖于国家标准。在GB7714-87中,明确规定“印刷型文献不著录此项”。),给作者和编者带来极大的不便,使文献标引混乱百出、乱象丛生,而且给读者“破译”和“解码”也带来不小的麻烦。如此看来,除了肥了那个以“克隆”、“翻录”印刷型期刊而闻名于世的电子杂志之外,真不知它还有什么“好处”!
以上我们逐条分析了编排规范存在的种种问题。此外在实践中对于大16开本的“准统一”要求以及将“目录”改为“目次”等做法都不同程度地浸透着形式主义,另有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叠床架屋的现象,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细说了。
三
综上所述,“新规范”不仅存在着使期刊“脸谱化”、“形式主义化”的问题,而且多处违背《著作权法》以及国家标准,名曰“规范”,实属“犯规”,至于其强制推行的做法更是具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
然则“规范派”制定“新规范”的思想认识基础又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二:一是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与国际接轨”是必然的,在对所谓“国际”的“轨”没有摸清搞透、对学科特点不加区分的情况下,在标准的制定上则盲目西化,甚至不惜与中国的传统全面“脱轨”;二是认为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印刷型期刊“为文献检索与计量评价机构提供服务”是必然的要求。由于有了这样片面的认识,致使“规范”的条款充盈着“利他主义”精神(注:这里的“利他”一词,是指在期刊编排工作中旨在为检索与评价机构以及英文读者片面提供服务的倾向和行为,正如笔者所论的那样,它不利于期刊的建设和发展。),而这种“利他”,又恰恰是与纸质期刊自身建设格格不入的、以牺牲纸质期刊的内在需要和编排规律为前提的。
至于说到“编排规范化”的思想认识基础,则恐怕只能说是“大一统”思想阴魂不散的表现以及追求光盘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说实话,其强力推行“规范化”,甚至不惜借助政府部门帮忙的做法,颇似古代政治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谋。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类似这种借政府之手打压异己自树权威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笔者认为,不同的标准之间应该通过公平竞争尽可由大家去自由评判和选择,不必强求,而行政部门以及行业组织也不必急于介入和干预。拿美国来说,就至少存在着《学术著作写作、编辑、出版技术规范》(即“芝加哥文体手册”)、《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手册》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三种不同版本的规范,而且不同版本的规范之间是平等的,美国行政部门也并没有扶持或鄙弃任何一种规范。而是尽可能地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机会,使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在竞争中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因此,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需要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不同标准之间在竞争的方式上真的是最需要接轨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将编排标准划一到自己旗帜下的任何企图都是有违公平原则的。
收稿日期:2003-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