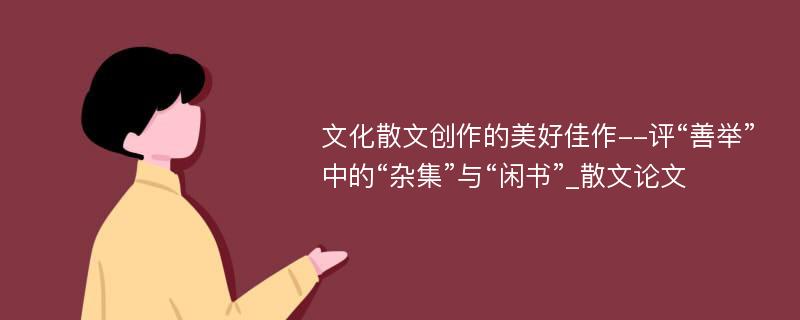
美仑美奂的文化散文创作精品——评在山居文钞《杂杂集》和《闲闲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仑论文,山居论文,散文论文,闲闲论文,精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与费在山先生相识于80年代初。那时,他在湖州王一品斋笔庄当经理。为了搜集茅公的墨迹,我陪同丁尔纲教授到笔庄,就此认识了费先生。后来,费先生以业余写作者身份加入湖州市作协;我也加入了市诗词学会,彼此过从甚密。
1990年11月23日,在湖州市社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书法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费在山先生将他自费印刷的第一部作品集《杂杂集》题上“广德同志方家指正”,亲手持赠予我。三年半之后即1994年5月,他又将自费印刷的第二部作品集《闲闲书》亲笔题上“广德方家指正”,托王一品斋笔庄的孟杏梅女士转交,馈赠予我。对于作家朋友、学者同仁的赠书,因为有书的作者的亲笔签名,且又是相互熟悉或有创作、学术交往的,我都很喜爱,很珍惜。而对在山先生的这两部书,我是格外喜爱和珍惜。为什么呢?一则他这两部书全是自费印的,这对一个靠工资收入的文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二则两部书的封面题签、序文均为名人大手笔,又有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教授、书法家为之题诗题词,而其文章更是篇篇锦秀,美仑美奂。近四五年来,我常常翻阅它们,深获教益。
那么,费在山先生的《杂杂集》和《闲闲书》是怎样的两部书呢?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言以蔽之”作简单的回答,而是要找出参照系加以对照,然后作出比较正确的评论。
在现今的文坛上,文章林林总总,书籍汗牛充栋。以文学作品的成就来说,小说、诗歌当推首位,散文、报告文学次之,而杂文、剧作和其它体裁又次之。其中越来越为读者喜爱而在书市上看好的散文,真个是佳作纷呈,美不胜收。《杂杂集》和《闲闲书》就是其中两部颇有特色的优秀作品。与当代散文名家的作品相比,这两部书和它们迥然不同之处在于其情趣隽永、知识丰富的文化内蕴,而这正是它最大的特色。一般的散文大都是吟咏性情的,以期引起和打动读者的心弦。这类作品,人们谓之抒情散文。《杂杂集》和《闲闲书》虽也透露出作者个人的性情,但却不是以吟咏性情为特色的抒情散文,而是既给人文化知识又予人情感影响的文化散文。我之称它为“文化散文”,而不把它归之于知识短文,是因为知识短文只有知识的元素而无情感的元素,它虽能给人知识的教益,却不能予人情感的陶冶,不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而这两部书则情感和知识二者兼而有之,它们的字里行间流动着真切的情感,又传输着文化的信息,于一体之中同时体现出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文化散文创作难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所以,一个从事文化散文创作的作家,必然既是诗人又是学者。
费在山先生于中国古今文化、艺术、文学和历史诸方面学识渊博,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和创作成果累累,在地方文史、文坛掌故和文房四宝等领域堪称专家。他又广为结交海内外文化名人,悉心搜罗、珍藏名人诗、画、笔、砚、篆刻,且遍游各地山川、名胜古迹,还有过长期经商和从政的阅历……。这一切使他在进行文化散文创作时可以信笔拈来,游刃有余。难怪人物掌故随笔大师郑逸梅先生在《杂杂集·序言》中赞其“风范雅尔”、“文采蜚然”、“溯往衡今,见闻博洽”。而新加坡著名作家周颖南先生则在《杂杂集》的序文中誉其文章“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结集起来,编织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他的作品,往往妙语成珠,发人深省,掩卷深思,回味无穷;宛若朵朵牡丹,织成一片锦绣,把人间点缀得更美丽,何‘杂’之有?”著名作家、学者叶至善先生说费在山的《杂杂集》“文章的确杂,总的来说还是讲的文学艺术”、“都不牵强,都是有话要说,而且有说可说而写的;读了之后都有所得,因而很感兴趣。”至于《闲闲书》这部书,叶至善先生评为“这是一本‘闲’书,生活中也必须有这样的闲,哪能事事讲功利。”林懋义先生认为此话“很启发人”,因为《闲闲书》“是有说可说而写之书”,“‘闲’书不‘闲’”,“这本书所说、所写的都是该说而说的话,没有废话、空话,没有无病呻吟,内容充实,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文风。”我认为这些名家的评价都是至为中肯和富有见地的。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必然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是一个经年累月、呕心沥血的辛勤笔耕者。费在山先生同样如此。在文体选择上,他爱好散文。他说:“我不讳言,平生不大喜欢看小说,尤其是长篇。我偏爱散文、随笔和游记。小说往往有虚构的一面,而散文、随笔有作者自己在内,是作者经历的,有生活气息和真实感。”(《〈缘缘堂随笔〉读后》)在创作态度上,他多年如一日,写作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打开《杂杂集》,可以看到编入此书中在山先生的作品有108篇,其中:“散文随笔”31篇,“怀念之什”21篇,“鲁迅十记”10篇,“书林拾枝”13篇,“不律杂话”16篇,“序跋题记”14篇,附录2篇,后记1篇。再翻开《闲闲书》,则看到在山先生的文章有117篇,其中:“随笔杂记”13篇,“人物掠影”21篇,“书苑印林”13篇,“诗余茶后”12篇,“菰城纪胜”24篇,“邮苑杂谈”10篇,“新光忆旧”12篇,“闲人闲话”11篇,后记1篇。两书共有作品225篇。这二百多篇作品当然都有其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是其中的四类,即:一、文人轶事、趣闻和掌故;二、诗词书画、金石篆刻等的识见和言论;三、关于毛笔(尤其是湖笔)、笺纸、碑刻、邮票等的收藏与研究;四、湖州地方的名胜、古迹、民俗、传说的研究及有关的文史资料。
首先,从作者所记的人物来看,大多是现、当代著名作家、书法家、美术家、出版家、戏剧家、金石家、学者、教授、美术工艺家。《杂杂集》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尹默、梅兰芳、梁漱溟、张宗祥、高二适、丰子恺、邵洵美、郭绍虞、沈从文、傅抱石、夏承焘、王驾吾、钱君陶、曹辛之、潘天寿、沈迈士、刘博琴、黄君坦、任小田、单晓天、钱仲联、叶至善、徐迟、周大风,以及诗人陈毅元帅等;《闲闲书》中除上述名人外,又有:俞平伯、潘孑农、包幼蝶、包玉珂、谢冰心、郑逸梅、费新我、沙孟海、夏衍、赵朴初、唐云、黄裳、柯灵、施蛰存、苏龙翔、苏仲翔、王秋野、王西野、谢孝思、谢加因、陈从周,尤淇、尢玉淇、韩登安、周哲文、矫毅、谭建丞、吕剑、周颖南、谢晋、张包子俊、徐永辉,还有日本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等。其中许多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山先生对这些文化名人中的大多数,或曾晤见,或曾拜访,或曾陪同游览,或有书信及诗文往来,双方(或与其子女)还结下了友谊。他以生动、形象的笔墨写下这些文化名人的一个侧面、一段经历、一席言语、一件书信,使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兴趣爱好,并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的建树及成就。
譬如《杂杂集》的头一篇,发表于1966年4月20日香港《大公报》,记叙了当年新春丰子恺偕夫人徐力民及孙女南颖游嘉兴、湖州等地的情形。读者从文中不仅可以知道丰子恺此行的一些趣事,而且能看到他此行所作诗、画的背景。它为《丰子恺年谱》提供了参考资料,也有助于《丰子恺传》的创作。再如同集中的四篇记写叶圣陶的文章,所作时间从1977年到1989年,发表在《随笔》、《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作者称他与叶老是“忘年交”,十多年间,他几次造访和聆听叶老谈话,文中所记绘声绘影,读者从中感受到叶老一贯的严谨负责态度和对他人循循善诱的精神。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叶老《题〈鲁迅十记〉》时有一段编者附记:“一九七六年春,费在山同志利用业余时间拟写十篇与鲁迅有关的读书札记(现在有的已经公开发表),请叶圣陶同志书写题记,叶圣陶同志即为作者‘奉题十二韵’。现征得叶圣陶同志同意公开发表,借以纪念鲁迅百年诞辰。”于此也可知费与叶老之关系。又如《闲闲书》中有关湖籍文化名人及其事迹的几篇文章,读者在此前的书报出版物中也难以见到。至于现代剧作家、《长城谣》词作者潘孑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包玉珂,著名作家、金石学家、学者施蛰存教授等皆为湖州籍人氏,则更少为人所知。在山先生文中写道:“学术界都知道施蛰存是松江人,《鲁迅全集》的注释中也作松江人,《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却作杭州人。光凭一方印章不能武断,于是我冒昧向本人请教。承复信云:‘……寒家于明末清初犹居吴兴,大约清代中叶迁居杭州,清末民初,我父亲以孤儿旅食苏松,遂为松江人。我用“吴兴施舍”,志南施郡望也……’是则,施蛰存教授也是吴兴人无疑的了。”(《闲闲书》第35页)这类考据文章,足可补充以前出版物中之不足或匡正其错谬。所以,我认为这些随笔、札记是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的宝贵补充和必要注释,也能给读者和研究者以莫大的助益和良深的启迪。
其次,作者在这两部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谈论诗文、书画、金石、篆刻和书籍装帧等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他的识见和议论虽不是系统的专论,但是都很有见地,尤其是关于书法、金石的识见,确为一家之言。
关于散文,他在《〈缘缘堂随笔〉读后》中认为丰子恺散文的“最大的特点在于‘朴实’”。他说,“读《随笔》,字里行间令人不觉得有半点不科学,不常识,不自然,相反,读者被天真、朴实、坦率所征服。”他的这种“朴实”说,在有关丰子恺散文的研究论文中虽属仅见,却是一语中的。我以为它较之“率真”说要好,因为“率真”是所有优秀散文都须具有的,是一种共性,而“朴实”则是一种个性;对于这种特点,评论者如果不具慧眼是难以发现的。他还认为,“《子恺漫画》和《缘缘堂随笔》是互相依附的,不过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不妨说,《子恺漫画》是用形象‘写’成的‘散文’,而《缘缘堂随笔》则是用文字‘绘’成的‘画册’。”(《丰子恺与西湖》)如果作者不是既识于文又谙于画,是说不出此语的。
这两部书中有几篇书评,其评语精当,入木三分,且表现了作者对文艺的高见卓识。如对晦庵著的《书话》,作者在《〈书话〉余话》中说:“我之所以喜爱《书话》,并不想步前人的后尘,搞什么版本研究,实在是被‘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这种别有一格的文体所吸引。”又说,“我觉得《书话》有其独特之优点:丰富的知识、简练的文字和多样的体裁。每段是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令人百看不厌。”还指出,《书话》“除了讲书本身的历史外,读者还可循此而搜索与本书有牵连的资料、轶事和趣闻,就这个意义来说,《书话》开拓的视野就比一般的散文、随笔广阔得多。”两书中写诗人与谈诗词的文章有多篇,从中反映出作者的诗词见解和创作主张。他说自己做诗的方法是“先抓意境,后押韵,再调平仄”。“而意境,我认为是做诗的最初动机,抓住意境,诗就活了,不能为做诗而做诗;诗是有感情的,要以情感人,否则谈不上诗。所以我认为诗当以意境为上。”当然,意境说不是一种创见,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意境的重视,对诗词创作要以情感人的强调。对于“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的问题,他认为,“新瓶也好,旧瓶也罢,‘瓶’总还是瓶。今天是新瓶,过了一些时候,也就成了旧瓶;而旧瓶经过改造、刷新也可以变成新瓶。所以,‘瓶’变来变去总是‘瓶’——‘瓶无新旧’;关键在于‘酒’——即文艺作品的内容。‘形式服从内容’这是普遍规律。内容依赖形式。好的形式必要有好的内容,这叫相得益彰。诚然,‘酒’也有老酒、新酒之分,劣酒、好酒之别,这就需要鉴别、比较。好的酒,喝了有益健康;劣的酒喝了既无益于身心,还有害于人体健康。所以创作愈认真、愈严肃,酿出来的‘酒’愈芬芳,也就是叶圣老讲的‘酒必芳醇’。”作者以此种“瓶无新旧,酒必芳醇”的观点进行创作和评论、要求他人,是很宝贵的。这些年来,他作为湖州市诗词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并主持《苕霅诗声》的编辑,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词,而且经他之手组织和编发了海内外诗人的多篇诗词佳作和研讨诗词创作、欣赏的短论、书信,为弘扬中华诗词并使之普及与提高,起了一定作用。
在山先生对书法艺术和金石印章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两部书里的几十篇专文中。这些文章中一部分是有关书法家(包括日本国)的,另一部分则是专讲书法的。从前一部分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外书法名家都很敬重,有的以师师之,请问求教;有的以友友之,以文会友。印象至深的是他写的关于沈尹默、费新我、沙孟海等人,尤其是回忆高二适、追忆青山杉雨的那些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对书法艺术的万分虔诚和无限热爱的精神,以及对书法艺术的一以贯之和上下求索的学风。对于书法,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是读了在山先生的《不律杂话》、《行书管窥》、《〈现代临书大系〉书后》等文章,我这个门外汉竟产生了一个关于书法的观点,这就是:书法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一个人要成为有大成就的书法家,除了高尚的人品、精美的艺术之外,他还要有文学、美学、美术、史学、书法史、文化学的知识,有笔、墨、纸、砚制作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的科学知识,对于其中的一些学科还要有一定的研究。几十年来,在山先生在对书法艺术进行追求和研究的同时,也不懈地进行着文学、史学、美学、金石学、文化学及“文房四宝”等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追求与研究,没有后者也就不会有前者。不知读者诸君可有同感?
这两部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其中有多篇关于湖州地方的文史资料及考证文章,尤以《菰城纪胜》中的各篇引人注目。这些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本地文物、名胜的介绍文字,其特点是它们的篇幅都较短,却有经过挑选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既有前人诗文的引证,又有自己的思考,且富文采。“阅文先阅题”,人们从《吴兴·〈吴兴赋〉·吴兴八景》、《白苹·白苹洲·白苹洲诗》、《墨妙·墨妙亭·墨妙亭碑》、《韵海·韵海楼·〈韵海镜源〉》、《爱山·爱山台·爱山书院》、《千璧·千璧亭·千璧留珍》、《潜园·潜园石·潜园寄客》、《管楼·管公楼·管夫人词》……,就可看出作者在拟题、选材、运思上如同作诗那样,是很花了一番心血的。著名老书画家谭建丞先生在《〈菰城纪胜〉后序》中称道:“费君《菰城纪胜》虽属小品,然于掌故史料,考证翔实,文字简练,可读矣。”这些文章给了读者很多有关湖州的地方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知识,其教育作用与审美作用兼而有之,不仅使本地人更爱其家乡,也使外乡人增加了对湖州的喜爱。对于从事文化、教育、创作和修志的人,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文中的不少看法和建议,对于湖州争取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工作也是值得重视的。
《杂杂集》和《闲闲书》有一个和一般作家的作品集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收进这两部书中的除了作者的文章之外,还有多件名人名家的题字、题诗、书信和书法、美术、金石作品。如关于这两部书的,就有茅盾、叶圣陶、冰心、俞平伯、顾廷龙、启功、钱君啕等的题签,施蛰存、顾学颉的题辞,钱仲联、苏仲翔、施南池、杜宣等的题诗,郑逸梅、柯灵、叶至善、林懋义、周颖南等的序言,以及茅盾、叶圣陶、俞平伯、沈尹默、高二适等赠作者的墨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它们使费在山的这两部书增光添彩,身价倍增。书中多篇文章也有书法或金石作品相配,使读者于阅读文学之时又可欣赏艺术,实乃一举两得之快事!加以此两书均由作者自己装帧设计,大方、典雅、朴素、秀美,使此两书成为精美的文品与艺品的合璧之作。
最后,我想着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费在山先生的这两部书成为不同凡响的文化散文精品集?我认为,除了这是他几十年辛勤笔耕的结果,还因为这是他自印的书籍。每个写作的人都有相同的体会,作品的创作过程如同婴儿由母亲怀孕而分娩,其苦痛与快乐唯有自知,作者对其作品之心爱也如同母亲对其孩儿之心爱。而作者在将其作品奉献给社会——发表或出版之时,则如同母亲将其女儿出嫁一样,是多么想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光彩出众啊!在这里,作者自印书就比交由出版社一般编辑和装帧设计者进行编辑、装帧设计要认真、精心得多。因此,中国文人自印书自古以来就有传统。王建辉先生作有《文人学者自印书》(1994年2月18日《光明日报》第5版)一文,他指出:“文人学者自印书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追求,也是一种文化情趣。”他又写道,说来你不会相信,陈垣在解放前是从未正式由出版社出过书的,他的所有著作集为《励耘书屋丛刻》,全部自印,木刻线装。鲁迅先生自己印过许多书,他不光印自己的书,还自编自印自己感兴趣的书,如《北平笺谱》、《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只要有钱,就立刻想到印书,往往因为不惜工本,全力以赴,结果弄得连生活也十分拮据。《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印成之日,他在送给挚友许寿裳的本子里写道:“印选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弗一册,以为纪念耳。”此书只印得103本,只出售了33本,其余均由鲁迅赔钱赠送。这部书的版权上印有:“有人翻印,功德无量。”熊十力34岁时,处女作《熊子真心书》自印行世。王统照自印过好几种书,如译诗集《题石集》、旧体诗集《鹊华小集》,后一书是1958年于济南自印的。“文革”以后,俞平伯曾致函姜德明:“承赠自印《周总理诗集》,书品颇精,谢谢。”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作家学者自印其著作的也有多人。而且,凡是文人学者自印的书,大都装帧精美,印刷考究,品位上乘,具有珍藏价值。《杂杂集》和《闲闲书》之为当代多位文化名人喜爱并予好评,不就是明证吗?
听说费在山先生的第三部书《了了篇》已经完稿,且已获得陈从周教授所撰之序文(刊《联谊报》1995年3月29日),即将付梓,而且仍是自印行世,不禁肃然起敬,深表钦佩!我相信,《杂杂集》、《闲闲书》和《了了篇》这三部优秀著作必将成为费在山先生创作道路和人生旅程上熠熠闪光的丰碑,并且对当代文化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产生良好的影响。
199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