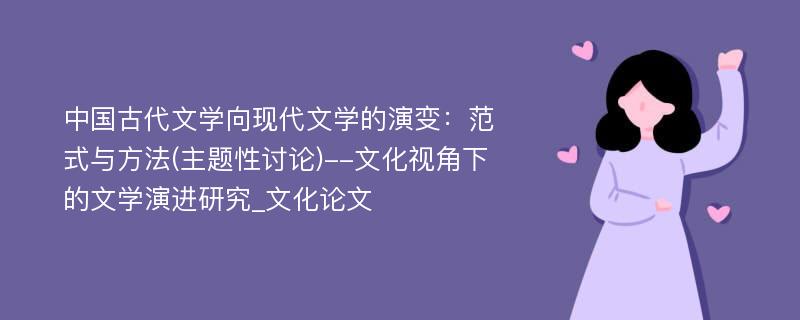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范式与方法(专题讨论)——1.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梅新林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2-0116-11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而文化精神的演变,也决定着文学形态的演变,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所以,探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要以文化演变为参照系,而且要通过彼此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而趋于更为内在、更为本质的学理境界。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与时俱进,就在于其能同时兼具自我更新与吸纳异质文化资源的双重能力,在纵横交汇、融合中吐故纳新,衰而复盛。站在21世纪的学术制高点上,通观中国文化的演变历程,可以重新划分为华夏之融合、东方之融合与世界之融合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华夏文化融合时期。从炎黄传说时代到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华夏各民族与区域文化的融合,然后逐步形成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体系。
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跨越黄河、长江两岸流域的三分天下格局,到夏、商、周三代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轴线上的由中部向东西不同方向的轮动,中国文化在实现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民族与不同区域的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从“神”的时代向“人”时代的过渡,直至春秋战国时代,终于迎来了西方学者所称的由神而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第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繁荣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士人崛起、诸子立派、百家争鸣,一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空前兴盛。进入秦汉之后,在国家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家(秦代)、道家(西汉前期)、儒家(西汉中期)的依次选择,最后确立了儒家的官方主流文化地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标志着汉代儒学作为正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奠立。在汉武时代,我们还应关注的另一重大事件,即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中,正式确认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具有中华民族血脉大一统的特殊意义,同样意味着中国文化第一时段——华夏融合时期的结束。
二是东方文化融合时期。从东汉时期到晚明时代,以儒学危机与道教兴起为背景,来自西域的佛教的传入及其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异质资源与重要契机,然后逐步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基于此前的华夏文化之融合转入东方文化之融合的重要标志。此后,伴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三教合一”与南北文化的相交相融,由表层而内质,由局部而整体,对本时段中国文化的重建与演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学衰微、佛教传入与道教兴起,三者终于相遇于东汉后期,一同改变了西汉以来儒学独盛的整体学术格局。此后,儒、佛、道三教开始了漫长的相争相合的进程。第一阶段是魏晋时期,集中表现为由儒、玄之争与佛、道冲突中走向初步的调和与融合,其核心成果便是玄学的兴盛,然后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而南迁,并鲜明地打上了江南山水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烙印。第二阶段是唐代时期,集中表现为儒、道、佛各自本身的融合南北的综合化与融合儒、道、佛三者的综合化,从而一同促成了唐代文化多元自由发展时代的到来。第三阶段是宋代时期,集中表现为儒、道、佛三教合流的深化,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理学的建构。较之前代文人,宋儒对于佛、道二教的修养更深,其所臻于“三教合一”境界也更趋于内在与深化。第四阶段是元代时期,集中表现为“三教合一”融入了包括回回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在内的更为丰富的多元文化,并促成新的宗教流派的产生与兴盛。第五阶段是明代,集中表现为“三教合一”在融入启蒙时代精神中走向文化解构与批判。尤其是从明中叶开始,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已无法适应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文化土壤与文化意识的需要,而宋、元两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市民思想意识,则在不断地通过士商互动而向上层渗透,这是推动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而由王阳明心学对官方禁锢人性的理学的变革,再经王学左派直到李贽“童心说”的提出与传播,实已开启了一条以禁锢人性、人欲始,而以张扬人性、人欲终的启蒙之路,已初步显现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相类似并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现象与态势。这说明基于思想启蒙与商业经济的刺激双向的推动,理学的衰落与启蒙思潮的兴起势不可挡;而起于南宋的陆九渊心学与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事功之学的后续影响,便通过从王学到王学左派再到李贽等,由思想界而文艺界、科学界得到了更为激烈的演绎。另一方面,当援引佛、道改造或消解理学已成为知识界尤其是思想界与文艺界一种普遍取向与趋势,那么,“三教合一”的发展便更具某种张扬佛、道的反传统的意义。这是本时段“三教合一”的最终归结。
三是世界文化融合时期。晚明之际,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极盛时期,中西方都出现了相近的文化启蒙思潮,一同预示着一种近代化态势。理学的禁锢与衰落,意味着中国文化需要再次借助和吸纳一种新的异质文化资源进行艰难的重建工作,而在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内部,已无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可能,这在客观上为中西文化的遇合、交融、重建与转型创造了条件。此后,以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进行“知识传教”为始点,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先后经历了三次运动。
第一次是明末清初时期以西方传教士为中介的“西学东渐”。这次重点在于宗教与科学文化的传播,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因中国末代封建王朝——清朝的回光返照而渐趋停止,结果不仅打乱了晚明以来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甚至中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前行方向。所以,本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成果不著。第二次是近现代时期再次的“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全面、激烈的碰撞与融合,终于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进程的中西文化之争,通过中西文化全面、持久而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化初步完成了世界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建立起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崭新体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三次“西学东渐”。此与前二次相比,似乎都是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由西学的冲击而起,但彼此的内涵与意义并不相同。明清之交的第一次浪潮仅是一个先锋而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西双方的文化地位。近现代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之际,中西双方的文化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激进的西化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而完成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立的,因此,其中诸多文化本身的问题未能得以比较从容而完善的解决,这就为第三次浪潮的兴起预留了文化空间与任务。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浪潮的再度兴起,本有“历史补课”的意义。然而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终于初步改变了前两次“西学东渐”单向传输的路径与命运,而逐步走向中西的平等交流和相互融合。诚然,文化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势能的较量,当我们既放眼于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舞台,又通观已经历三个文化融合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应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目标与神圣使命。
以上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重新划分,可以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新的文化参照系。在此,三个历史阶段的主流文化形态与精神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依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别从华夏之中国,到东方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与此相契合,中国文学也同样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变化。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1.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首先是一个历时性论题。我们应重点关注其中三个层面的意义切入:一是“窗口”。文学从文化母体中诞生,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因而从文化视野审视文学演变,首先具有为之打开一扇开阔“窗口”的意义。二是“本原”。文化影响于文学,不仅在于其形态,更在于其精神,所以由文化视野审视文学演变,显然具有探索其精神本原的意义。三是“动力”。文学发展演变的深层动力来自于文化,文化的发展演变——从形态到精神都制约着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演变。所以,由文化视野审视文学演变,进而具有深入探究其内在动力的意义。以上三个层面非仅就文学演变研究本身论文学演变所能臻达的。
2.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同时也是一个共时性论题。在此,我们应重点关注三重资源的交融关系。一是华夏文化资源。华夏文化本源于不同民族与区域,然后经过漫长的碰撞、交融,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流文化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先整合而成的本土传统文化。二是东方文化资源,以源自于西域的佛教文化为代表,自东汉传入后,经过漫长的碰撞、交融,逐步形成以儒、道、佛“三教合一”为主流文化形态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外来的佛教文化经过本土化后已成为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第二次整合而成的新本土传统文化。三是世界文化资源,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为代表,经过明末清初、近现代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三次浪潮的反复碰撞、交融,逐步形成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及西方的现代中国文化。在此,外来西方文化也已并将继续经过漫长的本土化后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第三次整合而成的新本土文化,只是它不是“过去时”,也不仅仅是“现在时”,同时也是“将来时”。以上三重文化资源的交融,不仅影响而且直接包含了文学资源的交融。因此,文化视野中文学演变的历时性展开,同时也是本土文化不断吸纳东方与世界文化资源,然后逐步融为一体的进程,彼此从不同方向共同推进中国文学从本土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
3.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还需要作一个文学本位立场的辨析。十年前,笔者曾提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位一体的理念,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应以文献为基础、以文本为轴心、以文化为旨归,有人称之为“三文主义”。同样,文学演变研究的重心也应回归文学本位,研究者最终应对文学演变研究作出本位立场的思考。此其一。其二,文学演变与古今文学演变具有广狭或泛指与特指的意义之别。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率先发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初衷,就是要贯通与融合长期以来分属于两个二级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人为隔离,进而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建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乃至形成一个新的学术传统。然究其实而言,应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的贯通与融合,因为并非打通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而统合为中国文学就算是古今演变研究,而应将研究重心定位于由“古”观“今”与以“今”溯“古”双向互动之中。也可以近代文学为中介,通过贯通古今而重点探索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形态、演变规律与精神邅变。然而,近代文学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近代文学元素更可以不断地朝前追溯。比如从宋元话本到明代小品文,皆具某种近代文学元素,需要加以细细梳理。其三,在古今文学演变的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应辨析三重文学形态与精神的因时变革与交融。一是古代传统文学形态与精神,因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与发展而逐步形成,具有源于不同时代、民族、区域的多元特征;二是近现代文学形态与精神,以西化为主流特征;三是当代文学形态与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其中后三十年渐显融合放眼世界与回归本土于一体的新的价值取向。以上三重文学形态和精神的因时变革与交融的历史进程及未来走向,应是基于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本位立场所必须思考的本位问题。
[收稿日期]2009-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