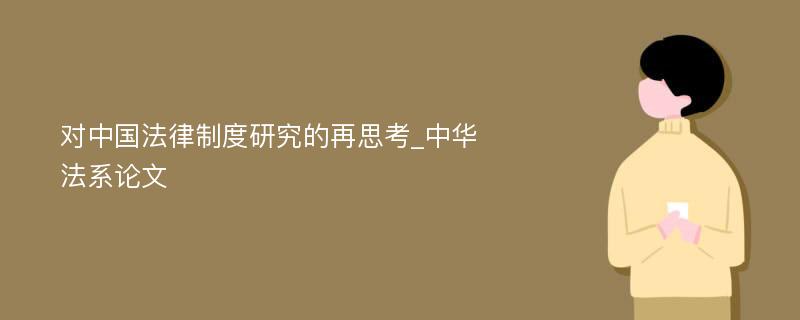
中华法系研究的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系论文,中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先生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他认为:第一时期为上世史,自黄帝洎秦统一中国;第二时期为中世史,由秦朝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第三时期为近世史,从乾隆末年迄今日(注:详细的讨论,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尽管梁启超的这一划分在细节上不无问题,但是,它在总体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以此检讨中华法系,我想把它归入“亚洲之中国”时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当时,不仅中国文明处于亚洲的“领先”地位,并且也是中国文明的“输出”时期。值得指出的是:就中国语境看,中华法系的形成当在先秦时期或青铜时期,可以归入“中国之中国”时期;那时,它的法律文化基因已经孕育成胎。这一法系的全面崩溃以及改弦更张,应在晚清“新政·修律”时期(注:一方面,中华法系早在19世纪即已解体。譬如,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标举“脱亚入欧”全面“移植”法德两国法律,表明中华法系作为一个法律文化的“家族”团体已经无法继续维系,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晚清“新政·修律”尽管象征着中华法系的崩溃,然而并非意味着中华法系已经彻底“死亡”;事实上,就中国而言,中华法系作为一种制度及文化背景,它的影响仍然不小。),属于“世界之中国”时期。
现在,我们依然面临晚清以降西方文化的“霸权”时代,处于“世界之中国”时期;就法律文化而论,同样处于国际化、全球化时代。在这个背景下,重新省察中华法系的制度与精神的资源,不论正反利弊,均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说,首先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其次才是研究中华法系;而就中华法系来看,首先是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其次才是研究中华法系(注:我的这一看法,主要是基于国内学者研究中华法系的实际状况而言的;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对东亚诸国法律文化的研究水平,尚未超越杨鸿烈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知识水平。)。一、回顾:中华法系的研究与问题
在我看来,“法系”一词至少具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法律研究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比较,对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进行分类;其中,既有“求同”的一面,也有“辨异”的一面。与此相关,第二是指法律体系的类型。经过比较,人们可以获得对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的认知结果,亦即对法律体系的类型概括。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兴起,既与西方各国认识“自己”的意图有关,也与西方法律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密切相连。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及西学东渐而来的是,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文化的冲突渐次加剧;特别是从20世纪初期起,随着晚清政府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全面“移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临彻底瓦解的境地;在此“生存还是毁灭”的当口,认识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清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双重的必要。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及日本学者研究的影响,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
就我所知,中国学者对中华法系的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也有一批研究成果出版,从时间看,研究中华法系的第一个热潮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根据学者的初步统计,刊布的论文约有20来篇;研究中华法系的第二个热潮是1980年代,出版的有关论著也颇不少(注:有关的部分资料介绍,参见曾宪义、郑定编著:《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7-83页。)。从方法看,是通过“比较”分析来揭示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或固有特征。这里,我想就手头的材料对某些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评析,以便了解学者对中华法系的基本看法;进而,检讨这些研究又有哪些“问题”?
前面已提到,中国学者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是在国外(西方及日本)学者的影响下逐步展开的;它的突出表现则是将国外学者对各个“法系”的划分标准作为一个不加反思的前提予以接受。譬如30年代出版的两本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权威著作,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注: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页。杨鸿烈的这一研究思路,直到7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依然不变,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1-20页。)与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注: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印影版,第52页。)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陈顾远先生对“法系”之得以构成的基本理由,有过简单的说明:
夫一法系之所以成立,必有其一帜独树之特质,与卓尔不群之精神,虽彼此或有相类之点,但彼此绝无尽同之事。例如印度法系之特色,在以阶级制度为其背景;回回法系之特色,在以“可兰经”为其依附;欧陆法系之特色,在以“罗马法”为其基础,而重视法典编纂,与创作性;英国法系之特色,在以习惯法为其法源,而重视前例解释,与保守性(注:前揭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52-53页。)。
这一“法系”划分的标准,乃是国外学者的基本看法。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起来那就可以发现:其一,与陈顾远自己提出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亦即它们与“卓尔不群之精神”不符;换句话说,印度法系、回回法系、欧陆法系、英国法系的“精神”特色又是什么呢?陈顾远没有回答。其二,四个法系之间的划分,同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印度法系根据“阶级制度”(今按:种姓制度);而其他三个法系则依据法律的“渊源”。这里,我不禁要问:何不根据《摩奴法论》界定印度法系呢?其三,在讨论中华法系时,陈顾远认为,它的特色在于懦家思想、家族制度、等级制度(注:有关的讨论,参见前揭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53页-91页。)。对此,陈顾远先生同样没有依据法律的“渊源”加以区别。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法系”的研究与划分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据我所知,时至今日,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法国著名比较法学者达维德对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划分,就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范例(注:对此问题的具体讨论,参见[法]勒纳·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另一值得我们追究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声称“中华法系”具有种种令人瞩目的特征;但是,在实际讨论时,往往关注的只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特征。然而作为一个“法系”,必有自身的“家族”成员,那么,这些家族成员的法律特色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它们作为中华法系中的成员,当然具有中国法律文化的某些特征;可是,家族成员之间只是“类似”而非完全一致。因此,它们肯定具有自身的法律文化的特征。我们知道,日本传统法律文化乃是“移植”唐朝法律体系渐次形成的,然而日本“律令”体系的精神与中国是否一样呢?再者,随着“律令”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武家”法律时代。这一时期的法律虽然继续受到中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不过,由于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日本法律也有相应变化。凡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法系时,往往没有予以措意或认真对待。故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虽然名义上是研究中华法系,实际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前揭杨鸿烈先生《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虽然没有明确标举“中华法系”研究,然而实际则可视为中华法系研究。只是,一如书名所示,这一研究比较注重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法律的“影响”;因此,对东亚诸国法律的“自身”特征,基本没有论述。非常可惜。另外,台湾李钟声先生《中华法系》(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5年版)虽然名为“中华法系”研究,实际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而对东亚诸国法律,只有非常简略的介绍,可以说是“名不副实”。)。虽然中国传统法律是中华法系的“祖宗”,也能反映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但是“子孙”当有自身的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法律“家族”的真正意义。
一如上述,中国学者对中华法系之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与此同时,这一研究不断朝着逐步深入的方向发展,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其一,对中华法系的固有特征的理解更为精深;其二,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语境。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华法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礼教中心;二是义务本位;三是家族观点;四是保育设施;五是崇尚仁恕;六是减轻讼累;七是灵活其法;八是审断有责(注:具体的讨论,参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3-59页。就总体精神言,陈顾远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无庸否认为农业社会文化,然无论如何,终系本于中华民族精神而表现之文化。虽奠离乎农业社会的基础,然在文化本身上,则始终把握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而不曾松懈一步。因而中国法系于‘国法’之外,而仍同时重视‘天理’,重视‘人情’以表现其特征。”据此,我们可以把陈顾远概括的上述八个特征视为“人文精神”的体现。)。这里,八个相互并列的特征,虽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括不无道理,然而毕竟显得有点就事论事,缺乏解读中华法系的基本“理路”;具体说来,其他七个特征其实只是“礼教中心”的自然延伸或应有之义。当然“审断有责”与法家思想稍稍有些关系。李钟声先生指出:中华法系的根本特征,实是“人本主义”精神(注:参见前揭李钟声:《中华法系》,第9-14页,第782-788页。)。这一概括突出的是中华法系的“人文”境界,是否得当可以讨论;但是,它的研究逻辑是比较彻底的,值得重视。自洎80年代,张晋藩先后在总结陈顾远、丁元普诸位先生对中华法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法系具有下列特征:其一,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兼融道释两家;其二,出礼入刑,礼刑结合;其三,家族伦理占据重要地位;其四,中央政府独占立法权与司法权,司法与行政合一;其五,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民刑有分、诸法并用;其六,以汉族为主体,兼融其他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注:详尽的讨论,参见张晋藩:《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张晋藩:《求索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51页。)。如果以此思路考察中华法系,那么张晋藩先生的新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对中国传统法律特征的概括,也可用以表示中华法系的特征:
出礼入法、礼法结合;恭行天罚、执法原情;法则公平、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独秀;以法治官、明职课责;纵向比较、因时定制;立法修律、比附判例;授法定罪、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注: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由上面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中华法系的梳理日趋精深完备,表明对此问题研究的“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研究的视角大抵相同。换句话说,在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稍可注意的是,郝铁川先生所著《中华法系研究》一书,在史料利用与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他指出,中华法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包括:法典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百姓大众法律意识的鬼神化(注:参见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前面两个特征的概括,我暂时不予讨论。在我看来,郝铁川对百姓大众法律意识鬼神化的解读,虽然尚有商量的余地(注:瞿同祖在讨论中国传统“神判”时说:“法律制裁是主体,宗教制裁则居于辅助的地位。”又说:“官吏遇有疑难不决的案件,往往祈求神助。”详尽的讨论,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0页-256页。);但是,他的研究视角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换句话说,他对中华法系的价值观念的解释,已经超越官方典籍与精英阶层而进入民间社会。而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华法系所缺乏的。事实上,无论是研究中华法系还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仅仅关注官方典籍与精英阶层,显然是不够的;法律作为构成百姓大众“生活世界”的另一侧面,他们对法律的所思所想或法律意识,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再思:中华法系的特征与精神
写到这里,我觉得应该顺便谈谈我对中华法系的一些粗浅意见。不过,我得声明:尽管我在前面指出,作为“法系”研究,应当关注各个“家族”成员的法律文化的特色;然而,由于语言障碍与平时缺乏专门研究,对东亚诸国法律文化的自身特色,我在这里无法予以检讨;故而,我的讨论依然限于中国传统法律领域,仅仅以此作为我们理解中华法系的固有特征与基本精神的一个“窗口”。
1.礼法文化:一个类型的解释视角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学者对“法系”的分类,至今缺乏统一的标准;而确定这样一个标准,对“法系”研究来说实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确定这个标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法律文化的规范特征与精神特征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思考。第一,从规范特征看,“礼法文化”是评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式特征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第二,就精神特征说,“天人合一”则是界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特征的一个相对恰当的依据。
下面,我先从“礼法文化”的角度谈些粗浅的看法。所谓“礼法文化”,既是一个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又是一个“类型”研究的视角。那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法律文化呢?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
梁漱溟先生基于比较文化的立场,不仅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而且认为中国属于“伦理文化”类型(注:关于中国“伦理文化”的具体分析,参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4页。稍可注意的是,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尽管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事实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理路更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并且,尽管其中颇有“洞见”,然而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认知,或有夸大之处。)。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讲,瞿同祖先生基于社会学的视域指出:对法律的意义和作用的理解,取决于对法律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理解(注:参前揭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第1页。)。笔者认为,从瞿同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身分社会”类型。据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属“身分法律”。正是根据梁漱溟和瞿同祖的上述分析,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界有人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归入“伦理法”或“身分法”类型。这种分样,当然有其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是仔细考究起来,总有未妥之处。因为,所谓“身分法”或“伦理法”云云,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法律调整的“内容”的概括;然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表现“形式”特征尚未予以充分揭示。当然,亦非全无涉及。因为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或“身分社会”的规则体系,乃是“礼”;并且,学者在研究和分析时也都极为重视对“礼”的诠释(注: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秋季号。)。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决定放弃“伦理法”或“身分法”等等的论断,而从“礼法文化”的视角来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对“礼法文化”这一概念,梁治平先生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里,曾经有过专门的讨论(注: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50页。)。只是,他没有明确提出“礼法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的概念,现在的问题是何以“礼法文化”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规范特征呢?当然,不仅仅是规范方面,同时也涉及精神方面。我在那篇评论里继续写道:
理由在于:其一,礼,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属于中国传统法律固有的,也是极为独特的概念;故而,它能够比较真切地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形式(注:顾晓鸣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礼’大致与西方的ritual或rite相近,哪一个民族设有‘礼’呢?老实说,犹太——基督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礼’之繁复和刻板绝不亚于中国文化。”如此看来,礼,似乎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独特概念的进一步开掘,成为一项前提性的工作。参见顾晓鸣:《对“礼”的文化机制本身的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日本学者池田温指出:礼,乃是汉民族数千年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精华的结晶。转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认为:“礼与乐二者的突出,形成为两颗牟尼珠型的人文观念,可说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要成就。”饶宗颐等:《礼:情理的表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页。我想,把以“礼”为精神归依的法律视作“礼法文化”类型,是比较合适的概括。)。其二,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的特点,不仅与天理、信仰、道德、人情等等“形上”和“形下”的理念相互关联,而且与法律的具体规则相连相通(注:当然,把“礼”作为一个分析概念,也有危险的地方;原因在于“礼”的内涵非常丰富,一旦进入法律文化领域,可能就会导致“意义”的失落。)。并且,礼本身就有法律的性质(注:对“礼”的法律性质等问题的详尽讨论,参见徐忠明:《“礼治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其三,礼,就其本义来说,具有“分”或“别”的基本含义和精神特质,这一含义和特质彰显的就是社会身分和政治等级。这样,礼,不仅可以包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分和政治等级的实际内容,而且能够体现法律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趋向。其四,礼,对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现代学者往往是在“礼”的名义下检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私法”、“自然法”、“无讼”以及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诸多问题的;所以,廓清“礼”的内涵和特质,对梳理和界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性格和精神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五,礼,作为一种较为特殊,并且能够兼容天理、信仰、道德、人情、法律性质的各个层面的行为规范,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刑治”主义特色。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社会“刑法本位”的法律传统之所以能够形成,固然有着诸多其他*
社会、政治原因;但是,就法律制度层面而言,则与“礼”的道德趋向有关,实际就是“礼”的道德追求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注: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刑”的关系的详尽讨论,参见徐忠明:《“刑治”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比较法研究》待刊。)。对中国传统社会这样一种法律文化来说,舍弃“礼法”两字,则无以名之矣(注:前揭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括,既是我对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主题”的解读,又是我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问题的粗浅思考。)。
据此简要评析,我想,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实系“礼法文化”,应该是可以的。当然,对其中的细节问题的详尽论证,囿于篇幅,只好暂时从略。
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法文化”的形成原因,在我看来,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关系或结构当中获得比较合理的解释。借用《慎子·佚文》“礼从俗,政从上”一言,则可以说:礼,源于早期社会的风俗、习惯,具有社会性的特征,随后渐次进入政治领域;政,可理解为“法”,起于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就中国情形而言,由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重要作用,故而法律的暴力色彩也就异常的突出。进而,基于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既相分离又相关连的独特关系,因此“礼与法”之间从来没有真正断裂;自青铜时代“礼与刑”洎汉代以降“礼与律”的变迁,都是这一“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关系的反映。对此问题,这里不便详论。
2.天人合一:礼法文化的精神境界。钱穆先生毕生精研“国学”,晚年发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彻悟”。他说:所谓“天人合一”思想,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归宿;这一思想的基本要义,乃是不仅不违背自然天命,而且还能与自然天命融合一体(注:详尽的解说,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1991年8月,第4期。)。就“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论,遍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构成中国古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注:有关的讨论,参见江晓原:《天文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另可参见陈江风:《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它不仅涉及中国古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求,而且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具体层面的“形下”建构。所以,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境界的,无疑是“天人合一”思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意要深入探究与领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特色,那就必须阐明“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角度讲,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以下的变迁和发展:这一思想的渊源可以溯及神话传说时期,它是初民社会“万物有灵”观念之反映,所谓“民神杂揉”和“家为巫史”即其表现。随着文明社会的来临,对政治权力的独占逐步出现,《国语·楚语》“绝天地通”就是经典话语。到了青铜时代,这一思想遂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终极根据。只是,周人对之有突破性的改造,提出“以德配天”的政治哲学,《诗经·大雅·皇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为明证。自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对“天人”关系作过多种多样的思考;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天道”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示范意义和制约作用。汉朝儒宗董仲舒更是兼综百家,提出“天人感应”与“天人相类”学说。进入宋明时代,理学家更加注重“天人”之间的内在相通,故而“天人”关系也就具有更加原理化和内在化的道德色彩;在理学家看来,“天道”与“人道”只是一个“道”。当然,“人道”与“天道”也有超越性的特征。
总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首先,“天”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具有完美的德性与自然和谐的秩序;这就是所谓“天道”。其次,“人”的德性源自“天”,因此必须依顺“天”而非主宰“天”;进而,要求“人”在建构社会秩序方面同样寻求“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和谐”。
那末,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在法律文化上又有哪些反映呢?朱勇先生指出:
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度遵循“则天立法”原则,以“天”为制定法律的最终根据;在法律的实施方面,实行“刑狱时令”、“灾异赦宥”制度;对于人命案件的处理,适用“以命抵命”原则,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法律的自然主义特征(注:朱勇:《中国古代法律的自然主义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有关的讨论,参见前揭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326-350页。另可参见徐忠明:《“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72页。)(今按:所谓“自然主义”是指“天人合一”思想的法律反映)。
这一简要概括,对“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已经基本涉及;不过,有些地方尚有必要稍加补充。一是“礼与刑”的关系问题。古人认为,对“礼与刑”的关系,必须依据“天道”加以厘定;《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就是一个著名例证。二是“身分等级”制度问题。对身分等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古人也从“天人合一”角度予以证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中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及“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是贵贱上下身分等级的通则;据此论证“三纲”的“天道”的依据(注:具体的论说,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三是法典“结构”问题。前面说过,“天道”是一个自足的、完备的、和谐的系统,一如昼夜、四时之运行,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自然而然。在我看来,古人思维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系统的自足性和完备性;号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的结构就是如此。从法典“结构”来看,同样具有这一特征(注:有关的讨论,参见前揭徐忠明:《“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顺便指出,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法典结构时,往往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的问题。)。四是“五刑”制度的解释问题。东汉《白虎通义·五刑》记有“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的说法,把“五刑”纳入“五行”制度的起源应与“五方”神祗崇拜有关(注:对此问题的详细考证,参见徐忠明:《神话思维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若干问题释证》,《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2期。),因此也与“则天立法”思想有关。五是“天道”公正问题。所谓“以命抵命”与“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等等,当然是古人的公正观念的体现;但是,更有进者,古人相信唯有“天”是最为公正的,而且能够“明察秋毫”;因此一旦疑狱或冤狱出现,便会诉诸“天”祈求澄清疑狱或平反冤狱,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注:有关的讨论,参见徐忠明:《〈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若干问题试析》,《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
至于其他种种表现,这里不便详述。综而论之,我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境界的最高体现;或者说是各种法律制度有终极依据。
写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果。不过,我想在此说几句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早在晚清“新政·修律”运动期,“礼教派”就有维护“礼教纲常”的鼓吹;即便“法理派”沈家本也认为:“吾国旧律,自成体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以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注:沈家本:《法学名著序》,《寄簃文存》卷3。)。因此,他主张“旧律”与新学“相互发明”(注:沈家本:《刑案汇览三编序》,《寄簃文存》卷6。)。这些说法,既有利益的动机,也有情感的附系。自洎30年代,丁元普等学者更有“复兴中华法系之精神”的吁求(注:丁元普:《中华法系与民族复兴》,《中华法学杂志》1937年1卷7期。)。凡此种种,多少包含我们在面临现代西方“强势”文化时,一则感到不得不变,再则又不甘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此“消亡”;所以,致有“挽救”乃至“复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呼号。如今,中国法律文化的西方化,已成不可避免之势;然而,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全盘西化”已经无人坚执,“固守传统”也无人提倡;但是,面对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两者之间如何合理协调?依然问题多多。有的学者主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论断,是林毓生在1972年提出的,详细的讨论,参见Lin Yu-sheng,"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in Benjamin I.Schwartz,ed.,Reflections on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MA:Harurd University Press,1972.这一看法在国内学界颇有影响,也有不少异议。最近,林毓生对此又予申说。参见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0-357页。),有的学者提倡法律现代化必须利用“本土资源”(注: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当然,苏力的“本土资源”并非仅仅是指传统法律文化,而更多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资源,包括法律文化资源。与此同时,苏力的“本土资源”的提法,并非仅仅是旨在从“法律实践”里提取某些法律资源。还应包含解读与理解中国“本土”法律文化的一种方法和立场。对苏力的“本土资源”提法的方法论意义,刘星先生有一简要评论,参见刘星:《解读本土法律文*
:评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2号,总第51期。)。他们的思路都是认为:传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可以任人“重组/改造”的。对我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一块“底色”,一种“语境”。对此,我们无法“抛弃”,就象语言之于我们,它是先在的、既定的;也好比我们不能拨起自己的头发,要求脱离地球一样;因此,我们也就无法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但是,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看到:现今,西方法律文化(晚清开始学西方,后来又学苏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新传统”,无论是法律的制度结构还是法律的学术话语,都是如此。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面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而是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的新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一“新传统”的语境里造就一个更加符合自由、民主的现代法律文化。这,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严肃思考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说到这里,或许还应加上一句,未来的中国法律文化一定是“西方化”的;但是,基于我们选择的文化语境与实际状况,这样一种法律文化同时又是“中国化”的。
标签:中华法系论文; 中国法制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法律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