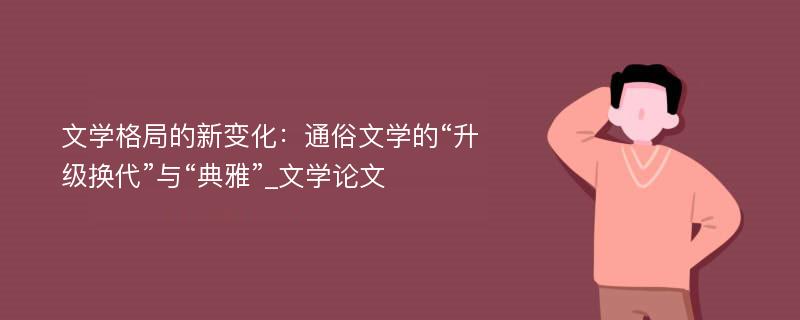
文学格局新变: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通俗论文,格局论文,雅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4-0130-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变化,导致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渐变 ,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一方面,高雅文学逐渐呈现出俗化 的倾向;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却有一股“雅化”的趋势,使得多年来雅俗文学相互对峙 、相互抗衡的关系正逐步改变为融合、互补的关系。大量高知阶层读者的介入,使通俗 文学逐渐脱离了“通俗”的概念和躯壳。目前通俗文学正一步一步跻身于主流文化,进 而准备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殿堂,名正言顺地与高雅文学并驾齐驱,而读者也以宽容的 态度同时接受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
一
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突出表现为许多通俗文学作家正在用高雅文学的话 语以及叙述方式讲述通俗文学的“故事”,并由通俗文学惯用的单纯“讲故事”方式改 为让形象丰满的人物“表演故事”,许多作家一改通俗文学以情节取胜的创作套路,变 为以塑造人物性格、挖掘人物心灵、描写人物心路历程为主要创作手段,使得作品的文 学艺术含量大大增强,也使通俗文学达到一个较高的美学层次。
形成这种新的文学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建国后我国通俗小 说发展的大致状况。由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特殊国情所造就的特殊的文艺政策,政府 查禁了带有所谓“封建色彩”的旧小说,如武侠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等(这类作 品也曾经是“五四”新文学所批评过的),只留下了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为 “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为工农兵服务”的题材一花独放。60年代到70年 代中期“为政治服务”的风气达到极致,以至于文苑几近凋零。70年代末,由于政局的 变动和随之而来的相应的政策的调整,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许多古典通俗文学作品 和外国的通俗经典,如《三言两拍》《基督山伯爵》之类作品相继得以出版,这些作品 以其情节的紧凑、离奇而获得众多读者的青睐,通俗文学的影响初见端倪。
80年代起,随着经济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政治的淡出,使人们在衣 食饱暖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与上层建筑的忧虑开始降低。生活不再无所适从,人们不 再急于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这样,文学开始由载道教化的工具逐步 回归自身,由强调其社会思想价值逐渐转向审美价值,由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转向着重 审美愉悦、文化消遣、自我表现、自我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作家也在日渐宽松的 政治经济氛围中卸下神圣但也十分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担子,由听命于政治、追求 社会效益转入比较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文学由此开始呈现出边缘化倾向,政治色彩愈 来愈淡。正是此时,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发展兴盛成为可能。
80年代大陆通俗文学热的现象,首先当推港台通俗文学的登陆。金大侠笑遨江湖,倚 天屠龙,白马啸西风;琼女士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引起极大反响。港台 通俗文学从70年代的金庸、琼瑶(注:金庸作品其时盛行江湖,但皆为盗版,大陆尚未 发行出版。琼瑶自1982年起,就已在《海峡》杂志上连载长篇《我是一片云》,其后, 由于同名电视剧的播出,琼瑶作品每部单行本发行量均以十万计。),延续到90年代的 梁凤仪和席娟。港台通俗文艺飓风登陆,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令人无法漠视、无法回避的 震撼。回肠荡气的江湖侠义,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文笔纵横捭阖,摇曳生姿,影响了 大批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培养了数千万亲历过“文革”荒漠的读者群,同时书商也个 个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种状况,极大地刺激了大陆作家的创作心理。大众文化消费 市场的建立,使那些曾经致力于纯文学、雅文学的作家们,在图书市场对作品的选择中 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读者的危机,对于已摆脱了正统观念、身心进入自由状态的作家来说 ,这一切显然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赢得读者的契机,使之看到了一种接近读者的方式,这 对他们进行自觉的通俗作品的创作,起到了引导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也开始关注文 学作品的消遣、娱乐功能。另外,由于这些作家高雅文学作家的身份,也使大陆本土的 通俗文学创作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并且从一开始就在审美意识、审美方式、价 值取向上与高雅文学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题材、主题、内容,还是在手法、风格、语言 上,都留下了鲜明的高雅文学的胎记,并由此而区别于港台某些纯商业化的通俗文学。 权延赤、叶永烈等人的传记文学,以及冯骥才《三寸金莲》《神鞭》和化名为香港“雪 米莉”的两位四川男作家的系列作品,张欣、刘西鸿等人的言情小说等等,即是在这种 环境下产生的,这些作品在市场上赢得了很大的成功。时至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发展的90 年代,通俗文学的畅销成为它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最大确证,因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由俗至 雅,也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二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读者的需求是形成这种新的文学格局的直接动因。文学作品的 艺术价值虽然决不能单单以读者的多寡来判定,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格局甚至风格、 流派、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与读者结构以及读者状况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20世 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九年义务制教育结出丰硕成果(根据调 查材料得知,目前农村男性外出打工者大多达到初中文化水平,也有读到高中毕业的)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希望通过他们能够接受的通俗 文学来补充知识、愉悦身心;而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也试图通过欣赏通俗文学 得到身心放松,以缓解或排除由于快节奏社会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负荷(注:严家炎在 谈论金庸小说时曾说:“连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政治家乃至一些领袖人物也会 入迷。像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像国际著名的中国文学 专家陈世骧、夏济安、程千帆,他们都喜欢阅读和谈论金庸小说。”(见严家炎:《金 庸小说论稿·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页 。))。为了满足这样一个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的精神文化需要,通俗文学方阵 的实力变得相当雄厚,呈现出作家多、作品多、期刊多的繁茂景象。还有不少作家从经 济利益出发,主动与高雅文学队伍离异,弃雅从俗,向通俗文学献媚,这种力量无疑壮 大了通俗文学创作阵营。全国各地的通俗文学刊物如《今古奇观》《中华传奇》《山海 经》《新聊斋》《通俗文艺大观》《大众小说》《故事会》《故事家》《中国故事》《 民间文学》……如春草萌生,千姿百态,其发行量几乎每一种都超过100万(远远大于任 何一种高雅文学的发行量),最多的达到650万,于是一些原来高雅文学阵地为了赢得市 场,也纷纷将刊物更名为《通俗文学》《文娱世界》《热点文学》等[1](P215),以强 劲势头占据了文化市场。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对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的全方位的影响甚至颠覆,人们的阅 读心理变迁得更快,对通俗文学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其时大陆通俗文学处于萌芽阶段, 港台与外国通俗文学乘机蜂拥而入,在文化市场上尽领风骚。虽然其中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但饥不择食的读者却掀起了一阵阵阅读热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精神文 明程度的提高、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对这些作品又产生了“审美疲倦”的阅 读逆反心理,读者在获得某种消遣、宣泄、补偿之后,又产生了希望超越原有作品的阅 读渴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回头去青睐高雅文学,而是标志着大众读者需要较高 品位的通俗文学——一种介乎于高雅文学与商业性文学之间而又与它们有所区别的文学 。这个变化也促使理论界、学术界面对不断变化的现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加强了对通 俗文学的评介和研究,并充分肯定了通俗文学的认识价值,这也对通俗文学的高潮迭起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可见,读者对通俗文学新的更高品位的需求与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构 成了20世纪90年代大陆通俗文学兴起和雅化的内在契机。
三
这里所说的“升格”与“雅化”,是以通俗文学层次的提高为前提,不是纯粹以高雅 文学的尺度和标准对其进行评判的。我们认为,通俗文学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坛“一代 天骄”的更内在的原因,则是其自身的“升格”和“雅化”。“在文学史长期以来的雅 俗对峙中,高雅文学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得通俗文学吸取对方营养以提高自身的素质。 ”[2](P179)吸取高雅文学的营养,这是通俗文学发生“质变”的必由之路。近十几年 来,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跳出了原有的圈子,努力提高思想性、艺术性,主动承担一定的 社会责任,力图超越“通俗”步入高雅的殿堂,使一些本来通俗文学标记清晰的作品变 得难以辨别,呈现出“俗”中有“雅”,若俗若雅的局面。
一般来说,通俗文学内容远离社会主流,理性负载小,不像高雅文学那样追求艺术趣 味,对语言文字、艺术技法不那么讲究,对细节的选择也不那么精细,对精神内涵的挖 掘也不那么深刻,有时有些作品还宣扬封建迷信或暴力。但是,最为可贵的是,通俗文 学作品不以文人审美情趣为本位,而是以较强的故事性、情节性贴近大众审美情趣,表 现他们熟悉的生活、人生趣味和人格理想,满足他们的审美愉悦。这些都决定了通俗文 学必定稳步走向市场。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主要的三大类(注:应该说,通俗文学还有侦 探类、科幻类等,由于其作品较少,稍嫌嫩弱,这里暂省略不计。)——武侠类、言情 类、史传类,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雅化”现象。“雅化”了的通俗文学作品不仅充分 吸纳了传统和民间的丰富营养,蕴涵着深邃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往 往以人的解放和时代精神为基点,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对陈腐落后的文化思想体系进 行成功的改造,如著名作家邓友梅的《烟壶》、冯骥才的《神鞭》《义和拳》、陆文夫 的《美食家》等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可以看作是“ 雅化”了的通俗文学。
金庸新武侠小说受到很高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突破了旧武侠文体中低层次的 、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体系,以五四新文化思想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思想。他以中国传 统文学为框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艺术表现技法,情节曲折生动,丝丝入扣,人物性格 复杂立体,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其艺术成就不仅在通俗文学界,即使 在高雅文学界,也备受称道,甚至有人将之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小说家之内,其作品也 多次入选为世纪经典。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受欢迎,可能反映出广大读者对我们作 品注重写实却缺少丰富想象力的状况不满足。另外,金庸把文学为人生与文学的娱乐性 统一起来,这点也很值得注意”[3],并且认为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模式有很大的 突破。从初期作品《射雕》三部曲对“侠”与“义”的弘扬,到后期的《鹿鼎记》对“ 反武侠”的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格的揭示,显示了一位作家对人生、社会日益深入的 理解。金庸作品将武侠小说的“哥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与 五四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金庸小说 把侠客“救民于水火”的个人狭义行为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联系起来,超出了个人 恩怨情仇和江湖英雄争霸的套路,突出“大侠”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品格,使读者得 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进而得到精神的升华。更突出的是,金庸新武侠小说改变了传统 武侠小说只重情节曲折而不重人物塑造的创作模式,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人物成 长的经历和过程清晰可见。作者还以写意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 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的学理来阐述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
另一位武侠小说高手古龙,在武侠小说情节结构上力图求新求变,将西方现代小说, 尤其是欧美的侦探推理手法融入武侠小说的创作,在语言上采用散文的笔调,精炼的句 式,并巧妙穿插格言警句式的人生感悟。这些特点都使古龙的作品在公认的“金庸模式 ”下另辟一种风格,并呈现出与传统武侠小说迥然不同的状态。正是因此,古龙被视为 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真正开创者。古龙的武侠小说虽然缺少金庸的博大精深,但其情 节的曲折诡异、文字的简捷敏锐及独特的哲理味道,无不显示出纵横的才气与魅力,受 到无数读者的喜爱。所有这些新的精神内涵和文学内涵不仅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突破和 超越,也为通俗文学的“升格”和“雅化”走出了一条新路。
四
通俗文学的“雅化”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包括历史)有继承有改造,如历史小说《李 自成》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百科全书”,其高出一般通俗文学之处在于强化了人物的形 象塑造,表现了人物在文本构造中所具有的深层的人性内涵。这部小说除了主要人物以 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亡国之君”。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作者“摒弃了把人作为 社会观念、阶级观念传声筒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思维方式,恢复了崇祯皇帝同时又是一个 具有社会复杂性的独具个性的人的本来面目”[4](P146),以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的“人”的存在方式出现。“帝王人性”的描写无疑是姚雪垠对史传类通俗文学描写人 性的一种开拓。20世纪90年代,在历史传奇写作这个领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张笑 天的《太平天国》、冯昭的《世纪之门》、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 、郑九蝉的《红梦》等。这些小说对历史的书写走出了专写起义农民的模式。凌力、二 月河的清宫小说,大胆地将笔触伸进帝王将相的天地,塑造了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帝王 形象,既有历史感又有文学性,使其在雅俗共赏的同时已深深带上了高雅文学的印记。 但是,这并不是一般的写作对象的转移,它在深层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中奴隶创造历史 的“英雄史观”,其哲学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通俗文学的“雅化”还表现在作家运用想像、创造意境、讲究语言。他们继承了中国 古典文学的精华,语言新鲜活泼、通俗精练,传神而优美。琼瑶言情小说表现了作家文 学语言的深厚功底,典雅婉约,凝练深沉。琼瑶有古典文学家学渊源,又偏爱古诗词, 特别善于运用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爱情故事,她引用、仿作的古诗词蕴藉含蓄、韵味隽 永,充满诗情画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尽管琼瑶小说构思落套,缺乏深度, 然而她的作品语言古典美的意境确是超凡脱俗的,是以往任何言情类通俗小说无可比拟 的。
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严格的高雅、通俗之分的,中国文学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 经·国风》。“国风”是《诗经》的核心和精华,是最有价值的部分。“风”原本是流 传于民间的歌谣,是相对于周天子所在的首都而言的各地方的土乐,即地方俗曲或地方 小调,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戏曲一样,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宋代朱熹曾言:“风者,民 俗歌谣之诗也。”他肯定的“风”,指的是“民俗歌谣”。当时编辑《诗经》是作为制 礼作乐的先期产品,目的是达到封建教化作用,到春秋时期“赋诗言志”,这一新的表 意途径才被广泛利用。《诗经·国风》在原先编辑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充实、调整,日 趋完善,最终成为一部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集优秀诗歌创作之大成的文学经典,被称 之为“经”。其后的乐府诗、唐传奇、宋词、金院本、元杂剧……原来也都是通俗文学 ,而现在“升格”为高雅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成为经典。又如,六朝时我 国的佛教大为发展,到唐朝时已成为统治阶级最崇尚和最提倡的宗教,僧人们为了宣传 佛经教义,将佛经编成浅显有趣、通俗易懂的“变文”故事,讲解给老百姓。这些“变 文”故事性很强,有人物、有事件、有情节,很吸引人,很有文学性。后来逐渐演变出 非佛教的变文故事,这些故事经过文人的介入走进了话本和讲唱艺术。直至元末明初,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正式将小说标题冠以“通俗”二字,说明其内容不是采于正 史。
考察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文学由“通俗”向“高雅”的变迁是一个规律 。世界文学名著如薄迦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唐·吉诃 德》、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本来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在 世代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表现的认识作用、文化历史传统或民俗民情产生了不可替代 的美学价值而“升格”为经典文学。
五
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几次通俗文学对高雅文学的冲击。比如唐朝以来,由于经济的发 展以及与外来经济、文化的交往,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变化,唐传奇、讲唱艺术、话本等 文学样式相继出现。这些本来是民间、坊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被文人们接受之后 ,产量渐多,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不但形成与当时文学的代表样式诗歌的对峙(或辅 助)形式,而且使这一文学样式得以流传至今。宋以后,民间文学兴盛,北宋杂剧、金 院本、南宋戏文、白话小说相继出现,词也从民间走向文坛。明清时由于小说的发展( 长篇《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西游记》《金瓶梅》成书于明后期, 《红楼梦》成书于清),拟话本和属于市民文学的地方戏曲、讲唱文学、民谣民歌的繁 荣昌盛,“通俗文学”对“阳春白雪”的传统文学(散文、诗词)形成了冲击。中国自古 以来,“小说”这个概念便与通俗相连,被称为“妾小艺术”。《汉书·艺文志》就有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巷谈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种观念,流传甚久 ,直至唐宋。而小说以其娱乐性、消遣性吸引了很多读者,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戏曲 以其优美的唱腔,精美的脸谱,动人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大量市民观众,而传统的“高 雅”文学却以其一贯“卫道”的面孔说理、叙事或代圣贤立言,并且文人拟古之风日盛 ,从文字上到内容上都令人生厌,因此只有少数人在写作、在小范围内使用,以致演进 成为人人厌恶的“八股文”。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就有“通俗 远行之文学”的提法,他们曾提出“国民文学”、“平民的文学”,他们的努力,使传 统的“高雅”文学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价值变更。
通俗文学的“升格”和“雅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提高审美层次、审美价值的过 程,是需要作者不懈努力的。随着新世纪审美文学的需要和发展,如何促进通俗文学的 “升格”和“雅化”,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亟需研究和正确对待的重要课题。通俗文学 也只有不断“升格”和“雅化”,才能真正跨入主流文化的行列,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 部分。同时,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 架子,在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比如,通过电视节目获得知识的需求以及现 代人对电视节目产生的依赖,也强化了高雅文学的变迁。央视就有十几个频道播出,再 加上各地方台的上星频道总共有几十个,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 八小时之外能够享受一些轻松、愉快,而各地方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观众,也在做大 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通俗文学靠拢,而通俗文学主动向高雅文 学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这种格局最终结果,那就是文学 的雅俗共赏。文学由“通俗”向“高雅”的变迁是一个规律。
当前,促进通俗文学的“升格”和“雅化”是文学家、评论家面临的一项责无旁贷的 任务,也是全体文学工作者无法逃遁的天职。因为高雅文学对通俗文学有着提升层次的 责任,产生着正面的影响;而通俗文学会对高雅文学产生辐射作用,如果这个问题处理 不好,会导致整个社会文学的“生态”不平衡。我们说,通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好 ,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 精神的力量。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整个社会审美文化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4-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