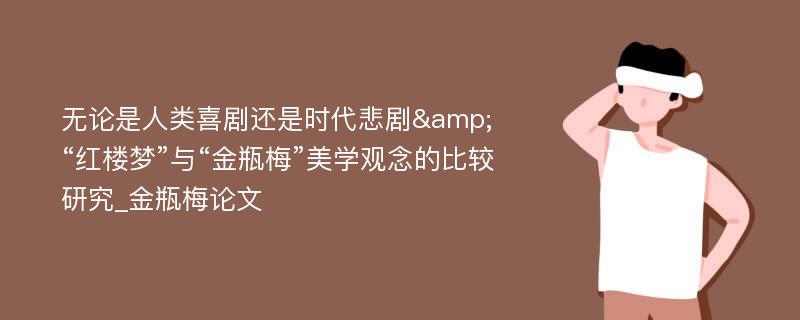
究竟是人间喜剧,还是时代悲剧——《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观念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金瓶梅论文,喜剧论文,悲剧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世情小说的两座高峰,没有《金瓶梅》的拔地而起也就没有《红楼梦》的横空出世。所以,二知道人说《红楼梦》:“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注: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所以,鲁迅说《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注:《鲁迅全集》卷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所以,脂砚斋说《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注:见庚辰本第十三回脂批,“壸”原批抄本误作“壸”。)。
然而,所谓《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当指其以一个家族的盛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人世诸相,论其审美观念却与《金瓶梅》异趣。说得明确一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在描摹人世诸相时注重于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呈现于他笔端的乃时代悲剧;而《金瓶梅》的作者在描摹人世诸相时则迷恋于将人生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所以呈现于他笔端的是人间喜剧。二者在中国小说发展上,“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都为后人的创作所难以企及。
二、从作品的描写对象来说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以“富而好礼”为其特点的。它是当时令人亦羡亦畏的诗礼簪缨之族;它是当时令人可赞可叹的忠臣孝子之门;它是当时令人可敬可亲的慈善宽厚之第(注:参见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称·<红楼梦>悲剧论》。)。清官林如海与贾雨村说贾政:“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梁轻仕宦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屑为矣。”村妪刘姥姥与女婿说王夫人:“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城市平民花自芳母子心目中的贾府:“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凡此,实反映了时人的看法,传达了贾府的口碑。然而,贾府的这个“富而好礼”之族又是以封建宗法统治为其法宝的,它虽则给大观园里的人们以锦衣玉食,却不准他们“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只准他们“各安其位,各操其职”。正因如此,所以,吴现于作者笔端的那些贾母们按纲常名教精心筑就的王道乐土,同时也就成为一座禁锢青年们肉体和灵魂的黑暗王国,而觉醒者要求自由的呐喊则声声可闻。马克思曾言:“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是以贾府的盛衰史当属时代悲剧。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家则相反,其特点是“为富不仁”。它作为官僚家庭,与朝廷奸党连络有亲,是权奸的爪牙;它作为地主家庭,与土豪劣绅俱有照应,是翻云作雨的恶霸;它作为商人家庭,与各级官府勾打连环,是依仗权势而生财有道的富豪。这种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就使它成为后世官僚资本家庭的最初雏形。要特别注意的是,支撑这一罪恶家庭的主要支点,却不是权势,更不是土地,而是金钱。书中写得清楚:是金钱使这一家庭获得了权势,权势又使这一家庭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土地则是其金钱和权势的副产品;是金钱和权势助长着这一家庭的淫乐之风,与日俱增的淫乐之风又成为这一家庭的对金钱和权势的炫耀,其结果是使这一家庭带着它的罪恶迅即走入坟墓。这是一种如实描写,因为旧时的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度,随着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而商人要想求得财源茂盛和地位稳固,便去一面勾结官府,以期获得一张特殊的护身符,一面花点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半个地主。这便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何以发展缓慢的文化原因,也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何以先于民族资本而出现的政治原因。正因为西门庆家是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结合而以金钱为其主要价值观念,致贪残无比,淫乐成性,小民为之蹙额,市肆为之骚然,是以这一家庭的兴衰史当属人间喜剧。
《红楼梦》作者笔端的主人公贾宝玉,是近代启蒙主义者的先驱。如果说,“情不情”是其思想性格的核心,那么,“意淫”则是其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和处世哲学的伦理原则。说得更明快一点,二者的关系是:“情不情”是贾宝玉的“意淫”的外在表现形式,“意淫”是贾宝玉的“情不情”的内在思想意蕴。而所谓“意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爱心,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是以贾宝玉的“情不情”,便表现为他对悲剧女性,不论亲疏,俱以一己真情去体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乃至“重情不重礼”(注:见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脂批。),认为女性是与男性相平等的人。因此,面对“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世道,他不以仕途经济、位列朝纲为念,而以“护法群钗”作为自己的“一番事业”。这不是在一般地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这是在否定以男性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合理性;尽管他在行动上是个势单力薄的泥足巨人,可在思想上却是个十分富有的铮铮铁汉,而这正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本然特征。这场斗争又是那么具有历史意义,它“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因此,贾宝玉的“重情不重礼”而终为“礼”所吞没,便成为令人遗恨绵绵的时代悲剧,更何况他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又属千古绝唱。
《金瓶梅》作者笔端的主人公西门庆,是近代官僚资本家的远祖。如果说,其思想性格的核心是贪婪,那么,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则是其价值观念和精神归宿。一是对女色的贪婪:他靠“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邓通般有钱”、“青春小少”和“闲工夫”,占有一妻五妾、四个通房丫环、九个姘妇、三个妓女;想淫而未及淫者,还有何千户娘子蓝氏、王三官娘子黄氏。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难怪时人称他为“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二是对金钱的贪婪:还是个破落户财主时,他便“与人把揽说事”,“又放官吏债”,捞取黑心钱;当上金吾卫副千户后,仅替扬州盐商王四峰说一回情就获取白银二千两。其“灰色收入”,于此可见一斑。那么,商业方面呢?他交通官府,欺行霸市,别人不敢做的买卖他敢做,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打不通的官府关节他能打通,别人需交的税他可免。其长袖善舞如此,是以不几年便富甲一方。三是对权势的贪婪:一旦由破落户发迹,他便以金钱和美女铺路,交结各色官员,与权臣蔡京的总管翟谦称兄道弟,在翟谦的全力关照下,直至官居金吾卫副千户,直至成为蔡京的义子,直至官居金吾卫正千户,而这正是比当时的堂堂京官还有权势的肥缺。然而,要注意的是,察其灵魂,他对金钱的贪婪有甚于对女色的贪婪,他对权势的贪婪有逊于对金钱的贪婪。正因如此,所以富孀孟玉楼其貌虽不及潘金莲,而他却搁下潘金莲先娶孟玉楼,盖以其有上千两现金和三二百筒三梭布也;所以他备重礼去给蔡京贺寿,其初衷并不是想官居五品,盖旨在为他的巧取豪夺找一政治靠山也。其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用他的自画招供来说,就是:“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他是在说:金钱可以买通政治权力,从而为所欲为,纵令天下女子供我片时之淫乐,亦理所当然。多么可笑啊,一个拜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的卑劣灵魂。因此,西门庆这种意气洋洋地驾着由女色、金钱、权势构成的三套马车之堕入深谷,便成为令人可卑可笑的人间喜剧,更何况他的贪欲得病而一命呜呼又属千古丑闻。
《红楼梦》中的群钗,是幅百美图。正如二知道人所说:“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去,除却怡红公子,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注: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6页。)且看“怡红院诸婢,醵钱开宴,为公子介寿、笑与抃会,欢将乐来。维时脱去边幅,率意承接,歌则殊声合响,觞则引满传空,诸婢乐公子之乐,公子亦乐诸婢之乐也。彼徒以寻香人为肉屏风者,何曾梦及!”(注: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1页。)则群钗灵魂之高洁,品性之不凡,亦欲浮纸面矣。诚然,她们既是食人间烟火的女性,当然也就各有各的心事和烦恼;以黛玉与宝钗、晴雯与袭人来说,彼此间便曾有口角含讽。然而,那是由于:黛玉和晴雯等固然不是女夫子,宝钗和袭人等行为,亦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因而“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注:庚辰本第二十回脂批。)正因如此,所以随着大观园在贾府家世利益的干预下变为一座大花冢,也就传达出一曲令人热耳酸心的青春的悲歌,从而发出一声声“救救青年”的呼喊。这青春的悲歌,不是时代悲剧又是甚么呢?
《金瓶梅》里的妇女,是一幅百丑图。张竹坡云:“《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这话说得虽有点绝对,但大致不差。环绕着西门氏的妇女不下一打,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然而“若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盖一面慈心冷之“奸险好人”而已。其他女人则几乎莫不是利欲熏心的“性饥渴症”和“性受虐症”患者,所以“邓通般有钱”和“驴大行货”遂成为她们人生赤裸裸的两大追求而尤以“驴大行货”为主,于是便去争当西门庆的“肉屏风”而以可耻作为荣耀。甚至为此而或谋杀亲夫,或与夫婿合谋,或以子媳作为穿针引线人。这种卑微的灵魂、卑贱的心理、卑劣的行为,正反映了当时以金钱为动因的病态社会在女性中所造成的病态人格与病态价值观念。论者或以潘金莲比包法利夫人,窃期期以为不可。包法利夫人所追求的是细腻的感情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其结果只是耽于物欲和淫乐。潘金莲所追求的是“邓通般有钱”和“驴大行货”,其结果是随着物欲和淫乐的获得而堕入罪恶的深渊。倒需一提的是:巴尔扎克将自己以揭露金钱关系乃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的一套小说称之为《人间喜剧》,盖因其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和“不正经女人”持讥刺态度也。那么,潘金莲等市井妇女在当时金钱关系的刺激下由追求物欲和淫乐而自我毁灭,兰陵笑笑生的这种“任何写照是讽刺”,不是人间喜剧又是甚么呢?
说《红楼梦》中的主人公们是在要求个性解放,人性自由,这在当前已几成社会共认。其实,《金瓶梅》里的主人公们又何尝不是在要求个性解放,人性自由呢!问题在于:个性解放,人性自由,属人性论范畴,乃哲学概念,它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冲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它本身并无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其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是来自与它相融会的观念:如果它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则呈现为善;如果它与极端利己主义相结合,则呈现为恶。这种善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一般反映为其体现者正面地或侧面地公然向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挑战。这种恶也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一般反映为其体现者既依附于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而又在暗中挖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墙脚。然而由于文学是人学,只应引人趋善,不应引人趋恶,所以只能歌颂善,不能歌颂恶。随着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方面出现了个性解放思潮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出现了个性解放思潮与极端利己主义的结合,二者乃历史的双胞胎,只是其体现者在道德上有贤愚之别而已。然而由于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一个是站在初步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立场观察社会和思考历史,一个是站在曾孝序之辈的思想立场观察社会和思考历史,所以也就出现了他们审美视角的不同:一个注目于贾宝玉式的近代启蒙主义者的先驱及其社会基础,故而笔端的作品成为时代悲剧,一个注目于西门庆式的近代官僚资本家的远祖及其社会基础,故而笔端的作品成为人间喜剧。可见贾宝玉和西门庆皆属“今古未有之一人”,且后世各有各的子孙,只不过一个道路口如碑,一个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已。单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和《金瓶梅》亦堪称为中国世情小说中光可鉴人的双璧,时代悲剧和人间喜剧的经典。
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来说
《红楼梦》的艺术构思是经典性的悲剧构思。要之,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问题:
该书的主题是三重悲剧构架。从接受美学来说(注:参见拙作《论<红楼梦>悲剧主题的多层次性》,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4辑。):一是情爱的颂歌,二是童心的赞歌,三是青春的悲歌,三者由表而里形成三个层面。从还原批评来说(注:参见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称·<红楼梦>结构论》。):一是作者要为一位“怡红公子”作传,即描写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把他的以“意淫”为内含的人生价值观念和人生足迹描摹给世人看。那似贬实褒的两首《西江月》,是小说的第一首主题歌。它凝聚着贾宝玉型精神悲剧的主要内涵,并界定了其质的规定性。二是作者要为一群青年女子作传,即描写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异样女子”的人生悲剧,将她们的真善美和才学识被毁灭、殊途同归于“薄命司”的苦难历程展示给世人看。那饱含着赞赏和痛悼之情的《红楼十二支曲》,是小说的第二组主题歌。它不失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缩影。三是作者要为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作传,即描写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贾府,由于坐吃山空、儿孙不肖而日益衰微的历史悲剧,将这个百年望族的人生价值观念及藏于礼法帷幕后面的“自相戕戮自张罗”情景描绘给世人看。那半含讥弹、半是挽歌的《好了歌》、《好了歌解》,是小说的第三组主题歌。它揭示了地主阶级人伦理想和人生追求的虚妄,勾画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之间为“冠带家私”鸡争鸭夺、兴衰荣辱迅速传递的历史图景。三者中最主要也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乃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显而易见,无论从接受美学来看,还是从还原批评来看,《红楼梦》的主题都是典型的悲剧主题,且可看出它的难能可贵之点是在于从这一悲剧主题中传出了“救救青年”的呼喊,而这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乃初步民主主义者的心声。
该书的主线是一主双宾(注:参见拙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称·<红楼梦>结构论》。)。其情节线索甚多,择其要者有五:一是甄(真)贾(假)冷(难)刘(留)故事,即以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刘姥姥出没于情节,形成全书的重要线索之一。其特殊作用是:由远及近、由外及里地写贾府,从而把贾府和外部大千世界及太虚幻境勾连起来,最后又对整个作品作了收结。二是元(原)迎(应)探(叹)惜(息)故事,即以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悲剧命运,作为贯穿全书的又一重要线索。其特殊作用是: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地写贾府与外部大千世界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从而把贾府内部的鸡争鸭夺与府外的政治风云勾连起来,指出那“从外部杀来”的势力却原来大多与贾府有“亲”。它们与贾府的关系,实际上是种大范围内的“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三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故事,而作为一以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它所勾连的主要是通部“情案”。四是王熙凤的理家故事,而作为一以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它所勾连的主要是通部“世务”。五是“顽石”与“神瑛侍者”的“下凡历劫”故事,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是通部主线。道理很简单:“顽石”与“神瑛侍者”一个祖居“青埂”——历劫“怡红”——返回“青埂”,记其“身前身后事”,是谓《石头记》;一个祖居“赤瑕”——历劫“怡红”——返回“赤瑕”,录其“身前身后事”,是为《情僧录》。“吾以知《红楼梦》之作,宝玉自况也。”(注: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故而以“顽石”与“神瑛侍者”的“下凡历劫”故事为主线亦即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为主线。它与处于第二个层次上的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故事和王熙凤的理家故事、处于第三个层次上的元(原)迎(应)探(叹)惜(息)故事和甄(真)贾(假)冷(注:据《广韵》,“冷”和“难”读音相近,可以相谐。)(难)刘(留)故事构成了一主双宾的对称美,而作者的浩叹亦寓焉!
该书的意境有三个境界(注:参见拙作《论<红楼梦>的三种生命说与两种声音》,见《红楼梦学刊增刊》('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专辑)。)。一是贾府正府,这是作者以“富而好礼之第”为原型造就的现实世界。它是地主阶级正统派的天地,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殿堂,古来传颂的王道乐土,而同时也是禁锢青年的精神和肉体的黑暗王国。二是太虚幻境,这是作者以自由、平等观念的幻影为心象造就的理想世界。它是个只知相互体贴而不知纲常观念为何物的女儿乐园,是个人皆可以“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美妙社会。三是大观园,这是介乎贾府正府与太虚幻境之间的中介世界,乃怡红公子与诸艳的游乐和栖止地。它既是以“不拘不束”为其特点的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同时又是以“体仁沐德”为其特点的贾府在世外的投影。正因为大观园交织着如此两种投影,所以它也就成为贾宝玉的“意淫”观念和孔孟的“仁政”思想之间不见刀光剑影、不闻战马嘶鸣的无声战场。其结果是,一支王道曲,千红无孑遗!死于霸道,人皆怜之。死于王道,又有谁怜?此所以作者有“一把辛酸泪”,并写一太虚幻境寄遐思也!
与《红楼梦》相反,《金瓶梅》的艺术构思则是典型的喜剧构思。要之,也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问题:
该书的社会画面虽也十分广阔,但主题思想却似乎并不复杂,作者显然是旨在写出钱权交易必导致人对物欲和淫乐的贪求,导致管场的黑暗,导致时风的颓败,而“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是于国则破,于家则亡,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以为世戒。因此,他安排了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是西门氏的盛衰,暗线是权奸们的荣辱,从而使作品形成一种网状结构形态。于是,上自宫廷间为非作歹的宦官、朝廷上擅权专政的太师、州群里徇私枉法的官吏,下至在市井间招摇撞骗的帮闲、蛮横狡诈的地痞、以色市人的妓女、弄神弄鬼的僧尼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就毕现其中了。因此,兰陵笑笑生完全可以如《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社会研究”。
该书写西门庆与官吏们的钱权交易,与其说西门庆想要官吏们手里的权,不如说官吏们更想要西门庆手里的钱,因此便出现了堂堂宰辅“礼贤下士”讨好“一介乡民”西门庆的“怪现象”。其始也,蔡京不只亲自接见了西门庆派往送礼的来保和吴主管,还平地选拔西门庆当上了“山东理刑副千户”,而这是西门庆所意想不到的。其继也,当西门庆携千金之礼至蔡府拜寿时,蔡京不只有求必应地认之为义子,还在正日那天亲自单独设宴为之洗尘,而却将前来贺寿的满朝文武弃于一旁。其终也,蔡京又设法调走夏提刑,将西门庆晋升正职,而这并非出于西门庆的谋求。其实,西门庆对于跻身仕途并无多大兴趣,他所以投靠蔡京,只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不法商业经营找个过硬的政治靠山而已。可蔡京对西门庆却青睐如是,说他是迹近讨好,恐不为过吧!堂堂宰辅如此,一般官员对西门庆的金钱就更如蝇逐臭。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一戴上“状元”的桂冠便成为蔡京“假子”的蔡蕴。这位蔡状元赴安徽滁州匡庐省亲,却特意绕道山东清河县,名曰拜访西门庆,实际是去打抽丰。西门庆出手就是:“金缎一端,钦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乐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要特别注意的是,《金瓶梅》有个板定大章法,那就是张竹坡曾指出的:但凡写西门庆“到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需予补说的是,这“一人”,一般是帮闲篾片应伯爵之流,而这“一官”却是形形色色的。兰陵笑笑生这么写,其用意是包孕着冷嘲的,想告诉人们的是:篾片们乃西门庆的“帮闲”,而官僚们则是西门庆的“帮忙”。正因为西门庆踏着这样的“风火轮”,所以在不到五年里便由一个破落户成为拥有白银九万余两的富豪。正因为西门庆的经营是有官府作靠山,所以赚钱特别大胆,花钱也格外大方。既然如此,反过来又怎叫帮忙官僚和帮闲蔑片们对这位“仗义疏财”之人不趋之若鹜呢?
《金瓶梅》的命名也是喜剧性的,实际上它在结构上点示了西门氏由兴而盛而衰的过程。张竹坡云:“《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这说法实在有点不着边际。孙述宇对《金瓶梅》的命名解释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她们所共有的特质,其实只是强烈的情欲。情欲本是人的通性,金瓶中有淫行的人不知凡几,可是真正无法应付自己情欲的重要角色,除了男主角西门庆外,就数这三个妇女。她们生活在情欲驱策的路,最后都惨死在情欲之手。……作者之命名小说,也是向人生的苦致意。”(注:《庞春梅:<金瓶梅>的命名》,见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这说法也和作品的喜剧风格不符,因而也难以令人信服。要知道,旧时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之说,而对后娶之妾的宠爱尤甚于前娶之妾,亦妻妾成群者的常情。因此,《金瓶梅》“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这就不只是个“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问题,作者显然是旨在藉以写出:潘金莲、李瓶儿作为“五娘”、“六娘”,乃西门庆六房妻妾中之最获宠爱者,而尤以钱财和色貌兼俱的李瓶儿为第一。庞春梅呢?于西门庆四个通房丫环中可谓鹤立鸡群,斯人实为潘金莲之副,所以也就成为西门庆庞爱之人。从而,始则以西门庆对潘金连的宠爱有加为中心写西门氏的“兴”,继则以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宠爱有加为中心写西门氏的“盛”,终则以西门庆死后春梅的被卖和得意周府为中心写西门氏的“树倒猢狲散”。兰陵笑笑生所以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金瓶梅》,我以为其深层用意实在于此。
显而易见,反复出现于《红楼梦》艺术构思中的主旋律,是作者笔端的主人公们在纲常关系下对可以“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合理社会的追求,以及他们不可避免地为封建等级观念和制度所毁灭的命运,所以是时代悲剧。与此相反,反复出现于《金瓶梅》艺术构思中的主旋律,则是作者笔端的主人公们在金钱关系下对物欲和淫乐的贪求而不惜祸国殃民,以及他们虽一时得心应手而却无法逃脱的自我毁灭的命运,所以是人间喜剧。
四、从作品行文如绘来说
“行文如绘”是《红楼梦》的特点,也是《金瓶梅》的特点。然而,《红楼梦》的“行文如绘”,其所绘者一般都是风刀霜剑下的“百花图”,呈现于纸面的是如花者的仪表美、才智美、情欲美、性灵美,以及作者对这种美行将被毁灭抛洒的一把辛酸泪,如“宝琴立雪”、“海棠结社”、“宝黛读曲”、“晴雯补裘”等便是如此,更不用说“黛玉葬花”。与此相反,《金瓶梅》的“行文如绘”,其所绘者则大多是金钱关系中的“春宫画”,呈现于纸面的是淫乐者的卑劣的行为,卑俗的心理,卑微的灵魂,以及作者对这种丑行将自我毁灭的冷嘲热讽的态度,如“西门庆露阳惊郑”、“潘金莲香腮偎玉”、“陈经济弄一得双”等莫不如是,更不用说“醉闹葡萄架”的场面。兹择与《红楼梦》相关而《金瓶梅》所绘又尚可入目者一二,略予对比以作论证。
《红楼梦》有幅“人在花外”图,即第三十回中的“龄官划蔷痴及局外”。《金瓶梅》也有幅“人在花外”图,即第五十四中的“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宝玉)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噎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架下那边有人。如今五月之际,那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象颦儿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想毕,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那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象是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之内的,却辨不出他是生旦净丑那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两次皆因造次了,颦儿也生气,宝儿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
一面想,一面又恨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竞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至恐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再看,还是个“蔷”字。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
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唰唰的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时湿了。宝玉想道:“这时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唬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写了,下大雨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嗳哟”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
(应伯爵郊园宴诸友),一个韩金钏霎眼挫不见了,伯爵蹑足潜踪寻去,只见在湖山石下撤尿,露出一条红线,抛却万颗明珠。伯爵在隔篱笆眼,把草戏他的牝口。韩金钏撒也撒不完,吃了一惊,就立起,裈腰都湿了,骂道:“硶短命,恁尖酸的没槽道!”面都红了,带笑带骂出来。伯爵与众人说知,又笑了一番。
这两个画面,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悲剧性的,它真切地画出了眉眼体貌皆有似于黛玉的龄官对意中人贾蔷的一片痴情,从而令人不难想象黛玉对意中人宝玉的痴情当比龄官对贾蔷尤甚,故而有《葬花词》的写作;它更真切地画出了宝玉的精神苦闷是来自以女子之忧为忧,而天下不幸人多,故而忧患日甚,当大苦恼。一个则是喜剧性的,它真切地画出了西门庆的一帮结义兄弟应伯爵之流,皆是些以灵魂市人的灵魂娼妓,故而其心灵的丑恶比甘以肉体市人的娼妓尤甚,以致以下作当作快乐,以无耻当作能耐,从不知脸红为何物,而甘以肉体市人的妓女韩金钏却知。
《红楼梦》中有幅“水亭扑蝶”图,即第二十七回的“宝钗戏蝶”,《金瓶梅》里也有幅“蕉丛扑蝶”图,即第五十二回的“金莲扑蝶”:
(宝钗)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
惟有金莲在山子后那芭蕉丛深处,将手中白纱团扇儿,且去拍蝴蝶为戏。不防经济蓦地走在背后,猛然叫道:“五娘,你不会扑蝴蝶,等我与你扑!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肠,滚上滚下的走滚大。”那金莲扭回粉颈,斜睨秋波,对着陈经济笑骂道:你这少死的贼短命!谁要你扑?将人来听见,敢待死也!我晓得你也不怕死了,捣了几钟酒儿,在这里来鬼混!”
这两幅画面,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悲剧性的,它画出的实际的宝钗的青春觉醒,于人后不是个女夫子,因为那“一双王色蝴蝶”固然是她眼前所见的景象,恐怕也是她渴求鸾凤和鸣的心象,而结果却使她成为单凤孤鸾。假若结合同一回所绘的“飞燕泣残红”看问题,则这一题旨也就更为清楚。因为“飞燕泣残红”也罢,“杨妃戏彩蝶”也罢,说到底只不过是贾宝玉人生道路上同一悲剧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与此相反,一个则是喜剧性的,它画出的实际是潘金莲与她名义上的女婿陈经济之打情骂俏,于是那双“滚上滚下”的蝴蝶也就随之而成为对这双淫夫淫妇淫心荡漾的写照。
诚然,《红楼梦》中也有白日宣淫的画面,其最典型者莫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然而,正如甲戌本该回脂批所说:“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声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方法,略一皴杂,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需略予补说的是,作者所以不肯“唐突阿风”,盖亦由于他意在将王熙风也处理为悲剧女性。可相形之下,《金瓶梅》则无这类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式的笔墨,而却偏多张竹坡所赞赏的“节节露破绽”,如“烧夫灵和尚听淫声”、“迎春女窥隙偷光”、“金莲窃听藏春坞”、“琴童潜听燕莺欢”,凡此等等。其潜听者所闻皆淫夫淫妇的淫声浪语,其窃窥者所睹皆淫夫淫妇的交媾过程。作者所以如此让丑恶的灵魂去看丑恶的灵魂,显然是旨在将这两方面人皆处理为喜剧性人物。
目下有个风尚,就是好以人性论研究作品。说正面人物品性之高尚也,谓其体现了“人性的美”。说反面人物品性之卑劣也,谓其体现了“人性的丑”。说正面人物之情笃与反面人物之性淫,则更囿于这一万变不离其宗的框套。窃以为这种研究作品的思维方法,与昔日之好贴“阶级标签”,实有异曲同工之点,是不可取的。以“情”和“性”而论,照我看来,“情”是人性中人所以为人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性”是人性中人所以为生物的生理层面、本能层面,二者的辩证统一是为人性之固然。其体现于两性间,“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诱发“性”,“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诱发“情”。但“情”以其高层面故也,可以包含“性”,而‘性“以其低层面故也,却不一定包含“情”。以前者为切入点而施之“行文如绘”,是为《红楼梦》的“比比如画”。以后者为切入点而施之“行文如绘”,是为《金瓶梅》的“比比如画”。则一寓悲剧性意蕴,一寓喜剧性意蕴,亦判然有别矣!但谁以为《金瓶梅》是部色情小说,那就错了。因为书中所写的西门氏的淫乐是以钱权交易为其支点的,所以对西门氏淫乐生活的冷嘲也就成为对当时在在皆是的钱权交易的热讽。这种写照都是讽刺,情节皆含控诉,倒是《金瓶梅》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创作经验,即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是也。
五、结论和余论
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注:《鲁迅全集》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无论从作品的描写对象来说,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构思来说,或者从作品的比比如画来说,《红楼梦》皆在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它本质上是悲剧;而《金瓶梅》则在将人生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所以它本质上是喜剧。
《红楼梦》以贾宝玉入空门作结,《金瓶梅》以孝哥儿入空门作结,集中反映了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都有”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思想。但这只是现象相同,他们产生这一思想的原因却是相异的,而认识这种相异至关重要。曹雪芹所以产生虚无思想,是由于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四大苦闷:“一是摒弃了传统的以建功立业为内核的人生价值观念之后,却找不到比较恰当的人生位置而产生的苦闷;二是亵渎了现存的以三纲五常为法典的人与人关系准则之后,却找不到真正和谐的立足之境而产生的苦闷”(注:刘敬圻:《困惑的明清小说·<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三是发现了人们于“体仁沐德”的匾额下畅饮“群芳髓”,却找不到普救不幸者的方舟在何方面产生的若闷;四是鄙弃了以维护封建等级制为准则的儒家仁政理想之后,却找不到“天不拘兮地不羁”的人间乐园而产生的若闷。这种精神悲剧,是古已有之的某些民主主义精神和时代造就的某种人文主义思想的融会,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消亡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则虚无思想亦不时向这位面对无际坟地的新时代的拓荒者袭来矣!那么,兰陵笑笑生呢?让我们先窥其本然思想。他称颂忠臣曾孝序而慨叹这样的好官在官场上却无立身之地;他称颂孝子李安而慨叹这样的孝子在社会上却友声难求;他称颂易辙守节的妓女爱姐而慨叹虽这样的妇女在市井女性中亦已属凤毛麟角;他称颂义仆安童而慨叹这样不忘故主的青年在尘世间已寥寥无几;他称颂壮士武松而慨叹这样的豪杰悌弟在当今之世却只能被驱为盗。凡此,说明了甚么呢?这说明:兰陵笑笑生的思想是儒家的。这还说明:面对钱权交易毒焰弥漫的社会,深感忠孝节义等儒家教义已成如磐夜色中的几点萤火,“王道乐土”已在这如磐夜色中再造无日,便成为这位天才作家油然而生虚无思想的基本原因。
然而,更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兰陵笑笑生,他们的真正特点,却是“云空未必空”;否则,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思想深层。何以言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人钱起无意中以这两句诗道出了中华民族审美思想的基本特点,而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则是得其个中三昧的两位文学巨匠,所以完全可以借这两句诗来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万境归空”与“空中有存”的关系。盖“空”者,“曲终人渺”,令人如梦如幻:如《红楼梦》之写贾府“树倒猢狲散”,花柳繁华的大观园亦随之而成为一座“大花冢”,贾宝玉亦投入空门;如《金瓶梅》之写西门氏“树倒猢狲散”,权奸们亦同步灰飞烟灭,孝哥儿亦舍入空门。盖“存”者,“江上峰青”,令人寓目遐思:如《红楼梦》写投入空门后的贾宝玉,谓之“情僧”;如《金瓶梅》写投入空门后的孝哥儿,不言而喻,当谓之“孝僧”。“情僧”一称,显然是取义于冯梦龙的“情教”说:“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难怪涂瀛说:“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注: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页。)这种“人情”,乃“东方的微光,冬末的未萌”,它本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观念,人权思想。正因如此,所以以正面人物贾宝玉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也就成为时代悲剧。“孝僧”呢?假若将冯梦龙的话活剥一下说之,当就是“四大皆幻设,唯孝不虚假”。难怪张竹坡说:“《金瓶梅》以空结,看来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结便知。然则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恶耳。”(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以孝化百恶”实即“以仁化百恶”,因为“孝悌其为仁之本”,而事实上《金瓶梅》也是以“悌”开篇的。正因如此,所以以“仁”骂尽人间诸“不仁”便成为《金瓶梅》思想意蕴的内在特点,从而也就使这部以西门氏等反面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巨著成为“人间喜剧”。
莫非由于作者和作品主人公是同一个营垒里的人物?曹雪芹对自己笔端的主人公总是充满激情,甚至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不时对人物的苦难遭际洒以辛酸之泪。因此他对小说主人公们形象的塑造,不仅有史笔、画笔,而且还有诗笔。因此《红楼梦》虽属时代悲剧,却越读越令人心头热热的。莫非由于作者和作品主人公是分属于两个营垒里的人物?兰陵笑笑生对自己笔端的主人公总是冷若冰霜,甚至好以冷眼审视人物的行为动作、心理状态,描写也客观得近于自然主义,而将自己的冷嘲热讽自然而然地注入对人物的言行、心理、思想、性格、命运的写照。因此他对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虽有史笔、画笔,却无诗笔。因此《金瓶梅》虽属人间喜剧,却越读越令人心头凉凉的。两部同以描写世情见称的小说,其审美风格又相异如是,真令人叹为观止。
要而言之,由于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的立场、思想性质、思想高度、文化素养,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视角的不同;呈现于他们的作品《红楼梦》和《金瓶梅》,二者虽同以描写世情见称于世,可却出现了审美观念的分野,即一为时代悲剧,而一为人间喜剧,堪称中国小说史上世情小说的双璧。
标签:金瓶梅论文; 红楼梦论文; 人间喜剧论文; 西门庆论文; 贾宝玉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曹雪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