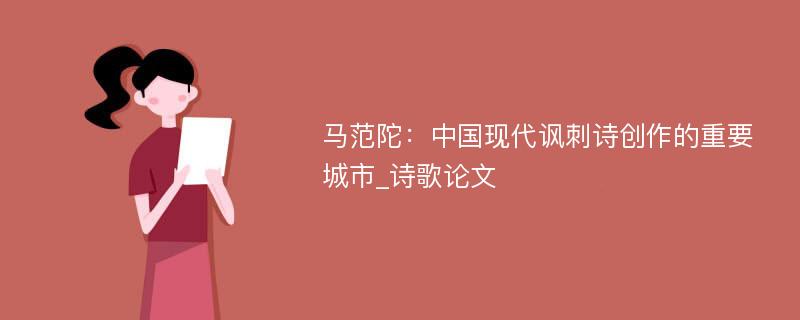
马凡陀:中国现代讽刺诗写作的重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讽刺诗论文,重镇论文,中国论文,马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
袁水拍(1916-1982),本名袁光楣,又名马凡陀。袁光楣在家是长子,取“光楣”,做名寓有重振门庭的意思(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在他开笔写抒情诗的时候,他取“水拍”做笔名,是因为有一句“□□□□水拍天”描绘江南水乡的诗句(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到40年代,他开始大量写讽刺诗时,他又取“马凡陀”做笔名,是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可以这样说,袁光楣一生是用两副笔墨写诗:当写抒情诗时,他是“袁水拍”;当写讽刺诗时,他却是“马凡陀”。因为本文主要研究他的讽刺诗,所以通常用马凡陀这个名字来指称他。
马凡陀,一米八二的个子,长方形的脸型,中间略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颇具英国绅士风度,言谈与写诗,都显示出“雅谑与机智之妙才”(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写作、出版了诗集15本(注:《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江南进行曲》、《今年新年大不同》、《华沙》、《北京、维也纳》(包括通讯)、《诗四十首》、《煤烟和鸟》、《春莺颂》,《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歌颂与诅咒》、《政治讽刺诗》。)(另有一本取名为《云水集》的诗集,他生前已编好,但至今未出版),诗论集两本(注:《文艺札记》、《诗论集》。),译诗集4本(注:《我的心呀在高原》(彭斯原著)、《旗手》(冈察尔原著)、《伐木者醒来》(聂鲁达原著)、《聂鲁达诗文集》。),以及其它著述4种(注:《马克思主义与诗歌》、《论诗歌源流》、《诗与评论》、《五十朵蕃红花》。),计25种之多。这些作品曾在社会上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马凡陀的山歌》的出版,不但成为香港、上海等地当年游行队伍的“旗帜”、“炸弹”,而且在文学界还引发过一场诗学论争,形成了“五四”以后诗坛少有的热闹景象(注:转引自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马凡陀既是位高产而又高质的诗人,也是位“奇伟而又不幸的诗人”(注:刘岚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赵超构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他,生前“热闹”,备受关注;死后“沉寂”,备受冷落。换句话说,40年代中后期写作“山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诗名,而“文革”后期由于做过几年文化部副部长,则给他带来了抹不掉的政治阴影。友人为他惋惜说:“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但学术界因此而有意忘却、遮蔽马凡陀,显然是意气用事的短视。马凡陀毕竟是位诗人,而且是位重要的诗人。建国初期,马凡陀的创作曾一度被文学界的权力话语指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倾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的第二部分《创作方面的各种倾向》,见《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被纳入毛泽东的“文学新方向”之列,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之中。
本文的写作,就是想拂去厚积在马凡陀诗歌文本上的历史尘埃,展示马凡陀山歌的本相,藉此引起人们对马凡陀的注意。
二、“它怀胎着一个激变”
马凡陀从小爱好集邮,“常常和两个弟弟拿了烧稻柴灶用的火夹,去天赐庄博习医院后边的垃圾堆上,翻旧信封上的外国邮票。记得他那时已经喜欢哼些诗歌,就创作过一首邮票诗:‘一分邮票,/三只铜板,/拨仔唔叫化,/买块大饼啊,/好当一顿饭’”。(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马凡陀当时还是苏州三元坊苏中学的学生,受当地吴歌文化熏染而自发地进行口头创作。而真正以袁水拍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是《我是一个田夸老》(后改名为《不能归他们》)。关于这首诗的生产过程,徐迟有过一段忆述。他说:“1939年春,戴望舒和当时在湖南的艾青合编诗刊《顶点》。望舒要我向这个苏州人约稿。大约早先已写过诗,欣然应命,三天后就交稿了。”(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两本抒情诗集《人民》(新诗社1940年版)和《向日葵》(美学出版社1943年版)的出版,充分展露了袁水拍作为抒情诗人的政治激情和艺术素质,在诗界颇获好评。李薇的评论有代表性。她在《起点的说明》中写道:“他写那逃亡的农民,好像就是自己在那里逃跑。他那种自然的与对象化合的敏感力,使他的诗保有强烈的亲密性,变化多端的新鲜,那几乎是与千变万异的客观世界同一的。”(注:李薇:《起点的说明——评袁水拍的两本诗集〈人民〉和〈向日葵〉》,载《新华日报》1943年8月9日。)她认为袁水拍的抒情诗与艾略特的《荒原》一样,记录了许多破碎阶层的混合体,一团糟的沉淀质;在这里,无论是从灵魂的身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绝望、混乱、粗暴、焦灼、噪音渗透了。袁水拍开笔写抒情诗。起点不俗、不凡,拥有了世界眼光。站在一个抒情诗人的写作立场上,徐迟对此也是赞不绝口地说:“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抒情诗。那应当是他最擅长的诗歌形式,自有他独具的优势和卓越的禀赋的。……如果袁水拍将他的才能集中于写这种抒情诗,他将得到何等的丰盛收获。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写得和彭斯一样好,和拜伦一样好,甚至可以,完全可以写得和所有那些大诗人的抒情诗一样好的。”(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尽管这是同行们根据袁水拍抒情诗写作的不凡起点所勾勒的想象中的诗歌辉煌,但是袁水拍在这之后的改弦易辙,的确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能的伟大的抒情诗人,却得到了一位出色的讽刺诗人。
在40年代中后期,马凡陀为什么放弃“美诗”写作而倾心“刺诗”写作呢?个中原因也是极为繁复的。
首先,是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40年代中后期的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面目暴露无遗,广大人民群众刚刚对日本投降感到短暂的喜悦,便又陷入更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中了”(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质言之,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的独裁,在经济上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勒索,在文化上扼杀民主进步文化,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这在袁水拍的抒情诗里早已有了写照。如:“疾病布满城中,没有医药”(《水齐到颈根的人们》);“大家给这可恶的日子,/这种横暴的日子,不要脸的日子,/弄得半白痴了”(《可恶的陌生地方呀!》;“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这样破碎,/样样不完全,眼前的事物,心里的花蕾?/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这样丑陋?/被损伤的脸,被压坏、扭曲的身子!”(《或人的问》),等等。而这种时代的凋敝、危机,又与30年代“密云期”不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虽严酷,但已濒临崩溃;黎明前的黑暗虽浓重,但天边已初露曙光,换言之,国统区广大民众虽有压抑与痛楚,但他们并不困惑与迷茫;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日益明确;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望。这时,“只要你耳不聋,或不装聋;只要你眼不瞎,或不装瞎;只要你心不死,或不装死,总不愁这些已死的、现存的、新生的、死而复活的事件,不来碰你、刺你,鼓动你起来”(注: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谈政治讽刺诗》,载《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袁水拍曾用“沸腾”来描述这种事态。他说:“把这五六个年头(1942-1946年)称为沸腾的岁月,我想谁都有同感吧,国内国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样燃烧我们,谁能够不沸腾呢?更有因心的腾沸而投身于事件中的许许多多的人。时常他们本身就成为事件的一部分,火的部分。”(注:袁水拍:《沸腾的岁月·后记》,新群出版社1947年版。)中国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波澜壮阔的画卷中看到了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沸腾的生活,沸腾的事件,沸腾的心,要求诗人写作像刀、像箭、像炸弹、像火一样的诗篇。而又只有讽刺诗才能锋芒毕现、一针见血地刺向黑暗的“黑心”。不再像二三十年代了,国统区弊端丛集的世相为现代讽刺诗的批量产生铺好了产床。其次,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民众对诗歌的审美需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人民需要的是愤怒的呐喊、锋利的冷笑和战斗的风采。因而,热烈、尖锐、泼辣就成为时人所崇尚的诗美风格。现代讽刺诗作为一种艺术的社会批评(注:伊恩·杰克说:“讽刺源于批评的本能;它是变成了艺术的批评”。转引自阿瑟·波拉德(谢谦译)的《论讽刺》,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恰好顺应了当时社会的、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趋向。最后,与抒情诗不同的是,讽刺诗的时评性特点明显,具有很强的政治批判能力,便于展示那个时代的主流力量;而且,现代讽刺诗自身的短悍和诗化口语的文体特点又为讽刺文(注:本文所说的“讽刺文”与传统意义上的“讽刺文”(pasq-uinade)不同。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上记载,传统意义上的“讽刺文”指简短的匿名的讽刺评论,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嘲讽当代的领袖或国事。本文所说的“讽刺文”是指在文体上与“讽刺诗”相对应的一种非诗文体。)所不及。总之,比起抒情诗和讽刺文来,讽刺诗在40年代中后期的国统区具有文体的优越性。
外部的生态与内在的优势,使得现代讽刺诗第一次获得了与抒情诗平起平坐的光荣席位,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个高潮产生了。臧克家说:“40年代的讽刺诗,来势之猛,如爆雷滚滚,如潮水高涨;影响之大,如穿破云的一道道阳光。”(注:臧克家:《讽刺诗这朵花——〈中国百家讽刺诗选〉序》,罗绍书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瑶也说:“政治讽刺诗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马凡陀曾说:“这是民谣复兴的时代。”(注:袁水拍:《祝福诗歌前程》,转引自游友基著的《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1944年以后马凡陀猛写讽刺诗,又与他自小就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素朴的阶级感情有关。据他弟弟袁光斗回忆:“他青年时,思想就比较进步。至今清楚记得他和父亲辩论‘不劳而获’的情景。他引证《诗经》中的话:‘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何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振振有辞,严肃认真的样子。”(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此外,马凡陀创作的转向,还与他在少年时代就特别喜好评弹有关。他对民谣、山歌有着特别的感情,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偏心”(注:袁水拍:《冬天·冬天》的《前记》,桂林远方书店1944年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与毛泽东的《讲话》号召分不开。对此,马凡陀的长子有一段诗学背景的交待。他说:“我父亲性格内向、谨慎。我父亲之所以写‘山歌’的原因,我曾问过。他说他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敢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就是一个‘恨’字,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政治太愤恨了。……后来风格一变而为‘山歌’,完全是因为在重庆时,通过地下党,他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倡文艺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我父亲说,身为共产党员,当然要按党的文艺方针的要求去做,从此,写了大量优质的山歌”(注:引自袁水拍的长子袁怀雨1996年9月4日写给笔者的信。)。马凡陀也就作为中国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人”而走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三、写在旗子上的诗
按徐迟的理解,马凡陀的诗歌有抒情诗、山歌和政治讽刺诗三大类型(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将着重论述后两类(其实,按我的理解,山歌和政治讽刺诗同属讽刺诗一类)。因此,这里所说的“写在旗子上的诗”(注:吕剑:《诗与斗争·听马凡陀》,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版。),指称的是马凡陀的现代讽刺诗。
1944年以前,处在写抒情诗阶段的马凡陀,就零星地写作了少量优秀的讽刺诗。比如,在他的抒情诗集《人民》里就有这样一些讽刺诗章:《海》(讥讽中国人传统的熬苦性格),《天气》(通过贫富对比来讽刺剥削阶段),《一个“政治家”的祈祷》(讽刺战争中的贪婪者)。又如,在他的另一本抒情诗集《冬天·冬天》里,讽刺诗的比例较《人民》中有所扩大,如《城中小调》(讽刺城市在乱世中沉沦),《神的殿》(揭露“神的殿”成了“贼窝”),此外还有《关于米》、《或人的独白》、《钉子》、《这是一个谎话》和《牛角上的苍蝇》等等。这两本抒情诗集中收入的讽刺诗可以看成是马凡陀早期的讽刺诗写作。虽是初出茅庐,但均出手不凡,显示了一位优秀讽刺诗人敏锐的政治思想和高超的讽刺艺术手腕。请读《一个“政治家”的祈祷》片断:“主啊!我祈求,用最温柔的语调,/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磨擦,/最好还是开火吧,这样中国就好自杀。/而我便可以穿上黄袍,跟那边的亨利一样。/比目前的小丑相岂不更加像样?/主啊!仁慈的主,美丽的主,我一切可以/让步,一切可以断送,名誉什么都不要,/我的灵魂可以整个拍卖送掉,/我的下贱的奴隶的身体献给你,/我率领全班伙计,恐怖党,猎犬。/你千万别相信花言巧语,不要脸的东西,/你明智的主啊,快不要三心两意爱上了,/那该死的南京和北平的人妖,/主啊!请别忘今夜给我支票!”诗中展示了一类在内战期间惟恐天下不乱的、惟利是图的、发战争财、发国难财的民族败类、历史小丑的狠毒心态和肮脏的灵魂。他们的“祈祷”实质上是他们无耻的自白。他们“祈祷”得越充分,他们的思想就显露得越清晰,他们的丑态就表演得越可恶、可笑!诗人不是直接地“说”出这些并随即讽刺这些,而是幽默而有力地让这类“政治家”自画像。这与诗人根据生活经验去揣摩这类“政治家”心态的机智与才能分不开;也与诗人的艺术素养分不开。诗人翻译过彭斯的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新群出版社1947年版),可以这样说,马凡陀的《一个“政治家”的祈祷》在结构艺术形态上脱胎于彭斯的《威利长老的祷词》。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凡陀一开始写讽刺诗,有一股来自域外的“贵族气”。它与现实政治,尤其是与《讲话》的指向不尽适应。于是,聪慧的马凡陀,开始把眼光从域外艺术资源转移到本土艺术资源,走一条本土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自1944年以后,马凡陀注重利用山歌等民间艺术形式来写作讽刺诗。郭沫若早就讲过,讽刺诗的“表现手法是离不开韵语的”,“利用旧式的诗形更可以增加效能”(注:郭沫若:《郭沫若诗作谈·关于讽刺诗及其他》,载《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所以,马凡陀的山歌的“效能”就比早期写的讽刺诗大得多。初时,山歌调子还不太流畅,次年就比较犀利,渐多佳作。到1946年,他越写越妙,简直达到了最好的民歌手的出神入化之境。
中国的山歌源远流长。“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山歌也有了新变化,在革命老根据地,老解放区产生了大量新山歌,歌唱革命斗争和翻身解放。”(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山歌”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马凡陀的山歌也可视为“新山歌”。之所以说它“新”,一是因为它发展了山歌讽刺暴露的一面,一是因为在写作方式上它非民间山歌集体创作而是文人创作。所以,茅盾在1947年就称之为“马凡陀的胎息于‘吴歌’的新诗”(注:茅盾:《民间,民主诗人》,载《文艺丛刊》之一《脚印》,1947年10月版。),肯定了马凡陀山歌的新诗品格。1949年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报告中,还把马凡陀山歌的写作路线称为代表了新中国人民文艺发展的“新的倾向”。当然,也有人否认马凡陀山歌的新诗的品性。如王亚平就说:“有人袭取了山歌小调的格式,说是诗,这是不妥当的。”(注:王亚平:《论诗歌大众化的现实主义》,载《文艺春秋》第3卷第5期,1946年12月版。)这是由于王亚平等人没有认识到马凡陀山歌是文人创作的实质所致。
马凡陀的山歌主要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生活书店1946年12月版,99首)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生活书店1948年6月版,83首)中,近200首。就像在马凡陀的抒情诗集中收有讽刺诗一样,马凡陀的山歌集中也收有少量的抒情诗,如《在一个黎明》、《上海解放歌》、《送军粮》等等。马凡陀山歌中,广为流传的讽刺诗佳作有《一只猫》、《主人要辞职》、《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老母刺瞎亲子目》,等等。
马凡陀山歌取材十分广泛,大至天下大事,小至身边琐事,而这些事又往往是国统区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本来是司空见惯,“谁都不以为奇……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注: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见《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5页。),现在经马凡陀艺术地揭示出来,就特别动人,从而激起民众的革命热情。依题材而论,马凡陀山歌有国际题材的,如《“温和派”艾契逊升官记》、《甲级战犯和甲级魔术》、《赫尔利这老头子》等;有国内题材的,如《一只猫》、《人咬狗》、《万税》、《主人要辞职》等。前者以讽刺帝国主义法西斯本性为指归,为数不多。后者以讽刺国统区苛酷的统治为能事,如虚伪的民主和敲骨吸髓的税收,占绝大多数。前者,如《希特勒的杰作》讽刺了法西斯分子的“胜利梦”——白日梦;《反抗》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我国本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我一斤面》讽刺了美帝国主义者假用面粉等做“救济品”以此欺骗国统区人民的丑恶行径,等等。后者,如《万税》讽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苛政猛于虎”,《踏进毛房去拉屎》和《如今什么都值钱》讽刺的是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朱警察查户口》和《警察巡查到府上》抨击了反动派的特务统治,《“国大代”》漫画了蒋介石政府“民主选举”的丑剧,等等。“这些山歌无情地解剖、暴露和猛击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凶恶暴行和无耻谰言”(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注:李广田:《马凡陀山歌》,见《论文学教育》,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5月版。),是“现实的体温表”(注:李广田:《马凡陀山歌》,见《论文学教育》,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5月版。)。
马凡陀山歌发表后,给“五四”以来原本平静的诗坛投进了一颗炸弹,由此引发了一场诗学论争。支持者认为马凡陀山歌具有战斗功用,代表了新诗发展的方向。如默涵认为它代表了诗歌的正确方向——面向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注:默涵:《关于马凡陀山歌》,转引自拙著《中国新诗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金大筠说:“从袁水拍到马凡陀,窄小的嗓门宏亮起来,这总是可喜的”(注:金大筠:《诗工作的道路》,同上。);李广田认为“其为诗,这是今天的国风”(注:李广田:《马凡陀山歌》,见《论文学教育》,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5月版。);冯乃超说:“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满,心中的怨望和烦恼,提高到政治觉悟的相当的高度,教他们嘲笑贪官污吏,教他们认识自己的可怜的地位,引导他们去反对反动的独裁统治”(注:冯乃超:《战斗的诗歌方向》,转引自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第105页。);吕剑也说:“马凡陀的诗对上海的民主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今天作一诗发表,明天游行时就唱出来了”,“上海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在旗子上的是马凡陀的诗”(注:吕剑:《诗与斗争·听马凡陀》,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版。)。批评者认为马凡陀山歌有媚俗倾向。如洁泯的微辞是:“袁水拍不该把‘风格’,把‘腔调’,一股脑儿交给了民歌”(注:洁泯:《洁泯文学评论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又如根据诗人穆仁回忆:“当时,‘七月派’一些诗人,对马凡陀山歌有看法,认为它常套用‘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曲调填词的做法,是迎合小市民趣味,是品位不高的诗歌创作倾向”(注:引自穆仁1996年6月21日写给笔者的信。)。我以为,由“山歌”引发的诗歌“方向之争”与“雅俗之争”,是“山歌”影响日益扩大的表现;具体到“山歌”自身而论,它不但不是马凡陀在诗歌写作上的滑坡,相反它却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与现代讽刺诗的刚健品格的成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许是因为讽刺诗因其民间性常与民谣、打油诗、顺口溜等民间艺术相邻,有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讽刺诗不具备艺术位格。我以为,这是对中外讽刺诗史和讽刺诗文体传统的盲识。在我国,《诗经》里就有了讽刺诗;而且“下以风刺上”(注:《诗大序》。)又是我国讽刺诗论的发端。文人的讽刺诗创作与民间的打油诗、顺口溜有别。此外,讽刺诗有一套自身的艺术评价标准。在“山歌”的论争中,绝大多数论者均用抒情诗的尺度来苛责或批评“山歌”。这种做法本身也构成了一个讽刺。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马凡陀山歌的独特品性。
1.马凡陀山歌的喜剧性
马凡陀山歌是笑的艺术,不过“山歌”的笑是“诙谐而阴郁”(注:鲁迅:《〈山民牧歌序〉译后附记》。)的。诗人是想揭露现实生活中具有喜剧因素的题材并对之进行审丑观照,然后“笑着向过去告别”(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笑着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法西斯专政告别。“没有使人悲观的讽刺与暴露”(注:茅盾:《暴露与讽刺》,见《茅盾选集》,第287-288页。)。请读《主人要辞职》末节:“‘我亲爱的骑师大人,/请骑吧!请不要装腔作势!/标语口号,概请节省,/民主,民主,何必再唱!’”在这里,“骑师大人”明明是发号施令的“主人”,为着嘴上的民主计,却硬要称被骑在自己胯下的百姓为主人。剥削阶级“主仆颠倒”,实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诗的讽刺矛头指向了国民党虚伪的民主。虚伪的东西总是用一些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包装来乔扮自己,给人以堂而皇之的错觉。因此,这种东西本身就具备喜剧因素。这种人为的东西,总是“以假装有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外表来掩盖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诗人只要用“突降法”(指说话或写作中从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或荒谬的内容)使讽刺对象从崇高处惨跌下来,便能有力地撕破它“外尊”的假面,露出它“内卑”的愚相。对此,马凡陀是自觉的。他在谈到写讽刺诗中的反面人物时说:“把他放在一个十分狼狈的境地”,“暴露他的丑恶本质”(注:马凡陀:《讽刺诗中的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形象》,见《诗论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这样才能达到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的艺术效果。
此外,马凡陀山歌的喜剧性还体现在它兼具喜剧与讽刺诗“合一化”的情节设计和用“以言写形”的漫画手法来塑造讽刺形象上。请读《大人物狂想曲》之片段:“分什么真与假?分什么此与彼?/让我们疯狂地乐一乐吧!/谁说我们是疯子,/谁就自己在发呆。”诗中,“大人物”的可憎,在于他是一个从穷光蛋靠发战争财进而成为终日沉迷于财色的人类渣滓。“大人物”的可卑,在于他毫不遮掩地自供出他的履历(劣迹),以至“狂”得是非不分。“大人物”的可笑,在于他在一片虚设的荣誉中尽情地狂想——妄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马凡陀使“大人物”永无休止地、自我损耗地、疯狂地表演着,最后力竭倒地、不攻自破。
受到战时文化心态的影响,马凡陀把他的讽刺对象划分为“下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把历史运动,看成是忠奸、善恶两大政治集团力量之间的较量和斗争的过程。当然,这种历史的道德观也就决定了马凡陀山歌的艺术形态。好在“山歌”喜剧性的存在使“山歌”写作避免了把人物处理为某种道德的化身而致使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单化、条理化。马凡陀山歌中抒写者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也是通过喜剧性得到节制地表现的。难怪别林斯基说:“理解喜剧性,这是美学教养的最高峰。”(注:别林斯基:《一八四一年的俄国文学》,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
2.马凡陀山歌的音乐性
“讽刺诗出于杂调曲,本为民间娱乐,重在通俗,即经转变,旧质仍有。故不避嘈杂粗鄙之辞。”(注: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第2卷《罗马》第7章诗二(十二,讽刺诗),岳麓书社1984年版。)马凡陀山歌继承和发展了讽刺诗的民间性、音乐性。如《一只猫》以七言为主,句式整饬,接近于南方民谚,有“吴歌”胎息,繁管急弦,有较强的节奏感。请读《人咬狗》的首节:“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此诗是用南方“稀奇古怪歌”的曲调来“填写”的,属于“旧调填新词”的山歌。它活画出了国民党特务统治下的古怪世象,辛辣地讽刺了他们“变态”的专政;而且,外部世象的深意的夸张,又有助于讽刺主题的乐化表达。马凡陀曾说:“要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的诗,必须使用民谣,必须重视民谣的传统,同时要扬弃它,要创造一个新天地。”(注:袁水拍:《冬天·冬天》的《前记》,桂林远方书店1944年版。)
3.马凡陀山歌语体的实验性
多年来,他在诗歌语言和诗体建构上不断进行探索。比如,在“山歌”中他大胆运用方言土语乃至外来语、时髦话。《东南西北古怪风》中的“稀勿弄懂”是江南口语。《毛巾选举》中有像“阿拉”之类的上海话,还有像“派司”之类的外来语。《海内奇谈》中有“打老虎”和“拍苍蝇”之类的熟语。此外,如《警察巡查到府上》连用8个“睡觉了”和《美术家的难题》间接连用了8个“可惜”这类排比、反复的极端的修辞方法。
有人误以为马凡陀山歌诗体形式单调,不值一提。而实际上马凡陀的讽刺诗体也经由了一个由粗犷到精致的探索发展过程。在早期,马凡陀的讽刺诗颇有些“西洋味”。请读《城中小调》之片断:
比布景还假的屋子,像谎话一样站在各处,
拆掉,给炸弹拆掉,重造让布景师搭起来,
刷上假漆,水,粉,泥,浆糊,木炭汁,猪血,
演员,台词,道具,灯光,效果,嗓子,
十秒钟黑场,警报,换景,一月坟场……
三月里来是清明,
叫声情妹我的人,
今晚与我宿一夜,
与你铜钱二百文。
全诗用战争与性为主线,用现代散文与民间小调交互组织成诗体结构。现代散文部分,节奏紧张、零乱,令人晕眩;而民间小调部分,缓冲了这种紧张情绪。文白掺杂,紧张与松驰、严肃与诙谐、散漫与整饬、战争与性爱、雅与俗等对立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这种“无主题变奏”,写尽了世相的病态。由此,我们不得不钦佩马凡陀的幽默才能和写作讽刺诗的艺术本领。
后来,马凡陀得山歌之精髓,写出了精致的“山歌体”,讽刺诗。请读《民国三十五年的回顾和民国三十六年的展望》之节选:“呃——嘿!/今天!/我们!/兄弟!/为了节约!/诸位的!/宝贵光阴!/时间!/呃,/这个,/今天的讲话!/就算,/这个,/告一段落!”马凡陀后来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采撷其中一些细节,一些语言,写一些旧时代的反动派,也许是一种新颖的需要写的题材”,“把反派人物生龙活虎般大书一笔。不是丑化,滑稽化,而是要现实主义。”(注:徐迟编注:《袁水拍致徐迟书简一束》,1962年6月29日,载《苏州杂志》1996年第4期,第78页。)此诗戏拟蒋介石的口气,通过言语——空洞无物、支支吾吾、颠三倒四,外尊内卑——和细节来反映蒋介石的怯懦的心理。这些语言像短命鬼临终的遗言,描述的镜像也是末日的虚幻的镜像。这得益于马凡陀巧妙地运用语言、细节、独白、戏拟、阻断语流、乃至诗体结构形态(吴歌中的“乱山歌”),使此诗的讽刺意味得到艺术地呈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感佩马凡陀不断求新求变的艺术精神及其艺术创造。用李广田的话来说就是马凡陀具有“勇于放弃自己,而又敢于尝试新鲜作风的勇气”(注:李广田:《马凡陀山歌》,见《论文学教育》,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5月版。)。
四、渐己逝去的幽默
五六十年代,马凡陀官至中宣部文艺处长。“他更加严肃、谨慎起来。他不能如鱼得水,反而远离了沸腾的生活,并疏离了故人”(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随政治风云变幻,他也身不由己,曾自杀过两次,一次是60年代中后期在中宣部宁夏干校,一次是在“文革”初期的北京。那时听他发言感觉不到什么山歌味道(注:参见李曙光长文,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雷声和歌声在他那时的诗歌写作中几乎尽失了。“因为他已不再是一个唱谐谑调山歌的歌手,更谈不上做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马凡陀已成为一个听话的行政长官了。“周扬有一次笑着对他说:你这个诗人现在写起文章来也惯用什么‘应该指出’,‘必须指出’了”。(注:参见李曙光长文,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马凡陀甚至还身不由己地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一代人的共同悲剧。
听“号召”听惯了的马凡陀建国以后又操起了久违的抒情诗之大笔,歌唱颂歌的年代。而这些“应景诗”比起他解放前写的抒情诗来,内中少了生命的真诚与个性的浇灌。那时,在一片颂歌声中,讽刺诗几无立足之地。讽刺诗的写作是见缝插针之为。比如1957年鸣放期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位作者联名怀疑“双百”方针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敏感的马凡陀由此有感而发写作了一首内部讽刺诗《摇头》,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第三天,毛泽东就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表扬道:“你的《摇头》诗写得很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注:参见李曙光长文,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他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请读末节:“滚开!对,应该滚开!/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许它们把我们的同志害!”随后,“反右”开始了,马凡陀为此做了检查。后来,他很少再写内部讽刺诗,而把他的幽默感宣泄到国际题材上,挖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等。如1962年11月11日写的《论“进攻性武器”》原本发表于《光明日报》上,修改后又发表于12月6日的《人民日报》,经殷之光到处朗诵后,在社会上颇获好评。也许,到这时,马凡陀才明白毛泽东对于讽刺的态度。毛泽东曾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马凡陀从这绕口令式的句子和语气中,体会到了毛泽东对讽刺这个敏感问题的审慎态度——有保留的赞同。因此,聪慧的马凡陀从此不再写那种“对付同盟者”的、“对付自己队伍”的内部讽刺诗,而把少有的幽默放到外部讽刺诗的写作上了。
直到临死的那一天,他还写作了一系列国际题材的讽刺诗,如《课长申辩增广》、《教科书歌》、《今文观止:文官武辨记》、《参拜神社》等,几乎都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这一做法,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权力话语对他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至死不渝的爱国思想和一以贯之的疾恶如仇的秉性。尽管这些“最后的讽刺诗”没有达到“山歌”出神入化之境,但是它们的面世再次证明了马凡陀毕竟是位诗人,而且最终也仅仅是位诗人。
五、并非结语的补缀:到家乡去过春天
“文革”后期“不光彩”的启用,使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被贬赋闲在家,从此闭门索居、与世隔绝,除了做一些“旧梦”(如写一些汉俳,听听评弹等),便一无所为。当时整个状况,使他昔日的“向日葵”歌者的激情和马凡陀的开脱幽默不知到哪里去了。难道不可以说,晚年的马凡陀不是又一次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了吗?大起大落的马凡陀。可歌可叹的马凡陀。
1962年6月29日在给徐迟信中,他写道:“你们能到家乡去过春天,真是羡欣之至。我们梦想能有这一天。”(注:徐迟编注:《袁水拍致徐迟书简一束》,1962年6月29日,载《苏州杂志》1996年第4期,第78页。)他的这个梦一拖就是20年,直到1982年人死的时候,才得以实现。诗人才得以从这个是非难辨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的马凡陀大概不会再遭遇政治了吧?大概可以像陶渊明那样作为一个诗人在家乡过着永恒的春天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