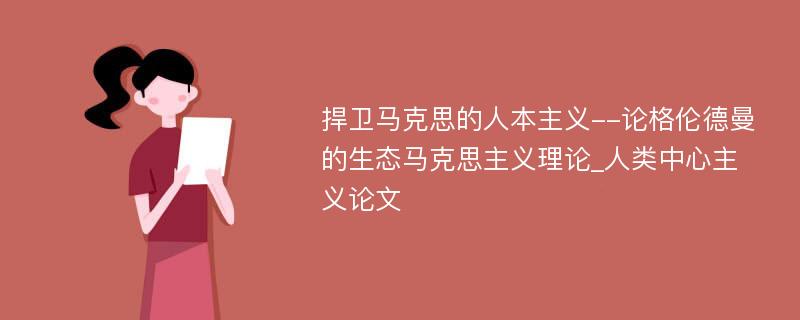
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评格仑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人类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A81
瑞尼·格仑德曼(Reiner Grundmann)是英国阿斯顿大学语言和社会科学学院的高级讲师,社会研究和社会变革研究生课程的负责人。他于1991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著作以及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一文,与泰德·本顿就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论战中阐发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针对本顿提出用生态学的维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绿色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受生态主义的浸染,格仑德曼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他提倡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来阐释和解决现代生态问题,并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了有力的辩护,赋予与此密切相关的“支配自然”观念以积极意义,创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格仑德曼抛弃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幻想,提出以人类的尺度来思考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因此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分析生态问题
在格仑德曼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为现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可信可行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对他那个时代生态问题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批判精神是有益于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的,因此,马克思用不着拯救,历史唯物主义用不着重建。具体来看,格仑德曼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了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对现代生态问题的分析。
第一,宽泛的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追求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然的繁荣协调一致。格仑德曼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意义上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格仑德曼指出,生产力问题是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对此马克思作出了自己的分析,“生产力增长”这一术语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思是指人类获得不断增长的支配自然的能力,扩大对周围世界的控制能力,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建造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发展被纳入到普遍的人类的范围,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层意思是指增长在经济意义上可用效率的经济标准来衡量,这就是狭义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经常遭到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生产力论的非难,那些非难者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做是狭义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的曲解。事实上,马克思把广义的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尊严要求摆脱饥饿,同样要求摆脱以一种异己的力量作用于人的敌对的自然”。① 马克思既反对由于改造自然而产生有害影响的现代文明,又反对回到在物质水平上人们的福利得不到保证的状态。在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马克思是完美主义者,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在于人类解放。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了人类既要在自然中生存又要与自然进行抗争这一生存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是马克思与现代生态问题相关的理论之一。格仑德曼说:“这就是说,人们为了生存(食物、住所等)必须和自然保持联系,但同样为了自己的目的通过技术手段改造自然,这种双重关系已从简单发展成复杂的形式。在原始社会自然仅仅是被‘占有’,即果实和蔬菜被采集以及动物被捕获。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占有自然不再是直接的,而变成有中介的,这个中介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称这个过程为‘新陈代谢’或‘与自然的交互作用’。”② 激进的生态主义者认为,对于自然来说,没有生产是最好的生产。格仑德曼认为生态主义的立场会带来谬误,因为人类如果停止在自然之内生产,就将无法生存。而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物质变换)理论消除了这种谬误。马克思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而生活,为了生存他们运用工具、器械、知识和技巧同自然进行相互作用,人把技术置于人与自然之间,人只有使用技术才能改造自然,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人类、技术、自然这三个因素参与了物质变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现代社会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是由技术作为中介的,再想回到直接占有自然的阶段是不现实的,因此,生态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采用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态标准是历史进步的标准之一。格仑德曼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相信人类总是朝着一个更加“自我实现”的理想社会前进。那么,如何解释社会的进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问题。格仑德曼首先考察了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认为其通常有三种类型,即经济标准、技术标准和精神标准。经济标准是生产效率或资本的收益,反映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即更高的效率意味着用更少的投资获得等量的收益,或等量的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技术标准是内在于技术的,用可靠性、速度、寿命、能量输入等来判断技术的特征。精神标准是要追问与历史上先前的状态相比人们是否更自由和更幸福。然而,经济标准和技术标准与精神标准是不统一的,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人类见证了失去美丽和安全这样重大的损失。马克思的历史进步标准不仅是经济的和技术的,而且也是精神的,是这三个标准的统一。
总之,格仑德曼坚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分析现代生态问题,不像本顿那样用生态学维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面对生态学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反应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
二、对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辩护
人们反思生态危机时,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哲学思想根源。生态主义者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和反生态性的,因而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试图用生态主义的思想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提出由红到绿地绿化马克思主义。格仑德曼则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这是其思想的突出特点,也是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
格仑德曼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主义,他的世界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对研究自然没有设置任何道德障碍,并提出了以下三点辩护理由。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不一定会带来生态问题,反而能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依据。格仑德曼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生态问题是由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只有赋予自然内在价值才能保护自然。这种世界观往往会陷入两种困境:一是人们必须在客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一个客体被赋予了内在价值,就不能同时被评价为有用;二是一个客体要得到保护,就必须赋予它内在价值。在格仑德曼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观点没有什么错,只要把工具主义的观点加以扩大,除了经济功用之外,加上科学的、美学的和伦理的价值因素,这种态度就不会排斥生态关怀以及并不必然会产生生态问题。他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没有赋予自然内在价值,而是工具价值。然而,如果把工具价值理解为包括其他因素(如美学的和娱乐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就可能会形成生态意识。”③ 格仑德曼的结论是,“从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观点的角度,我们能得出一个保护物种的人类中心主义理由”。④
第二,人类中心主义为评价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参考点。格仑德曼说:“人类中心主义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为评价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参考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人类个体、社会、整个人类、未来的世代)界定这个参考点。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界定它,它为如何判断现存的生态现象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标准。……定义自然和生态平衡是人的行为,人是根据人的需要、快乐和愿望来设定生态平衡的。”⑤ 可见,由于评价的参考点是人,对“自然”或“生态问题”的定义总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因素相关。格仑德曼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存在着不一致性的缺陷,这个不一致性在于,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却附会着自然人类中心化的立场。
第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自然的繁荣相一致的。格仑德曼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完全有可能去关心‘自然的繁荣’,它绝对不是引起生态问题的帮凶。而且,更有甚者,我坚持这一立场是唯一能够与保持‘繁荣自然’相一致的,并促进了对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⑥ 对此,格仑德曼从以下两方面作了阐述。(1)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如果人自身要得到繁荣,自然这个无机身体也必须得到繁荣。格仑德曼引用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名言:“我们依靠自然而生活”。这说明,自然的繁荣就是人自身的繁荣,人破坏自然也就是在破坏他自身。任何粗心地使用资源,污染土地、水、空气,超出了一定的程度都有害于人类的福利,破坏环境会造成人类生存的困难。格仑德曼还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使人口聚集在大城市所造成的城乡分离,进而造成人们以衣食的形式消耗掉土地的成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发生了断裂,因此破坏了土壤永久肥力这个必要的生存条件。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人类的繁荣与自然的繁荣是一致的。(2)从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的两个源泉的角度来说,如果人自身想要得到繁荣,这两个源泉都必须要繁荣。格仑德曼指出,马克思认识到了人和土地是任何社会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它们是一切财富的两个最基本的源泉,如果人想繁荣自身,那么,这两者同样都必须繁荣。这表明,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维护人类的生存权是一致的。
格仑德曼强调,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的尺度”,应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价值尺度。他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他辩护的只是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只有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才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评价现代生态问题提供正确的参考点。
三、对“支配自然”观念的积极解读
格仑德曼认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是“支配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的主题,这一主题比人类中心主义更富争议,甚至那些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人也极力想与支配自然的思想分离,威廉·莱斯等一些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支配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层的哲学思想根源。毫无疑问,支配自然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首先,格仑德曼坚定地赞同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观念,反对把“支配自然”观念说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格仑德曼指出,启蒙运动思想家培根和笛卡儿是“支配自然”观念的创始者和倡导者,马克思是他们思想的追随者。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在继承皮可(Pico)、培根、笛卡儿、黑格尔、尼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现代自然观。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占有自然和改造自然。占有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种形式,在狩猎和采集的社会里,自然仅仅是被“占有”。改造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种形式,工业和技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获得了更高的形式,人能够“操纵”周围自然的某些部分,自然被积极地改造,并被治理或支配。与此相关的是,马克思认为自然呈现为两种状态,即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是在人类改造之前的原生态的自然,第二自然是被改造了的文化的自然,人类越多地改造自然就越能理解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人类的发展就是第一自然转变为第二自然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使用了“支配自然”这一词语。
其次,格仑德曼赋予“支配自然”以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支配”概念有三层含义:(1)“支配”只有与支配者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考虑它改造自然的后果,也不能说成是支配自然。(2)“支配”不是破坏自由意志,不是主人—奴隶关系下的绝对统治。马克思在《经济学家手稿》中谈到主人—奴隶关系时预设了一个异己的意志,在这样的关系下,即便是动物、土地等也为人提供了服务,但不能真正地治理或支配,治理或支配并不是要违背自然,而是在服从自然中来实现。(3)“支配”是有意识地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控制。格仑德曼指出,我们使用的“支配”(domination)与“控制”(mastery)是同义词,在英文中mastery有两种含义:一是征服、统治;二是精通、熟练掌握。
再次,格仑德曼把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方案联系起来。他指出,生态问题不是支配自然造成的,而是由支配自然的缺失造成的,一个社会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就不能被说成是支配自然。反过来,“只有一个能够控制自身在自然环境中活动的社会才配称为共产主义”。⑦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⑧ 格仑德曼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支配自然”是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相联系的,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成功地支配自然。
综上所述,格仑德曼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理解为人支配自然不断扩展的过程,人不仅在自然中生存,而且还要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生存,人对自然的抗争就是支配自然。正确理解的“支配自然”是“人有意识地控制”,扬弃了征服、统治和主宰的一面,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在格仑德曼观点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继续使用“支配自然”的概念。
四、格仑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析
从总体上来讲,格仑德曼主张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解决现代生态问题,他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了有力辩护,并赋予“支配自然”观念以积极意义。在“绿色革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片批评之声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用生态学来修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氛围中,他率先提出回到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去,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
具体来说,格仑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如下特点。
第一,他主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之下充分地阐释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批判精神有益于反思带来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在应对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面前,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重建,只是他们重建的角度不同而已。“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从三个维度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是加拿大学者莱斯和本·阿格尔主要是从人的需要的异化所导致的消费异化出发,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以此为基础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美国学者奥康纳侧重于将‘文化’和‘自然’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技术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力图建构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三是美国学者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中生态哲学思想的挖掘,力图建构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和生态唯物主义哲学”。⑨ 英国的泰德·本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需要用生态学维度来重建,要建立一个绿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格仑德曼与他们相比完全不同,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划分为广义哲学意义上的和狭义经济学意义上的,他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尤其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是由于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狭义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应加深对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它正确地阐释了自然和人性的理论,以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它与现代生态问题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第二,格仑德曼开创了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深受绿色运动中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走向生态主义,在理论上实现颜色的革命,即用绿色的生态主义理论来改造红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绿色化。其典型代表鲁道夫·巴罗提倡从红到绿,泰德·本顿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批判和重建,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浸染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在90年代初,格仑德曼提出重返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作了有力的辩护,同时对“支配自然”的观念作了积极解读,澄清了人们思想中的混乱。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会带来生态问题,而且能够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价值尺度来评价生态问题,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依据,促进人和自然的共同繁荣。格仑德曼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以及乔纳森·休斯在《生态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中都积极地响应格仑德曼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形成了独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
第三,格仑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20世纪90年代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红绿交融互动的情形,格仑德曼不失时机地由从红到绿转向为从绿到红,因此激活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生态运动的指导作用。在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上,格仑德曼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内在价值作为保护自然的理由,并把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对立起来,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幻想。格仑德曼认为,应站在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坚持人类的尺度并保护自然。
格仑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侧重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视阈的阐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不够,如何思考消除产生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是他的理论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后来由佩珀进行了加强和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形态。
注释:
①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
② Reiner Grund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87,1991,p.107.
③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96.
④ 同上,p.26。
⑤ 同上,p.20。
⑥ Reiner Grund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87,1991,p.114.
⑦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
⑨ 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