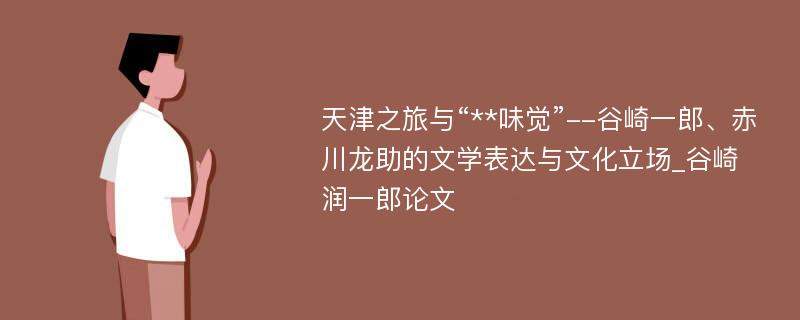
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那论文,天津论文,一郎论文,趣味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0-0103-06 按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说法,“支那趣味”一词最早出现于1922年,当时《中央公论》第1期设了“支那趣味的研究”专栏,登载了5篇①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之后“支那趣味”②这个词开始广为流传。“支那趣味”之所以能在大正时期得以迅速流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了明治时期的西洋化,日本人对邻国的优越感日益增强,逐渐开始用类似于西方审视东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并试图从中国这片古老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东方”寻求异国情调。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坛,欧洲近代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自然主义流派逐渐压倒传统的汉文学及日本古典文学占据了中心地位,出于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不满,文坛上开始出现回归古典的浪漫主义思潮,使得部分文人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于具有“支那趣味”的文人来说,中国是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土以及创作的源泉,大正时期旅游条件的改善也为他们亲自来中国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分别于1918年和1921年来到中国旅行。 明治大正时期来华的日本游客,大多要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留下足迹,谷崎和芥川也不例外。相比较而言,北京是具有深厚历史沉淀的充满梦幻的东方古都,上海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近代新兴城市,天津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混合型城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且呈相互独立的态势。尽管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长久以来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地位,但天津这座东西文化杂糅的城市,恰恰能为我们重新审视“支那趣味”提供崭新的视角。本文就将聚焦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之旅,在还原两人天津体验的基础上,分析同样拥有“支那趣味”的两位文人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一、带着“支那趣味”开始的中国之旅 谷崎润一郎曾说:“如今我们日本人表面上看来似乎全面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与之同化,但在我们的血管深处,所谓支那趣味的根深蒂固实在要超出我们的想象。”③谷崎所说的“支那趣味”,并非来自真实的中国体验,而是缘于他少年时代的汉学修养。谷崎幼时读过大量中国书籍,13岁开始在秋香塾学习中文,依次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古籍。在汉文学的浸润下成长的谷崎,脑中逐渐形成了来自于古典汉籍的中国幻象,刚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创作的《麒麟》、《秘密》、《魔术师》等系列短篇小说都取材于中国的传说或故事。 芥川龙之介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从小酷爱阅读《西游记》等汉籍,“曾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④。据东京日本近代文学馆《芥川龙之介文库》的记载,芥川共藏汉籍188类1177册,其中还包括不易收齐的《渊鉴类函》、《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隽永文辞、宏美意向给芥川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先后创作了《仙人》、《酒虫》、《掉头的故事》、《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之信》、《杜子春》、《秋山图》、《奇遇》等一系列取材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从而被称为“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的爱好者”⑤。 由此看来,在实际来中国旅行之前,中国对谷崎和芥川而言并非完全陌生,尽管在空间上相隔甚远且从未亲身体验过,却是一个在想象中环游过无数次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带着来自于古典文本的“支那趣味”踏上了中国的旅途。1918年10月9日,谷崎润一郎从东京出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之旅,经由朝鲜半岛先到达当时的奉天,最后从上海乘船回国。1921年3月28日,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开始了他近4个月的中国之行,先从门司出发乘船到达上海,最后从奉天经朝鲜回到日本。二人的具体行程如下: 谷崎:①奉天(沈阳)→②天津→③北京→④郑州→⑤汉江→⑥九江→⑦芜湖→⑧南京→⑨镇江→⑩苏州→(11)上海→(12)杭州→(11)上海。 芥川:①上海→②杭州→①上海→③苏州→④镇江→⑤扬州→⑥南京→⑦芜湖→⑧九江→⑨汉口→⑩长沙→(11)郑州→(12)洛阳→(13)北京→(14)大同→(13)北京→(15)天津→(16)奉天(沈阳)。 由上可以看出,尽管谷崎和芥川的行程方向相反,除了芥川比谷崎多去了⑤扬州、⑩长沙、(12)洛阳、(14)大同等四个城市外,游走地点大致相同。究其原因,除了芥川在计划行程时充分参考了谷崎的旅行路线等主观因素,主要还是受当时客观交通条件的限制。在20世纪初的中国,贯穿南北的铁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另一条是北京经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要想漫游中国,必然使用其中的一条,而内陆和长江下游城市之间并没有铁路,仅靠水路相连。”⑥ 谷崎和芥川的中国行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谷崎回国后陆续发表了《美食俱乐部》、《苏州纪行前言》、《苏州纪行》、《中国旅行》、《中国料理》、《观中国剧记》、《庐山日记》、《何谓中国情趣》等数篇与中国旅行相关的随笔及游记,创作了《西湖之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天鹅绒之梦》、《苏东坡》、《鲛人》、《鹤唳》等以中国之旅为契机的小说。芥川回国后先后发表了《上海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纪行作品,后来又在上述作品的基础上收入了未曾发表的《杂信一束》,由改造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中国游记》,并创作了《母亲》、《自第四个丈夫》、《马足》、《湖南之扇》、《发掘》等一系列以中国城市为舞台的作品。 二、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体验 天津是谷崎中国之旅的第二站,是芥川中国之旅的倒数第二站,尽管两人没有留下具体的“天津纪行文”,我们依然可以依据相关文章及信件还原他们的天津体验。 谷崎在奉天告别了老朋友木下杢太郎后,乘坐火车沿京奉线至山海关,随后来到了天津。谷崎10月24日从天津寄给木下杢太郎的明信片上写道:“昨日离开山海关来到此地。”⑦由此可以判定,他在10月23日来到了天津。另外,从明信片的落款“于天津法租界裕中饭店”可以得知,他在天津逗留期间住在了法租界的裕中饭店。 由于谷崎是个人之旅,可以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兴趣行动。来到天津后,谷崎为了观看京剧转遍了天津的大小剧场,“这里显然盛行戏剧,如果漫步在类似日本的浅草公园或道顿堀之类的老城区,就能看到卖报的拿着各种登载着戏目广告及剧评的小报沿街叫卖。我买了一张小报,按着上面广告中提到的剧场逐一去看。”⑧在谷崎创作的以天津为舞台的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细致描述了天津法租界及白河(今海河)海岸道的风景,并出现了“裕中饭店”、“朝鲜银行”、“白河海岸道”、“万国桥”、“美孚火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当时天津存在的建筑物及公司名称,这篇以实际天津空间为舞台的作品,应该是谷崎基于自己的真实体验创作而成的。 概言之,谷崎的天津之旅并不复杂,却在某种意义上体验了一个“全景天津”。尽管“西式”租界与“中式”老城的并存是近代天津主要的城市特点之一,但来到这里的日本游客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城市缩影”般的租界而完全忽视老城区的存在。⑨与之相比,谷崎既亲临了繁杂脏乱的老城区观看中国传统的戏剧,又在具有整洁气派街区的租界体验了充满西方元素的异国情趣。 再来看看芥川,根据其年谱记载,他于1921年7月10日下午从北京出发到达天津,住在了日租界内的长盘旅馆。⑩7月11日,天津在留日本人创办的杂志《日华公论》请求芥川谈论对中国的印象。(11)在津逗留期间,芥川曾给多位友人及家人寄去明信片,其中一封7月12日寄给南部修太郎的明信片上提到:“昨日令妹光临。诚惶诚恐。同时拜收贵函。”(12)南部修太郎与小岛政二郎、龙井孝作、佐佐木茂索一起被称为“龙门四天王”,芥川一直将他作为老师敬仰,他的妹妹当时随丈夫来天津赴任,看来是听说芥川来到天津,于是专门去拜访。 芥川于1922年10月1日在杂志《中国美术》上发表了随笔《中国的画》,文中提到:“天津方若先生的珍藏品中,有一幅珍贵的金冬心画。”(13)除此之外,芥川在中国旅行期间记录的《笔记》“第七”中有一段话:“万邱,稚拙可爱。唐寅,山水横卷,习北书之体。……方若家。”(14)由此可以推断,芥川在天津曾专程去过方若的家。这位名为方若的中国人是日租界长期豢养的政客,曾任《国闻报》主笔及日本人创办的《天津日日新闻》社长等职,同时还擅长诗词、绘画、篆刻,并以收藏考究古钱币著称。 在《杂信一束》的“十八天津”中,记录了芥川与西村的简短对话。那么,这位在天津陪伴芥川的“西村”究竟是何等人物?以往不少研究者认为他是芥川在芜湖的朋友西村贞吉,但姚红在论文中推翻了这一说法,因为1921年7月12日芥川曾从天津给芜湖唐家花园的西村贞吉寄过一封信,由此断定西村贞吉当时不可能在天津,并认为对话中的“西村”是《天津日报》的社长西村博。(15)对此笔者完全赞同,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报界人士的热情接待,作为《天津日报》社长的西村博陪伴芥川逛天津城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总体而言,芥川在天津逗留的两三天时间内,接触到的主要是在津日本人,而且多为报界人士。他没有像谷崎那样在天津老城漫步,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天津租界,看到的也只是令他倍感失望的“西洋式街道”。 三、“支那趣味”的创造与验证 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带着来自于经典文本的“支那趣味”来到了中国,但衰败落后的现实中国与他们心中的美好幻象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因西方国家的势力入侵而被染上西方色彩的中国,已经无法为他们呈现古老的纯东方景象。那么,谷崎和芥川会分别以怎样的方式处理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呢? 来中国之前,谷崎一直幻想着中国的京剧会和古典小说《老残游记》一样,可以将他带入如梦如幻的境界之中。但在奉天的第一次京剧体验就让他见识了简陋不堪的剧场、穷凶极恶的脸谱、震耳欲聋的声音,从而令他感到“心中的幻境就这样被击得粉碎”(16)。到了天津后,谷崎依然不甘心放弃心中的幻象,为了观看京剧转遍了天津的大小剧场,遗憾的是,他那在奉天被击得粉碎的幻境在天津再次遭受打击:“还是没有一处令人满意的。首先是戏院太脏,让人头疼,在舞台上一跳动就能扬起许多灰,四周变得灰蒙蒙一片。更过分的是,那些扮成俊男美女的演员竟然会在台上吐痰擤鼻涕。”(17) 幻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谷崎“深受打击”,不过这种“打击”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支那趣味”的追寻,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谷崎开始在文本中去创造。比如在《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叙述者“我”在法租界偶然碰到了一个衣着褴褛年纪在50岁上下的男人,“从那被晒成褐色的手背、宽大的手掌、骨节突出的粗手指来判断,确实像个干粗活的,但他的穿着又和那一带的苦力有所不同,就算是干粗活的也太肮脏寒碜了,怎么说呢,感觉更像个乞丐”。(18)然而,即便对于这样一个貌似乞丐的人,谷崎也不甘于将他描写为普通的俗人,而是将其形容为被破烂衣衫包裹着的宝玉,并且重笔墨描述了他那非同一般的眼神: 他的眼睛,就像变幻莫测的天空,忽而阴云密布,忽而雨过天晴。就在刚才,那一对眸子里似乎饱含泪水,亮晶晶湿润润。像是一阵忧伤涌上心头,脸上渐露悲壮之色。而刹那间又浮现出恍惚神情,像是丢弃了所有的一切,正在做着休闲之梦。忽而露出女人般温柔的眼神,忽而又燃起恶魔般卑鄙的欲望,忽而又闪过窃贼般狡诈的目光。(19) 谷崎用他唯美大师所擅长的绚烂华丽又行云流水般的笔调将“漂泊者”的眼神描绘得如此惟妙惟肖,可以说此时的谷崎并没有对他看到的事物进行客观描述,而是将他来中国之前在经典文本中联想到的各种美丽影像罩在了现实之上,依照自己的想象美化了现实的体验。不只是《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谷崎的其他中国题材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在《苏州纪行》、《庐山日记》中,他将运河、太平山、灵岩山、庐山的景色描写得如梦如幻、美不胜收,在《西湖之月》中更是把月下的西湖写得宛如仙境,将其比喻为拥有令人惊叹的美丽光泽和柔润的天鹅绒。 芥川龙之介在结束中国之旅后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他足迹踏过的城市大多有机会在其作品中出现,然而,不论是纪行文还是后来的文学作品,都很少能看到天津的身影。除了《杂信一束》中有抱怨天津西洋式街道的寥寥数言,关于天津的直接描述只能在他寄给朋友们的书信中找到。比如7月11日他曾给《大阪每日新闻》北京通信部的松本枪吉寄过一封信,信中附有短歌《天津贬谪行》: 又到黄昏时,万里来到此蛮市,怎能不伤情。 放眼望蛮地,不比北京之骆驼,丑陋胜驴子。 我身来此处,怎奈心头涌悲情,合欢无处寻。 花合树阴下,身着唐装走大路,思念难忍受。(20) 从北京来到天津后,芥川感觉自己像是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了边疆,天津是一个荒凉的“蛮市”,甚至比不上北京的骆驼,让他无比的苦闷。7月12日寄给好友小穴隆一的明信片上,芥川再次表达了对天津的不满:“此处与上海毫无区别,同为蛮市之地。”(21)以整洁的道路、西式的建筑为代表的近代天津城市风貌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游记中被褒扬的对象,为何唯独芥川要将天津称为“蛮市”? 芥川来到中国后,一直想通过旅行亲眼验证之前通过汉诗文及古典小说构筑起来的美好幻象,因此他会有意识地从记忆中搜寻出经典文本中的中国,然后将其作为标准来验证现实中的中国。芥川说过:“自上海以来,最使我感到幸福的便是扬州了。”(22)那是因为在扬州的画舫上,目送着载着扬州美人的船,看到在两岸静静的芦苇中间留下的一道微白水光时,芥川感觉到杜牧的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未必是夸张,“似乎在这扬州的风物中,有一种能够把我都变成诗人的舒心的惆怅”。(23)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中国并不具备他想象中的“诗情画意”,当他来到灵岩山的馆娃宫遗址目睹了那里的荒芜景象后,不禁大发感慨:“这样的情况,无论怎样的诗人,也不可能像我们的李太白那样沉浸在‘宫女如花满春殿’的怀古幽情里。”(24)来到天津后,随处可见的西洋式街道更是与他心中的“支那趣味”相差甚远,结果导致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彻底失望,于是他笔下的天津只会以“瘴烟深处”的“蛮市”形象出现。 尾崎秀实在《现代中国论》中分析道:“日本人从小开始密切接触中国的古典汉文学,然而,通过这些汉文学想象并描绘出的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中国社会之间处于完全被割断的状态,几乎不存在任何的联系。尽管有了上千年的事实上的跨越,却有人忘记了这种割断,甚至将其作为理解现实中国的唯一标准,结果不断产生错觉和误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25)这句话用在芥川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他恰恰试图忘记这种割断,一味希望在现实中国中验证那原本靠经典文本构建起来的“支那趣味”。 四、对待“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立场 近年来,中日学术界似乎热衷于用“东方主义”理论去解释近代日本人的中国体验及中国题材文学创作。学者王升远曾指出,“西方—东方”式的东方主义经过日本式的改造成为了“西方—日本—其他”的模式,对于本属东方国家的日本而言,自古而今,其与东亚诸国(特别是中国)的错综复杂关系很难以“东方主义”简单打发;(26)并在一篇讨论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人力车夫书写的文章中指出了“东方主义”在用以阐释中日文学文化关系问题中的限度和射程。(27)在分析谷崎及芥川的“支那趣味”时亦是如此,不能简单地套用东方主义,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客观审视他们对待“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文化立场。 在《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谷崎将背景设定为天津的法租界,“这里是天津城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来往行人大多是穿着讲究的西洋人,偶尔还会有涂成黑色的箱式马车路过”。(28)但是,这条华丽街区上的中心人物却是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污垢无精打采的流浪汉,谷崎没有点明是中国人,只是说肯定是东方人,作者特别强调,如果说在那洁净的柏油路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在移动,那就只有从那里路过的那个男人的脚。比起被踩踏的地面,反而是踩在上面的鞋子要脏许多。画面随着漂泊者的脚步继续延伸,走过整洁美丽的西式街区,来到白河海岸道上,“在河对岸,印有西方公司名称的石油罐比河面上停满的汽船船帆还要高,像山丘一样高耸入云。……旁边堆积着的煤山上,搬运工像蠕动的蚂蚁一样连在一起”。(29)在谷崎笔下,“西方”与“东方”总是色彩对比强烈地同时出现。“华丽的西装”对“破烂的衣衫”,“洁净的路面”对“肮脏的鞋子”,“高大的油罐”对“蚂蚁似的搬运工”。在这里,“西方”代表先进、文明、整洁,与之相对,“东方”代表落后、愚昧、肮脏。谷崎后来回忆道:“目睹天津、上海那整齐的街衢,清洁的路面和美丽的西式房屋,仿佛踏上了欧罗巴的土地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30)看来天津让谷崎感到高兴的是“欧罗巴般的土地”,而非中国的土地。 看来“支那趣味”和“西洋崇拜”这两个互相对立的观念在谷崎的思想中一直和平共处,并且呈现出一个横向的互动结构,甚至还可以说他的“支那趣味”是以“西洋崇拜”为前提和基础。包括谷崎来中国之前创作的被公认为“支那趣味”代表作品的《美人鱼的叹息》和《魔术师》,同样体现了“西洋崇拜”与“支那趣味”的融合,并将他对西方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美人鱼的叹息》中的主人公孟世焘是南京的贵公子,文中充满了浓浓的中国色彩,既有美味的中华料理,也有优美的古典汉诗文,然而主人公却对荷兰商人说:“欧罗巴是多么洁净,多么令人羡慕的天国呀。请带我和人鱼去你的国家吧,请让我也成为居住在那里的优越人种的一员吧。”(31)谷崎曾明确表示:“如果那时有钱,又没有家属牵累的话,我一定会飞到西方去,过西洋人的生活,(中略)大正七年我去中国旅游,可以说就是为了稍微慰藉一下这个没能实现的异国梦。”(32)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除了“西方”与“东方”这两个对比元素,以“我”为代表的日本究竟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东方主义》日文本译者金泽纪子在后记中说:“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日本无论从地理的,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自然属于客体=被观察方。但是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积极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视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观察方一边。”(33)在《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谷崎确实将“我”置身于观察方一边,但“我”并没有只观察中国这片所谓的“东方”,同时也在观察“西方”。在天津这座中西杂糅的近代城市中,“我”拥有了一份“左顾右盼”的从容,既能“左顾”肮脏的天津老城,也能“右盼”洁净的天津租界;既能“左顾”中国人的“矮小低贱”,也能“右盼”西洋人的“高大富贵”。此时的“我”,可以说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成了一个从容悠闲的旁观者。 与之相对,芥川则缺少谷崎的这份从容,他的作品世界中从未出现过“东方”与“西方”的相互融合。儿时的熏陶早已使东方的诗学传统内化为芥川思想的一部分,对于所谓的西方文明,芥川没有谷崎所持有的那种崇拜之情,相反,当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竞相学习西方时,他对日渐淡薄的传统文化感到惋惜,对日本移入西方文明的现象乃至西方文明本身都怀有深深的疑虑。对日本现实深感失望的芥川,只能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寻找躲避西方大潮的心灵港湾。在来中国之前,芥川创作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本的作品,如《尾生之信》是由《庄子·跖盗》中的一行字扩写而成,作品能带着读者走进那神秘而远古的中国。《奇遇》是由明代小说集《剪灯夜话》中的《渭塘奇遇记》改写而成,文中展现的中国犹如一首山水田园诗。《杜子春》中的舞台是唐都洛阳,在这梦幻般的都城里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可以说这一系列作品都保持了纯正的“东方”色彩,没有掺杂任何“西方”元素。 然而,现实的中国不可能像芥川希望的那样永远保持神秘远古的东方色彩,在西方国家的军事侵略下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西化了,实际来到中国后的芥川无法容忍西方异文化出现在他梦幻中的“东方”。当他在杭州时的浪漫情怀被喝醉了酒的美国佬打破后,心中燃起了十倍于水户浪士的“攘夷”之火,愤恨连西湖都染上了美国味。(34)可以说芥川的“支那趣味”不仅没有像谷崎那样以“西洋崇拜”为前提,而且要求绝对的纯度,排斥一切“西方”的元素。正因为如此,深受谷崎钟爱的上海和天津两个城市,由于表面被西方的滚滚车轮碾过,在芥川心中都是“蛮市”。他讨厌充斥着不伦不类西洋的上海,看到拥有九国租界的“欧洲城市缩影”般的天津,更是抱怨道:“走在这样的西洋式街道上,真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啊。”(35)而他所说的乡愁,并非指故乡日本,而是指具有浓厚传统东方色彩的北京。 然而有一点不能忽视,尽管芥川的“支那趣味”要求没有西方元素的原始状态,却对日本元素的加入没有任何反感,相反却感到高兴。他在上海参观同文书院时,在对面看到了风中飘舞的鲤鱼旗,这面充满日本色彩的鲤鱼旗让芥川骤然间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自己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对此他写道:“在遥远的上海的天空下,我看到了日本的鲤鱼旗,也多少感到了愉快。”(36)这不禁让笔者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天津没有“西洋式的街道”而全部是“日式的街道”,他是否还会将天津贬为“蛮市”? 对于在中国古典文籍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也并非“一无所有”地来到中国,而是带着提前储备的大量相关知识,带着对中国的幻象踏上了旅途。如果以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支那趣味”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正时期的“支那趣味”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当现实中国与幻象中国发生冲突时,不同的作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谷崎会根据心中的幻象去创造“支那趣味”,而芥川则在心中的“支那趣味”无法得到验证时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其次,与“东方主义”中的“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日本的“支那趣味”包括东方、西方、日本三个元素。在谷崎的世界中能够使三者和平共处,并能实现横向互动;而在芥川的世界中则呈现出“东方”(包括中国与日本)与“西方”水火不容的激烈对峙态势。 ①分别是:画家小杉未醒的《唐土杂观》、建筑家佐藤功一的《我的支那趣味观》、建筑家伊东忠太的《从住宅看支那》、建筑家后藤朝太郎的《支那文人和文房四宝》、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何谓支那趣味》。 ②根据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的界定,现在所说的“支那趣味”,主要指流行于大正时期的针对中国的一种异国情趣。 ③[日]谷崎润一郎:《何谓支那趣味》,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2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121-122页。 ④[日]芥川龙之介:《爱读书籍印象》,载《芥川龙之介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99页。 ⑤《新人眼中的新中国近日将于本报刊载》,《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3月31日。 ⑥[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4-125页。 ⑦[日]神奈川文学振兴会编:《谷崎润一郎展》,县立神奈川近代文学馆1998年版,第25页。 ⑧[日]谷崎润一郎:《观中国剧记》,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2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71-72页。 ⑨参见拙文《论殖民视角下的近代天津形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月增刊,第3-4页。 ⑩[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3卷,岩波书店1998年版,第150页。 (11)谈话内容以《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为题刊登于1921年8月1日《日华公论》第八卷第八号的《杂录》上。 (12)[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85页。 (13)[日]芥川龙之介:《中国的画》,载《芥川龙之介全集》第9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36页。 (14)[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3卷,岩波书店1998年版,第388页。 (15)姚红:《1921年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之旅》,载王晓平主编:《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16)[日]谷崎润一郎:《观中国剧记》,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2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71页。 (17)[日]谷崎润一郎:《观中国剧记》,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2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72页。 (18)[日]谷崎润一郎:《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6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第475页。 (19)[日]谷崎润一郎:《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6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第480-481页。 (20)[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84页。 (21)[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84页。 (22)[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9页。 (23)[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8页。 (24)[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1-102页。 (25)[日]尾崎秀实:《现代支那论》,劲草书房1964年版,第8页。 (26)王升远:《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7)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28)[日]谷崎润一郎:《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6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第478页。 (29)[日]谷崎润一郎:《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6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第479-450页。 (30)[日]谷崎润一郎:《忆东京》,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1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10页。 (31)[日]谷崎润一郎:《美人鱼的叹息》,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4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第205页。 (32)[日]谷崎润一郎:《忆东京》,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1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9页。 (33)[日]今泽纪子:《译后记》,载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主义》(下),平凡社1993年版,第393-394页。 (34)[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68页。 (35)[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页。 (36)[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页。标签:谷崎润一郎论文; 芥川龙之介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天津论文; 旅行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