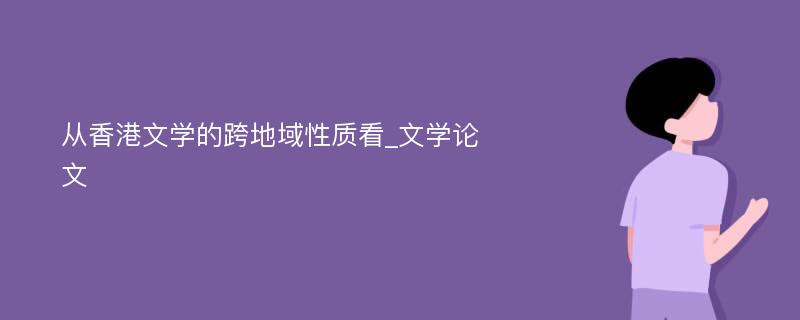
从香港文学的跨地域性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香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谈香港文学,按道理应该对“香港文学”这个词语先下界说。郑树森(香港文学的界定)一文以为:香港文学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广义的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①。这话当然说得不错,可是笔者以为此时此地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与辨析。
首先,谈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注意它所涉及的地域观念。文学是一个极为广泛而难以确定的观念,谈论它,可以从国别、种族区分,也可以从朝代、文类区分,其中颇为常见的一种,是从地域着眼。例如古代有公安、竟陵、常州、阳湖等等流派,近代有“京”派、“海”派等等。它们都是从某一地域的观点,来讨论作家及作品的问题。所谓“香港文学”,自然属于这一类。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讨论某一地域的作家作品时,往往是把它和其他地区的作家作品,一方面区隔出来,另一方面却又拿来互相对照比较,求其同,较其异,然后才可以看出各个地方区域的特色。而且,在对照比较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它必然有独特不同之处,也必然与其他地域有共同相通之处。前者我们称之为独特性,后者我们称之为共通性。
我们知道香港原是僻处岭南的滨海小岛,一百多年来,它却由以捕鱼为业的渔村,变成国际著名的金融大都会;它曾长期割让给英国作为殖民地,自1997年起,却又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的发展历程,自然值得寻索探讨。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居民只要不违背港英政府颁布的法令,那么,想要提倡中华固有文化,维护传统,或者师夷崇洋,全盘主张西化,都悉随尊便,可以各行其是。在上世纪中后期,就常听到有人戏称,大清律例、民国宪法和英国法令,同时存在于新界、九龙和港岛。即使是目前,大家也一再强调“港人治港”,表示香港居民有其自主性,希望外力不要干预太多。这样的情况,和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曾租界给列强的上海的一些地区,或者曾被英、法政府殖民过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都显然有所不同。这可以说是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的香港居民,无疑的,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都是过去一百多年间,由其他地区先后迁徙而来。其中以华人所占比例最大,他们之中,粤、闽、沪籍的人口最多。固然他们迁居香港,有的是为了经商谋生,但不容否认,有很多人是为了避祸逃难。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教界人士。他们分别在民国肇建、抗日抗争、国共内战及文化革命前后,南下避居于此。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观念自然不尽相同。加上英国殖民以后,欧西等各国人士来港者日多,华夷杂处,东西交会,一切显得纷繁而多样。大家为了生活和谐,社会安定,固然学会了包容异己和互相尊重,但也各自保存着一些原来的文化习惯。因而,所谓香港人,在身份的认同上,较之其他的地区或城市,也要复杂一些。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香港人,持有两种以上的护照或身份证件。他们自认是香港人,同时也是某某地方的人。这意味着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很大。过去,常有人说香港不民主,却很自由;也常有人说,香港“不中不西”,却又“亦中亦西”。我以为这些话都不无道理,但这也同时说明了:香港固然有其独特性,然而在其独特性中,实际上又与其他地区、城市有互通共同之处。我们称之为跨地域性。要谈香港文化或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从这里谈起。
二
谈香港文学,除了要注意其地域观念的特性之外,我以为还要注意到香港作家身份认同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香港作家?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香港文学?上文引用郑树森广狭二义的说法。狭义的那种,属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写香港的人情事物,在香港发表、出版,自是道道地地的香港文学,但这种说法画地自限,未免过于狭隘。广义的那种,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包括了原非香港出生的人,却曾经居住于此,后来又迁往台湾、大陆或欧美等地,他们的作品,也未必发表在香港。这种人算不算香港作家?郑树森以为应该算,但当事人自己怎么想,则不得而知。在我想来,恐怕因人而异。据说徐訏居住香港几十年,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要把他归属为香港作家,恐怕他不会乐意。余光中居港十年,写了不少歌咏香港的诗文,影响不小,谈香港文学,如果对他略而不提,恐怕也会起争议。有人告诉我,应该视这些作家是否曾经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证而定。如果他曾经拥有,当然算是香港作家;如果他从来不是香港居民,只是在香港投稿、发表作品,就把他列为香港作家,把其作品列为香港文学,似乎也不适宜。
这样的看法,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想,还是有讨论余地的。
我想到的问题是,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香港,但他后来写作、发表的地方,都不在香港,甚至所写的题材内容也与香港没有关系。一般香港的文学工作者,也不知其人。这样的作家,要怎样归类呢?
例如陈子善曾经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幻洲》、《现代小说》等刊物中,发现谢晨光其人,认为他是香港的“北上作家”第一人;说他擅长描写爱情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②,可是他在香港却罕见有人提起。又例如我以前在台北时,知道一位香港出生的政大侨生,本名叫吴思明,在台湾读书、就业,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笔名叫司马翎。我一直以为他和卧龙生、古龙是台湾武侠小说界最值得注意的代表作家。③同样地,他在香港也鲜有人提及。我常常想,这样的作家作品,如果不算是香港文学,那多么令人惋惜!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发表、出版的,可是作者却已不详,无从查考。例如我以前在台大读书时,看到香港出版的女侠盗黄莺的故事系列,作者署名“小平”及“一平”。我个人以为不止在香港,即使在中国民初的侦探小说,也罕有那样恢宏而缜密的格局。我到处向人请教。有人说可能是倪匡所著。我亲自请教倪匡,他说不是。他还说印象中书稿来自上海。文笔相当好,却无法得知作者是谁。卢玮銮教授则告诉我,最近已有人找到作者“小平”其人,现住上海浦东。我非常期待有进一步的确实数据。又例如我在四十几年前,从香港进入台湾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上读到一些至今记忆犹新的作品,一样不知若干作者为何许人。这样的作品,是在香港发表的,如果不视之为香港文学,又是多么令人惋惜!
因此,谈香港文学,我是主张放大眼界,敞开胸怀的,不妨把与香港有关的作家作品,都当成香港文学来看待。以前,我在台湾,曾主张不要把台湾文学囿限于台湾人写台湾事的小格局中,否则多少在台湾成长,对台湾艺文界极有贡献的一些“外省籍”作家学者,如白先勇、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朱西宁、司马中原等等,以及在台湾发表出版的一些名篇佳作,被摈弃在外,是多么可惜!也多么无知!前人说得好,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辞细流,故能就其深。我认为一个香港居民,既然可以拥有两种以上的证照,一个香港作家,也不妨可以拥有两种以上的身份。
也因此,我在这里要承应上文所说的,谈香港文学,不但要注意其跨地域性,而且要把它和同文同种的两岸三地文学,乃至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放在一起观察,这样才能在对照比较之余,了解香港文学与各地文学的异同,从而看出它的独特性与共通性。当然我在此必须强调,本文所说的香港文学,涵盖了港、澳地区,指的都是以汉字或华文所写成的文学作品。
三
上文说过,我们讨论某一地域的文学,往往是和其他地域来对照比较,然后才可以较其异、求其同。我们要了解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其他地域的共通性,就必须先把它放在两岸三地的文学中来观察。
两岸三地的文学,基本上是以汉语或华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自然会受到同一类型文化的影响。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百多年间,除了殖民政府英国之外,与它在文化、文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首推台湾以及在地缘文化上无法分割的大陆内地。它与大陆接壤,可谓唇齿相依,与台湾也只是一衣带水。而一般人所说的两岸三地,大致也是就上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以后,大陆与台湾两岸对峙的情况来说的。当时的香港,虽然曾有所谓美援文学,但毕竟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也可能在有意无意间,采取较为模糊的立场,因此左右双方在此明争暗斗。不管是大陆或台湾,他们要争正统,各有各的文化政策,旗帜都很鲜明,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主张,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当时南下香港的作家为数不少,固然有的亲左,有的亲右,不过也有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开始在香港定居下来,不再“东”张“西”望,也不再“左”顾“右”盼。他们在“各为稻粱谋”之余,从事了一些休闲娱乐性质的文章写作,甚至有人(像蔡澜)公开说:去他的什么使命感。我读过不少讨论两岸三地文学的文字,颇有一些是从这里切入讨论问题的。我以为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但究其竟,却不能竟委探本。因此,我要另外采取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一直认为,要谈香港文学的特色,或者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应该先注意到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新旧文学的交替。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各地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共通性。
先说中西文化的对立。欧西文明之传入中国,影响士人,当然非自清朝中叶起,但确实是从这时候起,也差不多是香港开埠前后,它才随坚船利炮而叩关直入。英法之联军,以至列强之瓜分,固然使变乱纷乘的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但不少爱国志士起先还以为中国武力虽然不振,远逊外敌,但论精神文明,则礼义之邦远非他国所能企及。所以有人故意译英国为“英狤猁”;有人以“射鹰”谐音影射要歼灭英国。等到清末民初,西学东传,政治、思想、文学著作经过译介之后,欧风美雨纷至沓来,中国读书人才惊觉西方国家不只船坚炮利,连精神文明也颇有一些超轶中国。关于这些,我们从民国初年,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旧学根底深厚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论著中,多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就可以看出这种风气的转变。而这种风气的转变及发展,我们从两岸三地分别来观察,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国共斗争开始以后,能继承民国初年西学风气,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化解对立而转为接纳的,首推香港。胡适在1935年来香港演讲《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时,就说过希望香港能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④。“新文化”当然是指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潮。有人说香港自上世纪中期,一方面带动了后来台湾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潮流,一方面也变成了大陆闭关自守时中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或许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由对立而转向接纳,香港因接触西方文明较早,因而走在台湾、大陆的前面。后来台湾一度超前了,政府民间都非常鼓励,出版品非常之多,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受到各方瞩目,因此也有人以为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台湾的脚步应该在香港之前,其成就也超过香港。现在则大陆正迎头赶上。
在新旧文学的交替方面,两岸三地也呈现了同中有异的情况。历来谈论香港文学,或者两岸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人,一向都只把眼光放在新文学上,而很少顾及旧文学。这里所说的新文学,指的是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在清末民初以前,绝大多数都是用文言来写作的。它历千百年而变动甚少,即使到现在,不要说是香港、台湾或大陆,就连世界各地都仍然有人在使用文言写旧诗,填词作文。我们不应该说现代人用文言写的诗文创作,不是现代文学。因此,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旧语文的交替与观念的嬗递。前者关系着诗文的新变,自清末民初开始,一切文章写作,已多舍文言而就语体,恰如1916年胡适文学革命之所主张;后者关系文学的观念和文类的发展,姚鼐所说的古文辞,大家认为已不实用,古人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却反而被一般人所喜爱,一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所鬯言。文学的观念改变了。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变而成消闲娱乐之用。它重在感染读者,而非直接宣扬政教。
这种风气、观念的转变,我以为最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一是从1906年起,旧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了,读书人求学、就业、谋生、应酬,已不再以文言旧传统为依归;二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学校制度改弦更张,逐渐加重外国语文、西方文明、现代科技的课程,而同时却削减了古典经史之类国学的肄习,三是文言难学,白话好用,又多不学而能。人们本来就容易趋易而避难。因此,先则经史子集,继则诗词歌赋逐渐鲜人问津,成了专门之学或绝学。例如1921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创刊《文学研究录》,主张因文卫道,发扬国粹,重视旧文学,而反对白话文。这反映了民初香港文坛的状况。难怪侣伦在其《向水屋笔语》中慨叹五四运动未在当时的香港起什么作用。⑤如今白话则已几乎取文言而代之,成为大众日常使用的共通语言。现代文学创作既以现代汉语为主,久而久之,大家所说的文学创作,也就约定俗成,以为全是用白话写作的“新”文学了。
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再来观察、比较两岸三地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大陆最早提倡普罗文化,一般人早已弃文言而用白话,文学创作者很难自外于现实的政治社会;台湾虽经日本统治,却一直文言白话兼顾,除近年来提倡本土化之外,一直以维护中华固有文化为己任;而香港在被英国管辖期间,文化政策一直模糊,因此国粹派、西化派,甚至鸳鸯蝴蝶派,都可以共存共荣。他们多数很功利,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
在大陆闭关自守时期,台湾和香港受到美、英等外国文化影响比较多,学界文坛来往交流比较多,因此台港二地在上世纪中后期,常常互通声气,在华文文学的影响上,一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止新、马、菲、越等地,连韩、日、欧、美各地的华文作家,在上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很少不在台湾出书或发表文章,很少不与台湾文教界接触。而在他们与台湾接触的过程中,也几乎同时与香港有所联系。
因此,有的人谈香港文学,说它具有“意识自由”、“题材通俗”、“风格多样”等特点⑥,我以为所言过于浮泛,未中肯綮。试问意识自由、题材通俗、风格多样等等,何尝不是台湾或其他某些地区文学的共同特色?也因此,要谈香港文学的独特性,除了应该从其语言习惯着眼之外,更应该从其某些文类的成就,去和其他地区比较,找出香港文学的真正独特之处。它应该是香港所独有的,或者它是香港所创始而领先的。
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香港文学,把它放在两岸及各地华文文学中来对照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下列几个特点:
(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承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之后,结合历史,熔裁诗词,运用电影等表现手法,融传统于现代,无疑为武侠小说开辟了新天地,影响了后来在台湾写作的卧龙生、司马翎、古龙等人。他们的作品不仅风行一时,至今而不衰,而且已倾销大陆,引起广泛的响应及盗印的热潮。这是香港文学的光荣。
(二)除武侠小说之外,香港所出版的新侦探、历史改编及科幻小说,较之其他华文地区,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至少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倪匡、南宫博等人,都是我们在谈张系国、高阳等等科幻、历史小说时,不能不提的香港作家。
(三)香港报刊杂志的专栏文字,篇幅极为短小,通常五百字上下,内容则无所不包。群雄各据一方,分而读之,有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合而观之,则俨然看到了香港快餐文化的缩影。真的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从早期左舜生、易君左、曹聚仁等人的文史小品,到现在董桥、陶杰、刘绍铭、李碧华等人的泼墨即兴之作,都可谓各领风骚,展现了香港专栏作家的学养才情。衡之其他地区,确属罕见。这何尝不是香港文学的独特处?
(四)以前有人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爱护香港文学的黄维梁,曾写专文加以驳斥。事实上,批评的人重点是说香港特重饮食男女,较少顾及其他。饮食、休闲、娱乐文化,如果真的是香港的特色,那么,何必强加辩解呢?在我看来,香港文学的独特之处,正是在通俗文学、庶民趣味之中,兼取中西一些新颖的形式技巧,加以糅合,因而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莫言写山东红高粱,李锐写西北黄土地,苏童写江南世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写台湾乡土人物,各有各的地方特色与语言习惯。香港人是学不来的,也不必学。那么,香港人写什么呢?语言出于中古粤语,文化属于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都会,香港文学能够出奇制胜处,正在于致力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学的写作。自古以来,城市文学就离不开饮食男女,离不开大众化、趣味化、通俗化、商品化。唐宋以后的传奇、话本、杂剧、戏曲,不都是因此而兴起的吗?
四
香港文学的独特性,既如上述,其与各地华文文学之共通处,其实上文亦已多有涉及。近年来,世界各地流行一种互相矛盾的口号,一方面提倡本土化,另一方面却同时高唱国际化。就文学创作而言,前者近乡土文学,后者近城市文学。前者比较容易凸显各地方各作家的不同特色,后者则往往在往来频仍、互通有无之余,渐趋于互通共同。就作家而言,多数居于城市,可是他们却往往原本植根于乡土。他们一方面希望面向国际,另一方面却强调本土意识。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乡村逐渐城市化,很多作家的乡土性越来越薄弱,而国际性则越来越强。因此,生活于香港、台北以及大陆重新开放的几个主要城市,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他们写的题材,逐渐趋于共同互通,往往离不开饮食男女,离不开情感的纠葛、性与暴力,离不开性别、阶级、家庭等等的恩怨情仇。除了各人各地难以改变的语言习惯之外,他们在表现艺术、写作技巧上,往往互相观摹学习,也不断地求新求变。
因为求新,所以他们多弃旧文学于不顾。旧文学的形式律则,例如诗词的格律、古文的义法,他们以为是陈旧落后的;旧文学所标榜的观念,例如载道、言志的传统,他们也多以为是陈腔滥调。因而新诗的写作,宁可模仿西方的十四行体,也要打破诗词格律的束缚;小说的写作,宁可取法外国小说的叙述方法,也不再采用章回对联花开并蒂的形式。这是一种趋势,虽然并不代表哪一种选择是好是坏。新与旧,本来就不是好与坏的等号。
因为求变,所以他们也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在翻新。今天流行张爱玲,就到处有人“看张、张看”;今天流行余秋雨,就有人要“石破天惊逗秋雨”。今天流行存在主义,他们就看卡缪;今天流行新社会主义,他们就学卢卡奇⑦;万一今天又流行后现代主义,他们也就赶快了解什么是后现代。
生活在大城市里,他们不能不求新求变,借以适应环境。或许由于各大城市生活形态相似,生活经验也大致相同,所以出身上海、久居香港的西西,可以写“我城”;来自上海的王安忆,可以写《香港的情与爱》;来自台湾的施叔青,可以写“香港三部曲”,似乎都驾轻就熟。因为上海、香港、台北三个城市,固然有不同的风貌,但毕竟有不少相似互通之处。上述的这些作家有才情,有创意,另当别论,但不必讳言,我们也可以看到若干城市作家在写作主题及艺术技巧上,常免不了予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我们在这里面固然闻到了不少商业气息,看到了文学大众化商品化的趋向,但也同时在求新求变的浪潮之中,看到了少数文学工作者严肃认真地思考,坚守纯正文学的立场。他们可以在政治高压之下,为文学保住清新;在商业挂帅之中,为文学保住纯净。在我所接触过的里面,香港如黄继持主编的《八方》,台北如尉天聪主编的《笔汇》、陈映真主编的《人间》,都是很好的例子。城市文学本来就比较多元多样。香港如此,台北如此,其他城市的华文文学亦当如此。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香港文学应当也像其他地区其他城市一样,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今天,至少面临两个共同的大挑战:一是文学阅读人口越来越少的问题,一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
文学阅读人口越来越少,不是泛指书刊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是指喜爱文学的读者比例少了。以前大家所说的大众文学,有人戏称,应该改为小众文学。很多读者已舍文学而就其他类别或实用性知识的读物。在台湾、香港、大陆的大书店中,很容易发觉文学类的柜架越来越少,而休闲娱乐以及实用性的读物则越来越多。就一般人而言,电影、音乐等艺术更容易提供耳目之娱,实用性的读物更容易切合生活的需求,计算机上网也更容易取得信息。这是目前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如何改进,如何因应,值得文学工作者观察、思考。
至于本土化和国际化,原是两种对立的概念,要调和推动,并非不可能,却实在不容易。就香港文学而言,什么是本土化?写香港的人情事物,就是本土化吗?这种题材何须提倡,相信大多数的香港作家,写的就是这些题材内容。那么本土化是指用方言来写作吗?用方言写作,自古有之,写得好,味道够,自然可以播诸人口,传诸后世;写得不够好,恐怕更不能吸引读者。什么是国际化?多写国际关心的事物,就是国际化吗?这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如果指的是把本地优秀的文学创作和新颖的文学论著,加以推介或翻译,互动交流,让别的地区了解,我个人是赞成的。也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和所谓本土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
五
两岸三地的文学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华文文学,早就有互动交流。举例来说,许地山生于台湾台南,但祖籍却是福建,甲午战争后,他迁回大陆,不但在北京燕京大学读过书,还到美、英等国留过学。1935年9月,他由胡适推荐到香港大学任教,对新文化的提倡及新文学的推毂,贡献不少。他所写的《落花生》等散文,为台湾大陆学生所习知,而其小说,如《铁血的鳃》,在香港发表后,不久即由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转载。这种互动交流,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就屡见不鲜。再举个例子,像台湾作家杨逵在日据时代曾用日文写了《送报夫》,1935年,胡风即曾将它译为中文。后来台湾光复了,杨逵还主编了一套中国文学丛书,用日文翻译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作品,推介给台湾、日本等地可以阅读日文的读者。他不但自己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与海外作家颇有往来。1949年他因在台中联合一些作家,公开反对台湾一切听命于美国,而被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所拘捕。与他有过往来的大陆画家黄永玉,立即在香港的《文艺生活》海外版第十七期,发表了一篇《记杨逵》的文字。⑧他对当时的台湾文坛及认识杨逵的经过,有颇为简明生动的描述。每次重读这篇文章,我都不禁为他们的患难交谊而深受感动。
从香港的角度来说,国共内战以后,台湾与大陆两岸对峙,断绝往来,数十年间,情势非常严峻,香港是两地唯一的中介。此前的华文文学,是以大陆为中心,此后的数十年间,因大陆正起文革热潮,而台湾发展经济,关心文化,因而华文文学一度以台北为重心。不管是心怀祖国,还是情系台湾,所有海外各地的华文爱好者,都不能不对当时的港、台另眼相看。
因此,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像杨松年)把世界华文文学,依地域分为好几块:大陆是一块,台、港、澳是一块,东南亚国家是一块,韩、日是一块,欧洲是一块,美、加是一块,随着新移民华人不断的增加,纽、澳又是新兴的一块。讨论问题的人曾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各地的华文文学,更容易了解彼此间流传、影响的情形。⑨而且大致认为台、港和大陆是最重要的地区,其他地区的文学走向,无不受其影响。因为今日的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是这几十年来从这些地区移民过去的,或者是在从事华文的写作道路上,与这些地区的文学界关系最为密切。
六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文明越来越发达,同时随着观念的改变,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切交流快,接触广,世界各地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小了,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交流也更为频繁便捷了。加上这十几年来,大陆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日益发达,全球的眼光又逐渐聚焦于此。王德威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结语说过:“香港的故事还没讲完,也完不了。”⑩事实上,香港如此,台湾与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关心香港文学的人,此时此刻,除了应该继续维持与台湾学界文坛的交流之外,也应该体认现实的各种变化,认真地思考:如何立足香港,关心华文,放眼世界。
收稿日期:2007-01-20
注释:
①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合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②参阅黄维梁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16-124页,陈子善《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谢晨光创作初探》一文。宏一按:谢晨光与侣伦等人,曾在1928年8月创刊的香港《伴侣》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过,谢氏在上海《幻洲》杂志发表小说,则始于1927年5月。又,同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小说家刘呐鸥,台湾台南人。早期台湾文学研究者亦不知其为台湾人。
③司马翎,政大新闻系毕业,曾服务于台北民族晚报社。其武侠小说如《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八表雄风》等等,皆善于刻画人性,描写情感的冲突与无奈。
④《胡适演讲集·三》,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版。
⑤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⑥参阅《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试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一文,第2-16页。又,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也说是有“自由性”、“通俗性”、“题材的平凡性”等,俱意见相近。
⑦卡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抒情与批评》、《西士福斯神话》等书。卢卡奇(Georg Lukae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审美文化》、《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书。他们的理论,对近几十年的台、港、大陆学者及作家,都有不小的影响。
⑧见《文艺生活》海外版1949年第17期。今收入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合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上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19-222页。又,从郑树森等人所编《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一书中,亦可看出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两岸三地直接间接的接触情况。
⑨见杨松年《世华文学论丛:世华散文评析序》。参阅《多元的交响——世华散文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版。杨氏序文中特别强调台湾学者在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如何受美华作者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他各地。而且他还说他“研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多年,深深感觉到全球华文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关起门来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不但不能全面了解有关文学的情况,也不能看到有关文学的特色和发展前景。”这些话都于我有戚戚焉,故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⑩据张美君等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41页。原文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