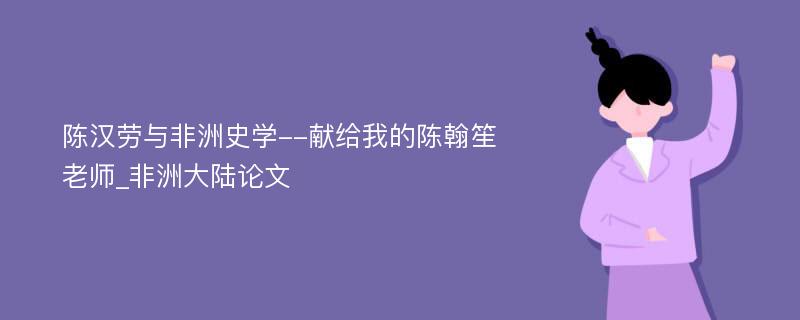
陈翰老与非洲史学——悼念我的老师陈翰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史学论文,我的老师论文,陈翰老论文,陈翰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翰老走了”。那几天朋友们相见时,经常带着无可奈何的惋惜心情,传递这个不幸 的消息。
近几个月,报刊上刊登纪念翰老的文章也比较多。翰老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专家。191 5年他18岁那年,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去美国求学,在美国读完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 922~1924年在德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学完后,他立即(192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 教,讲授欧洲史。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教授。在教书期间,他结识了中国最 伟大的教育家、学者蔡元培和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 认识到要救国,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必须首先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村经济。而要 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也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他参加了当时的北京革命运动。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 查。翰老自己创建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翰老全 身心地投入这个革命工作。当年他出国学习主要是想学习、了解西欧等国家经济发展的 历史,想从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找出中国前进的步伐。后来他改变了,认识到当时 最紧迫的问题是投身于革命运动。1927年,李大钊被害,翰老被迫出走苏联,后又去美 国、印度、南非。他在国外的30多年中,一面工作,一面从事实际的农村调查,并写出 大量文章宣传中国革命。1935年,他38岁时,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誉为中国 农村经济的权威学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家。1950年,他应周总理的召唤,回到祖国。据 统计,从1921年到1980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我仔细地阅读这 些文章,同时,我也不无遗憾地感到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翰 老,而80年代之后呢?我书架上的两大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历史卷,特别是他 倾注了大量血汗的约30余万字的非洲历史都是他在80年代后完成的(1979~1990年),我 书桌上的一叠《非洲史》书稿的详细写作提纲(共1.5万余字)也是翰老在80年代亲手写 成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中近十本是非洲历史小丛书,也是在80年代后 在翰老的关注与帮助下完成的。翰老在他老年时期对非洲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以 说是一位非洲史学家了。一个人的晚年一般是从65岁开始,但翰老从80岁至100岁间, 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非洲史的研究工作。
最初的几次会面
我最初见到翰老是在1978年,也是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年。我原单位是大公 报社,文革开始不久,大公报实行军管,报纸很快地被宣布停刊,职工停业学习。20世 纪60年代末,根据市委的通知,大公报被莫名其妙地撤销了,绝大部分人员被勒令下放 劳动。我在农村混了3年后回到北京。我原先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宣传,回到北 京后,我想方设法寻找一个符合我本人兴趣、专业的职业。经过反复折腾,我终于在19 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所,而翰老是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进所不久,大概在1978年底吧,所长通知我,说翰老要召见我,去他家谈谈。同时, 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说,这是我们这个所的规定,新来的研究室负责人都要去翰老家汇报 对研究工作的设想、计划等。我心想,这大概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面试”吧。我当然 满口答应,并约同室内的一个组长一齐前往。翰老当时住在东华门内的一个极为普通的 小四合院里。进门后经过一个小院子就到达他书房兼客厅的小屋了。我用手扣了几下门 ,翰老从玻璃窗内看见了我们,立即从书桌旁站起来,向我们招手。我进门后环视了一 下四周,房间的陈设极为简洁朴素,一张比较大的写字台和几个书柜,几张木椅。接着 翰老讲话了,他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吧。”
我立即向翰老伸手说:“您好。”他回答说“你好”。但他并没有跟我握手,他只是 用中国古老的见面礼拱起双手,向我作揖。我们坐下后,翰老说:“我们是初次见面吧 。”我犹豫一下说:“不,我见过您好多次了,只是每次您坐在台上,我坐在台下,您 不认识我,我认识您。”翰老笑了一笑,接着又问:“你最早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 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平起平坐的。”翰老问“什么时候?”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那是在1952年吧。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我在学校学习外 国历史,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国际部工作,研究和宣传国际问题。我们报社的头头 王芸生、李纯青把我带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我想目的是让我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会议 是在外交学会大厅内召开的,我们进入会议厅时,发现会议厅没有台上台下,大厅内摆 放着一大圆圈的椅子。椅子的背后还零星地放着几个凳子。参加会议的人大概有二三十 位,几乎都是老年人,都是有名望的资深学者,翰老就坐在那里。他们坐在前排,我自 觉地坐在后排。每次开会,至少半天,发言很踊跃。那天中午,外交学会还为我们准备 了丰盛的午餐。翰老问:“会议由谁主持?”我说:“杨刚。”我说杨刚是中国著名的 女记者,我佩服她。我记得当时会上发言最多的就是杨刚和罗隆基。他们对国际问题的 分析很精辟,头头是道。这时,翰老沉默了,他一言不语。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 既然认识杨刚,那么请你告诉我,杨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说:“我认为她是一个 好同志。”他又问:“她好在哪里?”我说:“她为人正派,讲话直率。”翰老不吭声 了。过了一阵子,他喃喃自语地说:“杨刚就是刚啊!”然后,慢慢地,他仰起了头。 这时我很快地发现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眶里缓缓地流下来了。为什么?我思索着。
我沉浸在回忆中,我的心飞了。过了一阵,我听见翰老同我所的那位同志在谈话。又 过了一会儿,翰老宣布,今天的会谈至此为止,以后再谈。然后,他对我说:“你今天 发言很少,下次,请准备一下,带着你个人的科研计划和全室的科研计划来。”
大概在1979年初,翰老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汇报工作。
我带了我写好的研究室内3个小组的《工作计划》和我自己的《工作规划》去了翰老家 。翰老粗粗地翻阅了一下,就把这些规划放进他桌上的卷宗里,同时问我:“你什么时 候开始研究非洲问题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是自学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历 史,但大学的史学课目里没有非洲史。我说我对非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这可能跟我上 的学校有关。我很小就在教会学校念书,因此很喜欢音乐。抗战时,日本鬼子侵占了我 的家乡杭州,我和母亲从日本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当时我只有12岁)。在朋友们的帮助 下,经过长途跋涉,极其艰难地逃到了当时的大后方——成都。在路上,我尝到了作为 亡国奴的痛苦。我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到成都后,我不久进入了最老的两所教 会中学和大学。在课后,我和我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唱歌。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就 是“松花江上”和“黄河大合唱”。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来中国后,他演唱中的《老人河 》和《老黑奴》又把我们的心吸引住了。可是,有一点是:我不知道黑人为什么生活得 这么苦;为什么他们去美国当奴隶!这个问题一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召开 前夕才明白。当时为了准备万隆会议的召开,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 愿意研究非洲问题,因为我原来是研究英国问题的。而英国是非洲最大的殖民帝国。我 满口答应,我说我对非洲不了解,我脑子里有很多问题希望得到解决。就这样,我怀着 喜悦的心情,到处寻找有关非洲的历史资料。那时国内很少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 写的非洲史的书,只有两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书。我又赶到北京图书馆里寻找。北图有 几本关于非洲的外文书。其中特别是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的书,它成了我研究非洲的 启蒙老师。我把这些书借回家来,日夜攻读,因此,到万隆会议开会时,我终于能在报 上连续发表了四五篇介绍非洲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1956年,我又赶写了一本《从黑夜 走向黎明的非洲》的小书。但好景不常,从1957年开始,国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 运动,我毫无例外地被卷进去了。但我对非洲的兴趣没有减退,只要有时间,我还是关 心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翰老听完后,马上对我说:我也是从50年代开始关心非洲,研究非洲的。他说,我关 心和同情世界上所有不幸的人。我过去首先关心的是我们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况,主要 表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太苦了,以后视野扩大了,我又关心我们的邻国——俄国和印度 等国。当时,非洲还处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整个大陆一直被封闭着,一片黑暗 ,内部情况无人知晓。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北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首先发出要求 独立的怒吼声,万隆会议后,黑非洲也行动起来了,黑非洲的文明古国加纳于1957年宣 布了独立。非洲到处都发生着请愿、示威、罢工以及大规模游击战争的行动,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非洲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蹂躏是史无前例的,现在他们 站起来了,我同情非洲人民,对此感到惊喜。从这以后,我也开始关注非洲独立运动的 发展,并开始寻找有关非洲的资料,从事非洲历史的研究。他还告诉我,他已收集了不 少有关非洲的资料,在文革最混乱的时代,他被下放,被囚禁,而他还在思索着要写一 本非洲史。
翰老已经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人了,他立志要写一本非洲史,这在我头脑里是一个头 条新闻。
翰老与中国大百科非洲史卷
一场考试 大概在1979年底,我访问法国回来不久,翰老打电话通知我,说要跟我谈 谈工作。第二天,我奉命前往。见了翰老,翰老劈头就说:“我今天要考考你。”“考 什么呢?”我心想。我已50多岁的人了,还要考试!可转眼又想,我从小学读到大学,我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考试,考就考吧。我对翰老说:考吧。翰老从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 英文《中国妇女》杂志,对我说:“请你把它的第一篇文章念给我听,然后翻译成中文 。”我说:“好。”我按着翰老的吩咐,读了一遍,又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翰老点点头 说,还没有考完呢。接着又拿着一份用信封装着的稿件,对我说:“这是一家杂志请我 审阅的稿件,请你看看,能否采用。”我看完说:这篇稿件不能直接采用,需要修改后 才能用。翰老问:“为什么?”我说有的观点不对头,我谈了我的看法。翰老听后说: “好的,请你给该杂志写封回信,把你刚才对这份稿件的意见写上。我马上写了回信, 请翰老过目。翰老说不用看了,你给我念一遍。我念了,翰老就在信的结尾签上了他的 名字。最后,翰老对我说,还有一项任务是:你回去到图书馆找找英国《大百科全书》 和美国《百科全书》中关于埃及这个国家的条目是怎么安排的,比较这两本书在这方面 的异同和它们的优缺点,半个月后再向我汇报。
听了翰老的吩咐,我很纳闷:我是搞科研的,正在研究非洲奴隶贸易问题,怎么又让 我搞《百科》。回家后的第三天,中国大百科出版社负责外国史的一位女同志来我家了 。她告诉我她们正在筹备出版中国第一本大百科全书。她说中央对这本书很重视,她相 信这本书出版后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它也是世界各大学、各学术单位和图书馆的必 备书。她并告诉我,目前,他们已拟定了全书的负责人,主任是胡乔木。副主任有好几 位,陈翰老是其中之一。目前正在考虑各学科编辑委员会负责人人选。学科负责人的挑 选难度比较大,他应该享有中外著名学者的声誉。陈翰老知识渊博,是中外知名的学者 ,是适当的人选。我们一再请他担任一两个学科的编委负责人,但他说他老了,他最多 担任一个,非洲历史。他还提出一个要求,说他老了,眼睛又看不见,需要一个助手帮 他处理日常事务。大百科出版社的负责人同意翰老的请求,并要他自己提出认为合适的 人选。出版社的这位同志对我说:“翰老点了你的名,他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并让 出版社的同志来我家征求意见。我听了后感到很为难。我告诉她:我来所不久,目前, 我负责一个研究室的工作,还要带两位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我哪里有时间兼搞《百 科》。她要我不要小看了《百科》,说它是国家级科研规划的组成部分,翰老是学贯中 西的大学者,“你当他的助手,拜他为老师,肯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你来讲是个难 得的机会啊”。我仍然摇摇头,请她另请高明。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谁也说不服谁。 最后她说,翰老已经表明,如果我执意不肯,他也不当非洲历史的主编,因为他老了, 视力不好,一个人担当不起啊。她还告诉我说,如果我拒绝,她就不走,因为她无法向 上级交待,我们的非洲历史书不能没有主编。无奈,我只好说,我考虑一下吧,请你也 向我们的所长汇报一下。就这样,我被拉进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卷非洲部分的编辑工作 。我被列为非洲史的副主编,翰老是主编。
“我不当挂名主编” 编辑《百科》,对我和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都是陌生 的工作。1979年开始,我们参与编写《百科》的人,首先就是要学习。这时,中国大百 科编辑部已经为我们编印了很多材料,主要是如何编写《百科》,翻译了国外大百科不 同条目的书写样本,等等。同时还列出时间讨论研究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的框架、条目 、字数的分配,作者队伍的建立。总之,事情很多。我感到有点棘手。这时,翰老对我 说:“你不用担心。我是主编,你是我的助手,我请你帮忙,但我绝不当挂名主编,我 们可以有些分工,有困难,我们可以协商解决。”接着,他提出分工的方案,说凡是重 要的集体讨论问题的会议,他力争参加。重要条目的审定,一般采取三读全稿,(1)即 首先由我看原稿,提出意见,即:可以采用或需要修改,或重新改写。(2)请其他副主 编和编写小组成员一起讨论,提出共同的意见。(3)由翰老最后裁定。翰老必须自己审 读原稿(院里当时为翰老安排了两位中、英文的秘书,专为翰老阅读文件,书写信件)。 翰老还告诉我他自己编书、写书的几条原则:(1)最重要的是精选作者,要采取“伯乐 识马”的方法,不要光看外表,光凭简历或者凭人推荐,要经过全面的考察,选择“良 马”。(2)撰写外国历史文章的人,还必须掌握外语,还要有著作成果。(3)文章采用的 资料必须以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为主。我认为翰老定下的这3条原则是保证质量的基 本条件,我表示我将努力去执行。
翰老自己确实按照分工的程序去做。我记得,从1979年大百科外国历史卷(共3卷,300 余万字)正式上马后,大概在头三年的暑假,参加全卷的主编、副主编及分卷的正副主 编及编写组成员,由大百科出版社安排,利用暑假,去西山半腰的兄弟楼,集中讨论外 国历史卷每个国家的框架、条目、分类、字数,等等。每一次翰老都如约参加。兄弟楼 在半山腰。因此,为了到达目的地,80多岁高龄的翰老总要步行一段路程。在审读条目 中,我和其他同志有时遇到不同意见,相互争论不休时,我们也采取集体方式去翰老家 ,找翰老,各人在翰老面前陈诉自己的意见,倾听翰老的意见。我的感觉讨论是愉快的 ,问题大多能得到解决。
一本未完成的非洲史书稿
《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两卷本到1990年出版了。大概在1987年,条目基本已撰写 完毕。从1979年到1987年,特别在头两三年,我大概每个月至少要去翰老家两次汇报工 作。1988年秋,翰老告诉我,他从刊物上见到我写的关于奴隶贸易的文章。他认为这是 一个很有意义、值得研究的题目。同时,他建议我再写一篇文章,题目,他说他已经想 好了,是《大批黑人是怎样到达美洲的》。我告诉翰老,我应邀即将访问美国,过几个 月就回来,这件事等我回来后再谈吧。他说,这很好,你有机会在美国,多收集一些这 方面的材料吧。我答应,我说我一定利用这个时机多收集一些我所要的有关黑非洲的材 料。1989年春,我回来后很快去访问翰老。我向翰老汇报访美情况。翰老听了一小会儿 ,就说:“先讲到这里,我打算把几位最近访美回来的同志一齐召集到我家,开一个座 谈会。”说完话,他进屋拿了两份稿件交给了我。他说,一份是关于《大批黑人怎样到 达美洲》一稿的提纲,他已粗拟了一份,说它可以作为我写作时的参考。第二份是厚厚 的一叠稿纸,外面用一个旧信封装着,信封上写着:这是交给吴秉真同志的。他指着信 封说,这是他在文革中写下的,他当时计划写一本非洲历史,但文革中生活很动荡,他 被下放、被囚禁。因此,他只写了一份详细提纲(约1.5万字)。改革开放后,工作又很 忙了,坐下来写稿的时间不多,目前,他老了,视力更差了,写书、看材料全靠别人是 很困难的,他希望我能把它完成。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完成这项任务,但不可能很快完 成。我回国后,我们所根据院的规定,已经给我办了退休证,但由于我手头任务多,因 此,所里又给我办了返聘证。这样,我就得照常上班、工作。工作很忙。翰老点头表示 同意。
最后的一见
大约在2001年春节前后,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翰老,翰老的妹妹素雅说,翰老病了 ,他正在床上呻吟,你听听。素雅把耳机移动一下,我就听到翰老痛苦的呻吟声:啊唷 ,啊唷!……我问为什么不送医院?素雅说,他身上的病太多了,但他一边叫,一边还能 吃饭,有时还能起床走走。我问:我能来看看翰老吗?她说:等晚上我问问我女儿再说( 她女儿童大夫全面照顾翰老的日常生活)。晚上,我又打电话给童大夫,她回答说:可 以。约我第二天下午3时去他家。第二天,我敲门进去后就坐在他的书房里,不久,我 听见翰老从卧室里往书房走的声音,这声音很奇怪,是有节奏的跳跃声:一、二、三, 吴秉真;一、二、三,吴秉真。当他走进书房时,我一看,原来翰老的左右两旁各有一 位阿姨搀扶着,而翰老是每走一步就跳一下。当他走进书房前,家人已经告诉他,来的 客人是吴秉真,因此他嘴里就喊着我的名字。我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发现翰老有了一 些比较大的变化。他的身材变矮小了,人瘦了一点,微微地驼着背。当他伸手跟我握手 时(他已不再拱手了),我发现他的手背上全是黑斑。讲话时有点孩子气。他坐下后,我 问:翰老,您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你,你是吴秉真,是个女同志。接着他问我目前 在干什么工作。我说我依然在忙着赶写有关非洲的文章,您交给我的两本书,我还不能 交卷,因为我现在的视力也不好,工作速度很慢。当我提到非洲这几个字时,他记忆之 门似乎打开了。他忙着问我:你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吗?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然后他停顿了 一阵,对我说:“你要知道,我有生之年,是在等着这两本书的出版呢。”听他这么讲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翰老,对不起,我一定努力去完成。”翰老是病人,我不宜 多讲话,很快地向他告别。
2002年,大概在3月初,我打电话给翰老,想给翰老拜个晚年。翰老妹妹素雅在电话中 告诉我说翰老于前几天(2月23日)送进协和医院了。她说他目前发着烧,血压也低,不 能不住院。说他过去眼睛看不见,现在耳朵也听不清了,过去吃饭由阿姨喂着吃,现在 只能用鼻饲,同时,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掌握了。我问她翰老在医院的病房号码,她告诉 了我,并一再叮嘱:不用去看他了,因为他基本上已失去记忆,什么人也不认识了。
今年3月23日,我接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寄来的讣告,说翰老已于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翰老以108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大概在我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之中是极为难 得的了,而他从事工作之久,更是罕见的。他在晚年仍然埋头工作,以一颗火热的心投 入工作,投入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写作,直到他百岁以后死神来敲他的门为止。在他30 多岁时,他曾说过:“假如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 ,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旨趣。”(注:见《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 3年1月1日)。)他的梦想可以说是实现了,他为革命,为学术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种 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