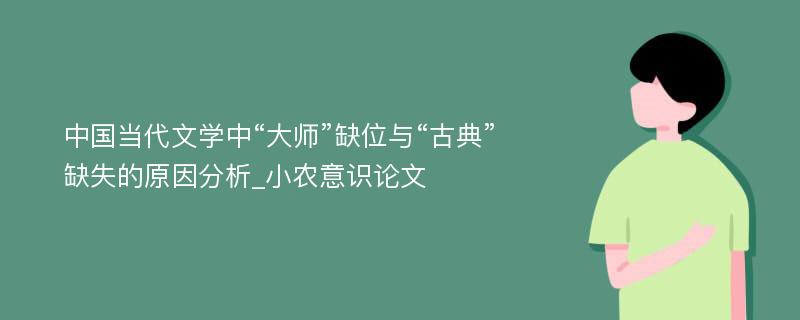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经典”匮乏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匮乏论文,中国论文,大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4-0036-04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大师”的缺席和“经典”的匮乏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针对造成这种“不争事实”的原因,评论家吴炫先生诊断出的结论是“思想的贫困”、“穿越意识的淡薄”。而我的结论则是“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贵族精神”阙如。而无论“小农意识”、“市民气质”还是“贵族精神”都与出身有关,都与家族、血缘有关。也就是说,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生存境界作一些遗传和变异的生物学分析还是必要的。出身虽不能决定人的一切,但一些根深蒂固的关乎人性的东西,也并不是在后天的短时间内就能修炼成的(比如道德和文化)。血缘、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几乎是多位一体的,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多半是因为我们本身大都就生长在一个平均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对贵族的仇视不但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广泛的共鸣性,很难超越自己的出身去接受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一、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太重,这是影响中国当代作家走向“大师”境界的第一堵墙。所谓小农意识,是指根植于小农经济土壤之上的一种极容易满足现状的思维观念。封闭性、保守性和狭隘性是其显著特征。中国当代作家——无论是意识里还是潜意识里——普遍地具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即便是被看好可以靠拢“大师”的几位也是这样。这是妨碍他们走向“大师”境界的几乎无法根除的痼疾,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
贾平凹的出身之地是关中奇穷的商州,其出身之家虽然是有点文墨(其父是小学教师),但仍然没有超越贫穷。如此的出身,如此的处境,却没有使贾平凹产生一丁点批判意识,相反“土”与“穷”、“原始”和“丑陋”却成了其反复渲染甚至炫耀的审美对象。对真正“粗”、“俗”的咀嚼和品咂,对纯粹“野”、“蛮”的眷顾和留恋,对所谓“淳”、“朴”的把玩和欣赏可谓深入骨髓。贾氏这种对“故土”的一腔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而言,决不能让这种“深情”老是感动自己,他应当提防这种“深情”会不会成为他抵达至高境界的障碍。《废都》中的庄之蝶虽然不能简单机械地等同于贾平凹,但庄之蝶的人生历程活脱脱是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打入了城市,步入了社会上层,实现了其人生价值的贾平凹;书中虽未明显写到庄之蝶的出身,但我敢断言,这种没有一丁点道德底线约束的“放荡”,绝不是一个道德和文明的因子已渗入骨髓的高贵者所为。
中国当代作家“小农意识”太重的原因是很显然的。第一,出身使然。中国当代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贫寒的农家,正所谓“根正苗红”。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都是以农业立国的社会里,“贵族”本来就是稀有之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极少数”、“一小撮”,再加之一次次的军事暴力冲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消灭了“贵族”产生的土壤。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士大夫文化”被彻底地扫荡进历史的垃圾箱,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是的,“苦中苦”固然砥砺出了不少“人上人”,但“出身贫寒”给人所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在幼年,尤其是在灵魂深处。对那些经历了“十年寒窗”,身心俱疲地走向“天子堂”的“田舍郎”们,单单是经由后天习得的道德和文化水准,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估计过高的。因为,十年的痛苦熬煎足以彻底败坏一个读书青年的全部朴素本质。第二,政治文化的推波助澜。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大陆的文艺界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和国的成立更是使这种“变化”变本加厉。所谓“十七年文学”都剩些什么?我想毋庸我在此多嘴饶舌。在一个把诸如高玉宝、赵树理、浩然等作为典型推崇的文坛上,文学艺术的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是当1970年代“朦胧诗”“崛起”的时候,那么多的中国作家、评论家竟因“懂”与“不懂”展开了笔战。在这种政治文化对“小农意识”的极端推崇、导引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创业史》、《艳阳天》式的作品堂皇地走进了文学史,成了“红色经典”。第三,对“经典”的“误识”与“误读”。中国当代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崛起的时候,正是饥渴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大规模引进所谓西方“经典”的时候,且不说译介者本身的水平直接限制着他们对“经典”的认识水平,单单从接受者来看,大都对“经典”存在着极大的误读。张贤亮之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莫言之于福克纳,寻根作家之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他们大都停留在形似的境界,神似都没有达到,更遑论什么超越了。比如莫言的“嗜痂成癖”,“嗜酷成病”,实在没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可供诠释。在这一点上他连比他小几岁的余华都不如。对西方“经典”的误读似乎还可以理解,毕竟隔了一层,但对本土“经典”也会误读,则似乎有点不应该。比如“二张”对鲁迅的误读。老实说,中国当代作家大都不缺少才华,只是渗透于血缘的“小农意识”使他们很难走向“大师”的境界。什么时候中国当代作家能告别刘姥姥,什么时候中国当代作家也就向“大师”迈近了一大步。
二、小资情调
“小资情调”太浓,这是影响中国当代作家走向“大师”境界的第二堵墙。先来看什么是“小资”。按照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的解释,“‘小资’最初是文革前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批判性称谓,它曾经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三等级’,而现在则成了准中产阶级或预备役中产阶级的临时代码。它还包含新滥情主义、自恋状态下的感伤主义、小布尔乔亚美学、都市怀旧主义、青春期的愤世嫉俗(‘愤青’)等各种当下流行的精神倾向,他们在网络原创叙事中卷土重来,犹如一场规模盛大的流行感冒”。那么小资情调则是如上各种“主义”者们领导的一种潮流,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它首先指一种个人的内心渴望,其次,夹带着一系列的物质包装,是追赶时髦的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品牌之一,模仿性、流行性和肤浅性是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不幸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很大一部分感染上了这种“流行性感冒”式的“小资情调”。
先来看“小资”们展现其“情调”的阵地。倘论阵地,网络自然是其首选,但中国大陆的网民仍然是少数,报纸杂志在大众阅读当中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读者》惊人的发行量也不能不被“小资”们看好。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厌其烦始终如一地勾兑着感情,设计着智慧,拷贝着思想,拼贴着幽默,大把大把地赚取着“感情”、“智慧”和“思想”的懒汉们的钞票和眼泪。
再来看“小资情调”制造者的队伍构成。朱大可先生开列的名单有:琼瑶、三毛、亦舒、金庸、古龙、王安忆、陈丹燕、各色“宝贝”。据我看来,还应当包含刘墉、汪国真以及步余秋雨后尘的一些散文家。他们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拒绝痛苦,拒绝信仰,拒绝深度,拒绝悲剧。
最后还得看一下酝酿“小资情调”的典型文本。首屈一指的当推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已经流行了十多年了。据说在它的母国曾经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那就送她一本《挪威的森林》。再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部作品中经由他所重新阐释的“媚俗”,竟然真的成了中国当代“小资”们酝酿“情调”的道具。再就是《情人》等一大批流行过或正在流行着的所谓“经典”。在一个“小资情调”泛滥的中国当代文坛上,真正的“大师”只能是欲哭无泪,真正的“经典”也是被模仿得面目全非,被解构得支离破碎。
造成今天这种“小资情调”泛滥的原因不外如下几点:第一,仍然是出身。小资文艺家们的出身大都是大中城市的小市民家庭,或者说是农村中“先富起来”的那类家庭。通常生活较为宽裕,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偏下的水平。吃饱穿暖早已不成问题,因此就要追求精神、生活上的一种水平、格调、品位。这种“小市民”、“小富农”的出身便决定了他们文化水平的“含墨量”:不可能太多,也不可能空白。第二,经济文化的耳濡目染。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文化浪潮的裹卷下,农村青年打入城市的途径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升学”、“打工”、“参军提干”等,彻底告别了粗鄙的农村文明。城市青年则在通过父辈或自己的努力赚得足够的钞票后开始了对时尚的追求:“卡拉OK”、“MTV”、“摇滚乐”、“扮靓”、“扮酷”、“追星”、“另类”……总之,在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一个真正的“有闲”阶层业已诞生。“有闲”,这是“小资”们玩“情调”的最必要的条件。第三,文艺思潮自身的反拨。“革命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差不多都是关乎历史、文化的“宏大叙事”,新一代的文艺家们感觉到了这种“宏大叙事”的疲惫,断然放弃了这种沉重的思考。再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国门之外的各种非理性思潮的大规模涌入,使得“小资”们似乎更找到了理论支撑。
必须承认,“小资”们仍然是很有才华的,有时候还很深刻,但是,基于“才华”之上的“深刻”和基于“思想”之上的“深刻”毕竟是两回事。更何况“小资”身份使得他们对自我有着超常的自恋,以至于成为一种“情结”,指望他们成为“大师”更是妄想。
三、贵族精神
如果说:“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是影响中国当代作家走向“大师”境界的两堵“墙”,那么“贵族精神”的阙如,则是影响中国当代作家走向“大师”境界的致命伤。“贵族”,英文的书写是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总之,都是一种褒扬。而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对“贵族”的解释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享有经济、政治特权的阶层,直接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颇浓的说法,完全是贬义的。无论东西方贵族在命名和传统渊源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在“贵族精神”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比如他们都具有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人格尊严、人性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道德性、创造性和审美性是其重要特征。
中国当代作家,“贵族精神”严重阙如,其明证就是“贵族精神”的反面他们都具备,而且是非常充分,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金钱支撑起一个个高昂的头颅;善良被看成是怯懦,正直被当成无能,诚信被视为迂腐……
先从创作界来看,看看我们这些文艺家们的笔下都活跃着些什么样的人物,也就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指向。中央电视台近些年来所播放的电视剧就很能说明问题:宫廷帝王戏一部接着一部,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比如几大“王朝”剧。问题不是这些帝王剧不能写、不能演,而是我们的文艺家怎样写、怎样演?他们到底想给老百姓提供些什么?他们把歌咏、赞叹和景仰的目标投向了刘邦、曹操、武则天、韦小宝、薛宝钗;他们揶揄、调侃和嘲笑的对象是项羽、刘备、堂吉·诃德甚至鲁迅先生。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能够带来欲望满足的“性事”;他们怀疑消解的是能够导引灵魂上升的“爱情”……
再从评论界来看,看看这些所谓的评论家都“吹捧”些什么,“绞杀”些什么,也就大致可以看出这些评论家们的“原则”、“标准”和“趣味”。笔者曾经对某一年的《文艺报》做过粗略的统计,吹捧文章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那么久的规模盛大的鼓掌喝彩声中,“大师”仍然缺席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与《文艺报》相比,民间色彩相对较为浓厚一些的《文学自由谈》,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打着“自由谈”的招牌实际上已经沦为了泼妇骂街的场所。一“捧”一“骂”,骨子里所奉行的原则都是“利益”或者说是“变相的利益”,哥们意气、圈圈垛垛,一派江湖相。总之,在这两份据说是“权威”、“核心”的报刊上,你很难看到超越于个人利益恩怨之上,眼界高远的、与人为善的学理性色彩强烈的评论。
那么,这种“贵族精神的阙如”的原因在那里呢?第一,还是得从出身上考究。茨威格在1928年祝高尔基60寿辰的致敬词中曾经这样写道:俄罗斯文学之父亚历山大·普希金出身于贵族,列夫·托尔斯泰出身于古老的伯爵家族,屠格涅夫是庄园主,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官吏的儿子,但也是高贵的。这些人无一不是高贵的……只有他们把俄国、俄国财富、俄国民族、俄国力量和俄国精神展现在世界面前。而中国呢?鲁迅之后,中国作家的“贵族精神”便“随风而逝”。第二,“中国士大夫文化”与“中国流氓无产者文化”长期斗争,而且总是“中国流氓无产者文化”占上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可供辩论的命题,诸如“道与术”、“德与才”、“名与实”、“体与用”等,其实都可归结为上述两大文化的斗争。“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神圣的道德律令”,这是以“道”、“德”、“名”、“体”为本位的“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真诚供奉;高蹈而虚空,鼠目寸光,实用主义盛行,这是以“术”、“才”、“实”、“用”为本位的中国流氓无产者文化的真诚供奉,实在而可行。斗争的结果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贵族无用,非但无用,而且反动”。第三,世纪末颓废思潮的深刻影响。历史也如生命,也如四季,每到一个百年的关口,就好象到了一个大限,死亡的气息异常浓厚,因而人类精神格外地颓废,“寻找精神家园”的呐喊也格外地响亮。19世纪末,正是鉴于人类精神的普遍粗鄙化,尼采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了“上帝死了”,追求一种“超人意志”。其实“超人意志”不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吗?20世纪末,尽管人类的生存境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类的精神境界并没有多少提升。“后现代主义”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思潮,无论它是否到了“后工业社会”。在这种“一切都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思潮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坛走向“欲望化”、“粗鄙化”和“肤浅化”也是“大势所趋”。
综上看来,“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和“贵族精神”阙如成了制约着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家抵达“大师”境界的三大痼疾。三大痼疾都与家族、血缘有关,都与出身有关,这样强调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平民”当中不也同样能够产生“大师”吗?是的,这世界的确也有不少“平民大师”,但这种“平民大师”与我所强调的“贵族精神”并不矛盾,“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与“贵族阶级”相联系,也不必然地与等级社会相联系,相反,倒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关系密切。因为也只有在这种“公民社会”/“市民社会”里,公平竞争才成为可能,起跑线的整齐划一才能使强者脱颖而出。这些真正靠游戏规则的公平,靠个人的奋斗而走向高层的作家,也就真正具备了一颗“平常心”,离“贵族精神”也就不远了。说“平常心”离“贵族精神”不远了看似矛盾,其实统一。因为,真正的“贵族精神”其实也就是基于“平常心”之上的悲悯情怀。“贵族精神”与“平民意识”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贵族”虽然不等于“平民”,但“贵族精神”与“平民意识”却可相通。因此“贵族精神的阙如”也可以置换为“平民意识的阙如”。如此看来,我所强调的“贵族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超越意识”,与出身并无必然联系,只不过“贵族”出身较之“平民”出身拥有这种“超越意识”的空间更大,几率更高,可能性更大,因为毕竟是首先“拥有”了然后才可以谈“超越”。这也是我再三强调出身的原因之所在。
标签:小农意识论文; 小资情调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贵族气质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