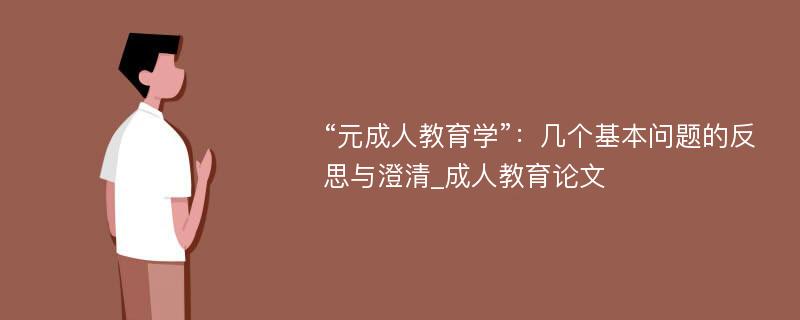
“元成人教育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反思与澄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教育学论文,成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06)04-0005-03
一、“元成人教育学”的涵义
20世纪70年代初“元教育理论”(meta-theory of education)一词正式出现。作为一种新兴的元理论体系,目前正在孕育发展中。“元”的西文为“meta-”,具有“在……之后”、“超越”之意。它与某一学科名称连用,通常表示这一学科的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它具体包含两层涵义:其一,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该词源于“metaphysics”。后人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的著作称为“metaphysics”。它探讨的是超经验的、世界本体的终极原理,与我国古代的“道”的学问相近;其二,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
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首次提出“元理论”概念,并把数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数学哲学研究,这种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即为“元数学”。随后,“元物理学”、“元化学”等各种元学科相继兴起。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在元教育 (meta-theory of education)或元教育学(meta- pedagogy)的概念下从事教育学认识论的探讨和建构工作。其中德国教育学家布雷岑卡(Brezinka,W.)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元教育理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基础导论》是最早的以体系状态呈现的“元教育学”。[1](P5-16)
本文所谓的“元成人教育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系状态”或“学科性质”的元理论。因为元教育理论是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行为为对象进行再研究而形成的教育理论的体系,而我国的成人教育研究相对薄弱与滞后,且学科体系正在构建中,所以现阶段还不可能出现“学科”意义上的“元成人教育学”。本文借用“元成人教育学”这一概念的初衷旨在选择一种研究的视角或方法,尝试从成人教育理论认识论层面上反思、澄清成人教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期对成人教育理论研究有所促进与帮助。
二、成人教育研究中“真问题”的反思与澄清
吴康宁认为,“教育研究者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可从教育理论发展或教育实践改善是否迫切需要及研究者本人有无研究的欲望和热情这两个维度大致区分为‘异己的问题’、‘私己的问题’、‘炮制的问题’及‘联通的问题’四种类型。”[2]“联通的问题”即本文所谓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真问题”,是既能有助于教育理论的发展,又有利于理论主体科研素养的培植与发展的问题;只满足上述一个条件的问题分别为“异己的问题”、“私己的问题”以及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问题为“炮制的问题”。在本文中后三类问题通称为“假问题”。
只有“真问题”才是教育科研和教育实践过程中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理论主体自身生命运动的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有的成人教育理论主体没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出于“非本真”研究目的,选择了“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然后遵循着写文章(撰专著)“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计算成果”评职称这一模式运转。这样出来的科研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往往大打折扣,而且也很难体现理论主体的精神特性和人文气质;同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理论主体很难体验生命的价值,更不能有意识或主动地把科研作为自己生活、生命的有机构成部分,也较难达到培养理论主体的科研素养和建设理论主体队伍的目的。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学界也有多位科研能力和学术声望不凡的俊杰之士,但是成人教育理论主体整体较薄弱且还没有形成结构合理、分工科学的研究群体。同时,我国成人教育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给出解答。鉴于以上分析,成人教育理论主体把“真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或主攻方向是成人教育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真问题”从何而来呢?一般认为有三个来源:其一,成人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实践主体各因素自身的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实践客体各因素自身的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二,成人教育理论形式,主要涉及成人教育理论形式中载体各因素自身的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媒体各因素自身的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载体与媒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三,成人教育实践与成人教育理论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主体、客体、载体、媒体各自自身的问题具有多样性、交互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以及它们自身之间的“复合——裂变”,该领域的问题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交互性和复杂性。
三、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背离的反思与澄清
在理论研究上,目前成人教育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之间在观念、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严重背离,主要表现为:其一,理论主体多以“纯理论演绎”为其研究取向。他们多以普教理论或国外成人教育理论为模本,演绎出所谓的“成人教育理论体系”,看似科学性、创新性较强,实则适切性较差;其二,实践主体多以“经验性总结”为其研究取向。他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特点一般为:选题追“热”化,探究表面化,结论简单化,效用短期化;其三,“无依据的预设”。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预设或假设——一种理论一旦出现,就认定其必然是正确的,立即聚焦于理论对实践的导向功能,而恰恰忽视了理论应首先接受实践的检验与拷问,这一假设显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追问:是什么导致两主体的背离呢?笔者认为:除了两主体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现实的“刚性教育结构的制度化”是导致两主体背离的症结所在。正是这种刚性教育结构的制度化,使两主体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完成不同的任务,受不同的“群体规范”或“游戏规则”的约束,并且两主体已习惯于各自的“群体规范”或“游戏规则”。
继续追问:那么怎样走出两主体背离的窘境呢?一般思路是,理论主体实践化与实践主体理论化,这样真的可行吗?现实的成人教育处于一定的文化范式之中,理论主体深入实践中,研究显性文化材料,体验隐形文化特质,进而使实践中的“缄默因素”得以表达,使原理论上升到理论形态。但这仅仅是应然而已,而实然为:理论主体受主体与社会建制、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奖励体系、科研成果的鉴定与评审体系的限制,理论主体实践化终难成为现实。那么,实践主体理论化可行吗?显然也面临着与理论主体实践化同样的制度化阻隔,同时考虑实践主体自身理论素养的局限性,实践主体理论化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可见,只有破除“刚性教育结构的制度化”这一阻隔,重构成人教育科研制度,建立两主体的联合体,同时建立富有成效的评价系统,进而促使联合体形成共同的“群体规范”或“游戏规则”,才能真正走出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背离的窘境。
四、学科体系建构中“目的与目标”之别的反思与澄清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指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和连接概念的判断,通过推理、论证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逻辑系统。尽管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构建已取得显著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成人教育学还仅是教育学园地中较为“幼稚”的一门学科,还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尚待澄清。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成人教育研究的目的:一是构建学科体系;二是指导成人教育实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商榷之处:构建学科体系只能是目标,而不可能是目的。
其一,某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发展路线通常为:一般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学科体系建构。显而易见,体系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是研究的一个发展阶段;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研究的一种载体。如果说体系构建是目的,必然导致研究目的是研究的悖论。加之,由辩证唯物认识论可知,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实践。显然,不能把学科体系建构误认为研究目的。
其二,任何学科体系结构一旦确立,就有很大的惰性和维护自身原来结构完整性的天然倾向,这必然与“鲜活”的成人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新知识、新理论发展冲突。在此背景下,理论主体研究兴趣与方向必然由体系建构转向解构,在“建构——解构——建构”这一循环过程中,理论主体不断丰富着成人教育学的内涵、拓展着成人教育学的外延,进而为实践指引发展方向和提供价值判断的标准。可见,体系构建是理论研究的阶段目标而非目的。
成人教育理论主体在关注学科体系的原创性、完整性、合理性和逻辑性之前,应首先确认体系建构是目标而非目的这一基本认识。这关涉到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问题。每一时空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应该是柔性的而非刚性的,应有持久的亲和力,以及在体系的每一节点上都应预设新知识、新观点的接口和预设自我更新乃至“自我革命”的机制。
五、理性批判缺失的反思与澄清
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相比较,成人教育理论主体具有一些显著的优点:团结协作,任劳任怨,不计名利,自强不息,等等。例如,在团结协作方面,各级成人教育科研机构及个体科研人员经常进行科研协作,无论是同专业纵向、横向的“强强联合”,还是跨行业、跨专业的“互补协作”,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开发聚合科研人才。当前成人教育理论主体之间并不缺乏相互理解、沟通、交流协作和相互欣赏的雅量,也不缺少信念上的融通和共鸣,但缺失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理论研究氛围,特别是理性批判。
理性批判的功能主要包括:其一,扬弃功能。理性批判不仅要说明对象理论所能说明的一切,而且还要能够解释该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说明的事实、现象或问题,这是批判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其二,评价功能。任何教育理论都是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统一体,所以评价不仅要考虑理论的结构和功能,而且还要考虑历史方面的因素。
下面是其他教育领域理性批判的实例:
有位学者对近几十年的中国教育学理论作分析时指出:教育理论(以《教育学》为例)在其成果的实现过程中,还存在着“为评职称突击编写的所谓‘复印式’教育学;热衷外延轻视内涵,套用新概念叙述旧话语的所谓‘装满式’教育学;借权行事利用行政手段与‘红头’文件发行所谓‘树碑式’教育学;‘跨校舍股’自编自用短平快的所谓‘同仁式’教育学;以实利为目的的编写的所谓‘创收式’教育学。”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也将这类“教育学著作”称为“教育理论”的话,那么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意义和魅力。[3]
还有,吴康宁教授与谢维和教授皆是教育社会学的知名学者,但吴康宁能就某个问题公开同谢维和进行商榷。[4]
像这样中肯的、尖锐的理性批判以及公开的“商榷”层次的探讨,在“天下成教是一家”的理论界是少有的。理性批判是自觉的、敏锐的、艰难的、螺旋式上升的。任何教育理论内涵的充实和提高都是在批判中完成的。所以成人教育理论主体开展“商榷”层次的理性批判对理论发展及主体自身科研素质的提高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可见,成人教育理论主体应有意识的开展理性批判,同时相关机构或部门也应为理性批判创造必要的条件。
成人教育理论主体之间开展理性批判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批判要客观、全面、公正,力戒固执和偏见,因为任何理论主体及其研究成果都是不可避免地易犯错误的;其二,力戒批判为感情、先入为主、个人欲望、功名实利所左右。批判的激发和唤起,需要非理性因素,诸如兴趣、情感等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始动性或驱动性的,当进入批判状态后,批判就变成一种质疑、追问、思辨、澄清、扬弃和评价的理性思维过程。如果批判主体带上有色眼镜,为批判而批判,那么理性批判必将滑向非理性批判,不但达不到反思、澄清的目的,反而形成不良的学术风气,阻隔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也就背离了开展理性批判的初衷。
结语
陈桂生直言:“由于‘元教育学’局限于对‘教育学’的研究,它是脱离教育现象的研究,对于解决教育问题,其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它代替不了教育研究,代替不了教育学。”[5](P16)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对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的成人教育学也是适切的。尽管如此,如果基于这样的考虑——成人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科相比更具有“后发外生”的特点与优势,以及成人教育学科建设及体系构建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态”,此时尝试用“元成人教育学”这一研究视角或方法,对现有的理论以及研究行为进行反思、澄清,乃至尝试构建“元成人教育学”自身理论体系,以期建立“边学科建设、体系构建,边反思教育理论、研究行为”这种成人教育科研模式,应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或尝试。
收稿日期:2006-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