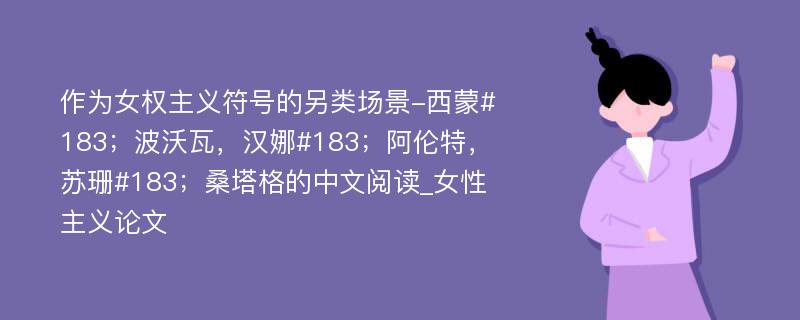
作为女性主义符号的另类场景——西蒙#183;波伏娃、汉娜#183;阿伦特、苏珊#183;桑塔格的中国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伦论文,西蒙论文,中国论文,符号论文,场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女性主义进入中国的方式,可说是出版传播的奇迹。一方面是作为理论的旅行,另一方面更是作为女性主义者形象的旅行,后者更由于其生动可仪的女性主义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女性主义的想像和接受,也极其生动地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的生长和开发。由于中国语境的不同需要,西蒙·波伏娃(1908—1986)、汉娜·阿伦特(1906—1975)、苏珊·桑塔格(1933—2004)这三位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作为女作家、女学者、女思想家,她们推动和影响了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但她们分别是在中国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即中国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经由出版传播的不同选择,以相继相承的翻译文本、以文本的女性主义符号,先后抵达中国,并与中国语境发生作用的。她们不同却互补的思想,在中国当代思想解放深度推进的不同历史时段,经由中国式阅读,构织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不同时段的言说之声,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巨变现实中,文化重构所面临的困难和需要面对的不同话题。借助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等西方女性主义符号的亮光,中国女性主义在近二十年生长发展中,已将一些幽暗沉默的经验,包括性别经验和国家民族经验,渐渐地带到思想语言的明亮地带。虽然这种借助光照的旅行过于短促和匆忙,其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阶级分层与中国的性别结构变动同步发生,错综而复杂。本土经验的深刻、复杂与辽阔从一个角度仅可作一斑之窥测,但是,如何借助异域权力话语表达激变的中国生活,仍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如何与中国现实生活对话从而在本土环境中呈现出自身存在的特点。
西蒙·波伏娃——开启中国女性主义的主体成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结束政治动乱重新回到城市化轨道,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折,而前所未有的社会竞争和个人竞争,也使得中国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开放的中国出版界敏锐感觉到存在主义读物在中国的需求,萨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国阅读视野。进入中国的西蒙·波伏娃是以萨特终身伴侣和事业搭档形式为中国读者接受的。大约1980—1985年间熟悉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动态的研究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西方女性主义对于中国的特别意味,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女性主义本身存在的状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随着各种纷繁而至的外国文学理论一同被介绍进中国,却没有明晰的概念和界定。而女性主义作为思潮和理论,远没有引起出版界重视。但是此时的中国女作家已经在她们的写作文本中探讨中国的爱情婚姻矛盾,并进而质疑中国的男女平等现实,《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方舟》等在今日被视为中国当代最早的女权主义文本,在当时已因其揭示中国现实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人们从这些文本看到的是中国性别的存在状态,同时感到了中国女作家的敏锐发言。
1986年堪称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着陆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它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二卷,原著的第一卷后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这种支离的出版,却正体现了翻译和出版的权力运用。关心中国读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说是关心女性主义在中国语言环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命名,也是一个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可以马上理解的词汇。相比第一卷太深的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二卷要感性得多,可说是直接讨论女性的困境。这和当时中国女作家讨论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如出一辙。翻译文本和现实文本一拍即合的认可,正是女性主义获得生长的契机。此后,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权威著作逐渐被翻译进来,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开始了符号之旅。
西方女性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影响,是从其符号之旅才真正开始的。早在1955年西蒙·波伏娃与萨特一起访问过中国,并作为法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国庆节那天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她回法国两年后还曾出版中国随笔集《长征》。但是,那时候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西蒙·波伏娃,却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空间活生生的人物,没有对于中国女性主义产生传播意义的影响。
1988年初,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的声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我还想得到更多”,《女性的奥秘》是挑战传统性别和社会结构的有力的女性主义宣言。1989年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还翻译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8年宣读的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伍尔芙对女人社会地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男性世界中的宗教、法律和经济条件时常成为女人思想和行为的枷锁,要解除这种枷锁的困扰,女人就该有勇气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1989年构成女性主义理论气候的重要著作还有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玛丽·伊格尔顿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这些出版物都体现了对于中国现实需要的话语关怀。但是,一方面由于存在主义思潮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急速转型带来的个人焦虑缓解的需要,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转型与性别结构调整怀抱理想主义期待。
和以上的出版物相比,西蒙·波伏娃本人的传奇与她的著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语境,更被当成一个时代的阅读时尚,以符号传播的意义而获得更为广泛的阅读。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理论以其新锐启人心智,不如说西蒙·波伏娃与萨特的不婚关系更令阅读者充满愉悦想像。西蒙·波伏娃与萨特的生活被描写为爱情神话,相关的出版物介绍他们共同的事业与生活,或是通过他们的关系介绍西方知识分子的新式生活。中国城市读者,特别是职业女性和知识女性读者,在阅读接受的想像空间中把西蒙·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理想化和浪漫化,以对抗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运转加速而日益加重的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
这个时期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妇女研究丛书”出版,其中一些著作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性别问题。但是,中国的理论界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中国现实性别问题的理论。而最为畅销的《第二性》,以翻译语言的方式,无疑参与了中国社会最激动人心的性别变动与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从英语译来的这个汉语名句,显明的意义所在是:女人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人们不关心法语原句型,也不追问译成英语的句式是否符合波伏娃原意,这个充满辩证思维的汉语句子,才是变动的中国现实生活所需!人们需要理论高度的概括性和指引性,“因此,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历史地表”。[1] 求变的中国更有求变的女性,变便是汉语的发言,是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女性的发言和意义。
畅销的《第二性》在中国有多种版本出版,直到200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第二性》全译本,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时间已是18年。从已有的译介文章看,很少将西蒙·波伏娃放在一个历史的过程审视,也很少文章介绍之后的女性主义对于《第二性》的突破。可以理解的原因除了对于《第二性》的推崇,更因为中国现实的性别问题很复杂,中国所期待的女性主义符号,是建设性和非破坏特点的,变,但要朝向可以把握的方向变。这或者就是另类场景的生长:不自觉之中一个新的爱情神话就缓冲了两性冲突的尖锐,更缓解了诸多复杂冲突中难于抉择的困难。新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式?西蒙·波伏娃如同一扇天窗,她的阳光明媚的生活方式以想像符号,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理论一起,引领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成长方向。
汉娜·阿伦特——言说:中国女性主义渴望的政治关怀
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嫒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是第一本由国内学者编辑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运用译介的权力,编者第一次将“女性主义”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合法化。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2] 更为深层而真实的理由,则是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女性主义”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能令人接受的词汇,避免了中国文化对于“权”的敏感和拒绝,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也意味着战斗硝烟已然过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进一步获得了通衢。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收集了19篇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中前沿性的研究论文,作者包括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乔纳森·卡勒,佳查·斯皮娃克,法国的波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尽管由于篇幅限制,书中的每位学者的思想都只能反映出一鳞半爪,但是这么大的阵营本身就有很大吸引力,这是一个集群的符号,对于激发文化想像力的作用是空前的。从前言来看,编译者应该是有意识地将“西方”两字从书名中隐去了,这两个字的空白,可说为阅读传播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想像图景:当代女性主义是全球性的。那么,在当代女性主义中,中国的声音是什么呢?
加入世界的声音,体现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时流行的正是中国主流与世界接轨的政治理念。中国政府欢迎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配合这个大会,中国出版界首次成批出版女性读物和女性主义学术著作。1995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蓁翻译的《女权辩护》,约翰·斯图加特·穆勒著、汪溪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早期女权主义及自由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把《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谈到的“女性主义”第一阶段“女权主义”时期的“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的努力过程,以翻译符号的形式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而同年,伊丽莎白·温德尔著,刁承俊、许医农翻译的《女性主义神学景观》,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理论著作呈现的是“女性主义”“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的知识特点,它不仅是第二阶段的产物,甚至可说是晚近的知识风景,它所做的对传统神学最彻底的更改和批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而新异的经验:基督教的起源有母性文化基因,但被男性神学和教会清除了;新约正典之编纂是适应父权制社会之确立;上帝是我们的母亲,而非仅是“天父”;新约关于耶稣的原始记述表明,马太、末大拉的马利亚比耶稣的门徒更理解耶稣,而且是耶稣复活的最初见证人;在由男性记述的基督教会史后面,隐藏着一部被隐瞒的女性基督教会史和信仰经验史;等等。[3] 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这些论点几乎可以看作是翻译文本要表达的一个核心信息:女性主义具有宗教立论的正义性。
通过世界妇女大会的造势,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权威性地位。原来比较敏感的论题开始获得中国语境的回应。作为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理论标志的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翻译出版,一下出了两个版本,分别是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和《第二性》专注于女性处境研究不同,《性政治》敏锐而激烈地抨击男权制,把男女两性关系纳入“政治”范畴,认为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是政治运动,有其明确的政治理想。
在讨论女性主义的政治理想上,中国理论界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或者说,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权威存在,中国女性主义者感觉到默契或默认的必要。翻译传递工作变得饶有趣味:20世纪90年代关于权力探讨的各类西方著作在中国出版,中国文化界对于权力话题的热切关注深入到权力的形成、演变和解构;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网络时代的到来,汉娜·阿伦特这位西方影响重大的女政治哲学家,为中国女性主义的政治关怀提供了理想的话语场地。女性主义学者崔卫平对汉娜·阿伦特做了多角度的阐述,在论述汉娜·阿伦特对于极权批判的思想价值时,特别分析了汉娜·阿伦特与支持希特勒极权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的情人关系。崔卫平认为汉娜·阿伦特能够从任何负面关系中取得正面经验因而能够成就大业,她的《积极生活》和《为阿伦特一辩》在网上广为流传,体现了读者渴望也愿意从个人生活方式角度理解女思想家的思想的特点。[4]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女性主义者形象的旅行,更由于其生动可仪的女性主义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女性主义的想像和接受。事实上由林骧华译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大陆并没有正式的简体版本。但重要的是,汉娜·阿伦特与极权关系提供的想像资源:她既是最无情的批判家又是难舍难分的情人,她的“积极生活”为读者启动了多元思考空间,为言说政治与个人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
中国女性主义既要关心政治又要找到合适话语,对汉娜·阿伦特的网上讨论正是这一有趣现象的注解。而西方女性主义“性政治”所以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各种翻译文本,全方位进入中国传播,也是由于出版界采用了合适的时间策略,利用了中国主流政治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世妇会搭建的中外妇女对话平台,为中国女性主义演练思考、思想和想像力,提供了既安全又必然是场景式的政治参与空间。事实上,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带给中国的女性主义政治方式至少有:非政府组织,弱势群体关怀,社会公平、公正的理念,社会性别意识的提高等。但是,这些真实的政治参与需要漫长时间和艰苦努力。而通过对汉娜·阿伦特这个已然行动者的阅读、阐释和讨论,却能产生场景和话语演习的激情。某种意义上,翻译文本阐述的汉娜·阿伦特形象呈现的正是中国式的女性主义的政治关怀。
苏珊·桑塔格——从政治关怀到消费文化批评: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与转型
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需要真正参与行动也需要行动经验的提升。尽管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主义部分地开始了介入社会变革的行动,但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对于自身状态改变的温和诉求,更多的仍然是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学习与移植。这便是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西蒙·波伏娃和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的缘故所在。然而中国女性主义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借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参照以及反思和批判的资源,对西方女性主义某种重要话语的复述或阐述,呈现出中国女性主义的真实境遇和现实主题。
2004年12月28日,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著名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岁。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种名号和赞誉:“唯一的明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识分子”等等。英国BBC称她是“美国先锋派的大祭司”。 中国的网络和报刊在对西方媒体纪念文章和称誉进行转载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自己的评论文章。在强调苏珊·桑塔格的知识分子立场时,特别指出了她的特立独行和先锋意义。有文章甚至就苏珊·桑塔格与中国新左派的纸上谈兵进行对举,认为美国左派苏珊·桑塔格政治上的言行一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德行之镜。“她始终是独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义者,持久地抗议一切全球的、国家的和地区性的霸权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5] 更有文章指出:特别是在中国的当下,她是评论界与阅读界的一个流行符号,她的思考也正在代替某些人的思考。[6] 在此我们再次体验到苏珊·桑塔格的传播效应在中国语境中的发生。严格意义上苏珊·桑塔格的英文著作中国读者知之甚少,中译本的资料也并不齐全,中国读者了解的所谓独立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不过是传播中的有倾向的评介而已。然而“她是评论界与阅读界的一个流行符号”却中了要害:作为一个流行符号的苏珊·桑塔格,不仅是中国语境的阅读倾向,更是一个反复谈论的、中国21世纪初的热点话语:流行。也就是消费文化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指认参照,中国女性主义不得不关注的新的话语场地。
至21世纪初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然形成,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却远不如经济本身繁荣,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文化空间尚未发育完好。一方面不得不摆脱以政治为中心的情结,另一方面又难以掌控市场中心文化,游走在双重边缘的处境令一些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选择。所谓独立便是这种双重边缘处境的自我确认。对苏珊·桑塔格的借用,为的是有清晰而又高贵的符号,为的是对于不能合作回敬以高傲的姿态。但是,流行的选择显然更加国际化也更加容易获取经济资本,于是,苏珊·桑塔格的时尚、前卫、对于消费经济时代处以轻松阐释的牛仔作风,无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阅读的“流行”。尽管苏珊·桑塔格崛起于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之中,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恩人》为汉娜·阿伦特所激赏,但出色的女性主义思想方法更体现在1966年结集的、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评论集《反对阐释》中。可是在介绍这部重要评论集时,译介鲜有对于女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强调,而更多从中国语境出发,将之定位在后现代主义的流通之中。如果按照苏珊·桑塔格在接受陈耀成采访时说的话:“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即是说,把一切等同起来——是消费时代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便于令人囤积,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理念。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7] 可知苏珊·桑塔格不仅不是后现代主义,且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非批判性理念持反对立场。然而她和她的思想在中国流行的处境,却恰好反映了一个后现代囤积的、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状态。
这状态是由全球资本文化向中国冲击所制造的:1980年代至21世纪初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升可类比1960至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腾飞,受到现代技术和物质严重挤压的当代中国,急需对于技术和物质的理论进行阐释,而过于庞大的历史积累与过于超荷的时空逼迫,使得面向美国的借鉴几乎从物质到思想。苏珊·桑塔格1977年出版的《论摄影》在21世纪初的中国流行,正可说是提供了某种适当的阐释。更何况苏珊·桑塔格还有电影、时尚及国际政治的诸多阐释,用她的“反对阐释”理论来说,多元的、从容不迫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人在全速改变的生活场景中应该具备的素质。一些迷恋、一些分析、一些批判,保有人对于物质的主体体验。
除却人与物质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特别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在一个全速转变时期,认识自己成为人最隐秘而急切的需要。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和续篇《艾滋病的隐喻》,也许是她在中国拥有最多读者的著作。《疾病的隐喻》风行于中国的“非典”流行病之后,绝非偶然:人们太需要安全而又合理的阐释,尤其需要说服自己的理由。《疾病的隐喻》以体己的举证和精致的分析,为阅读找到了最合适的口感,既释放了集体惊扰的情绪,又深入个体生命日常的关怀。之后再读《艾滋病的隐喻》就很容易了,因为血液管理不当而导致的中国艾滋病严重状态,非常需要集体情绪安抚和个体关怀体贴,有这样充满生命体贴的分析,受欢迎的理由已很充足。
甚至不需要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苏珊·桑塔格做出阐释。她在中国的流行就是阐释,这种阐释反对阐释,因为一切显得多余。关心人在消费时代与物的相处,关心人与人、特别是与自己的相处,才是苏珊·桑塔格的人道主义核心所在。她在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文体所探索的,就是我们时代所遭遇的。而这遭遇不仅有了倾听者也同时有了对话者,苏珊·桑塔格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之旅就是倾听与对话之旅:倾听与对话,这就回到了女性主义的方法论。
颇有意味的是,大多数介绍苏珊·桑塔格的文章都会写到苏珊·桑塔格的长发和眼睛,她的出众的长相和个性化的穿着,并且通常用来比喻她的文字,特别是批评文字的个性化。也就是说,人们愿意接受她的女性/个性化风格,从外在到内在。在此意义上,又是女性主义的荣幸了。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来说,苏珊·桑塔格的流行,或者体现了女性主义较好的环境,或者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性主义的渴望与需求。
这便是中国女性主义可以多元行动的理由了:21世纪初,一部分中国女性主义开始探索社会介入,如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等对于孙志刚案、黄静案的法律援助,[8] 另一部分继续进行文化移植或者思想对话。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女性主义的不同的努力正在深化。如苏珊·桑塔格指出:“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9] 认识到阴郁、焦虑、鲁莽、草率无力和恐惧,这一切构成人类文化缺陷的消极因素的危害,正是我们迈出健康步伐的前提。
自近现代以来,借助翻译文本和西方符号的中国旅行,对于所处时代作出相应的阐释,已是汉语学术界的习惯,现代汉语对于古代汉语的革命,在根本上便是翻译语言与文化对于汉语的加入和生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女性主义正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符号旅行过程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以上分析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三位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传播过程与特点,体现了阅读旅行过程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意义,不仅是眼光和思想的修炼,更是经验的唤醒和开发与命名。无论是作为女性的存在,还是中国人的存在,中国女性主义目前正处于如何真正独立思想、言说和行动之际。在此维度,我们有理由期待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并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的中国女知识分子或女性主义者的出现。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西蒙·波伏娃论文; 阿伦特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疾病的隐喻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苏珊桑塔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