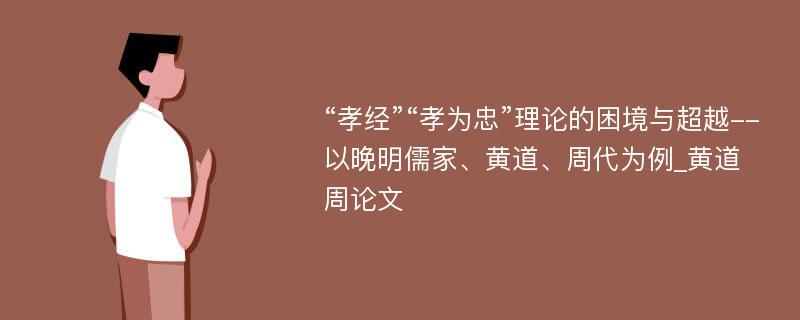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经论文,大儒论文,黄道论文,明末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057-07
一、《孝经》“移孝为忠”说的提出与存在的问题
《孝经》是先秦儒家阐述其孝道观的一部著作,孝与忠的关系之阐发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孔子曾说过:“孝慈则忠。”(《论语·为政》)但这只是孔子将孝慈的品格内涵扩展之后提出的一种做人之准则,与忠君没有直接关系。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关系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以“礼”为条件,而与“孝”亦无直接关系。《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①《孝经·士章》云:“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广扬名章》又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是《孝经》孝道观与早期孝道观的一大不同。在《孝经》的孝道思想中,事亲只是孝的一个初级阶段,而事君处于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忠君是孝的必然发展,也是个体建功立业的最重要的凭借,这就由早期强调家庭伦理之孝转变成强调社会政治之孝,“孝道”也由此向“孝治”转移。自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推许《孝经》,他们不仅看重“孝”对稳定社会的巨大功效,更试图以“由孝而忠、忠孝合一”的人生设计来规范士人的思想与行动。
事实上,在宗法社会中,由“治家”向“治国”的转移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移孝为忠”在中国“修齐治平”的传统历史语境中亦自有其理论的自洽性,但其中也存在两难选择:当孝与忠发生矛盾时,如何求得忠孝两全,抑或去此而存彼?当同样是《孝经》所宣扬的敬爱父母所遗之躯体、“不敢毁伤”的主张受到君王的无情打击时,孝子又将如何全忠尽孝?对于这个问题,历来的《孝经》注疏与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②。明末大儒黄道周“移孝为忠”的人生经历及其与同僚杨嗣昌关于“夺情”的论争,为我们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二、从黄道周的经历看《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另一种演绎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漳浦县铜山深井村(今属东山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殉节于唐王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笔者之所以选择黄道周,就在于他是一个合乎传统孝道的孝子。理学在明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理学基本经典的《孝经》也得到了明朝历代帝王的重视,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即有意识地自上而下推行孝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导向。黄道周故里漳州为朱子“过化之邦”,孝道彰明,他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极其重视《孝经》。他在《孝经集传》序言中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1]他将《孝经》作为立身之基、治国之本。其门人洪思于《黄子讲问》中云:“夫子忧曰:士者必不复谈敬身之行,人心乃遂至此哉,吾将救之以《孝经》,使天下皆追文而反质,因性而为教,因心而为政。”③在传统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晚明,黄道周尤其看重《孝经》的教化功用。他在《〈诗〉一房制义序》中也说:“泛泛看房稿,不如诵《孝经》。”④他本人亦身体力行,洪思《收文序》说他“其学皆可以为《易》,其行皆可以为《孝经》”,并概括说:“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③。
综观黄道周的一生,可见其人生道路基本符合《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未入仕时,黄道周在家躬耕以养父母,辛劳备至。如洪思所言:“子耕于铜山之下,以事二人。时负米归,则与兄把锄,必十指出血也。”[2]虽如此,黄道周仍然认为自己事亲不力,以致家境贫寒。其父殁后,他悲哀欲绝,即使在仕亦念念不忘回乡庐墓;他事母极孝,母亲去世后,七日不食;于妻、子皆以孝顺言传身教。而居官时,他移孝为忠,心忧国事,秉承《孝经·谏诤章》大旨,敢于谏诤。当时即有论曰:“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3]。从天启朝的触忤阉党、辞官归乡,到崇祯朝的屡次上书直谏、被贬入狱,再到隆武朝的出师抗清、慷慨就义⑤,其确如洪思《收文序》所言:“立臣子之大节以归于《孝经》。”③但是,与黄道周践行《孝经》的不遗余力相比,在他身上,忠与孝的两难亦体现得异常突出,其“移孝为忠”的过程充满着困惑与艰辛,而这也是我们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1.反对夺情,维护孝道——忠与孝的直接冲突
《礼记·王制》云:“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旧时官员遭父母丧,即应弃官家居守制三年,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而大臣丧制未终即被朝廷召出任职,或朝廷命其不必弃官去职,称“夺情”,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明会典》卷十一载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规定,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而嘉靖元年更将此形诸律令:“命自今亲丧不得夺情,著为令”[4]。但一些人为了个人私欲,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有关伦理问题的争议,明朝中季张居正夺情一事即为显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夺情的施动者是国君,大臣夺情起复,于家可称为不孝,但于国却可称为忠君,这一矛盾是《孝经》“移孝为忠”说所无法回避的。下面我们通过黄道周论杨嗣昌夺情之事试加分析。
(1)杨嗣昌夺情一事的论争凸显出忠孝矛盾。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陕西总督杨鹤之子,于崇祯八年(1635)起连丁父母忧。但崇祯帝看重他的军事才能,次年秋因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夺情让其代之[4]。这对于恪守孝道的黄道周来说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而杨嗣昌的“溢地、均输”以筹集兵饷之策在黄道周看来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补于国事,故于崇祯十年闰四月上《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⑥,反对杨嗣昌夺情出任兵部尚书。
而崇祯帝坚持重用杨嗣昌,并于崇祯十一年提拔他入阁。黄道周又连上三疏直谏,其中《论杨嗣昌疏》言:“陛下孝治天下,缙绅家庭小小勃谿,犹以法治之,而冒丧斁伦,独谓无禁,臣窃以为不可也”⑦,直指杨嗣昌夺情一事为“冒丧斁伦”。陈新甲当时亦丁内艰,杨嗣昌荐其为宣大总督,崇祯帝即下诏夺情任之[4],故黄道周《论陈新甲疏》言其“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天下即甚无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无济于艰难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⑦,亦对陈新甲夺情起复一事加以抨击。二疏皆以忠孝大义为据进行谏诤。
关于这场论争的原因,侯真平先生认为,黄道周等人反对杨、陈的主要原因在于杨嗣昌与东林党人有隙[5];辛德勇先生在其《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一文中指出,在黄道周看来,杨嗣昌与阉党余孽之间肯定存在某种交结,这应当是以维护“天地纲常”为己任的黄道周不顾一切、竭力阻止杨嗣昌入阁的根本原因[6]。而我们则认为,这场论争凸显了“忠”与“孝”的内在矛盾。
崇祯十一年七月,黄道周于崇祯帝平台召对时,就杨嗣昌、陈新甲夺情一事与崇祯帝展开了更为直接而激烈的辩论。崇祯帝怀疑黄道周疏论杨、陈二人源于自己不能入阁,故怀私怨。而黄道周则明言:“臣所奏关天下纲常、边方大计。”[7]所谓“关天下纲常”,如黄道周所言:“有孝弟之人,才能经理天下,发生万物。如不孝不弟之人,无有根本,如何生得枝叶?”[7]故黄道周认为“孝”乃天下万物之根本,而不孝如杨嗣昌、陈新甲之辈必不可用。所谓“关边方大计”,应指杨嗣昌于崇祯十年“阴主互市策”、十一年与高起潜“主款”等暗中欲与后金议和之事[4],这也是黄道周及东林清流所坚决反对的。故黄道周后来之《感恩疏》曰:“至于不清不本之臣,遗祸苍生,失误大计,臣犹自悔知之不尽,言之无力”⑦,丝毫不改初衷。其所谓“天下纲常”与“边方大计”实二而一之事,即借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及陈新甲夺情起复等事,反对其加派军饷、增加黎庶负担、与后金暗中媾和等执政方针。因此,反对杨嗣昌夺情,并非黄道周迂阔不知变通,更非对自己不能入阁心有私怨,而是儒者所特有的社会关怀与其“不孝即不忠”的个人评判标准相交融的体现。在之前所上《论陈新甲疏》中,他已不避嫌疑,勇于自荐:“天下即无人,臣愿解清华,出管锁钥,何必使被棘负涂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⑦
假如此处我们不论及党争及双方政见的分岐,单从黄道周与杨嗣昌对“守孝”与“夺情”的态度来看,就可分明见出“忠”与“孝”的矛盾冲突。应该说,杨嗣昌所持论亦非无理。他本身可称为孝子,其父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不力而获罪,他曾三疏请代,使父得减死;而且在崇祯帝的夺情命令下,也曾三疏请辞[4]。但他还是认为忠君为上:“今之君臣乃一统之君臣,为臣子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无所逃,臣又逃于何所。”[7]《杨嗣昌集》中则有《召对纪事》记载此次平台召对,其中对杨氏父子所受君恩有更详细记载:“臣父剿贼不效,自分严谴,蒙恩减死论戍。及闻卧之日,臣哀恳皇上,不待部复,先复臣父原官,早瞑臣父之目,果奉谕旨,这是何等天恩!臣父九原有知,不知望臣如何图报!”[8]可见杨嗣昌认为忠大于孝,故不惜夺情以报君恩。而黄道周则以自身孝行作为例证:“臣二十年躬耕,手足胼胝,四十丧亲,负土成坟,诚不忍见有夺情之事。”[7]其《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亦云:“古之圣人以为:忠信可学,至孝难尽”⑥,明显将孝置于忠之上。
(2)黄道周、杨嗣昌二人孝道观之不同。比较黄、杨二人的孝道观即可见出,黄道周的思想更接近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及《孝经·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的理念。当忠孝相抵触时,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孟子认为事亲、孝顺父母是头等大事:“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下》)。稷下儒者田过更是明确指出亲重于君,《韩诗外传》卷七载:“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这种“孝亲”高于“忠君”的理念显然为黄道周所接受。他大力维护孝道,在孝与忠之间发生矛盾时,舍君而护亲。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与文震孟、郑郧相约疏论权阉魏忠贤。文、郑二人皆已上疏,黄道周因为要迎接母亲入京,有所顾忌,如《救郑鄤疏》所云,其“三疏三焚,郑鄤尝以为怯”⑥。他在忠谏与孝亲之间几经挣扎,最终选择了孝,放弃上疏,以全孝道。可见,黄道周对母之孝超过了对君之忠。他在撰成于崇祯十六年,主要针对杨、陈夺情而作的《孝经集传》中对此问题也有不少论述。如反对“以君灭亲”:“或曰:天子制四海,四海之内,不得有其亲。则是以君灭亲也。以君灭亲,犹之以亲灭君者也。”[1]他又说:“以孝作忠,其忠不穷。”[1]认为忠必须建立在孝的基础上才具有永久性。
而从杨嗣昌所论来看,他更多的是依据荀子、韩非子、《白虎通义》及《孝经》“以孝事君则忠”的观点。《荀子·礼论》云:“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认为君王兼父母之美,忠应大于孝。《韩非子·五蠹》更指责为了奉养其父而临阵脱逃、背弃君国的人为“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班固之《白虎通义·五行》亦有对于忠孝抉择的论述:“不以父命废王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即以五行生克来附会,认为如果父命与君命发生矛盾,就应像土生金而金却惧火那样,遵守君主的命令。故方光华先生认为,虽然《白虎通义》亦表现出对孝道的高度认可,但如果孝道与君道发生矛盾,则毫不犹豫地维护君道[9]。法家重视君主权力的加强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白虎通义》更是由帝王钦定的旨在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的著作,持忠大于孝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而《孝经》提出“移孝为忠”,正是要把孝导入忠的轨道,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后世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往往正是“移孝为忠”之后弃孝而取忠的说辞。
(3)“移孝为忠”说与忠孝的两难。通过对黄、杨二人在夺情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分析,可见忠与孝在君王强力意志面前,或者在臣子自身的政治、伦理观念面前,都会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不是《孝经》原本设想的“移孝为忠”的模式所能解决的。黄开国先生曾撰文探讨了儒家孝道派与奉《孝经》为经典的孝治派的区别,并认为《孝经》之“孝”是政治学之孝而非伦理学之孝,在孝与忠的关系上,孝服从于忠[10]。笔者赞同此观点,同时以为,《孝经》“移孝为忠”之说正是孝道理论向孝治理论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主张;但也正由于它脱胎于孝道理论,不能根本改变“孝”为“天之经、地之义”(《孝经·三才章》)这一最高范畴的定义,因此“忠”要凌驾于“孝”之上总是缺少理论上的充分准备,这也使得《孝经》在接受层面出现了两个向度。由于人生经历、文化背景、个性特征等原因,黄道周对《孝经》的理解更倾向于孝道派的主张。于是,在刚愎自用而又急于摆脱困境的崇祯帝那里,黄道周及其所代表的先秦儒家孝道观被摒弃(崇祯帝是否认为黄道周反对杨嗣昌夺情就是对他的不忠?),此事终以黄道周被降六级调用、告病还乡而结束。
2.亏体辱亲,血书《孝经》——忠与孝的另一冲突及弥合途径
由于前一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循例举荐部属,首推黄道周,小人从中作梗,使崇祯帝疑其结党,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黄道周被逮至京,与解学龙各受廷杖八十,又入刑部监狱,后转北镇抚司,受尽酷刑。黄道周《京师与兄书》其六云:“在北寺五月余,拷打讯问四五次,备极惨毒”⑧;《狱中自明揭》云:“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满衣,疮痂蔽褥”⑨。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唐玄宗注曰:“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孝经·感应章》云:“修身慎行,恐辱亲也。”辱亲者,一则如前所言,怕肢体有伤;一则惧犯有罪名,有损先祖清白名声。而黄道周虽下狱受刑,但自认为无辜,问心无愧,所以主要是担心前者。他深感自己入狱受刑有辱先人,于《狱中悔罪自明疏》云:“毁伤肤发,无以见父母于九泉。”⑦《狱中答卢云际书》云:“舍生取义既无益于君,亏体辱亲徒有乖吾素耳。”⑩《京师与兄书》其四云:“周不肖,负祖宗父母之恩,去岁过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死”⑧。僚友黄景防在《黄道周志传》中言其探视黄道周于狱中,道周“创虽重,神气未损,独以亏体辱亲为言”[11]。
如果我们置身于黄道周之处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难以解答的悖论:正是由于君王的过错而使自己躯体遭受创伤,从而违背了《孝经》“不敢毁伤”之训,以致辱没先人、陷己于“不孝”境地,那么,作为臣子,与“孝”并称的另一道德准则——“忠”又该如何维系?这种忠与孝的冲突又与当初论杨嗣昌之夺情一事不同了,它如此尖锐地存在于黄道周的内心,所造成的精神的痛苦或许比肉体的痛苦更甚。
面对忠孝两难之处境,黄道周首先是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将“毁伤”的不良后果降至最低限度。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充满自信,在《赴逮与兄书》中自陈:“生年以来,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鬼神,明不可告于黎献者”,因而问心无愧:“吾于德业无所亏损”⑧。在《京师与兄书》其六中也云:“吾一身与苍生分痛,当事虽不谅,天地鬼神自当谅之”⑧。在《与内书》中他自我宽慰:“吾为国家受此困苦,虽毁伤肤体,犹是显亲扬名上事,未至辱亲也”⑧。将自己的苦难等同于国家的苦难,这样就把个人肤体毁伤的惨痛化解、升华了。同时,在《孝经集传》中,他对“毁伤”本身也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不敢毁伤,厚其本也。……然则毁伤何谓也?曰:暴弃之谓也。孟子曰: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暴弃其身,则暴弃其亲。肤发虽存,有甚于毁伤者矣。”[1]也就是说,他把毁伤肤体形而上化了。在他的心中,仁义、礼义的保全比肤体的保全更重要。而仁义、礼义即“道”,因此,“身殁而道不著于百世,则是未尝有身也。未尝有身,则是未尝有亲也”[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黄道周言论皆作于其入狱受刑之后,这是深受《孝经》影响的士人在一种特殊境况中的痛定思痛,可视为对《孝经》“不敢毁伤”诸语具有创新性的阐释。
其次,黄道周还通过在狱中带血书写120本《孝经》这一举动来弥合忠孝之间的裂痕。据《黄道周年谱》载,其直接动因是狱卒向他乞书(黄道周是当时知名书法家),他即“书《孝经》一百二十本”,“以当役钱”[2]。洪思在《收文序》中引其父、亦同为道周弟子的洪京榜所言:“吾见夫子之为《易》、《孝经》多在诏狱中,十指困于拷掠,指节尚摇摇未续时便写之,至今血犹渗漉纸墨间,稍一流览,便如有闻锒铛桁杨之声,人皆谓其可以御鬼也。”③结合黄道周的遭际与个性特征,其狱中书写《孝经》当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该《孝经》是饱含着黄道周鲜血与心血的杰作。刘正成先生在《黄道周书法评传》一文中指出:“‘孝’是黄道周从政二十年中所不遗余力维护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核心,这是他用生命和鲜血所维护的道统纲常。如果要找到黄道周在狱中所书的一百二十本《孝经》的艺术原动力,就应该在此。”[12]而身处囹圄仍血书《孝经》这一举动,则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对君王、更是对国家社稷的“忠”。据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记载,崇祯帝在宫中看到流传入大内的黄道周所书《孝经》,指曰“沽名”,这个名不单单是“孝名”,更是“忠名”,而且,“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③。也就是说,黄道周的这种特殊的表白方式似乎也打动了崇祯帝。加之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杨嗣昌因农民军连克州郡而畏罪自杀,崇祯帝指望他夺情立功的想法终成泡影,对当年抗疏直陈杨嗣昌之非的黄道周当不能无愧于心。据《明史·黄道周传》载,崇祯十五年八月某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谈及黄道周时,众辅臣为其求情,其中陈演即言其“事亲极孝”,“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4]。崇祯帝之笑所包含的深意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黄道周的“忠孝”品格毕竟是他获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历史上,忠君爱国却往往因忠而见疑入狱受刑、“亏体辱亲”,从而导致不孝的不在少数,忠与孝似乎是无法避免的矛盾。黄道周却在对《孝经》的不断书写中,消解不孝,表达忠心,从而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移孝为忠”。
3.慷慨就义,立身扬名——“移孝为忠”的终极途径
黄道周在父母辞世后,已有尽忠报国之志,如《赴逮与兄书》云:“自母殁后,以身许君。”⑧他对崇祯帝的感情是复杂的,忠而被谤,贤而遭贬,亏体辱亲,自是不能无怨,但最终蒙恩获释还职,还是心念君恩的。如其在《免戍辞职疏》中云:“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戆召还,未有迂狂贾罪如臣而得起于戍籍,申以华奖者也。”⑦《文明夫人行状》又载黄道周留都应征召出山与夫人辞行时言:“吾欠先帝一死,此身不复能依依松楸,遂终二人墓下。”③可见其早已有以死报君之心。甲申之变后,“君死社稷、臣死君上”之想法更加坚定。而这个想法如果说在政治昏庸的弘光朝无由变成现实的话,那么隆武帝的知遇之恩可说是加速了黄道周以身许君的步伐。弘光元年(1645),黄道周初晤唐王朱聿键,“见所谈论慷慨,以恢复自任,因同众交拜,约成大业”[2],可谓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并成为隆武朝的开国勋臣。在大势不可挽回的情况下,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毅然出师北进,力尽被俘,义不降清,最终完节于南京孝陵之侧,得偿宿愿。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唐玄宗注曰:“中者在于出事其主,忠孝皆备,扬名荣亲,是‘终于立身’也。”《孝经》一方面要求敬爱父母所遗之躯,另一方面又以“立身扬名”为孝之终极目标,而殉节即能得忠君爱国之大名,从而“扬名荣亲”,是为大孝。曾子亦云:“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因此,黄道周的殉节,是对“移孝为忠”这一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过程的总结,也是封建时代士人所能选择的终极途径。蔡世远所作《黄道周传》云:“少负奇节,以孝闻。”其论曰:“道周学贯天人,行本忠孝,入则言朝,出则守墓,讲学著书,清修自饬,金陵一节,堪为殿后矣。”③亦可见出后人对其忠与孝合一的评判。而同样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另一个明朝重臣、也是黄道周的福建老乡洪承畴在松锦战败被俘后,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他犹豫、彷徨了两个月,也曾绝食过,但仍选择了苟且偷生。于是,历史也为他写好了定评。《广阳杂记》记载他迎母进京后,“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13]。洪承畴成了不忠不孝之人,在乾隆朝更被列入《贰臣传》。死与不死,结果大不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以《孝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大力宣扬的“忠孝”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历史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11)。
三、“道在天下”——黄道周对《孝经》“移孝为忠”说的诠释与超越
从黄道周的一生来看,他事亲孝而事君忠,评价其“忠孝合一”当无疑义。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他与《孝经》的“移孝为忠”的主张又有着某种程度的背离,他于事亲与尽忠之间心存犹豫与矛盾,其忠君却又被逮下狱受刑、亏体辱亲的遭遇更是充满悲剧性,这让我们看到了《孝经》宣扬的“移孝为忠”所存在的种种困境。黄道周三疏三焚、反对夺情、血书《孝经》、以身殉道等人生历程,为“移孝为忠”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诠释方式。
这种诠释自有其现实依据。在明代,专制皇权达到了一个顶峰,商传先生认为:“明朝所施行的文化专制统治,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秦鉴在先,明鉴在后’,这是中国文化专制最突出的两个阶段之一。”[14]廷杖、诏狱,东厂、西厂……使明代士人无时不在承受着巨大的肉体与精神压力。而明末时局的艰危,更令士人心萌退意,在忠与孝之间彷徨。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黄道周时常责备自己“不忠不孝”。如《乞归疏》云:“臣少值家贫,父丧不举,强仕葬母,拟追制六年,比闻□(12)警,挈家出山,遂弃坟墓,是臣不孝;生逢有道,自誓鼎镬,有所不辞,比当云汉之会,下诏求言,臣反奄然,自同结舌,是臣不忠。”(13)《请告疏》则云:“臣一生孤立,无竞无营,但以学不纯师,穷理未尽,为孝不遂,抱忠多惭。”⑥他在《狱中与兄书》更劝子弟不要再入仕途:“生平孝弟功疏,受此奇祸,劝诸儿只读《孝经》,不必更作举业也。”⑧“东林六君子”之杨涟甚至这样交待家人:“汝辈归,好生服侍太奶奶,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15]对忠君的失望最终使读书人选择了“不读书”,由“忠”而退守“孝”。而且当时有这种想法者绝非一二人。
黄道周《孝经集传卷一·庶人章》注经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云:“‘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显亲’,孝之终也。谨身以事亲则有始,立身以事亲则有终。孝有终始则道著于天下,行立于百世。”[1]可见他主张把“孝”、“事亲”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同时他把“天子”也纳入“孝子”的范畴:“天子者,天之孝子也。”[1]按此定义,则天子行事首当遵循孝子之规范。所以黄道周在《书古文孝经后》中又说:“臣子不敢毁伤其身,天子不敢毁伤天下人之身。”④对天子滥施刑罚给予批评。因此可以说,“移孝为忠”虽然具有一种巨大的文化惯性,但具体到黄道周的一生,“孝”的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了《孝经集传》外,他还著有《孝经外传》、《孝经本赞》等多种《孝经》类著述,无不大力推衍孝道,试图以“孝”而非以“忠”来挽救世道人心。
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明清易代之际,黄道周对“身”与“道”有独特的体悟,他发扬了先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把“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理解为:“始于事亲,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终于立身,道在百世”[1]。“道在天下”的提法明确了“事君”的目的并非仅效忠于朱明一姓、只为君一人而已,而在于天下苍生。其《博物典汇》卷十六“兵书”曾引古兵书《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16]故己身已不独属于亲、君,而更忠于一“道”:先天下之忧而忧,以身报国,杀身成仁,最终完成完美人格之塑造。因此,其“如不为天下百姓,要此己何用”[17]的开阔胸襟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又是对《孝经》“不敢毁伤”的超越。试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所言:“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8]可知黄道周的观点并非个别言论,而是代表着当时士人的主流思想。陈来先生认为黄道周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包含了他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问题的思考和回应”[19]。可以说,黄道周大体遵循着《孝经》“事亲—事君—立身”的模式,但又超越了这个模式,构建了一种新的范型,可视为《孝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变。
收稿日期:2011-05-03
注释。
①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页2545-2562,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本文引用《孝经》文字皆据此版本,不再出注。
②有关“移孝为忠”的几种著述及主要观点有:刘学林、王楠《〈孝经〉思想论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强调了忠君与忠于国家的紧密联系;李建森、杨权利《“移孝为忠”评析》(《华夏文化》2000年第4期)认为忠是孝的进一步发展;张晓松《“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孔子研究》2006年第6期)则探讨了孝由“敬”而“忠”的转化过程。
③见黄道周著、陈寿祺编《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以下简称《黄漳浦集》)卷首。
④见《黄漳浦集》卷二十二。
⑤关于黄道周的孝行及其与《孝经》的渊源,可参见郑晨寅《黄道周孝悌行实考》(《闽台文化交流》2010年第2期),郑晨寅、汤云珠《黄道周与(孝经)的历史遇合》(《孝感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⑥见《黄漳浦集》卷二。
⑦见《黄漳浦集》卷三。
⑧见《黄漳浦集》卷十九。
⑨见《黄漳浦集》卷二十八。
⑩见《黄漳浦集》卷十七。
(11)但我们发现官方对黄道周的评价更看重的是“忠”而非“孝”,如隆武朝谥曰“忠烈”,乾隆四十一年则特谥“忠端”。可见,在“孝治天下”的官方话语中,“忠”才是一个臣子的最高道德评判标准。
(12)“□”字原缺,当为“虏”、“胡”等清朝时避讳字。
(13)见《黄漳浦集》卷一。
标签:黄道周论文; 孝经论文; 元末农民起义论文; 天下父母论文; 明朝论文; 杨嗣昌论文; 崇祯论文; 崇祯帝论文; 白虎通义论文; 孝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