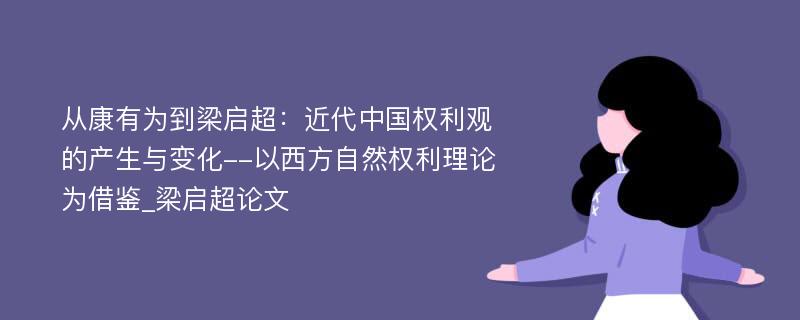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中国近代权利观的产生与变异——以西方自然权利学说为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利论文,学说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康有为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第476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权利学说。它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利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成长历程,确乎源远流长。古希腊思想家们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十七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理论上对自然权利学说进行了经典性论述,从而使得这一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法律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权利学说;二是社会契约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越来越摆脱“神性”的羁绊,逐步走出神学的思维路径,“人”不再被视为上帝的造物,而是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且,人还是自然界的中心,是自然发展的“目的”,人的现实感性欲求成了人们界定“人性”的关键,七情六欲因此而得以正当化,自然人的价值、尊严和个性由此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张扬,人性论实现了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转变。而社会契约论则是与自然权利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社会契约论是自然权利运用于国家理论的必然结果,而自然权利说恰是社会契约论得以完成其使命的逻辑前提和价值基础。霍布斯说:“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方便自己权利的实现,才彼此订立契约而组成国家的。
一
既然西方权利观主要包括自然权利与国家契约这两方面内容,因此,我们亦以西方权利观为参照物,对康有为等人的权利观进行一番剖析。
首先,关于自然权利观。在西方文化中,自然法是一个与人定法相对应的概念,是由非人的意志所创立的法,它不以任何人类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其演化过程中获得了“上帝创世”一般的尊严和神圣,永恒性、绝对性和超验性是其主要的特征,它不仅先于任何社会的人定法或者人们之间的任何约定规则,而且是人定法或者人们之间的约定规则之道德正当性的神圣来源。而在近代中国,康有为在一个所谓的“公理”的价值预设之下展开自己的“权利”话语实践。他认为,“公理”乃是人类存在之价值和意义的根源,尤其是人类社会政治法律秩序的道德正当性渊源之所在。康有为的个人权利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人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在他早期撰写的重要著作《实理公法全书》中说,“主旨便是依人人自主之权来讨论中国的伦理和制度。”(注: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康有为指出:“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注: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凡例》、《总论人类门》、《朋友们》。)康有为当时对几何学颇有兴趣,在撰著时期模仿了几何学的推证结构和方式。他所谓“实理”,相当于欧氏几何学的“公理”,是人类所必须创设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规范(包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习俗的)之最高价值本源。所谓“公法”,相当于欧氏几何学的“定理”,是根据“实理”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关于确保“实理”得以贯彻的各项基本原则;所谓“比例”,是指运用“实理”、“公法”系统,对中外古今各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习惯逐一进行分析、比较,而作出的去留取舍和优劣评判。如果从法文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康有为所说的“实理”、“公法”与“比例”分别相当于法律价值观、法律原则与具体的法律制度。而“人人有自主之权”正是这个法律价值观的核心之所在。因此,康有为仿照欧氏几何学由“实理”到“公理”推进,实质上是由“自然”,亦即关涉人之天性(本性)的“公理”推导出人人“自立”、“自主”的“权利”、“人权”。具体而论,康有为提出了关于人之“公理”的四条“实理”(注: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凡例》、《总论人类门》、《朋友们》。):第一条,“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第二条,“人各具一魂”,故有知识,所谓智也。然灵魂之性,各个不同。”第三条,“人之始生,便具爱恶二质。及其长也,与人相接时,发其爱质,则必有益于人。发其恶质,则必有损于人。”第四条:“人之始生,有信而无作,诈由习染而有。”康有为在对人性及人的本质之判断的这四条“实理”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人是天生自由而平等的,人性尊严应当得到制度之保护的自然权利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公法”。既然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且“人各具一魂”,均为“天地之精英”,那么,任何人生来便拥有其无所依傍的独立自主的价值和尊严,便应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立权利,“人有自立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是理所当然的,是完全正当的。
第二,主张人拥有平等与自由的权利。康有为认为人有“自立之权”,“自主之权”,即有自由权。同时,康有为更为关注平等,他指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此几何公理所出之法,最有益于人道。”(注: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凡例》、《总论人类门》、《朋友们》。)据“实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关系。虽然他认为,在生物界的发展中,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客观事实,所谓“盖差等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为也。”(注:康有为:《孟子微》。)但他特别强调,差别并非根源于人性。在人性上,则人人是平等的,在康有为看来,人性平等恰是人人皆具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就像在霍布斯的思想世界里,尽管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但对安全的需求却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所以,安全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康有为说过,就人的自然天性而论,“同是视听运动”,“同是食味别声被色”,“人人相等”,故孔子说“性相近”,“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注:康有为:《长兴学论》。)。并且他从平等及自由观出发,对“三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注:康有为:《大同书》。)认为所谓“君为臣纲”,都是人为地创出来以限禁名分、遂其私欲的教条;他认为“一人身有一人身之自立,无私屑焉”,如果父母虐待子女,那就“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注:康有为:《大同书》。);他认为男女平等乃是天赋予人之权利,男尊女卑完全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公理,他说:“……以公共平等论,则若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
“公理”世界观无疑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的产物,一方面,它与程朱“天理”世界观存在着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西学”无疑是康有为他们构筑新世界观的重要精神资源,这种世界观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一样,高度肯定人的价值地位,人的价值体现为与天地宇宙的整合。
其次,关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西方权利学说认为,在个人与社会整体、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上,它持个人主义和国家工具主义观念。认为个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赋予其终极价值。而国家仅是保护和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国家一切政治权力运行的最根本和最终的目的在于保护和保障基于人之本性的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实现,背离了这个根本目标,国家权力就丧失了正当性根据。康有为等人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第一,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整套纲常伦理来加以正当化论证和制度化调整的,并由此形成了颇有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这个文化视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被消融在群体的神圣高调之中,个体权利意识缺乏滋生、培育的土壤。康有为等人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必须走出虚假的群体利益,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说:“礼者,各因其宜,而拱持其情,合安其危,而人已各得矣。夫天生人必有情欲,圣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然纵欲太过,则争夺无厌,故立礼以持之,许其近尽,而禁其逾越。尽圣人之制作,不过为众人持情而已。夫与人必生危险,常人日求自安,不知所以合之。然自保太过,侵人太甚,故立礼以合之,令有公益,而各得自卫,故尽圣人之经营,不过为众人保险而已……圣人之礼,无往非须乎天地,顺乎人情,顺乎时宜。”(注:康有为:《孟子微》。)“礼”等制度的制作不再是为了人的“忠”、“孝”之类德性的实现,人的自然欲求通过“礼”(制度)而能够比较顺利而合理地得以满足,在近代思想家看来,国家政治权力如果离开了这个价值基点,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存在了。
第二,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传统中国“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在戊戌新一代之前,中国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只有发达的天下观、君主观和家族观,天下为皇帝一人之天下,民权与国家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批判,并且指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未来社会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如康有为设想:大同之世,没有国家,没有君主,没有军队,没有监狱,只有民主选举出来的“公政府”;大同之世,无等级之分,无种族之别,无贵无贱,无差无好,男女无别,人人平等,天下平等。而且,康有为在《孟子微》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他在解释孟子“民为贵”之说时指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之事,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人。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注:康有为:《孟子微》。)这已经完全是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了。《孟子微》虽然是戊戌变法以后才发表的,但这些思想的形成则应是戊戌变法时期或更早些。
然而,康有为的大同设想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因为按大同设想,皇帝当废,官僚当走,土地当公,民主制度应立即实行,但他当时进行的却是依靠皇帝实行渐进的变法。他甚至不敢将《大同书》、《孟子微》等书公布于世,“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几,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注:张柏侦:《南海康先生传》,《沧海丛书》,1932年版,第66页。)只有联系近代中国实际,才能真正理解康有为的权利学说和他的矛盾。
二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列强凭借他们的坚船利炮逐步把中国变为了他们的半殖民地。摆脱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近代中国的其他问题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有它的存在意义。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是必须“变”。近代中国要摆脱贫困屈辱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以旧的方式,维持现状,独立于世界的现代化之外,必须“变”。同时,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必须“全变”。不仅要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军队,而且要创造富国强兵得以实现的一整套社会条件,因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变迁。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而且,中国的现代化总体上属后发外生型,即在列强的侵扰下,中国为了生存自救,被迫中止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是从一种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强制性变迁,它的主体是国家。因此,近代中国要走向繁荣富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进现代化事业。从而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又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必须建立和强化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军队和警察,以此保证国家推动社会现代化过程(注:苏力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权威。而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论无疑与这一点产生矛盾。因为西方权利学说是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产物,这种思想与必须建立强有力国家政权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变革走向富强的中国实际产生矛盾。因此,康有为不得不在维新运动中走一条与自己思想不一致的路。他之所以主张君主立宪制,是因为他想依赖于皇帝的权威而实现变革,以使中国走向富强。他指出:“天下之命,悬于人君”(注:康有为:《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灾折》,1889年1月17日。),“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言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因此“今日地球各国之中”,中国变法维新最有条件,“一二人谋之,天下率从之,以中国治强,犹反掌也。”(注:康有为:《阖辟篇》,作于1877年前。)虽然他也强调设议院,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并非为了保护人民个人之权利,而是为“设议院以通下情”,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他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注: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这一思想与社会契约论思想是不一致的。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宪政是作为一种社会契约而不存在的,他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对权力专制和腐败的深深不信任而确立起来的用理性的制度来约束权力,而约束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平衡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因此,康有为学说的理论与他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他提出了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类似的权利学说,而在实践中却走的依靠皇帝实行的变法,民权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补充。这种矛盾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梁启超则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他试图将权利学说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统一起来,使他的权利学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他在自然权利观与国家权利正当性方面同康有为的权利理论完全一致。他宣传“人人有自主之权”,把“权利”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他说:“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重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保权利两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苟不尔者,则忽丧其所以为人之资格,而与禽兽立于同等地位。”(注:梁启超:《新民论》、《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第31、36、104页。)他赞成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他指出:“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政府之所以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民约之义法国硕儒卢梭倡之,近儒每驳其误,但谓此义为反于国家起源之历史则可,谓其谬于国家成立之原理则不可,虽憎卢梭者亦无以难也。”(注: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第1页。)
其次,他将权利学说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联系起来。他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言民权。”(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第73页。)由于将权利学说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联系起来,使得梁启超的权利学说呈现出中国式特点:①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他强调个人权利的基础性地位,但他亦强调作为群体性的“公”的权利和个人对群体的义务。梁启超指出:“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注:梁启超:《新民论》、《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第31、36、104页。)“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应相均。”梁启超在这里既肯定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又对个人之于群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给予了高度重视,这甚至是个人权利的内在要求。之所以如此,其现实原因在于,维新派思想家们面对中国当时的积弱挨打的现状,极大地希望“民权”的理念能够激活中国集体性活力。这样使得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区别在于西方自然权利学说,西方自然权利学说凸显的是个人权利时神圣性。②在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关系问题上,他在将国家政府权力的正当性落实在人们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同时,又把国家视为高于政府和人民,代表最高主权而有其独立人格之存在。1902年他指出“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注: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第1页。)1903年,他在介绍伯伦兹的国家学说时指出:“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注: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这里国家很明显被界定和注解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有机实体。这与西方的自然权利学说有所区别。西方的自然权利学说是从机械论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国家的,也就是说,国家除了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外,没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它因此根本不可能在价值上高于个体,它不过既为实现的目的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而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放弃了民权。他试图将国家主义与民权统一起来,在肯定国家主权至上、强调个人对国家之责任的同时,又不至于忽略和遗忘个人自由权利这一终极价值。他指出:“主权者,绝对者也,无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为源泉。人民皆自由于国家主权所赋予之自由范围内,而不可不服从主权。”(注: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
但是,将个人权利与国家主义理论统一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对民族和国家整体性利益的关注常常使他们将个人自由和权利等闲视之,而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审视也因此转移了方向。就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注: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并据此得出结论说:“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注: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民国初年,已是国权党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在检讨所谓“极端之民权说”的不完善之后,明确指出:“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家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况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此宪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注: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9页。)在此看来,此时的梁启超在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同时,将个人自由与权利问题逐渐淡化和遗忘。
因此,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权观的产生与变异的过程。首先康有为及梁启超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权利学说的内在精神一致的民权学说,但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康有为民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他走了一条依赖皇帝变法的道路,而梁启超试图化解康有为的这一矛盾,试图将民权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统一起来,使民权理论获得更多的现实性,同时也极大摧残了民权学说,个人权利与国家主义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关注民族和国家整体性利益时常常淡漠了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审视也因此转移了方向,以致于权利理论最后淹灭在国家主义的氛围之中。
标签:梁启超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契约论论文; 饮冰室合集论文; 公理系统论文; 大同书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