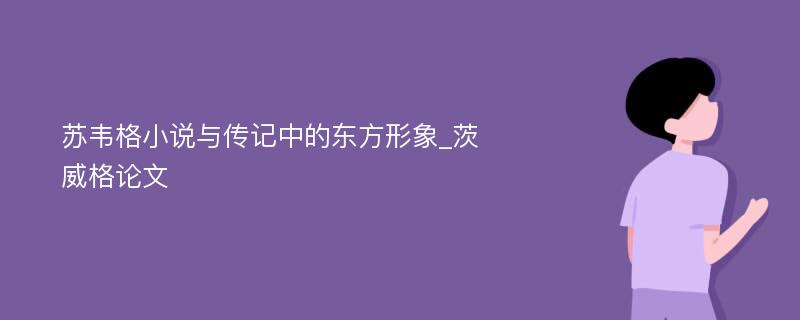
茨威格小说和传记中的东方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形象论文,茨威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蒂芬·茨威格是著名的奥地利籍犹太裔作家。这位饱受法西斯摧残、流亡巴西最后 绝望自杀的作家颇受世界关注。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追求一直是倍受瞩目的焦 点。在许多评论者看来,他“用世界主义的目光关注全人类的命运,用激情点燃人们的 心灵,用人道维护正义与和平”(注:雷庆锐:《关爱人性 追求人道——论茨威格小 说创作的主题意识》,《新疆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7月。),“他用德语思考和写作 ,但他的心灵却是超越民族、国家、语言,而属于欧洲、属于世界。”(注:杨荣:《 斯蒂芬·茨威格的“维也纳情结”》,《中州学刊》2002年4月。)这的确是对茨威格为 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所做的努力的褒扬。然而,这也许只是茨威格人生观与世界观的一 面。茨威格有不少作品涉及到东方形象,如印度智者维拉塔(《永恒的目光》)、以色列 先母拉结(《智激上帝的拉结》)、犹太民族“纯洁的人和明智的人”拉比埃利泽尔(《 蜡烛台记》)等都是他衷心赞美的东方形象。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他对东方叙述的笔 调与措辞并没有显示出一个“世界主义者”应有的公正。
一
茨威格一生著作颇丰,体裁多样,以中短篇小说和传记最富盛名。我们看到在他的作 品中主要存在两种东方形象:(一)弱者东方;(二)强者东方。
(一)作为弱者的东方形象主要出现在《热带癫狂症患者》、《昨日的世界》、《一个 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作品中。这些东方形象的特征是落后和怪异。
《热带癫狂症患者》发表于1922年,是茨威格成熟期的作品。故事发生在荷属殖民地 马来西亚。一位荷兰巨商的妻子在丈夫去美国期间和一位年轻军官有染并怀有身孕。为 了在她丈夫回来之前掩盖事实,她想请在殖民地工作的欧洲医生来堕胎,并许以重金。 但是她的高傲伤害了医生而拒绝了她的要求。当医生后悔并赶到时,她已经让一个肮脏 的“中国老太婆”做了不科学的人流,生命奄奄一息。医生陪她度过最后一夜。为了彻 底替妇人保密,在回欧洲的客轮上,医生携带妇人的棺材坠入海底,故事本身没什么特 别,只是有些叙述显得比较重要,作家在这里使用的词汇充分体现出他对殖民地的贬低 和歧视:
“我几乎完全在土人和牲畜之间过了8年”(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 二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11、11、26、40、45页。)。
“在这不堪忍受的孤独中,在这噬蚀人的灵魂、敲骨吸髓的可恶的国家里,我已经不 知羞耻为何物了。”(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二卷,高中甫编,西安 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11、11、26、40、45页。)
“一个欧洲人从大城市落到这个满是沼泽的可恨的鬼地方来,不知怎地就失去了自己 的本来面目,迟早总要出点毛病,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另一些人变成凶残的野兽, 每个人都会染上一点坏毛病。”(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二卷,高中 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11、11、26、40、45页。)
异乡人不能适应新环境很平常,但医生将欧洲人的“毛病”完全归因为那个“可恨的 鬼地方”却是不公平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医生之所以会来殖民地工作,恰恰是 因为他在莱比锡医院工作时因结交女友不慎而贪污公款,以至名声破败不得不离开欧洲 ;他起初拒绝她仅仅是出于“男人的反抗心理、屈辱感”,而“出生名门”的女主人公 则是丈夫离开才5个月就红杏出墙,而诱惑她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白人军官。
再看这位医生对马来侍者的描述:
“一个黄种贱胚抓住白人‘老爷’的自行车而且命令他,命令‘老爷’留在原地,这 是多么无礼。我不由分说给了他一耳光……幸亏我身边没有手枪,否则我一定会对这个 蛮子开一枪。”(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二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 社1995年5月版,第10、11、11、26、40、45页。)
“我真想再揍他一下,但是……他对她那种狗似的忠诚感动了我。”(注:[奥]茨威格 :《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二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11、11、2 6、40、45页。)
“他看着我,浑身发抖,好像等着挨打似的。……这样一个未开化的生物怎么会如此 懂事?为什么这类完全没有文化的迟钝的人在某些瞬间会有如此温柔的感情?”(注:[奥 ]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二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11 、11、26、40、45页。)
这几段叙述语言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套话的使用。套话是“stereotype”的汉译 ,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 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2、24、7页。)。 它忽视个体情感特征,是对异国形象的集体描述,引文中“黄种贱胚”、“未开化”、 “没有文化”、“迟钝”等语汇都属于欧洲对他者形象描述时使用的否定性套话。“黄 种贱胚”是基于白人优越论产生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未开化”、“没有文化”、“ 迟钝”是基于欧洲文明优越论对殖民地提出的蔑视。形象学认为:“我想言说他者(最 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者,而言说了自我 。”(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2、24、7页 。)黄种侍者的忠诚是作家要表达的表层意义,而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是叙述达到的最后 效果。尽管作家写作时也许并未有清醒的意识。
对印度,作家也有类似的描写。一位欧洲妇人声称她丈夫因为“从前在热带地方的长 年生活使他得了肝脏病”,她所指的“热带”就是印度,因为他丈夫曾在“驻印度的英 国军队里服务过10年”(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三卷,高中甫编,西 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17、668页。)(《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在自传 《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这样回忆他的印度之行: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 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注:[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 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205、206、13、14页。)
“我看到的印度,并不像皮埃尔·洛蒂所描写的那样:给它涂上一层颇具‘浪漫主义 ’的粉红色彩,而是一个令人警觉和注目的国家。这是指那些我新认识的人,那些另一 个世界和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些人和一个作家在欧洲内地通常遇见的完全不同。”(注 :[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三联书 店1991年3月版,第205、206、13、14页。)
我们不能否认作家对印度人民的穷困饱含同情,但相同文字也传递出另外的信息。作 家到印度之前,他思维中已经存在一个先验的印度,或者说想象中的印度。这想象来自 文学作品和前人的描述。“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 象密不可分……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其 他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是社会中之 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 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7月版,第12、24、7页。)因而,茨威格能够接触的关于印度的文本,并不是现实的 印度,而是欧洲集体想象中的印度。当他亲自来印度旅行时,除了惊诧现实印度与先验 印度的差异外,他还理所当然地将印度划分在“另一个世界”。他说过:“旅游使我再 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注:《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1 0月版,第49、393、438~439、418页。)。在东方的旅行让他真切的感受到了欧洲人的 优越感。这种心态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的产物。
(二)茨威格笔下也有作为强势力量的东方形象,其特征是强悍和野蛮。
在《拜占庭的陷落》中,作家塑造了土耳其苏丹马霍梅特这样一个强悍的侵略者形象 。马霍梅特集多种类型的性格于一身:“既虔诚又残暴;既热情又阴险;既有教养,酷 爱艺术,能阅读用拉丁文写的恺撒和其他古罗马人的传记,同时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野 蛮人……他证明自己一身而三任:不知疲倦的工人,凶悍勇猛的战士,厚颜无耻的外交 家。”(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一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 月版,第301、322、317、548、571页。)他智勇双全,阴险狡诈,表面与邻国定下互不 侵犯的盟约,暗地里却积蓄力量,准备攻打拜占庭。当时,拜占庭被视为西方文化神圣 的象征。占领拜占庭也就意味着土耳其默罕莫德对基督的胜利。强大坚实的军事力量, 蓄谋已久的计划,拜占庭方面的内部不和,马霍梅特终于如愿以偿。
在《大探险家》中,当葡萄牙殖民者妄图以坚船利炮打开东西不合理贸易的大门时, 马六甲苏丹机警地看出了气势汹汹的来者心怀不轨,他佯装热情招待,暗中分散敌人力 量并给以重创,维护了民族利益。马克坦小岛的邦主也拒绝给殖民者供给,在和以麦哲 伦为首的殖民者交战时,他英勇善战,将麦哲伦刺于马下,并且不愿“为了几面小镜子 、玻璃珠和色彩斑斓的天鹅绒而卖掉敌人的尸体”(注:[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 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71、73、156、170、73、35 、23、24页。),显示出胜利者的尊严。在《蜡烛台记》中,茨威格也记述了古罗马多 次被东方民族如匈奴、波斯、巴比伦等东方民族侵占的史实。那时的东方处于主动地位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强者角色。
茨威格笔下的古老东方是富庶迷人的。马六甲海港“停泊的船只比世界上任何一地都 多。帆樯林立,各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暹罗的大的、小的、白色的、彩色的船只, 中国式的帆船、马来人那装有桨叉托架的帆船纷纷挤进宽阔的泊地。”(注:[奥]斯蒂 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71、73 、156、170、73、35、23、24页。)菲律宾的一个小岛“风景如画,气候条件优越,犹 如人间天堂:土著人热情好客,依旧生活在无忧无虑、和平安宁、勿需操劳的黄金时代 。”(注:[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 年1月版,第171、73、156、170、73、35、23、24页。)
需要思考的是,茨威格是出于真情赞美东方吗?答案是否定的,拜占庭被占领在作家看 来是西方文明的耻辱,“整个西方为它(十字架)的倒塌而震颤。惊耗在罗马,在热内亚 ,在威尼斯发出回响。”(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一卷,高中甫编, 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1、322、317、548、571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称马 霍梅特为“暴君”和“杀人放火的野蛮人”(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 一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1、322、317、548、571页。)。在《 蜡烛台记》中,他将曾经侵占罗马的匈奴可汗阿提拉描述为“异教的”“可怕的”(注 :[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一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 01、322、317、548、571页。)的人,将曾经占领耶路撒冷的东方国家巴比伦称为“野 蛮民族”和“魔鬼的奴隶”(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一卷,高中甫编 ,西安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1、322、317、548、571页。)。而击败麦哲伦的西拉 普拉普被作家贬损为可笑的“人虫”和“令人怜悯的蛮夷”(注:[奥]斯蒂芬·茨威格 :《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71、73、156、170 、73、35、23、24页。)。古老的东方确实富饶瑰丽,但茨威格对东方的赞美文字中却 包含了另一种欲念,那就是占有。葡萄牙人本为殖民来东方探险,马六甲的繁荣景象更 加刺激了他们的贪欲,“葡萄牙人从船上远眺这座通都大邑,不觉惊叹万分,他们渴望 得到这颗在刺目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东方明珠,它,这无价的宝石应该镶嵌在葡萄牙的王 冠上。”(注:[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 000年1月版,第171、73、156、170、73、35、23、24页。)当马六甲苏丹识破葡萄牙人 的诡计后,茨威格对马六甲人的描述就不再“客气”了:“由于苏萨的警觉以及麦哲伦 的敏捷,马来人的袭击遭到了失败。至于那些上了岸的葡萄牙人情况就大为不妙了。他 们毫不怀疑对方,没有思想准备,分散在马路上,遭遇数千名奸诈之敌的袭击。”(注 :[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第171、73、156、170、73、35、23、24页。)茨威格对殖民行为的合理性没有丝毫质 疑,本属正义的反抗被贬损为“奸诈之敌”的“袭击”。而先前对马六甲苏丹英勇的描 写无非是为了更加鲜明地衬托欧洲人的“警觉”和“敏捷”。如此是非不分的描述很难 让人信服茨威格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二
无论是弱者东方还是强者东方在茨威格笔下都是作为与文明欧洲和文明白人相对立的 身份出现的,并没有得到作家公正的描写。无论东方形象在作家笔下以何种面目出现, 都有深刻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古代东方的富庶和强大是举世公认的史实。因此,茨威格笔下的古代东 方形象是强盛的、智慧的,如土耳其苏丹马霍梅特、马六甲苏丹和印度智者维拉塔,到 了近代,西方不断向东殖民,东方成了他们的财富来源。在其殖民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殖 民主义话语体系,给野蛮残酷的殖民事业套上神圣的光环,掩盖了殖民的血腥和罪恶。 茨威格的叙述正是殖民话语的有力证明。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为海外殖民地的分割而争执 时,罗马教皇“明白无误、光明正大的把各民族、国家、岛屿和海洋分赠给这两个国家 。”(注:[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000 年1月版,第171、73、156、170、73、35、23、24页。)如此乖谬悖理的事情被茨威格 解释得有理有据:“乍一看,这豁达与慷慨使人感到十分乖谬,根本无视世界其他国家 就把整个世界轻易分赠出去,但我们不得不赞许这种和平解决方法是历史上罕见的理智 行为。”(注:[奥]斯蒂芬·茨威格:《大探险家》,黄明嘉、卫茂平译,漓江出版社2 000年1月版,第171、73、156、170、73、35、23、24页。)在茨威格的时代,欧洲在世 界范围内拥有广袤的殖民地。从物质上看,它远远高于东方,因此,茨威格以一种高高 在上的优越感来蔑视东方,也就很自然了。
从当时流行的创作模式看,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东方大多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爱对印度的印象就是炎热和死亡:“我觉得 ,在印度的太阳照射下,我活不了太久……我去印度就是过早地走向死亡。”(注:[英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赵琪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02页。)海 涅笔下的“中国形象”充满了“古怪”和“奇物”的异国情调;哲学大师黑格尔把“中 国形象”贬抑到了极点,并且完全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局外(注:《中国文学在德国 》,曹卫东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9、393、438~439、418页。);1877年 至1880年,德国科学家克莱特纳(Gustav Kreitner)称中国人天生就是说谎者(注:[德]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8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总结到:“在我第二章分析的19世纪作家中……他们几乎原 封不动地沿袭了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堕怠性”(注:[美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0月 版,第262页。),这些作家包括赫南、马克思、福楼拜、内瓦尔等人。由此我们得知, 茨威格对东方的负面描述非常接近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从个人身份来看,茨威格是位犹太裔的欧洲人。经过几千年的流浪,犹太民族急切渴 望过一种安定生活。他们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努力“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 普遍的人性。”(注:[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205、206、13、14页。)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分析 ,外来者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有效的捷径之一就是通过叙事话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 份,表明自己既有人类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为了尽快获得欧洲主流社会的 认同,茨威格积极主动使用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他“好像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历史和 世界的,那眼镜有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名字——‘欧洲中心主义。’”(注:留白:《茨 威格的瑕疵》,《读书》2002年4月号。)于是,历史上曾经强大的东方给茨威格留下的 印象只是“强悍”和“野蛮”,而不是“文明”;当象征西方文明的拜占庭被东方民族 占领时,他心中充满了对西方文明堕落的失望和对东方的憎恨。
但是,茨威格也有强烈的民族情结。在当时,反犹情绪十分旺盛。这可以通过一个例 子来说明;“马克·吐温于1896年在维也纳发表演讲,弗洛伊德也到场了。因为马克· 吐温有很多朋友是犹太人,他的女儿也嫁给了俄国犹太裔指挥家奥希普,所以维也纳报 纸骂他同情犹太人,甚至说马克·吐温就是犹太人。1898年前后法、比、奥、德、俄等 国正为犹太裔法国军官德赖法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马克·吐温在维也纳挺身而出为他 辩护。”(注:《新编美国文学史》,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朱刚主撰,上海外语教学 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9页。)
于是他在《蜡烛台记》、《智激上帝的拉结》、《雪中》和《生命的奇迹》等作品中 热情歌颂自己的先民,为犹太民族受到的野蛮待遇而痛心疾首。对拉结和拉比埃利泽尔 的忠诚赞美,就体现出作家强烈的民族情结。不过对其它同样受压迫的民族,他就很少 同情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尽管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东 方充满了敌意,“黄祸”之论泛滥于整个西方,然而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有道德良知的知 识分子用文化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发难,要求停止殖民,放弃霸权,变征服东方为 学习东方。德国作家卫礼贤“坚决批判西方文化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赫尔曼·海塞 (1877—1962)嘲笑英国人是“天生的殖民者”,称在马来西亚原始森林犯下滔天罪行的 白种人为“强盗”和“刽子手”(注:《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花城出版社200 2年10月版,第49、393、438~439、418页。),伊丽莎白·冯·海京说:“殖民的幌子 不管多么堂皇,说穿了就是两个字‘欲望’……欧洲所谓的‘进步’,完全是一种意识 形态,是在替其‘欲望’找借口,这种‘进步’是建立在对弱者的褫夺和镇压上的。” (注:《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9、393、438~4 39、418页。)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更是为世界各个被压迫的民族摇旗呐喊。然而茨威格 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进步的动向,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如《大探险家》《昨日的世界》 中都没有改变对东方的负面态度,仍然尽情为殖民主义高唱赞歌,尽管他当时对欧洲文 明已深感失望。
茨威格认为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至少他觉得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他成长的维也纳是 座历史文化古城,他说那里的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 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注:[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 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205、206、13、14页。)。他在 自己的简历中写到:“我的目光总是注视着世界主义,我的思想远离开赤裸裸的民族主 义。”(注:[奥]茨威格:《茨威格小说全集》第三卷,高中甫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5 月版,第517、668页。)然而事实上,茨威格从小接受着典型的欧洲教育,他在思想上 很难逃脱欧洲中心主义樊篱。
“在获得世界观的时候,人们总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是和他采 取相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切社会分子之集团。我们全都是这样那样的顺从主义者 ,总是群中之人或集体之人。”(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这种“集体之人”的特性决定了人必须 受社会的制约。就茨威格而言,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是由他的欧洲人身份和犹太血统 制约而成的。人毕竟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因而也就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影响。我们肯 定茨威格对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他对道德沦丧的谴责、对残酷战争的批判和对良知与 正义的呼唤都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他当成空地里的英雄去膜拜 ,而是应该恢复他的完整性,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 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环绕先贤的文化生态环境做更深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