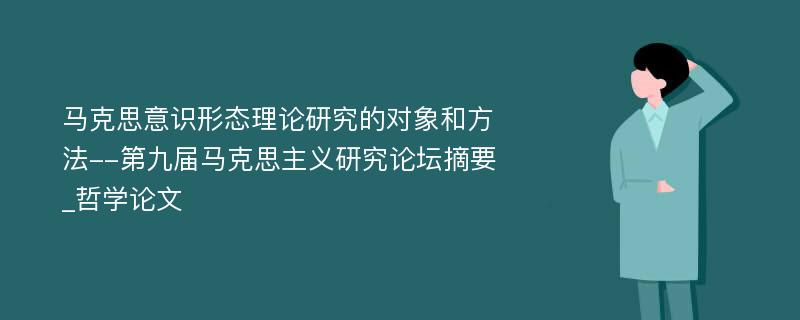
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第九届马克思学论坛”会议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第九届论文,摘要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8-0023-10
2008年12月19日,马克思学论坛第9次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张秀琴副教授做了题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专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和中央编译局鲁克俭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重点评析。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委党校、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了本次会议讨论。以下是大会发言内容摘要(按照发言先后顺序):
张秀琴(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①。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议题,因此,以意识形态问题为切入点,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比较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意识形态学说,并以此梳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基本观点(它的发生、构成、演化和它的实践关怀与可能的未来),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发展史的脉络,是我十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研究的主攻方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作一汇报。
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即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它包括马克思本人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述。该报告立足于马克思毕生(已公开出版的)与意识形态论主题相关的代表性文本(包括手稿、笔记、书信和论著等),力图概括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轮廓,它主要包括:第一,意识形态的概念定义、基本类型及主要特征。这是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上来回答意识形态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主要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第二,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历史影响及其实现途径。这是从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意义的角度来回答意识形态能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做好的问题,它同时也主要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
我的基本观点:首先,从认识论基础来看,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观念或意识系统,但它既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一般意识,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意识或观念的范围,而是渗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观念意识,即既表现为理论层面的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艺术和道德等基本形式;又表现为制度层面的政治法律制度与设施、宗教仪式、艺术样式、道德规范、哲学世界观和生活组织方式等日益丰富的市民社会或公共生活领域的制度系统;同时意识形态还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活动,这个领域,是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学院哲学意识形态和民间常识意识形态具体互动而表达和延伸出来的人们的具体生活状况。其次,从方法论框架来看,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主要研究的就是批判的方法,特别是异化批判和拜物教批判。最后,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逻辑结构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批判活动,即哲学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和黑格尔派)批判、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法国政治思潮和实践)批判、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批判。这三者既表现出历时性,又表现出共时性②。
文本研究并不旨在揭示业已在“事后”达到成熟状态的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是如何在其各个时期特别是早期文本中就已初具规模的,而是要探索它在各个时期不同文本中如何借助于不同的范畴群、丛结式的论点而得到具有差异性的理解和阐述的,并以此来揭示和梳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逻辑结构和论述层次。正是基于此,我把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文本演化逻辑划分为三个阶段:1844年之前的第一阶段、1845年至1866年的第二阶段,以及1867年以后的第三阶段③。
在第一阶段(1840-1844年),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虚构④的花朵”来说明意识形态是“颠倒”主客体关系的“神话”。在第一阶段,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概念已正式出现在文本中⑤,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概念群,以辅助说明意识形态的含义、属性和功能,它们包括:“颠倒”、“神话”、“空洞的假说”、“浪漫的幻想”以及“虚构的花朵”等。尽管马克思在这里已开始使用德语的意识形态一词,但他主要还是在传统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思辨哲学的主客体关系中来探讨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第二,马克思还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如政治、法律、宗教乃至文化等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领域进行了批判,但他主要是从哲学意识形态的视角,以费尔巴哈色彩的唯物主义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分析。第三,马克思由此延伸出意识形态论的另外一个维度,即批判的方法,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赋予了这一批判方法以逻辑结构,这就是异化批判。这是一个深受黑格尔影响的逻辑结构。因为有了异化范畴,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颠倒和虚幻等属性的分析就有了一个逻辑的落脚点。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所包含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意识形态是什么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说明,特别是富有马克思特色的比喻性、解释性和批判性说明。但这一说明仍然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因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先是把“现象”当作“现实”,以后又把“事实”当作“现实”,接着又把物质的、直接的感性“生活”当作“现实”。现实概念在这里虽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马克思依然没有把它确立在自己的理论所期望达到的高度,即用“实践”范畴来恰当地说明主客体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互动张力关系网络中所延伸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活动空间和价值表现。而这一具有超越性的高度,是在第二阶段形成的。
在第二阶段(1845-1866年),马克思用“雅鲁斯的脑袋”来比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战斗口号和衣服”。这一阶段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正式形成,首先表现在因称谓的变化而带来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转向:从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立场转向政治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开始正式称呼黑格尔以及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体系为“意识形态”(而不像过去一直所称呼的思辨哲学或“唯心主义”⑥),并称他们本人为“意识形态家”而不仅是“唯心主义者”⑦。这不是简单的称谓上的变化,它标志着马克思通过批判他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德国哲学”,对自己过去的意识形态观开始进行清算,即过去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或“黑格尔体系的基地”,而在这样基地上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只是“哲学批判”,即立足于哲学意识形态对宗教和神学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尽管也有政治国家和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但也是把后者归结为前者之后再进行批判。
在第三阶段(1867-1883年),我们可以用马克思曾经使用的“玫瑰色”的资本来形象说明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这一阶段马克思主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群,回答的是意识形态论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结构体系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表现出它的一系列特征和属性,并因此完成了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一句话,意识形态是如何干好它能干的事的。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发现,意识形态对于自己的掌握者来说,至多是悬挂在头顶上的剑(既有可能砍掉下面的人的脑袋,也有可能斩断绑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对于其他人群来说,则只能是鞭子或绳索。马克思的《资本论》⑧,就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次最为系统、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批判,马克思完善了自己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并发展了自己业已建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然这一过程,是与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独特的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法,它既是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即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写作之前的其他一些经济学手稿中相关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从拜物教形成的视角,通过对社会关系、劳动、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的抽象化分析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现象所做的深入而细致的批判。这是马克思继之前特别是1859年以来的经济学⑨研究,最终正式完成了从最早的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经由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向经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转变的标志。
鲁克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首先,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研究应该注重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既要避免因不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陷入低水平重复,又要避免直接将国外学者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而不告诉读者。报告人的做法比较合乎学术规范,既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阶段划分的不同观点,又分析了这些不同观点的不足之处,并进而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其次,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第一个阶段的探讨,有进一步开阔研究思路的必要。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在《晚近的哲学家》(写于1844年5月,发表于1845年6月)已经明确有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利意识不过是自利实践的理论表达。没有自利的实践,自利意识就不可想象,就像没有罪,罪意识就不可想象一样”。而鲍威尔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明确提出:宗教是“虚幻的”,是“装饰在锁链上的花朵”,是“人民的鸦片”。这就说明,尽管Ideologie这个德文词是马克思独立提出的,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内容的把握是有其思想来源的。最后,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是否是“虚假意识”的问题有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应该从意识形态“真”、“假”二元对立的思路中跳出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既不“真”,也不“假”,而是不可证伪的。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实际上将实证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并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无所谓“真”“假”,但却是有意义的,比如它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论证。在“科学”与“哲学”能够明确“划界”的前提下,“科学的意识形态”正像“科学的哲学”一样,是非常不严密的说法。
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秀琴老师在报告中谈到的一些问题给我很大启发。这篇文章的总体认识是“意识形态”是超越了古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把握是很准确的,我个人非常赞同。对于这一判断,我想再做进一步增补。正如马克思哲学的其他概念一样,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一直受到人们的误解。意识形态是一种反映特定经济形态、阶级利益的观念或意识系统,这没有错;人们认为,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是不同的,通常又将它阐释为一种“虚幻意识”,这也没有错;人们还认为,意识形态要反映并服务于阶级意识,这都没有错。这三个肯定通常就是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但问题是:当我们在把握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开始就把虚幻看作意识形态的一种错误,一种虚幻或颠倒现实的观念系统怎么能够反映阶级利益?一种虚幻或颠倒现实的观念系统又怎么能够服务于阶级利益?除非统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比阶级的条件更基本、更源始。而无论如何,这就是马克思的看法。他用十个字的命题清楚地表达统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存在关系比阶级的条件更基本、更源始的观点,这个命题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哲学开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论境域,意识形态概念是以这个前阶级意识的“无知”天幕为背景的。为此,我提出两个命题用来说明我的这种解读:
命题1:在马克思那里,不可能将反映与被反映者、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作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区分和理解。马克思并不关心涉及“真理”、“意识形态”、“虚假”、“错误”这些特征的知识划界。他也不关心如何在幻象背后寻找更加实质性的真理这件事。相反,他关心的是有关“活动”的前提,关心确定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性。
命题2:既然如此,就不能指望马克思将基于社会阶级分裂状况之意识形态虚幻作认识论的定位,尽管常常有人大费周章地认为他确实这样做了。
我认为,这两个命题已经足以提出一个与古典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区别,大家在提到马克思的时候可能常常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划分。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虚幻定位问题:如果意识形态是“虚幻意识”或“错误观念”的话,那么,我们该怎样把握意识形态虚幻维度?意识形态的虚幻究竟何在?是存在于主体的认识中,还是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答案是明白的:正如有人肯定,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存在于主体的认识中、观念中。与此同时,许多有关意识形态概念的讨论大致也是在“知”或“认识”的那个方面规定自己的视域。这个观点的要害在于,它试图将意识形态虚幻还原为一个视角,或将它等同于可笑的“心理主义”那样的东西。结果,在这种意识形态虚幻的定位之下,我们立即想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家的形象,一种人类历久弥新的解放的兴趣,一种启蒙家的信念。启蒙哲学家相信,对意识形态的批评没有被他所批评的缺陷所伤害,没有被意识形态“虚幻”所伤害。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全靠他们具有一个阿基米德支点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全知全能的历史观察者”存在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阿基米德支点上,一种具有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才能产生出来。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受这种想法误导,也从这种立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只是强调西方哲学意识形态的疏忽,强调意识形态是用来指称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马克思的理论敌手的“意识”或“观念”,是不同于马克思本人的别人的“意识”或“观念”,是自称能够获得真理却是个谎言的系统,是对统治阶级有辩护作用的意识或观念。一句话,是错误和谎言的代名词。显然这已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迷雾。即使康德也已经在“知识论”的范围内提出了告诉,那种对敌手采取批判的姿态,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姿态是多少在耍孩子气。而马克思自己做的榜样是:应该恰如其分地批判他的哲学前辈,也就是不能从知识意义上去批判他的哲学前辈。
第三个问题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另一面”问题:我们在面对那些被扭曲的社会现实时,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通常就被理解为“揭露”、“批判”。这种“揭露”、“批判”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事批判,从而明确批判的必然性。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著作的题名很多就标有“批判”两个字。不过,“批判”这一词本来是用来表明对某事某物持贬义的立场的意思。所以,它被滥用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如果我们认为只要通过批判抛弃扭曲的意识形态就可天下太平,那么这差不多只是反思的天真;如果我们认为祛除意识形态虚幻在于“揭露”、“批判”,使用“揭面具”、“撕面纱”等性质的隐喻,那么我们对切中“隐藏的现实”的关切就潜在危险。这次又让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没有穿衣服的皇帝”。正如揭露走在大街游行队伍中的没穿衣服的那个皇帝而令其出丑的不是那些围观的大人,而是那个天真的小孩。小孩之所以那么天真,在于他没有感染意识形态病菌,他不懂大人那一套,大人就反过来要膜拜那个小孩。把他当作偶像,把他的话当作绝对真理;小孩在这种神化中已经升人绝对知识行列,这个小孩的行为在知识层次上恰恰就是有关现代意识形态生动的例子。用马克思哲学来解读这个童话,结论是,扭曲的现实恰恰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而自我复制的。因此,马克思才认为要搞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得参照宗教世界中的情形。
第四个问题是意识形态最为基本的定义出自《资本论》。《资本论》里讲,意识形态的虚幻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是通过人们的“意识”。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虚幻存在的特性是它的“物质性”,但是这种“物质性”是被某种“虚幻意识”(或它的“纯粹性”)所掩盖的。用阿尔都塞的话讲,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本身。这些话说明了,为什么在黑格尔的伟大哲学思辨失败之后,马克思就不能再满足于讨论哲学的错误本身,而是应当更进一步去探讨这种错误的存在论根源。从马克思开启的存在论境域看,“青年黑格尔派”“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对此他们真的一无所知。意识形态虚幻本身成了他们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事实上也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比如,有些人明明很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也很清楚事物的真相,但是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如果认为这是因为看上去作为某个人的理性虚弱,看待事物难免偏颇如此等等,那么要改变这种“错误认识”易如反掌:仿佛他当时不要这样想就行!可是,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就在你内心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现实中什么也没有变。因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以戏剧化形式生产幻象,你再来多一个想法就变成幻象的平方。我们明明知道从传统权威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仍然不自由,但我们仍然继续追寻这一自由观念。总之,用《资本论》的话来讲,好像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这样做了;而且,只要我们将某种程度是由现实保证来支撑的价值、教育、法律权威等等符号秩序体验为“真实而永久的”,它们就如此起作用了。这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和偶像崇拜,是我们共存的社会现实的存在论基础。第五个问题,这是一个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何理解意识形态“颠倒的颠倒”的隐喻之哲学性质。
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当前国内意识形态研究弄得非常玄,走的恰恰是与马克思相悖的研究路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式”这两词的区分,并且非常看重“形式”(form)的用法。那么,“意识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会是何者的形式呢?其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研究关注的正是某一形式与其他形式本身之间的关系,历史有个“内核”,而“形式”就像是历史“内核”(现实)的不同“衣服”。生产关系是第一层衣服,然后国家是第二层衣服,意识形式是第三层衣服。亦即“内核”加上关系就是一种形式,然后是形式的形式,亦即形式的平方和立方。马克思认识到,这些“形式”恰恰是对历史“内核”亦即现实的掩饰,不能就形式论形式,也不能站在一种形式上讨论另一种形式,而且形式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强调,“意识形态”与“意识形式”不同之处恰恰在于,要透过所有这些“形式”或者“衣服”去看待和分析历史现实即“内核”。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呢?这实际上涉及到所谓“意识形态的自反性”问题。马克思用“唯物史观”解构了意识形态,破解了意识形态的这种恶循环。因为马克思公然声明自己哲学的主体,明确声称自己乃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而不是像哲学史上那些代表某种特定立场却标榜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意识形态家”那般口是心非,对此,估计马克思是受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跳脱英国利益并代表世界主义的启发。由此,马克思真正将意识形态还原成作为“衣服”的意识形式,从而不再是意识形态。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始终不变的一点就是,马克思始终是将意识形态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应该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种幻想,直至后来,马克思也从未将其作为一种正面的东西来说明,因之马克思讲的是“反映各种社会冲突”的意识形态。第二个问题,张秀琴老师文中“对自己意识形态观点开始进行清算”的提法,似有不妥。因为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唯物史观的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本人还是用他自己的哲学去批判其在莱茵报时期所发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幻想,故不能说该时期马克思已经否定了自己从哲学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批评。此外,“没有历史”部分的口头表达与正式成文还有一定差距,意思有所出入。第三个问题,鲁克俭刚才的发言有些过于抬高赫斯,殊不知赫斯与马克思两者有很大的差别,赫斯更多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提出继承黑格尔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实践改变对象,对象又改变自身”这一最根本的思想。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最重要的思想,也有不妥之处,因之教科书上讲的唯物史观很难说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只讲生产力,却并没有说谁决定生产力发展,工具是人制造的,制造工具的思想又决定生产力,最终不就是思想观念决定一切么。事实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和根本不同在于,对整个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实践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唯物主义解释,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三条对人和环境关系的论述,意识形态包含在环境之中,如果说思想观念决定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思想观念仍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第一,考察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用的是从后思索的方法。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就需要找准典型形态并向后思索,这才是有预见性和理论价值的研究方式。因此张秀琴老师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可以消除研究过程中的“恐惧”,希望文中再加上意识形态论在当代的意义问题,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否属于真理范围,是否属于科学情境,如果意识形态既不属于真理范围又不属于科学情境,那么学者们聚在一起研究一个虚幻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不能用认识论来评判意识形态,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例如,从人类历史上来讲,早就有哲学、宗教、法律和国家等意识形式及制度,意识形态是否也有观念和组织这两个部分呢?那么应该用真理的、科学的还是观念的东西来鉴定这些现实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哲学问题。第二,关于意识形态的发生学问题。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或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然后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形态学来源于现象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究竟是继承了何人、何人著作?科学和真理是否等同?科学和真理究竟有何区别?在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无与其他学说的批判往来?希望学者们能够找出这些相互的驳诘,并从中找出真正科学性的东西。此外,文献研究虽不应被局限在一个过于狭窄的范围,但仍应抓住最经典的文本多花精力搞细搞透。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受该讨论启发,我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新探”为题来试着说一说如何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成果。张秀琴老师在文末所提出的一些“困惑”,非常出彩,足见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甚至比文章主体的论述更为精到。目前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否仅仅是一个贬义词,亦即“虚假意识”?如果像俞吾金那样回答“是”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在当代还有什么用处?马克思本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心,在19世纪50年代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中心,在19世纪60年代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中心,在19世纪70年代以《法兰西内战》和晚年笔记为中心,而西方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19世纪早期著作,而我们完全可以将研究重心后移,尤其关注《资本论》及其后的观点。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意识形态”主要是一个贬义词,当然也不乏中性用法的萌芽,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开始逐渐明显,从相关文本多处均可得到印证,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第42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否也可逻辑暗含着在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后,“工人阶级也有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第44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越来越……的思想”对于当代倡导的“普适价值”思想也很贴切;等等。进入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借助“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交易就是自由”等概念或命题更科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虚幻出现的原因,并将抽象的普适价值及其根基统一起来了,希望张秀琴老师对此进一步发掘。那么在马克思的晚年著作中,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否也有某些新观念的萌芽呢?不要忘记,法兰西内战中巴黎公社那时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是否会引起马克思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权是否也需要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是否是一套论证国家政权合理性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应留意列宁有关著述和葛兰西“思想领导权”理论对意识形态中性化的努力,创造性地回答当代的现实问题。最后,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是否是意识形态,我认为不能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原来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它第一是科学,第二在科学的基础上也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以这种二重性的态度来理解意识形态可能更好。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张秀琴老师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文本考察很扎实,无论是研究结论还是研究方法都让我很受启发。结合张老师的论文和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我谈几点体会。
首先,我对张老师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区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有些异议。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为“揭穿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这一“历史的任务”服务的。意识形态因其作为自我异化的表征和对此岸世界真理的遮蔽而被马克思所批判。意识形态作为整体“曲解”了人类史,马克思也是从整体上对之进行批判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哲学、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但并不能还原到这些领域。对于马克思而言,其对政治事件、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新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意识形态批判之后的实证研究——或者用恩格斯的说法: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顺便提及的是,张老师在文章中指出“经济是意识形态发生和发展的背后的本质和基础”,这一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经济意识形态是所有意识形态之根本”的说法则有失偏颇。
其次,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幻性(illusory)或虚假性(false)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小点看法:一是要把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幻性、虚假性问题与意识形态在历史中有真实的基础和发挥了真实的作用这个问题区分开来。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或虚假性,但从不否认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真实作用,而且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同时,虚幻或虚假的意识形态恰恰是由真实的历史现实造成的。二是我不同意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贬义词的说法。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或虚假性,只是表明其要被批判和证伪,并不能说明它是贬义词。正像我们说资本主义是要被批判和超越的,但不能说“资本主义”这个词是贬义的一样。三是我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还是虚假性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看来它是需要被批判和超越的。因此,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更多地应该指向意识形态虚幻或虚假的彼岸,那就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最后,我们应该从“历史科学”的反义词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所要正面考察的是“历史”,它包括自然史与人类历史两个相互制约的方面,但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他着重研究的是人类历史。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之谜最终要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解决: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但历史之谜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矛盾的解答。从人学或存在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历史之谜只能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前提下,而不是在“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才可能解答。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这一问题清楚地表述为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换言之,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及所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都源于这一矛盾。马克思所谓“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目的就在于证伪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历史之谜的解答。
袁吉富(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首先是三阶段的划分太过逻辑化,不一定很准确,例如将“商品拜物教”概括为一个阶段是否妥当?是否应该考察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社会意识理论中的地位?还有意识“花朵”与意识形态“虚构的花朵”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另一个问题也是有关意识形态虚幻性的解释。如果将社会意识理论作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两个角度来理解,那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将可能不同于非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这一点需要深挖。最后一个问题,文中第一部分将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否也有问题的。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博士论文选题以来,张秀琴一直持续关注意识形态专题,关注马克思本人及西方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治学路径,就是对该问题一如既往地长期钻研。目前研究中“痛说革命家史”的说法,多少忽略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前人的继承性。那么,应如何研究这种带有专题性质的研究呢?哪些思想值得探讨呢?
第一,应讨论马克思一生思想中持续关注的重要观点,前后反复谈论的思想;第二,必须通过马克思重大的思想和主旨来透视其系统演化;第三,必须针对其具体文本中的具体对象和具体环境来谈论问题。因为“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是一个原理性的看法,不能把马克思当时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视为对其精神实质的批判。易言之,不能将马克思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等同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否则体现不出马克思在该问题上的思想深度。意识形态在起源、发展过程和归宿上都是彼此联系的,不同年代所发生的不同社会事件,都将影响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本身的看法,亦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演变的,这样才能勾勒出马克思思想的复杂内涵。当然,按年代来区分思想阶段,也是一种较为冒险的尝试,因此我不是很赞同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存在一个特别清晰的界限。
吴向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张秀琴老师的文章抓住了一个重要话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自特拉西经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到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乃至拉康、曼海姆、齐泽克、詹姆逊、伊格尔顿等形成的意识形态理论谱系中具有承上启下以及分水岭的作用。厘清马克思本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阶段对于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可或缺的,进而对于理解意识形态理论谱系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张老师的文章采取了合理的研究方式。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很容易陷入抽象研究,研究抽象的一般,而忽视具体和特殊。马克思认为构成发展的是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所以特别强调注重研究具体,而非一般,强调不是去研究应用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那种抽象一般规律,而是去研究每个历史时期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张老师在文章中自觉到并采取了这一具体、历史的研究问题的方式,不是抽象地谈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而是以丰富文本为依据,仔细探究马克思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理论内容、方法以及特点等,以期揭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逻辑,并取得积极成果。
当然,有些具体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文章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观念或意识系统,一种制度系统,同时还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一宽泛的定义就使得本来含义复杂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加的复杂化。阿尔都塞也曾经把意识形态看成一种附着在一定机制上,对个体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他还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但是,附着在实体性的国家机器上的意识形态与实体性的国家机器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有意识的活动与活动中的意识也是不相同的。将意识形态明确为一种观念也许可以能更清楚地讨论问题。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和异化。文章把异化与意识形态相勾连,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中,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在某种程度上文章作者似乎把异化和意识形态等同。仔细考究,这两个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成是“意识的幻想”,是虚构的幻象,它反映和维护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产生的客体转过来反对主体自身,它否定着主体的利益。作为一种虚构的幻虚,意识形态概念揭示的是人受自己观念的欺骗,而异化揭示的则是人受自己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压制和支配。
第三,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文章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第二阶段揭示意识形态的双重性,即虚幻性和所具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进展与研究重点或研究视角转换之间的差别。如果说第一、二阶段还能看到明显的逻辑进展,或者说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发展,那么,在第二、三阶段之间,与其说是存在着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阶段性的发展,不如说只是马克思研究重点的转换,或者研究视角的转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前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是在哲学的框架内进行的,奠定在一种哲学——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则将其分析奠定在对一种经济形态的科学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对当时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和特点等,但是其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外,在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二重性时,问题的重点不在说明意识形态的二重性,而在于分析马克思为什么从强调意识形态的虚构性转向强调意识形态的二重性?是怎么实现这一转换的,转换的基础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唯物史观的核心观念: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这一观念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哲学),以及社会的结构、意识形态的功能、价值与历史的关系、理论与实践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和内容,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及其内在的逻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会呈现出来。同时,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探究意识形态时,重点不是揭示意识形态的虚构性,而是揭示意识形态虚构性的社会关系、物质关系的根源,并进一步揭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合法性而采用的种种话语策略和隐蔽手法。
张立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听了张秀琴博士的讲座很有收获,诸位前辈和同仁的评议也给我很多启示。这里,我简单地谈点想法。张博士文章的三个小标题,都包含比喻,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总是离不开比喻,是很值得探究的。比喻会把问题引向哪里?当我们说“小李是一朵花”时,本意是夸奖小李,但比喻的语义效果使得关注点偏离了小李,转向“花”,“花”成为真正的聚焦点。马克思在论述意识形态的时候使用这样和那样的比喻,是否也引发同样的效应呢?
当代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强调,比喻、转喻、转义是一脉相承的东西。discourse(话语)这个词的形容词形式是discoursal,一些学者译作“离题的”,可谓传神之笔。话语总是离题的。马克思论述意识形态时,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围绕意识形态这个词打转,而是把意识引向意识形态之外的事物、地带和领域。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但又不是意识形态。进而言之,马克思不是为了研究意识形态而研究意识形态,不是为了批判意识形态而批判意识形态,他的目的在别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机器或者说武器上的一个构件。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马克思不同时期都在谈论意识形态,但始终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严谨的界定,原因或许就在于此。我甚至想说,马克思那里至多有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形态的理论。所谓的意识形态论,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包括我们出于研究的需要和目的弄出来的一个东西。质言之,马克思只有一个理论,那就是批判理论。
张博士谈到,马克思不是在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确如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时,也应该避免采用马克思所反对的方式,否则,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悖论。另外,文喜教授点评时谈到“皇帝的新装”,我做点小小的附议。马克思1842年5月5日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里,提到歌德《浮士德》中“无罪的天使”,并引用了席勒的诗:“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马克思把歌德和席勒的意象相提并论,暗指《国家报》也想使普鲁士臣民保持“天真”,并鼓励那种不存任何疑虑、乐意尊崇父辈权威的“孩子般的单纯”。
梁树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今天的汇报和讨论气氛非常好,大家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虽然是小型的但却是高水平的专业讨论。汇报人就自己的汇报内容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大家的评议也很热烈,论题很集中。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一个范畴还是一个理论问题,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与讨论的问题,其实践意义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今天,大家⑩就张秀琴的汇报,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如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发生学问题的研究、对该研究文本依据的进一步探索和文本资源丰富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进一步完善等,这些都值得汇报人参考和借鉴。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继续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注释:
①该文已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上。
②也就是说,其逻辑演化线索是寻找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现实”。而在这一寻找过程中,上述三个层次的批判既表现为方法又表现为内容,即哲学是意识形态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政治是意识形态最直接而明显的存在场所,经济是意识形态发生和发展的背后的本质和基础;而且它们还在三个阶段中依次作为主导逻辑而并存。
③俞吾金教授曾经在其《意识形态论》中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分为三个阶段,即1845-1856年的第一阶段、1857-1870年的第二阶段、1871-1895年的第三阶段(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英国学者乔治·拉雷恩在其《意识形态概念》一书中提出了两阶段说,即第一阶段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端,一直持续到1858年;第二阶段开始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见[UK]Jorge Larrain:The Concept of Ideology,London,Hutchinson & Co.Ltd,1979)。稍后,这位英国学者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受另一位西方学者Rafael Echeverria的影响,提出了三阶段说,即1844年之前的第一阶段、1845年至1857年的第二阶段、1858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参见[UK]Jorge Larrain:Marxism and Ideology,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④英文翻译成了imagine,马克思后来在第二阶段以及第三阶段的许多文本中都提到了这个词,但它在后来的著作中大多被翻译成“想像”,而非这里的“虚构”。学界普遍认为,在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中,它是一个与“现实”(reality)相对应的观念(ideal)的存在,有学者考证说,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Vorstellung这个德语词,它被翻译成英文的imagination(想像),其实它更应该是“观念”(conception)、“思想”(idea)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参见[US]Paul Ricoeur: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p75,Edited by George H,Taylo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⑤第一次以“意识形态”术语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另外还有两次以“意识形态家”的形式分别出现在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和《神圣家族》中。
⑥因此,有西方学者还把唯心主义当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同义语。在他们看来,“综观其一生,马克思都是在唯心主义(idealism)和辩护(apologia)这两个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参见[UK]Bhikhu Parekh:Marx's Theory of Ideology,introduction p.1,London,Croom Helm Ltd.,1982)。
⑦Bhikhn Parekh:Marx's Theory of Ideology,p.1,London,Croom Helm Ltd.,1982.
⑧《资本论》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中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在《资本论》中寻找,而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来寻找(参见J.Mepham: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In J.Mephem and D.H.Ruben(Eds.),p.145,Issues In Marxist,3 Vols,Vol.III,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79)。
⑨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也说,“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7页,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⑩因有些发言人录音资料不清晰,事后也无法及时联系上,也因篇幅有限,这里未收录所有发言人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