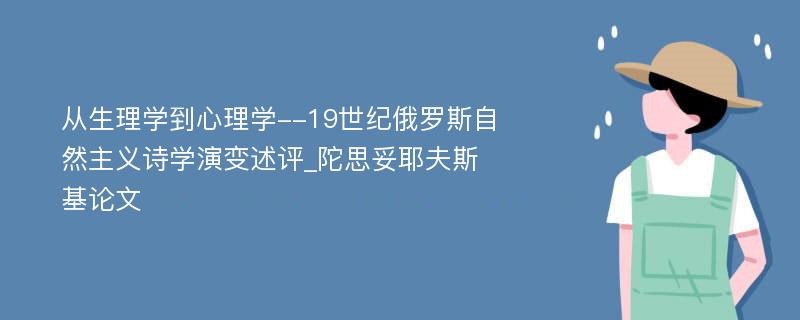
从生理主义到心理主义——观照19世纪俄国自然派诗学的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主义论文,诗学论文,轨迹论文,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40年代,俄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俄国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就是进步阵营的一些年轻作家形成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新流派,即“自然派”。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别林斯基美学纲领的指导下成为果戈理的追随者,他们在作品中自觉地攻击着俄国社会的虚伪和停滞,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自然派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绩,成为整个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但是,到了50年代自然派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流派而存在,曾经的自然派作家都陆续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自然派内部一些诗学思想的极端发展渐渐背离了其最初的艺术思想,对人性的终极拷问替代了对外部现实的强烈关注,这已经违背了自然派最初的创作宗旨,尽管心理主义只存在于个别作家的作品当中,但是心理主义所呈现的诗学倾向已经注定了自然派历史命运的终结。
一
19世纪俄国自然派文学是从生理特写起步的,184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的文集《彼得堡生理特写》问世,正式宣告了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存在,文集中的所有作品都指向同一个描写对象——彼得堡,把彼得堡当作一个有机体加以细致的研究,因此文集才冠以“生理特写”的名称。生理特写在自然派作家的笔下变成了一把犀利的手术刀,解剖的对象就是整个俄国社会,它所揭露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种种隐藏在暗处的罪恶和污浊,生理特写因为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时代感和平民性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生理特写以“生理主义”作为主要的诗学方法,所谓“生理主义”就是借鉴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解构和分类,揭示出内部的隐藏在日常生活和习惯下面的东西,力求详尽、完备地对客体进行分析,凡是过去作家在描写中没有说尽、形象多义的地方生理特写作家则要求清晰而完备,强调闭合性与完整性,我们来比较一下生理特写作家达里和果戈理的作品来看一下其中的差别。果戈理笔下的涅瓦大街呈现的是神秘的幻象,成千上万的各色人物,首都各个阶层的居民来到这里,然后又不知所踪,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无从得知。达里则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在《一个人的一生,或涅瓦大街上的徘徊》这篇作品中作者只将目光集中在一个人物——小官吏奥西普·伊万诺维奇身上,以涅瓦大街为背景描写了他的一生,从他出现在涅瓦大街的那一刻直到他彻底的离开;从生到死,将一个人物的命运完整地呈现出来,描写人物的一生是生理特写的常用手法。
“生理”的另一层意思即自然、即真实,即以科学的精神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生理特写作家常常清楚地界定所描写的范围、研究的对象,我们将之称为定位,即集中描写某个范围,其宗旨是概括性、普遍性,描写的是类型,而不是个体。比如,描写送水工,描写的不是某个具体的送水工,而是从全体送水工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形象。所以一个人物身上体现的是普遍性,而不是典型的个性。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果戈理笔下的皮罗果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某个阶层或职业的典型。果戈理笔下的人物是更高水平的典型性格,但是却并不是由职业或阶层特点所集中而成的典型人物。果戈理笔下人物的社会归属是不确定的,而生理特写却将社会阶层和职业的划分放在了第一位,材料的选择,叙述的风格和人物的语言都服从这一原则,给读者似乎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生理特写作家似乎有意将社会分成一个个的方格,然后用不同的作品去填充它。对果戈理来说重要的是扩展人物的生活内容,对生理特写作家来说重要的则是明确限定所写的内容,对人物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是生理特写作家与果戈理的重要区别。
在生理特写的范围定位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以下几种方向:1)描写属于某一社会阶层和职业阶层的人,如格里戈罗维奇的特写《彼得堡的流浪乐师》、达里的特写《彼得堡的守院人》、巴纳耶夫的特写《彼得堡的小品文作者》。2)根据地点来描写,这些地方通常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人物发生冲突的地方,如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格列平卡的特写《彼得堡区》。3)第三类生理特写不是以类型和地点为基础,而是描写某种社会习惯,日常习俗。可可列夫最擅长此类特写,如《莫斯科的婚礼》,《莫斯科的轻工业》都是此类作品。
要找到生理特写的源头并不难,对生活的描写就源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兴趣,生理特写是以最纯粹、最直接的方式关注着社会现实。社会成为一个硕大的有机体,被分解成了许多小块,这些小块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每一个部分都因为自己的独特性吸引着艺术家深入其中。在浪漫主义作家的观念中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在最初的现实主义大师的思想观念中二者之间也是和谐的、相互联系的,而在生理特写中这种和谐被有意地破坏了,现实的完整性被打破,生理式的描写正是对现实的解构。B·维诺格拉多夫曾这样写道:“对类型化流行病似的渴望,试图挑出些傀儡作为某个特定阶层、职业或是在他们的境遇下心理状态的象征,有时甚至是某种激情的化身,这就是自然派的典型特征。”[1](147)
二
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生理特写展开的基础,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使生理特写走向了两级,其中一级的代表是达里的生理特写。达里的生理特写的典型特征是人物与环境的融合,他们与环境的关系就好像是蜗牛和蜗牛壳,人物的习惯、爱好、行为都与环境融合在一起。
达里的《彼得堡的守院人》中的两个守院人格里高利耶夫和伊万的性格是通过他们的行为、生活规律和习惯来呈现的,人和人周围的物体和环境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格里高利和过路人,以及他的同行伊万的互动场景有机地融入到背景当中,在这背景之中渐渐凸显出了主人公格里高利的形象,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和作者对他生活环境的描写格里高利的形象直到特写的中间部分才彻底形成。主人公“我”的自我显示是间接的,人物淹没在物体当中,甚至被物体所取代。我们来看一下作品中的一段描写“但是在这些娱乐的间歇,伊万和格里高利也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为他们工作。天一亮就起床,打扫院子,一直打扫到大门口,准备好全家十口人要用的水,把木柴搬到四楼,一个月为此得到50戈比。有时他将整整一垛柴都扛在肩上,所有人都想一次就干完,绳子放在帽子底下,直接绷在脑门上,后面用手托着。”[2](76)整个人物都淹没在劳动之中,肩上重重的柴禾把人物推挤到了视线之外,他完全被自己的劳动对象所支配。在他的私人空间里他的位置也被取代,取代他的位置的首先是他的那个小房间,然后是床,然后是他的毛巾。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床,这张床“过着完全颠倒的生活:它只在白天打盹,就像灰烬中的火星那样,到了晚上就完全苏醒过来,吞噬着我们健壮的守院人肥胖的身体。”[2](76)“床”在作者的笔下复活了,像一个真正的生命体。无论是床,房间,还是毛巾都是主人公的外化形式,它们将主人公挤出了画面占领了人物的位置。详尽与完备是生理主义的要求,达里的作品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要求,果戈理曾评价达里说:“他不是诗人,没有掌握虚构的技术,甚至也不追求创作有创造性的作品。”[3](424)这并不是在贬低达里,而是在称赞达里的观察能力和作品的现实性。
生理特写的演变是与时代的社会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本主义进入生理特写是40年代末的事情,两种极端的艺术思想在较低的水平上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感伤主义的生理特写。感伤主义的生理特写代表了生理特写的另一极,这类特写以感伤主义为基础同时又加入了自然派的写实性,在这样的作品中人物不再是环境的附庸和奴隶,开始出现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探寻。
在一些作品中对人性的探寻是通过插叙的形式体现的,巴纳耶夫的作品《野驴》中出现了一段关于“人”的抒情插叙:“天知道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要藐视‘人’这个字眼,这是个美好而又含义深刻的词儿,这个词儿单独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加上从我们这个社会获得的三个附属品之后才有了重要的意义:名声显赫的人,当官的人,有钱的人……我的读者,请指出我们中间纯粹留给人的位置在哪儿?”[4]此时抒情插叙是独立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的。
巴纳耶夫的另一个特写《太太》中已经不是作者的插叙,而是人物的内心独白。主人公芭拉戈雅死后,她的儿子想起了母亲在死后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想起了因为暴风雨的冲刷而露出一半的母亲的坟墓,想起了争抢他扔出去的那些钱互相打架的穷人,在他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扪心自问:“难道这就是生活吗?”
格里戈洛维奇在彼得堡的流浪乐师中写道:“只要好好地看一看这个人的内心,你就会经常在他那粗糙的外表下找到非常美好的源头,那就是良心。”[2](85)
在感伤主义生理特写中人性已经不再隐藏在行为的背后,而是与人的行为和思想结合在一起。人物对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和探寻所彰显的正是在黑暗肮脏的环境中人身上仍然保存的道德良心和人性的美好。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人物与环境,人身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由环境造成的,而所有美好的品质则是人的天性,好的品质从恶劣的环境中脱离出来并且高于环境。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已经不可能使自然派作品局限于生理特写的框架之内,生理特写类型化的局限、过分的细节描写都妨碍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化,人本主义将人的本性置于高于暂时的现象之上,从人本主义出发描写人物需要完全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内在的本质。生理特写的诗学特征已经制约了对人性的深刻探索,随着对人性日益强烈的关注更适于表现社会与人的复杂关系的小说体裁逐渐成为自然派创作的主流。
三
冈察洛夫的小说《平凡的故事》和赫尔岑的《谁之罪》都是自然派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平凡的故事》反映了时代要求和人的本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亚历山大本是一个怀有浪漫主义梦想的热情的年轻人,他带着对美好前程的希望、对爱情的向往来到了首都彼得堡,然而在现实的压迫下最终变成了和叔叔彼得一样的实用主义者。如果说亚历山大的经历体现了现实的强大且无法抗拒的力量,体现了人性在现实面前的脆弱,而彼得在结尾处所流露出的痛苦则代表了人性只能被抑制却无法被消灭这样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精神和尚未被完全压抑的人性之间的分歧。冈察洛夫通过彼得的痛苦向我们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即在时代精神的强大力量之下人的本性并没有被完全毁灭,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是难以根除的,它也许会被暂时地抑制住,但是不会消失,或早或晚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平凡的故事》相比赫尔岑作品的人本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进一步强调了人的本性的无辜,正是外部环境的力量扭曲了人的本性。在小说中他记录了大量人物的生平,在人物从前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中寻找不幸、不正常、甚至犯罪的根源,从新的角度来解释“恶”。小说中的三个人物都失去了生活的幸福,在结尾处克鲁奇费尔斯卡娅即将死去,克鲁奇费尔斯基整天酗酒度日,别里托夫又开始了孤独的游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问题的答案留待给读者去思考。过去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过于简单了:这是专制农奴制的罪恶,是环境造成的等等。B·布津采夫反对将赫尔岑的小说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他公正地指出,正是后来的事情“促使我们严肃地寻找造成主人公悲剧人生的罪魁祸首。”[5](62)仅仅从社会的角度来解决“谁之罪”的问题已经过时了,而是应该从新的、更符合赫尔岑本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将这一问题深化到普遍人性的层面上来,正是个人意志和追求的不可调和才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正是赫尔岑作品的复杂之处。
小说中已经没有了纯粹的恶人,产生“恶”是由于苦难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受到了伤害才趋向“恶”。别林斯基对小说的这一层面理解得很清楚,他写道:“他推向舞台的人物都不是恶人,甚至大多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常常是带着良好的而不是卑劣的意图折磨迫害自己和其他人,常常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出于邪恶。”[6](325)赫尔岑在作品中是在为人的本性辩护,在柳帮卡身上表现出了涅格罗夫本性中的良好倾向,是环境改变了人的本质,才产生了恶果。作品中的人物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环境,时代气氛,而不是人物彼此面对,对于“谁之罪”的问题,赫尔岑的回答是:没有人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正确的,同时又是有过错的,但这不是个人的罪责,而是时代所形成的行为准则所造成的错误。
人物在时代面前低头,在这一过程中人物与现实逐渐走向了两级对立的状态,如果说偏见、仇恨、嫉妒等卑劣的性情都是时代的现实所造成的,那么人善良的本源也不时地从现实中挣脱出来。在自然派创作中生活被理解为现实与人的本性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美学形式上产生了人本主义的趋势。
四
对人性的强烈关注促使一些自然派作家开始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状态,从40年代末开始在自然派内部关于诗学的讨论日益激烈,心理主义渐渐取代了生理主义成为自然派后期创作的主要诗学特征。我们可以从谢德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大量的心理描写已经完全取代了对外部现实的关注,谢德林的作品《矛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采用的都是最容易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书信体形式,《双貌人》深入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被野心所激发的变态心理,在此我们不想分析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手段,大量的文学研究者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我们要分析的是在心理主义的背后自然派的诗学思想如何受到了颠覆。
谢德林的小说《矛盾》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小说主人公纳吉宾深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陷入了无力摆脱的矛盾之中,理智与情感、行动与思想进行着永无休止的角逐和争斗。纳吉宾同样承认现实对人的巨大压迫力,但是他对现实和人性的理解却和以往的自然派作品有所不同。自然派认为是环境扼杀了人的美好品质,让人变成了利己主义者,纳吉宾虽然不否认是环境扼杀了善的一面,但是却不同意是环境让人成为利己主义者,他认为利己主义就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就像人的其它美好品质一样。纳吉宾没有为现实辩护,他也认为是现实让人陷入痛苦之中,从这一层面来说,这篇小说仍然属于自然派作品,但是他坚决地把人的自私性也引入对现实的理解当中,他所提到的现实不仅指外部环境,同时也包括人的利己主义。
关于“谁之罪”的问题,谢德林也给出了不一样的解答。谢德林认为一个人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犯了罪并不是个人的过错,社会因为他的罪行而惩罚他也没有错。这和自然派以前的回答有所不同,自然派通常认为人在客观环境的压迫下犯了罪是没有过错的,但是自然派坚定地认为社会是有罪的。谢德林却不想给出这样的回答,因为这个社会正是由无数个坚持利己主义的个人组成的。“谁是有罪的?这就是谜题所在,但是现在还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因为没有找到方法。随着时间流逝谜题终将揭晓,找到有罪的人,但是现在……黑的是对的,白的也是对的……无论您怎样竭尽全力,怎样深入思考,都无法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7]谢德林似乎希望从内部扩展自然派的视野,在自然派的主要描写范畴,即现实与人的关系中挖掘出更复杂、更有深意的内容。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倾向,从《穷人》到《双貌人》的过渡鲜明地体现了心理主义日趋强大的诗学发展轨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自然派的典型冲突之上的,它的情节核心是一个不幸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穷人对一个姑娘的爱情,并由此产生的悲剧。瓦莲卡的命运,周围各种各样的穷人,因肺结核而死的大学生,小说的感伤风格强化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现实的冲突,这些特点都承袭了自然派的诗学特征。因此,《穷人》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自然派作品。
《穷人》已经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人物心理的巨大才华,外部对人物的压迫完全是通过人物自身的感受来体现的,巴赫金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不是贫穷的小官吏,而是贫穷小官吏的自我认识。”[8](64)作者以感伤的语调描写了一个小官吏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自我确立却无法实现的绝望处境,通过他可怜的自尊心来强调人物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肯定。
在另一部小说《双貌人》中主人公的野心已经达到了非正常的地步,作者的视角已经完全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严格地说,主人公已经不是一个贫穷的小官吏,这一点不同于杰乌什金和他周围的人。造成人物不幸和痛苦的原因也不再是自然派所钟情的说法,即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人物的不幸。别林斯基立刻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是“野心”让高略德金发了疯,“他在这世上活得并不坏,但是他性格中病态的怒气和多疑成了他生活中的恶魔,这注定要使他的生存成为地狱。”[6](563)换句话说,高略德金的不幸同他自己的要求和野心密不可分。因此他本人对自己的不幸是负有责任的。他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导致他不幸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他无法抑制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双貌人》更接近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而不是《外套》。幻想的逻辑、不合理性的主题形成了《双貌人》的怪诞风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传统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幻想色彩编入到了现实主义的经纬当中,正如维诺格拉多夫所说“清除了悲剧式斗争的幻想世界和模拟现实的可笑细节之间的清晰界限。”[9]284
谢德林将利己主义带入到了自然派对现实的理解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将带有强烈自尊心和野心的人带入到自然派文学当中。无论是哪种情况,两位作家都体现了自然派后期的主要创作倾向,即解剖人的本性。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与自然派最初的创作原则相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主义拒绝了生理式的描写转而从内部揭露社会的溃疡,其中不仅隐含着对人本主义的否定,同时也隐含着对整个自然派艺术思想的否定。别林斯基清楚地看到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自然派区别开来的一些因素:将带有强烈“野心”的人物推到了主人公的位置,幻想成分抹杀了主观感受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界限,只选取一个主人公,拒绝了对话冲突的多个主人公的模式。别林斯基将这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复兴,一个人反对所有人,一个人高于所有人的模式。在人们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自然派作家的时候,别林斯基以其卓越洞察力已经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思想上与自然派的不同。
极端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导致了对人性的极端拷问,人性中恶劣的一面逐渐被挖掘出来,在“谁之罪”问题上的人不再是环境无辜的受害者,人性的弱点也成为导致人物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这样的解释已经背离了自然派文学的初衷,诗学的颠覆最终导致了自然派的解体没落,一些自然派作家纷纷冲出了自然派诗学的框架,走上各具特色的文学发展道路,自然派的时代渐渐成为俄国文学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