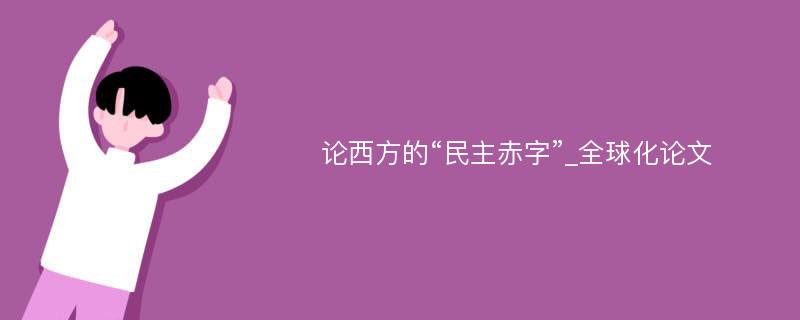
话说西方“民主赤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字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在全球化巨大冲击下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悖论:一方面民主在全球广为传播,但另一方面,在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对民主的幻灭与日俱增。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参加选举投票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议会政治兴趣大减,令西方政治家备感担忧。
民而不主:政治家及政府机构信誉下降
据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公布的报告,目前世界上有120 个“民主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该报告还将过去的30年称为“民主的时代”。
然而就在西方国家热衷于帮助亚洲、非洲、拉美和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推销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时,却发现自身的民主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民意调查表明,“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特别是在美国,民意调查和研究成果显示,公众对政治家是否诚实、政治家是否真正关心选民的利益的判断和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趋势。60年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出现暴跌是由于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使6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随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这一现象并非只发生在美国,在绝大多数“成熟民主国家”中,公众普遍对政治家、政府出现幻灭倾向。
不仅政治家失去人们的信任,连政府机构也信誉不佳,特别是在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和美国更是如此。一项分别在1981年和1990年两次全球性的民间调查表明,人们对议会、军队、司法、警察和公务员的信任程度下降了至少6个百分点。
在美国,60年代初期,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尚可。1964年,只有29%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政府是由少数大利益集团所控制,到198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5%,1998年又进一步上升为63%。在60年代,2/3的美国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大多数当选的官员并不真正关心公众的利益。1998年,却有2/3的人赞同这一观点。1966年,42%的公众对政府还有“相当的信任”,到1997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2%,对国会的信任程度也从42%下降为11%。
在西欧,多数国家民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度也日趋下降。1985年,48%的英国人对下院还有信心,但1995年就只有24%了。1968年,51% 的人不赞同这种看法, 即政党只关心选票,而不是选民的意见;到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8%。1986年,51%的人对议会还称有信心;但到1996年,这一数字却只有19%。在德国,1978年,55%的人对议会有信心;到1992年,下降为34%。在意大利,认为政治家并非真正关心选民的看法从1968年的68%上升到1997年的84%。
民主赤字: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对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国理念的冲击是巨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权势已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一定程度上正成为全球化的对立面。
全球化在创造价值和带来利益的同时,使犯罪、毒品、黄色产品、道德沦丧、儿童受虐待、妇女被侵犯等都“全球化”了,在这些政府无力管辖的“灰色地带”或某些脆弱的结合部,全球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也更加明显。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成为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化表现。它作为一支“超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其本身的发展壮大,使西方民主国家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比如在西欧,欧洲委员会是决策机构,欧洲议员是选举产生的。随着欧洲一体化增强,欧洲委员会权力更大了,而同时,它实际上离公民也越来越远了,公民对这个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越来越不感兴趣,对选举欧洲议员并不热心。
对一个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来势凶猛,使政府在巨型公司面前束手无策或无能为力。政府是选举出来的,应该为选民负责,而跨国公司不是选举出来的,它们不必对选民负责,只对股东负责而已,唯利是图是其本性。公民感到政府与他们日益拉开了距离,而跨国公司又不关注其利益和需要,人们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民主危机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参加政治党派的人减少,二是投票的人减少。据美国一项分析表明,20个西方民主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投票人数与50年代相比均呈下降趋势,降幅达10%。另一些政治学家还认为,60年代以来各种抗议活动增多也表明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失去信心。其他人认为,对民主体制最大的威胁来自各种专业化的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它们在幕后千方百计地对政府施加影响,维护其特殊利益,却将选民的利益置之度外。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欧洲议会上对一种反常现象表示吃惊:一方面,一体化给欧洲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和空前的繁荣,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强有力的一极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使公民看到欧洲稳定和进步的希望。另一方面,欧盟扩大的前景,又使公民对一个没有边界没有特性的欧洲感到害怕,对欧洲建设的热情正在下降。加之人们对欧洲低效的官僚体制日益不满,对欧盟扩大所带来的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前景的担忧增加,欧洲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1999年6 月欧洲议会选举,有57%的选民没有投票,其中英国和荷兰的投票率只有24%和29.9%。欧洲还需要什么?普罗迪的回答是:欧洲需要一种观念,欧洲经济和社会体制应该“以人的尊严为本”。
为什么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对其政治体制反而失去信心和信任,会出现这种“民主的不满”呢?
应当承认,今天人们对政府的期望更高、要求更多,因此才更容易失望。人们要求政府保护或改善环境,维持较高的就业率,对道德观进行仲裁,确保对妇女和少数民族平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问题”,有些还颇具争议。
如何填补:“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行?
面对“民主赤字”究竟该如何办?西方学者认为,要将公众的失望情绪视为一种机会,它表明现行的各种参与渠道均难以完全适应公众要求,必须进行改造。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称,答案就是“民主化民主”,这种民主化不能只局限于民族国家水平,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答案都必须是全球性的,政治领域亦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派在欧洲历史上首次同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大国主政,显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泛市场经济理论的反思,它的得势反映了自由主义作为西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内在矛盾发生了尖锐碰撞。在“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能否抑制市场能量的“无序释放”,从而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开明”、“人道”。通过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通过对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造等手段过滤掉资本主义的野性,使它变得“温情脉脉”。“民主的民主化”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英国是向地方下放权力,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日本、新西兰等则考虑修改选举制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全民公决或其他形式的直接选举更加热衷。有的则削弱议会权力,授予法官新的权力以审核政治家的决定。各国对政党和政治家的竞选资金来源均严加限制。同时,还考虑尝试“替代民主程序”,特别是在做出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决定时,如“人民陪审团”或电子公决。吉登斯认为,这些方式虽然代替不了代议制民主,却可以是一个有用的补充。
他们还认为,政治党派还应当更多地与单个问题组织如生态集团等合作、协调。这类单一问题组织往往最先提出一些最前沿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又常常被正统的政治党派或决策部门所忽视。比如疯牛病爆发之前,英国就有这类小组和运动警告食物链中的污染可能带来的危险。“民主的民主化”还将依赖于培育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市场是培养不出这种文化的。吉登斯说:“在我们的思维中不应当只有两个部门,一是政府,一是市场,或公与私,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个广泛的公民社会地带和其他非经济性的机构。”因此应当重视和尊重这个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
可见,“民主的赤字”是近来在西方国家日益受到关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恰好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是一个靠“填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似乎正在落入“民主的陷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