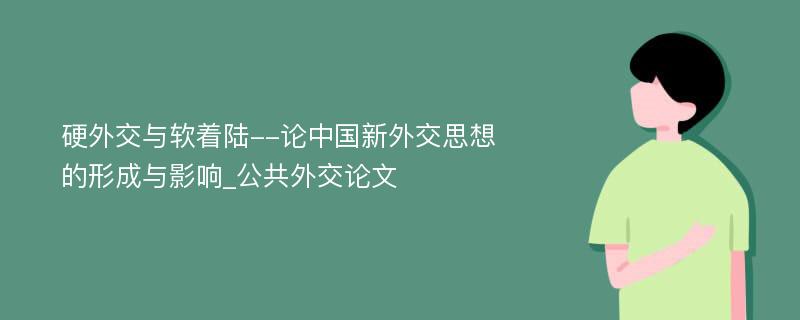
硬外交、软着陆——试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形成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软着陆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中国新外交
在学术界,不少外国学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线,将此后的外交称之为“新外交”,以区别于此前的“旧外交”。(注:参阅哈罗德·尼可尔森:《现代外交学方法的演变》,麦克米伦公司,1954年版;默尔森·普利斯科:《现代外交》,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协会,1979年版;周启朋等:《国外外交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相比传统的旧外交,新外交的范围扩大超越了欧洲中心,外交的内容也大大拓展,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外交、体育外交、军事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多边外交、地方外交、人民外交以及人权外交等等,都成为外交的内容。(注:参阅肖宪主编:《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125页;金正昆著:《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然而,外交的此等变化不过是外交形态的变化,外交依然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事务,在对外交往中依然奉行着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政治的逻辑。
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传统的现代外交精神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针对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制度面临的挑战,许多学者,比如马特斯(Henry E.Mattox)、汉弥尔顿(Keith Hamilton)与朗霍尔(Richard Langhorne)、巴森(R.P.Barston)、安德森(Jim Anderson)、哈洛普(William C.Harrop)、塔伯特(Strobe Talbott)、肯楠(George F.Kennan)、及朗霍尔与华勒斯(William Wallace)等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Henry E.Mattox," 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 Foreign Service,Journal 72,September 1995,pp.38-39; Keith Hamilton,and Richard Langhorne,eds.,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Its Evolution,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6; 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2d ed.,London:Longman,1997; Jim Anderson," The Future of Diplomacy," Foreign Service,Journal 74,May 1997,pp.26-31; William C.Harrop," The Future of the Foreign Service," Foreign Service,Journal 74,May 1997,pp.32-37; Strobe Talbott," Globalization and Diplomacy:A Practitioner' s Perspective," Foreign Policy,No.108,Fall 1997,pp.69-83; George F.Kennan," 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s? " Foreign Affairs,Vol.76,September/October 1997,pp.198-212; Richard Lanhorne,and William Wallace," Diplomacy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Foreign Ministries:Changes and Adaptation,ed.Brian Hocking,New York:St.Martin' s,1999,pp.16-22.) 上述学者认为,在信息流通自由、议题复杂、国际行为者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现代外交精神面临诸多考验,必须加以调整以顺应新时代的需要。面对挑战,近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研究外交改革问题,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代表,一些国家已经掀起了研究外交改革的一个热潮,一大批智库推出了大量的论证报告。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1998年10月发表的《再造信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书,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有关虚拟外交研讨会的详细资料,请参考“虚拟外交首页”(Virtual Diplomacy Home Page),网址:〈http://www.usip.org/oc/virtual_dipl.html〉。“信息时代之美国外交再造报告书”全文则刊载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上,网址:〈http://www.csis.org/ics/dia/diadraft.pdf〉,9 October 1998。) 超越现代外交精神,规划全球化时代外交新思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一个潮流。
置身于这一潮流中,中国外交也在发生深刻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系列新思维,比如对于多边外交的重视、逐步融入国际组织、加强公共外交等。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也提到了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问题。埃温·米德罗斯(Evan Medeiros)和弗莱沃尔·泰勒(Fravel Taylor)教授在《中国新外交》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后外交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其中包括中国扩大了双边关系的数量和深度,深化了对各重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外交决策更加制度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受害者的心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各种利益诉求和责任感的、正在崛起的大国。(注:Medeiros,Evan S.,Fravel,M.Taylor," China' 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3,pp.22-35.) 另外,一些西方新闻评论人也零星提到了中国的“对美外交新思维”和“对俄外交新思维”,但基本上还停留在描述的层面。本文主要从考察中国外交行为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外交新思维的内容及其意义。
双边主义中的共同利益思维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采取“整体打包”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推动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这与双边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问题密切相关。在双边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还停留在政治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则更依赖于此种“整体打包”的方式,比如中苏之间最初依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依赖于周恩来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双边外交更多地产生了大量的“原则”、“立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就是积极与周边各国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即所谓“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注:方长平,“多边主义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22页。) 在东面,江泽民主席1998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国与韩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南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连续迈上新台阶。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确定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双方还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于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的努力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向外界发出双方愿致力于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和平方式处理本地区争议的积极信号。在西面,中印两国1996年决定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同巴基斯坦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北面,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中国与中亚邻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随着双边关系深入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保等深层领域的时候,中国处理双边关系更加强调通过建立机制来谋求共同利益的增长,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处理双边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最初中美关系更多依赖《中美联合公报》来指导和规约双边关系的发展。随着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深入,双边外交的机制化趋势日益明显,高层形成战略对话机制、外交形成合作磋商机制、社会形成互动交流机制。首先,中美两国首脑利用参加国际会议、首脑互访、热线电话等各种渠道定期举行会晤,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首脑之间的对话日益机制化,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注:本报评论员,“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1998年6月18日,第1版。) 其次,中美两国外交层形成了合作磋商机制,已经建立了部长级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内阁和次内阁级官员的定期互访以及在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防核扩散、人权、法律合作、两军关系等若干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交往机制。再次,中美两国社会领域的互动交流机制逐步健全,比如从1998年起,中美智囊战略对话开始定期举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美议会交流小组、中美教育交流机制等等,都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逐步确立。尽管中美的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但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化,两国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动日益机制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靠实际运转的交往机制,而非仅仅依靠中美之间形成的战略定位,这是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的基础和平台。其实,由于双边交往的深入而形成的众多交往机制并非仅限于中美关系之间,中国的其他双边关系也形成了大量的类似机制,这是双边关系发展极为重要的成果。
多边主义在中国外交的兴起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外交更强调双边主义,注重通过外交谈判和交往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即使是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国也一直坚持奉行双边主义的理念。至于后来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以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等多边场合,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多边主义,而是借助多边的舞台来推行双边主义的理念,是形式上的多边外交,实质上的双边主义。
中国对于多边主义的疑虑和顾忌是中国近代历史反复教训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国家利益屡遭侵犯后的历史遗产。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联合侵略,中华帝国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无论作为晚清政府第一外交官的李鸿章,作为北洋军阀政府外交代表的顾维钧,还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都在西方列强的多边国际会议上深感屈辱。尽管不同政权代表中国民族和国家利益不同,但无疑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出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理念,中国共产党则更加清楚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根本宗旨。无论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还是独立自主的方针,贯穿始终的无疑是双边主义的理念。
新中国多边主义理念的发轫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是在外交实践中逐渐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种种理由操纵联合国,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把联合国变成敌视中国的工具。正是面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方面遇到的阻力,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联合国在美国控制下只可能做坏事不可能做好事”的判断。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对此,中国政府极为愤慨地指出:“自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我国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即已断然自绝于中国人民;此次联合国大会又非法通过美国这一提案(指要求所有会员国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只是再一次证明联合国已日益不可挽救地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注:“外交部发言人斥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中朝禁运案的谈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友人斯诺关于“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时表示:“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吧。”(注: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54页。) 可见,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使得中国对联合国失望到了极点,此后再也没有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恢复合法席位的要求。1971年10月,在亚非国家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但由于受到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国内就是否派代表团出席当年联大问题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联合国是资产阶级政客的讲坛,是美苏两霸的御用工具”,“是喝咖啡、聊天、打嘴仗的官僚机构”,主张“观察一年,准备一下,明年再说”。(注:曲星著:《中国外交五十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8页。) 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平息了分歧,提出:“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马上派代表团去联大。”(注:翁明,“临行点将——‘乔老爷’首次率团赴联大”,载《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8页。) 尽管如此,当时中国对联合国总的看法没有多大改变,依然认为联合国只是一个揭露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反映发展中国家呼声的讲坛,中国可以利用这个讲坛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如果我们分析一下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发言,很容易就会发现此种“道义外交”的形象。总体来看,80年代之前,中国在参加联合国外交方面依然服从和服务于“国际阶级斗争”的大局,借助联合国的讲坛,通过双边的外交谈判和接触,把联合国视为“承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地位,反霸(反苏)和反美活动的工具,而没有把它当作促进中国利益和发展的舞台”。(注: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谈不上参与联合国的多边主义机制,有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的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参加安理会关于维和问题的投票,并声明对维和行动不承担财政义务。(注:盛洪生著:《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律问题研究》,军事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由此充分表明,80年代之前,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了联合国,但外交理念实际上并非是多边主义,而是双边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影响力,认识到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个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在的混合物,不能轻言“砸掉一个旧秩序”而单枪匹马与之作对,应该在参与联合国的实践中逐步改造联合国。此种看法最为集中地体现在198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之中。他指出,“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一样”,“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注:“赵紫阳总理在联大举行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5日。) 如此之高的评价以至于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有些“不切实际”,但的确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外交方面的理念转变,中国采取了“积极主动,逐步深入”的方针,在80年代全面参与了联合国几乎所有政府间组织,并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在柬埔寨、西撒哈拉、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东帝汶等地区的维和行动,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制定以及联合国在裁军、人权、防扩散、环境与发展等若干领域的国际谈判并积极支持。可以说,从80年代开始,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实践中已经开始逐步确立了多边主义的外交思维。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思维进一步蓬勃发展,一方面中国全面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各项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7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加入了大量世界和地区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有关问题领域中的国际机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不遗余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外交运动。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朝核六方会谈、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等方面表现积极,行为果断。可以说,多边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标志之一。
公共主义与中国外交的透明化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美国学者和外交官使用的说法,在英国称为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主要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交往。(注:韩召颖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国际文化项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共外交”是1965年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首次使用,后来在其教科书中将公共外交界定为“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注:Harold Nicolson,Diplomacy,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1988.) 公共外交绝非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更加深厚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美国前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John Reinhardt)在谈到公共外交时认为,美国公共外交是“美国政府进入国际思想市场的活动”。(注:Allen C.Hansen,USIA: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New York,1988,p.2.) 从更广泛的意义言之,公共外交所反映出来的是一国政府着眼于沟通不同思想文化,促进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的外交努力;或者说从根本上昭示了一国政府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开展国家行销、塑造一个良好国家形象的战略策划。近年来,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形成一种潮流,特别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带头在全球掀起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新高潮。可以说,公共主义越来越成为外交运行的一个重要理念。
中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向自觉的过程。最初,中国根本无所谓公共外交,“国外的外交学研究机构对公共外交的问题已经开始予以重视并进行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仍然是空白”。(注:曲星,“影响外交的因素在不断增加”,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23期,第40页。) 中国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最早见于1990年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等编译的《国外外交学》,主要介绍了公共外交的概念,比较简单和粗略。后来,鲁毅教授在1997年编著的《外交学概论》中进一步进行了分析和诠释,明确了公共外交(在书中称为“公众外交”)的含义,认为公共外交包括两大类:一是对外传播,二是发展国际文化关系。认为公共外交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起到沟通和影响的作用。(注:鲁毅等著:《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64-165页。)。同时,鲁毅等学者把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结合起来,认为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创举。《外交学概论》作为外交学中国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基本确立了公共外交的学术地位,但是整体上还比较粗糙,只是一些框架性的建设,缺乏血肉的附加。
学术界尚且如此,外交界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就更加有限。由于缺乏公共外交理念上的指导,中国政府一直把塑造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活动等同于“对外宣传”、“民间外交”,而且后者更多地服务于国家的政府间外交;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则同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活动一起放在了地方或者部门外事活动名下,很少贯穿影响或者改变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印象的外交使命。由于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一个公共外交的理念作为统帅,“政出多头”,导致中国的公共外交体制比较散乱,缺乏整体的协调和配合,缺乏制度化的协调机制,调集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作为公共外交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形成。我国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随后,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李肇星、沈国放等一批新闻发言人应运而生。后来,国务院和中央其他部委纷纷仿效,1991年1月,国务院成立新闻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新闻办),进一步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和机构化,主要职能是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供书籍资料、影视制品等方式开展工作,对外介绍中国;协助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以便有效、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广泛开展与各国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交流、合作;与有关部门合作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国媒体对各国情况和国际问题的报道,以便中国受众及时了解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新发展。到目前为止,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各部委、各级政府纷纷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非意味着公共外交理念的形成。中国政府真正认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是在2001年,特别是随着美国在“9·11”事件后日益重视公共外交,中国外交部也把公共外交纳入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02年开始,外交学院举办的外交干部培训班开始把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必要的培训内容。2003年外交部新闻司内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全面负责公共外交事宜。不过,相比公共主义理念对外交运行机制的要求来说,中国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还十分有限。开展公共外交,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闻司、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机构和媒体,用各种传播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政策,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理解”。(注: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机制还显得滞后于公共外交实践的需要。
虚拟主义与中国外交的智能化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技术工具诸如传真请愿书、电子邮件游说、网上论坛、按键式投票(keypad vote)、调制解调器计算机网络等日益普及,民众可以借助网络创设的虚拟世界直接告知领导者,告诉他们对这些政治人物的期望,希望他们去做些什么。信息时代的浪潮对社会各领域包括对外事务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学界开始讨论所谓的“无外交官外交”(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是否会出现。对国家政治而言,计算机网络造就了电子民主时代,若将互联网应用于国家外交之上,则为“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简单的说,“虚拟”(virtuality)指的是透过电子工具协调的互动,而非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虚拟外交”便是国家及社会透过各种电子媒体进行互动,以达成沟通目的或处理国际事务,亦即使用信息科技以协助国际关系相关事务及活动的处理。
外交中的虚拟主义并非仅仅是信息传播技术与外交的技术上和形式上的结合,而是触及到外交内容和本质的变化,它涉及到外交运行过程中一系列环节和机制的变化。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逐步推开的即时使馆(instant embassy)、虚拟团队(virtual teams)、外交部官方网站以及外交人员网络职业训练等均是虚拟外交的表现。不难看出,应用现代信息科技于外交工作当中乃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虚拟外交的各项表现正为国家外交体制的改革与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方向。身处信息时代,面对多变的国际环境,在国家关系紧密、国际议题与行为者均复杂且多元的情况下,外交运行机制面临了许多挑战,必须进行改革以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虚拟外交在中国得到重视始自90年代中后期,是互联网普及过程中的产物。据原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朱邦造介绍,外交部网站建于1998年7月,1999年10月第一次改版,2001年第二次全面改造。(注:http://sydney.china-consulate.org/chn/xwdt/t41476.htm) 新网站形象现代、清新,结构布局更合理,内容进一步丰富,包括“外交部”、“外交政策”、“双边关系”、“背景资料”、“服务项目”五大栏目,动态和静态信息共计500多万字。作为中国外交部开展公众外交的一个窗口,新网站具有较强的交互性,更强调为公众服务,增设了嘉宾访谈、即时评论和邮件订阅等功能,还适时邀请中国外交界人士就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与公众进行网上对话,请公众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评论,从而增加了普通公众参与中国外交的机会。
同时,为了给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展网上宣传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外交部与彩练信息系统(北京)公司合作,开发建设了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一体化的因特网信息发布管理系统。该系统是基于浏览器操作的共用信息发布平台,各驻外使领馆通过共享中央信息库和网页自动生成软件,实现了对各自网站的管理和维护。外交部可通过该系统向我驻外使领馆网站提供在线技术支持,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新系统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可扩展性,同时也为系统内各网站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外交部已开始在我驻外使领馆逐步推广这一系统,并在2002年建成以外交部网站为核心、驻外使领馆网站相配合的一体化的中国外交系统因特网信息传递体系。
外交部新闻司是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因特网宣传工作的主管部门。近年来,新闻司加强了虚拟外交事务,专门设立了网络处,注重做好外交部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注意及时更新和不断充实主页内容,确保重大外交动态信息在第一时间上网,静态信息不断丰富。目前,外交部网站已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政府网站。国内外读者对该网站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外交部网站内容丰富,更新及时,是了解中国外交信息的权威站点。
总体来看,近年来,外交系统的虚拟化、电子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初步奠定了电子外交或者虚拟外交的基础。但是,与信息时代的需要来看,仍然还很不够,虚拟外交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更涉及到理念、体制、制度和运行机制等众多层面。比如在驻外使馆建设方面,传统上,建立一个新驻外使馆或外交据点所要花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可至数月甚至以年来计算。而在信息时代,只要一张机票、一台笔记型计算机、几部电话再加上一本外交护照,外交人员便可以“随到随上工”(hit the ground and run)。再比如,在具体外交事务办案上,在过去传统的官僚体系之下,外交官往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理上的障碍使得若身不在当地则无法负责该地的工作,外交工作的进行常牵涉到距离、人员调度及联系不便等困难,而在信息时代,通过信息传播科技的使用,驻在不同地方的外交人员可以相互将其专才结合组成虚拟外交工作团队,藉由遍布世界的网络连结一同处理正在发生的国际议题,而不必将所有的人马都集合在事件发生地,从而构成一个包含众多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统一网络和虚拟团队,集中集体智慧处理同一问题。(注:在1996年扎伊尔(Zaire)危机时,加拿大所组成的虚拟外交团队,其成员遍布非洲、渥太华、纽约及华盛顿各地。此外加拿大外交部亦架设一高科技平台(platform)" SIGNET" ,将加国驻在世界各地外交工作人员的计算机相连结成一个网络,透过此种连结提供各种议题的虚拟服务、线上服务。于是," SIGNET" 将97%以上的外交人员相连结成一虚拟组织,来协助解决发生的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开展面向所有外交官员的网络培训、设立外交事务电子档案、开发对外事务管理系统、开展外交事务计算机模拟演练、建立对外行政模拟仿真系统等等,全面推动中国外交运行的虚拟化和智能化进程,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息时代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是总体性的,甚至有可能带来外交形态的全面转型。
结论
中国外交新思维的发展,顺应了当今世界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外交的发展和和平发展的道路意义深远,应在外交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完善、提高。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中国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大局,在外交思维上进一步增强共同利益思维、多边合作思维、公共外交思维和虚拟外交思维,更好地适应全球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