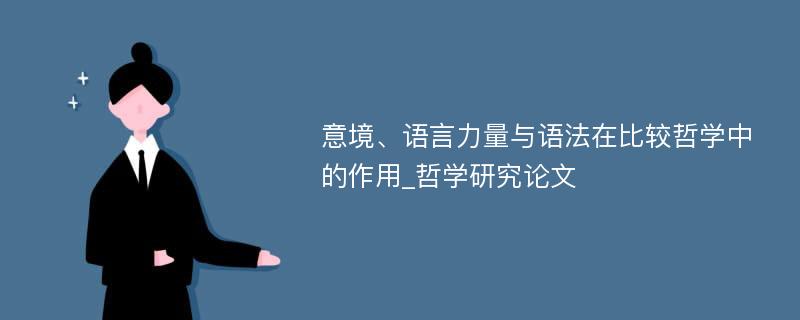
语气、语力以及语法在比较哲学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语气论文,哲学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130-06
一、导言
比较哲学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对不同传统的哲学文本进行翻译、解释和比较时,自然语言语法的研究和分析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发挥作用。与这一问题有直接关联的一个论题主要涉及意义的复合性(compositionality),哲学家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自然语句含义的结构或逻辑形式可以通过其句法的复合性来系统地考察。如果是这样,那么有可能表明,支配自然语句的句法规则可以同确定的语义操作联系起来,这些操作作用于语法成分意义的方式与这些成分在句法中的组合方式完全一致。
在那些对语法在日常语言活动或交往活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持谨慎态度的人看来,这样一种观点很可能并不成立。这些哲学家往往会怀疑,语法事实能否对哲学著作或哲学陈述的解释或翻译的各种理论做出裁决。由此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比较哲学的领域,研究语法是枉费精力,多此一举;或者认为应当用其他的方法取而代之,比如那些充分考虑了交往语境、常识、历史证据或轶事等因素的方法。简而言之,拒斥这一基本观点的人更倾向于强调语用学在比较哲学中所起的作用,而非形式语义学。
虽然我与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我认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似乎源于他们没有清晰地理解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基本区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至少能够澄清,哪些意义上的语法研究可以与比较哲学相关或者起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将不会直接讨论复合性论题,即根据比较哲学的语言学或语法学进路为之辩护,而是会做出一些评论,以捍卫它所蕴含的一个更为狭窄的论题,我称之为“语气—语力关联论题”(mood-force correlation thesis),以同前辈学者保持一致。非常粗略地说,这一论题主张,遵循语法规则的语气(grammatical moods)①与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s)②之间密切相关。
例如,戴维森就反对句子的行事语力由语言约定来支配。他劝告我们放弃那种认为语力和语法语气密切相关的看法③。一个更近的例子是,肖阳曾针对作为非屈折语言或非“分析性”语言的汉语发表看法,认为“我们必须考虑说话者做出陈述的‘整体语境’”,因为“在一个句子的语气指示标记与句子的语力之间没有严格关联”④。值得注意的是,肖阳把这一观点推广到了包含屈折语和非屈折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并且把它当作比较哲学的语用学进路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本文中我将论证,持一种强语用学倾向的比较哲学家往往会低估语法研究对意向和交往活动之本性的揭示,从而轻视语义学在比较哲学中所起的作用。
二、语气与语力的关系
我们一般都承认,口头交流要比用句子描述事实做的事情更多。自然语言是一种工具,它能让我们问问题,发出命令,提出请求,提供建议,表达愿望或歉意,就过去和将来做出假设等等。对句子的各种用法可以对听者产生各种预期效果,这些效果有时被称为“行事语力”。如果我的意向是让另一个人按照我的愿望行事,那么我就会使用这样一个句子,其行事语力是发出命令⑤。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用有些自然语言(也包括英语)写成的句子会有一些语法属性,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各种不同的语气。比如一个句子可能具有陈述式、疑问式、命令式、虚拟式等语气⑥。这些语气通常通过屈折变化的属性来区分,即动词的标记或变化。虚拟句通过主要(虚拟式)动词的时态与其他类型的句子区分开来。例如,“I would know it if it were true”中的虚拟式短语要求动词“be”变为过去时的“were”。尽管整个句子的意义并不是指过去,但仍然需要做这种变化。而命令句的动词则总是以不定式的形式出现,比如“Open the window”中的“open”一词。严格说来,如果认为语气通过屈折变化而被个体化,那么英语中并没有疑问语气。这是因为,英语中的疑问句并不是通过对动词做系统的改变而生成的,而是通过其他手段,比如重新排列语法成分,或者添加像“do”这样的助动词⑦。根据这样一个假定:语气不仅通过屈折变化来区分,而且还通过其他显然的语法特征来区分。
这一假定之所以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尽管汉语并非屈折语,但汉语句子却可以根据语气进行分类。这是因为,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有一些语气词可以用来指明语气。例如在古汉语中(孔子的《论语》提供了许多例证),疑问语气由位于句尾的语气词“乎”来指明。类似的具有疑问功能的句尾语气词还有“诸”。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语气词“著”和“好”,表示命令语气⑧。在现代汉语中,“吗”是一个位于句尾的疑问语气词,“吧”则往往用来请求同意或用于劝说,指示命令语气。其他例子还有不少⑨。
我们现在转到原先的问题:在语气(英语语法的一个特征)和行事语力(句子的一种预期效果)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关联?英语句子的各种用法(通过其行事语力来辨别)是否显示了与它们所属的语气之间存在着系统关联?例如,陈述句是否仅仅用来做出断言或者描述日常语言活动中的事实?疑问句是否总是为了提出请求或提问题?命令句必定是用来发出指令或命令的吗?
为了说明本文的观点,我们不妨看看肖阳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相反意见。肖阳说:
一个句子的语气指示标记与这个句子的语力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 因为说话者总可以意在用这句话来做一些未被其语法特征或约定特征所决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说话者做出这个陈述的“整个语境”⑩。
为了说明这一点,肖阳提供了一些例句,其中有些是从戴维森那里来的,它们的行事语力似乎与它们的语气相抵触。他以《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为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
肖阳认为,孔子对叶公的回答虽然是陈述语气,但它显然不仅仅用来描述一个事实,而是为了“进行规范的教导”。显然,孔子的确使用了陈述语气这个事实与他的交往意向并不相关。事实上,这样看来,假使孔子使用了一个疑问语气的句子(在古汉语中,只要出现疑问语气词就可以了),所获得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哪怕孔子说出以下这番话,也能获得同样的行事语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译者加):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乎?(12)
的确,当我们就行事语力或一般的交往活动做出判断时,考虑“整个语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说话者未必会遵照语法特征或语言习惯使用句子(13)。假如真的像肖阳所认为的那样,古汉语中的语气和语力之间不存在重要关联,那么唯一重要的便是一般语言背景和非语言背景中所揭示的孔子实际的交往意向,而与如何选择语气无关。事实上,当肖阳声称“语气不重要和不相关”时(14),他似乎认为,言辞只有通过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归纳推论的(inductively inferential)过程才能被理解:它不仅仅涉及将对方的语词进行解码,通过诉诸惯常的语法规则来导出其意义,而且说话者必须考虑各种信息以理解对方背后的含义和意图。
在我看来,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忽视了重要一点,即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对翻译和解释的方式造成影响,而这对于比较哲学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比较哲学的任何一种完备方法都应当把严格考察所涉及语言的(由语法属性所体现的)语气当作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说话者对语气的选择一般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句子意义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气的影响,而语气总是与人们的习惯和期待相联系的。我们应当特别考察语法影响语力的确切方式,因为它为整体语境中可能出现什么提供了蛛丝马迹。
即便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要力争能够确定,说话者对语法习惯以及对这些习惯的任何可能偏离所能激起的他样行事效果有什么样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偏离所造成的各种结果总是构成一个组:有些会导致冒犯,有些则会给人一种勉强或顺从的印象(比如前者可能是因为使用了一种命令语气而不是通常的陈述语气;而后者则可能由于在通常使用命令语气的时候使用了疑问语气,等等)。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对某种语气的新奇用法或特殊用法,而且还有这种新奇用法或特殊用法在什么意义上偏离了在那种语境中更常用的语气。毕竟,孔子在这里使用陈述语气而不是(比如说)疑问语气,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因为疑问语气可能会造成一种不同的行事语力效果。
三、语气选择及其在交往活动中的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在正常的交流会话语境中完全可能出现的简单例子。假定玛丽在一家鞋店买鞋,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她对售货员约翰说,“我偏爱9码的鞋(I would like a size nine)[为了和下文内容对应,这里做了特别的翻译——译者加]。”于是约翰走到货架拿了一双9码的鞋回来。我们考察一下玛丽说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情况似乎是,玛丽通过说这样一句话,不仅期望它完完全全就是她所说的那个意思,而且还期待某种更多的东西。或者更加具体地说,玛丽想要交流的至少有两种东西:首先是直接说出来的陈述本身,其大意是指,玛丽偏爱某种鞋;其次是没有直接说出的东西,它也许可以描述成一种以特定要求的形式表示出来的辅助含义,这种意思如果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诸如“请给我拿双9码的鞋。”(Please get me a size nine.)这样的命令句。根据Searle(1975)的说法,我们称后一种含义为初级的行事语义(primary illocutionary meaning),前一种含义为次生的行事语义(secondary illocutionary meaning)(15)。
我这里试图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经过理性重建,就能解释约翰如何能够辨别出玛丽的初级行事语义。也就是说,他是如何“把她的话听成一种要求”,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偏好的陈述。毕竟,人们并不是任何时候听到这样的陈述都会做出这种反应的。假使在饥肠辘辘又无食物可寻的情况下,我对正在荒野中跋涉的朋友说,“我真想立刻要一个火腿三明治”(I really would like a ham sandwich right now),这当然不会“被听成一种要求”。因此,这里有一种重要的行事表意行为需要给予解释。
肖阳也许会认为,玛丽通过她的言辞所要表达的意思就类似于“请给我拿双9码的鞋”。例如在肖阳看来,“日常生活中看似朴素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范围极广的事物”(16)。在我看来,这种认为句子可以意指范围极广事物的看法对语言交流做了极度简化,因为它将说话者的意思与句子的意思相混同,从而混淆了行事语力和意义这两个概念。这就好像认为,句子除了字面的语义内容,还必须根据当时的语境而具有“语用含义”。然而一旦承认语用含义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随用法而改变),那么句子本身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因为意义被个体化的条件必须由语境来提供。根据这种观点,只有作为句子个例(token instances)的言辞(utterances)才具有意义,这将意味着把意义与句法径直割裂开来。
这些观点没有认识到,句子往往只作为对意向的提示而被我们说出来,而我们想到的大量事物则尚未明说。换句话说,认为我们习惯于在说话的同时,期待这些话能够被对方以不同于其语法形式所指定的方式来解读,这是对交流意向的误解。当玛丽说“我想试一下9码的鞋”时,她希望售货员做的完完全全就是这件事。她是在陈述一个关于态度的事实,而不是在表达一种愿望或要求。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她期待着这种交往语境已经足以使售货员洞悉她未明言的那部分想法或意图。
这背后可能存在着许多原因,这里无法充分讨论,我只提出三种以供参考。其中两个原因是经济性和惰性,即说话者总是希望使用最少的手段和精力,及时而有效地交流他们的思想。第三种原因是礼貌。为了避免冒犯,玛丽并没有把她所希望或期待的东西和盘托出,而是话中有话。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可以依赖社会和语言习惯,共同分享大量语言和非语言的背景信息,很容易基于双方都可能承认的前提而得出有效的推论。一般而言,对语气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我们关于“对话者渴望在社会中的自主和自决”身份的复杂心理假定。
应当指出,我在这里所捍卫的观点与肖阳及其他采取语用学进路的哲学家并非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也相当强调说话者在确定意义时的扩展推理。交流主要是一种让人的意图能够被理解的行为,交流的成功将总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归纳推理以及推论出最好的解释。然而与此同时,一个人参与这种扩展推理的能力将大大依赖于在推理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种种信息,它们对应于复合性的约束以及字面含义的约定。要想把握说话者的意思(不一定通过言辞来表达),我们必须首先把握句子的字面意思。但是没有必要认为,当说话者用一句话来提示听者想到一大堆东西时,这些想法构成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或部分含义。句子的含义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原样,它不会因语境而改变。听者并非即兴地按照语境来重新解释听到的语词,而是照字面来接受其含义,并且根据它们可能的相关性假定和推断,判断其行事语力。
这样说有些简化了。但我认为,我的比较哲学进路与受语用学支配的理解意义的进路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这样两条方法论的假设:首先,任何一句话的意义都已由它的词项内容和逻辑形式所穷尽。这个意义有时被认为是一句话的“字面意义”。但在我看来,“字面”一词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可言。这些意义是被给予的,而不是在语境中产生的,它们与业已确立的语言习惯和规则无关。研究意义的学科主要是语义学,它关注的是那些与通常固着于句子本身(即句子类型,与言辞相对)的词项内容和逻辑形式相关联的属性。
其次,言辞并不具有独立于句子的含义,因此它们不会改变、拓展或取代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具有的意义。言辞是自然语句的个例,比如在特定语境下写出或说出的话。就这一点而论,它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而研究言语行为的学科主要是语用学。语用学考察的首先是在特定语境下写出或说出的专属于自然语句的大量复杂事实,其次才关注意义,即说话者以多种方式利用或运用自然语句的意义,以获得特定的行事效果。
四、语气及其在比较研究中的作用
本文主张,在这些问题上持一种强语用学进路的哲学家容易忽视比较哲学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我们能够基于对语气如何限制语力的思考提出一些关于交往意向的重要问题。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方法大致与下面一些问题联系着:给定一种自然语言L,是否存在着任何语气是由屈折变化或除L的屈折变化之外的句法手段或属性所标记的?这些特征的缺少如何可能作为一种偶然事实鼓励或阻碍特定的交往活动?如果存在这些特征,那么语气如何往往会限制L中的行事语力?关于L中使用的陈述句、疑问句、命令句和虚拟句,可以说明哪些语言的、社会的或行为的活动或习惯?在一个特定的交往语境C中,通常选择什么语气来交流某一特殊意向?如果在语境C中,实际选择的语气碰巧不同于通常选择的语气,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它?为什么说话者在这种语境下偏离通常的做法?通过使用这种不同于往常的语气,说话者在这种情境下试图传达出什么别样效果?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总是现成的,特别是在我们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而且即使证据充分,也往往不能平息长期存在的争论。在为跨文化比较而对哲学文本进行解释和翻译的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肖阳本人注意到,一代代的注疏家对于《论语》中言辞的行事语力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判断,单凭这个事实就已经加剧了这项工作的不确定性。这里可能并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17)。然而即便如此,面对着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屈从于言辞可能具有的行事效果来限制我们的方法论见解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我们力争找到支持我们选择的解释和翻译的强论证,通过努力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我希望已经表明,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对我们评判各种不同的解释或翻译提供很大启发,而且应当因此而被看作比较哲学的一个固有目标。这方面的成功将依赖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日常语言活动背后的习惯受制于我们对语法规则的一种心照不宣的习惯性遵守,对这些规则的分析对于研究这些活动十分重要。
注释:
①作者在mood前加grammatical,一是强调mood指语法上的“语气”,而不是平常说的“情绪”;二是强调语法的作用。下文中出现的mood大多与grammatical连用,为了简洁,下文一律译为“语气”。——译者注
②illocutionary一词有多种译法,比如《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42页)译为“语内表现行为的”。《现代语言学词典》(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7页)的解释是:“示意[言行]。言语行为理论术语,指说话人通过说出的一个话段所实施的行为,即示意言行(illocutionary acts),或称示意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示意言行的例子有许诺、命令、请求、洗礼命名、宣布逮捕等。这一术语与发话言行(‘说话’行为)和取效言行(按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来定义的言语行为)相对立。”根据这种解释,illocutionary force或可译为“行事示意语力”。为了简洁,下文均译为“行事语力”。——译者注
③例如参见“Moods and Performances",pp.109-110,in Davidson(1984),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Xiao,Yang(2006),"Reading the Analects with Davidson:Mood,Force,and Communicative Force in Early China",in 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Constructive Engagement,ed.by Bo Mou,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p.266.
⑤应当注意,就我的理解而言,任何句子的行事语力都是它在听者那里造成的一种实际效果,尽管这一术语可以用来仅仅描述一种意向的或预期的效果,即说话者希望通过使用它所造成的效果。这一差别在后面的讨论中并不重要。
⑥下列例句对动词“to carry”做了屈折变化:(1)We are carrying our umbrellas today.(陈述式);(2)Are we carrying our umbrellas today?(疑问式);(3)We should carty our umbrellas today.(命令式);(4)We were to carty(could have carried) our umbrellas today.(虚拟式)。
⑦比如英语陈述句“We are going to the grocery”通过颠倒前两个成分的顺序而变成问句:“Are we going to the grocery?”英语陈述句“We always remove our shoes before entering”通过添加“do”而变成问句:“Do we always remove our shoes before entering?”
⑧这些语气词在Xiao,2006,pp.255-258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在p.257的一个脚注中,肖阳请读者参见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关于古汉语中用来指示命令式的各种语气词的详细讨论。
⑨关于对这些语气词的实用而详细的探讨,参见Li,Charles & Thomoson,Sandra A.(1989),Mandarin Chinese: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⑩(14)Xiao,2006,p.266,251.
(11)参见Xiao,2006,p.259.这段话引自Yang,Bojun(1980),Lun Yu Yi Zhu[The Analects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s] (Beijing:Zhonghua shuju)。肖阳使用的是他自己的翻译,不过承认受到了译者Simon Leys和D.C.Lau的影响。
(12)肖阳遵循Simon Ley的做法,将《论语》开篇带有指示疑问语气的尾助词“乎”的第一句话翻译成:“The Master said,‘To learn something and then put it into practice at the right time:is this not a joy?’”(肖阳将这句话解释为一个断言,尽管它是疑问语气)我在这里设想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话变成了出现了尾助词“乎”的与此类似的疑问句[译者按:请注意,汉语古文中无标点符号]。
(13)当然,语气和行事语力之间并不存在律则性(law-like)的关联,也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联。因为任何自然语句都不能够迫使说出它的人根据某个目的使用它,就像锤子不一定总是为了敲钉子。任何陈述句也可能被用来问问题、提出请求或表达愿望等等。虽然我很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要比许多语言哲学家所认为的少得多。事实上,我拒绝声称表明这种观点的许多典型反例。例如经常有人说,疑问句所做的事情似乎要多于问问题:考虑“你能把盐递给我吗”“你确信不是在开玩笑”以及“你注意到琼又戴上了她那顶紫色的帽子吗”这三个句子(最后一个句子引自Davidson,1984,p.110)。不仅如此,我们似乎还可以用命令句或陈述句问问题:考虑“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想知道你的电话号码”这两个句子。还可能认为,命令可以用陈述句来表达:考虑戴维森的绝妙例子:“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进门之前要脱鞋。”修辞问题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强,比如:“还有比六月天更珍贵的吗?”(What is so rare as a day in June?)在我看来,这些例子说明了什么其实并不清楚。如果它们旨在显示,句子的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比由句子的词项内容和逻辑形式所确定的更为复杂,那么我认为它们并没有达到目的。依我之见,一个句子除了它的语义(或“字面”)内容之外,不可能具有语用含义。如果说这些例子说明了什么,那么我以为就是,日常语言交往涉及的东西远远不止是:说话者用一句话来传达一种思想,听者用传达一种思想的另一句话来回应那一句话。例如,在说出“你能把盐递给我吗”这句话的时候,很容易猜想说话者是为了表明“把盐递给我”,而没有别的意思。本文当然不可能就我在这里认为必要的解释做出完整讨论,但我希望最后的这些评论能够表明,要想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就这里起作用的过程提出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图景。
(15)塞尔关于言语行为的著名观点使我深受启发,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间接言语行为的分析,它们揭示了看似简单的会话中所包含的惊人复杂性。参见Searle(1975),“Indirect speech acts”,in Syntax and Semantics,3:Speech Acts,P.Cole & J.L.Morgan,eds.,New York:Academic Press,pp.59-82.在这篇论文中,塞尔是这样提出由间接言语行为所提出的问题的:这里的问题是,说话者如何可能在说一件事物和领会它的同时还意指其他事物。由于意义部分在于在听者那里造成理解的意向,所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听者如何可能在他所听到和领会的句子意指其他事物时,理解这个间接言语行为(p.60)。在我看来,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是足够清晰的,但在这里仍需小心。塞尔显然想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概念,一种是句子层面的,另一种则是(非语言的)意向层面的。也就是说,他承认句子有意义(即使只是[在心灵中]衍生地),但说话者可以独立于他所使用的句子来意向一种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样来改变塞尔的第一种说法:“这里的问题是,说话者如何可能在说一件事物和领会[他所使用的句子的字面意义]的同时还意指其他事物[即某种不同于他所使用的句子的字面意义的东西]。”我认为这样来澄清问题是重要的,因为我否认存在着所谓的“语用含义”,当我们声称,在说一句话的时候,说话者可以“领会一件事,同时又意指其他事物”,我们很容易危险地假定,说出这个句子可以同时意指两种不同事物。这种错误是我们希望避免的。一个人可以用某个句子S,虽然使用它可以意指某一特定命题P,但句子本身却可以意指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比如命题Q。事实上,虽然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在我看来,它并不像许多学者所愿意认为的那样常见。但是无论如何,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应认为蕴含着:句子本身S有两种不同意义;S只有一种意义,它不大随交往语境而改变。
(16)这段话引自Xiao,2006的第一个脚注。肖阳似乎只是顺带地评论了一句,但我认为它很能说明他背后的预设,所以不应当被忽视。
(17)Xiao 2006,p.266,footnote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