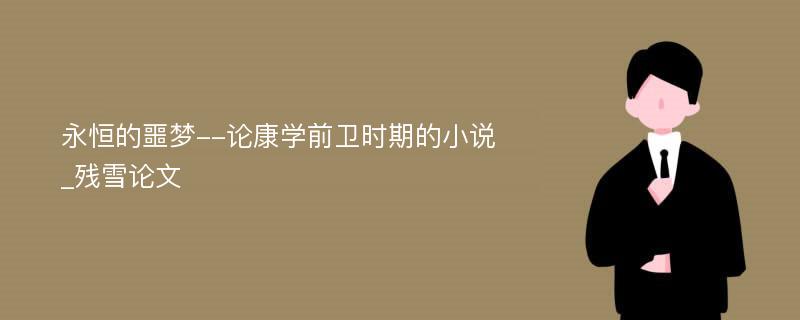
永久萦绕的噩梦: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雪论文,先锋论文,噩梦论文,时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次采访中,当残雪的日文译者问及她的作品缺乏“横向”(线性叙事发展)时,残雪的回答是:“或许那与记忆有关吧。我认为自己是丧失了记忆的人。写水平流动小说的人肯定有记忆。因为我的情况是丧失了记忆,所以既不考虑、也不想考虑以前的事。我总是只考虑现在。”①
残雪强调现在才是她叙事的唯一时间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然而,余华清醒地意识到神经错乱的意象群体所蕴含的现在同时包括过去和将来,而残雪对记忆的态度首先是暗示的(“有关”),其次才是否定的(“丧失了记忆”)。因此,我们阅读这个段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她的小说与她失去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她的小说读作记忆的绝对空无。
先是提起记忆然后又对记忆加以否定的做法,意味着在意识中建立起抵御过去精神创伤体验的心理屏障。残雪的短篇回忆录《美丽南方之夏日》就是例证,残雪在文中回顾了她在国家与个人的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度过的童年时代。她在开场白中写道:
1957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1959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少挣扎着。②
这个段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残雪童年生活的历史背景,正如她在整篇回忆中所做的那样,残雪绝口不提在此期间她的记忆必须面对的所有精神痛苦。残雪强调的是当时生活的艰难。父亲被划为“阶级敌人”,全家都被赶出城市中心,不寻常的是,现实迫害却没有被提及。通篇回忆主要描写她外婆神秘而又精明的性格以及她父亲乐观坚韧的气质,全然没有她小说世界中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不过,其中也不乏精神骚乱的蛛丝马迹,尽管没有涉及历史根源,却也显示出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特殊处境中饱受骚扰的精神状态。推开厨房的门,她“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③,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走动。夜间去山坡上的厕所解手时,她老是害怕那里“埋伏着一只蜥蜴”④,这令人联想起她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山上的小屋》中的场面。
这篇回忆以及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独特意象,是身体的肿。在本篇回忆中,残雪经常受到松毛虫引起的“红肿”的折磨⑤。她的外婆死于水肿病的时候,身体“肿得如气枕”⑥。尽管与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肿的意象却可以被理解为激发当时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种症状。残雪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肿的意象。在《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我的“脸部肿起老高,一天到晚往外渗出粘液”⑦。在《山上的小屋》里,每当“母亲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的后脑勺……就发麻,而且肿起来”⑧。在《天窗》中,“因为被尿泡过,长大起来,我的眼珠老往外鼓,脖子软绵绵的,脑袋肿得像个球”⑨。在《黄泥街》里,齐婆的嘴里一咀嚼,胡三老头的腮帮子就会肿起老高⑩。肿象征着肉体对无法彻底把握的暴力作出的反应。在这些情况下,肿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创伤的形象隐喻,原因大概总是那些不可理喻或者似是而非的力量。外在骚扰引起的肿的症状是如此难以捉摸或牵强附会,以致显示出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面貌。
在余华的小说中,对残忍暴虐的不恰当叙事是对遭受过精神创伤的主体的隐喻。在残雪的小说中,肉体痛苦极为丑陋的意象以及对那些经常看似合理的思想的不连贯表述,就是对无意识中精神创伤记忆含混暧昧和不可追踪的痕迹的暗示。残雪把余华的无动于衷、无可奈何而又病态乖张的叙事声音转化为一种极度敏感的语调,以此揭露不可思议和不合情理的动荡现实。
一、骚扰与分裂的世界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像肿那样令人不快的意象并非外来攻击的结果。在残雪的中篇小说《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中,肿的意象再度扮演了意味深长的角色。阿文踢着墙在屋子里四处找人,把脚趾也踢肿了;医生/侦探从屋子里跌出来,跌得鼻青眼肿;在“我”眼里,阿文的母亲像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据她说,她的脚“肿得像胡萝卜”(11);一天早晨,“我”的腿肿得很厉害;阿文妹妹的脚扭伤了筋,“肿得像水桶大”(12)。
这些肿的症状不是自发的,就是一个人自身行为的结果。尽管这篇小说的确展示了人际的攻击、怀疑和背叛的惊人景象,让我们联想起社会动乱的历史时期,但真正的痛苦并不总是可以直接触摸得到的,罪疚的原因也并不总是有形可见的。《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由不同叙事者的叙事组成,叙事者包括阿文(“我”)、阿文的三妹、侦探或医生(阿文三妹的未婚夫)以及阿文的母亲。每个人在不同的章节里都沉浸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观察之中。阿文在小说开头的评论“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的”(13),暗示他的观察是不可靠的,这样的不可靠进而扩散到了整个叙事之中。例如,墙上会讲话的假面结果变成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老头死后,他又声称自己变成了侦探/医生。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像吊死在阿文家门框上的那个老头,行为举止古怪离奇、令人费解。阿文的父亲故意弄断自己的腿,为的是装上假腿(他希望自己更加好看),他临死之前非常热衷于去绿山出游。他死在一棵板栗树下,旅行袋里装满了腐烂发臭的死黄莺和死山鸠。我们从他的出游计划中看到的只是荒唐和徒劳,这样的计划与残雪自己的父亲以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规划同样不值。
余华揭示了人类天性中的暴虐与残忍,而残雪与余华的不同在于,她注重畸形猥琐的人物。尽管如此,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从来不把表现理性和逻辑的故事当作对政治或社会不公平的直接控诉。残雪的多元悖反的主体声音像是在叙事的困惑中挣扎却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譬如,在假腿与好看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关联。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他关心被杀死的鸟类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关联只能用作者记忆中无法诠释和含混暧昧的过去的精神创伤体验来解释,堕落邪恶可以化作道貌岸然。像这样混淆愉快与痛苦的崇高审美观来源于不能清醒回忆、在理性的范围内无法把握的那种令人恐惧敬畏的东西。无意识的影响来自重复出现的过去经验却又不具备整体的框架或形式。
《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中的人身攻击、人与人之间的怀疑和背叛似乎也跟历史背景和政治影响无关。然而,出乎意料和毫无道理的人身攻击和互相背叛正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运动期间流行的社会通病(14)。阿文担心自己“从未看透”他的父亲,而母亲声称能够“看穿任何人的诡计”(15)。三妹的未婚夫自称是医生,他用听诊器检查阿文房间的墙壁。所有这些人的想法和行为之所以荒唐,不仅因为这些想法和行为毫无意义,还因为他们试图使这些想法和行为产生意义却又无法做到。这些想法和行为展现的无非是由怀疑和恐惧引起的那些也许是没有任何实质的精神骚乱。每当天黑的时候,阿文就开始挨个房间地寻找那些人,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在他看来,“这套房子一到夜里就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人全躲起来了,门窗也找不到了,如一个密封的铁匣子”(16)。叙事者承认,他在寂静中打开窗户,不断地朝无边的黑暗吐唾沫,直到嘴巴发麻。接着他又拿出铁锤整夜敲砸墙壁。除了搜查看不见的东西之外,我们不知道阿文为什么要搜查、躲藏、吐唾沫、拿铁锤砸墙壁,整个场景似乎毫无意义。尽管如此,诸如此类目的性的缺乏,非但没有否定精神骚乱的现实,反而体现了无法追忆的震惊造成的心灵深处对现实的躲闪。
因此,我们也许再也不会对阿文母亲自相矛盾的陈述感到惊讶,她先是抱怨她睡在箱子里,她的儿子踩到她的眼珠上,她为此痛苦不堪,接着她又声称整个故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如此这般的(自我)折磨的幻觉或者现实构成了片断的或不连贯的叙事。整个故事由一系列意外事件组成,这些事件营造出一种精神异常的气氛,好像那里是丛林而不是家庭。阿文的三妹非常好斗,她赶走了在黑暗中讲话吓唬人的母亲,用一把铁铲扎她。每天早晨,她与未婚夫把阿文赶出他的屋子,把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扔得乱七八糟。阿文则端着一把玩具枪把水射向墙上的影子,他怀疑这些影子想要杀死他。他试图折磨并且赶走住在厨房水池里、用手遮挡自己下体的三妹夫。另一方面,阿文的三妹也用她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射击她的未婚夫,用铁锤砸他。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用在这个只有敌人没有盟友的家庭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不连贯和不确定的骚乱也许是这篇小说最令人困惑的因素。小说的叙事没有就暴力行为与施暴的动机之间的脱节作出合理的说明。小说不仅由不同的叙事者组成,而且人物本身就是遭到无法解释的疑虑和恐惧折磨的叙事者。残雪的叙事是对无法表述的事物的一种再体验而非解释。侦探(即医生或三妹的未婚夫)在他叙事的那个章节里承认,他“绕来绕去,永远没法接近实质,只要一开口,就发现自己讲一件编造出来的事,而不是那件事”(17)。这里强调的“事”恰恰就是被残雪的叙事忽略的那种无法追忆和不可再现的事。人物本身有时也会暗示自己有记忆困难或者无法表述。阿文的母亲声称,“我失去了记忆,所以这件事无法肯定”(18)。当阿文想讨论“语言表达的障碍”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脑子里出现这句话”,然而他的“嘴巴动不了”(19)。
有名无实的走廊空间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在阿文的母亲和侦探看来,这条走廊“真吓人”(20),对阿文的三妹来说,它“朦朦胧胧,充满了诡计”(21),是“灾难的”(22)。然而,走廊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唯一“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就是阿文的姨妈在走廊里用手电筒把人照得眼花缭乱。其他与走廊有关的怪事发生在阿文的梦境中:走廊里养了两头豹子,一只狐狸从走廊的窗口跑进了云层。豹子和狐狸给家里带来野蛮的气息。换句话说,家庭变成了真正的丛林,丛林法则理所当然在那里统治着一切。要知道,丛林法则就是进化理论的核心,邪恶就是推进宏大历史进步的力量,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从中得出的结论。汉娜·阿伦特在她关于极权主义的著名论述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就是关于生存的历史法则,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却是关于自然的法则(23)。
阿文在梦中从家里逃出来,变成住在崖洞里的穴居人。令人难堪的是,这个家充满了残忍野蛮,而崖洞(根据阿文姨妈的暗示)却被精心布置成充满情趣的家。他在梦中经历的这种精神困境暴露了他的无助。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野蛮残忍的饥渴,对文明的向往与对非自然之物的偏好交织在一起。直到小说结尾,叙事者才终于声称,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结出了成熟的果实。这个田园诗一般的场面与先前描述的只有恐惧和危险的走廊大相径庭。然而,丛林再度显示出它的美丽,正如一个集权社会总要炫耀它的华丽庸俗的装饰那样。真实与不可能,诱惑与憎恶,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意识的潮流中纵横交错、难解难分。
总而言之,通篇小说缺乏线性情节,它由不同叙事者对自身体验的陈述以及对梦的描写片段构成。现实与幻觉难以分辨,所有的景象和事件犹如扭曲、错位或浓缩的梦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能被当作梦境来诠释。残雪的风格与奠定了意义的绝对真理的现代叙事范式背道而驰,反而倡导难以捉摸、躲躲闪闪的表现,以此暗示叙事扭曲失真的根源:历史精神创伤打断了自信与完整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残雪作品中的恐惧与骚扰并非来自真正的攻击,残雪所要表现的就是无法从无意识中现身的精神创伤记忆。正因为如此,真相不能得到完全彻底和恰到好处的表露,传达的真相看似扭曲而且如梦如幻。当众多作品记叙现实迫害下的悲惨经验,进而把绝对主体当作寻找安慰的避风港,残雪的叙事并不依赖表达真相的作者权威,而是注重于历史精神创伤造成的主体分裂。正如凯茜·卡露丝指出的那样,那就是“同时作为形象和遗忘的重复强加”的那种精神创伤,它“唤起了由发生之不可理解所构建的一种历史的艰难真实”(24)。
二、冷漠与恐怖的世界
相对于《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这个梦境和幻觉的大杂烩而言,残雪的另一部小说《苍老的浮云》情节就比较具体。小说的主要线索就是虚汝华出于对她丈夫、亲戚和邻居的恐惧,把自己关在一个门窗被铁条钉死的屋子里,她的身体逐渐变成了填满芦杆的空躯壳。这篇小说反映的也是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残雪仍然没有提供现实迫害的背景,她描写了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精神骚扰的无意识效应。这里的精神骚扰令人联想起特定历史时期标志着社会敌对气氛的言语攻击。例如,母亲在虚汝华的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很大的字:好逸恶劳,痴心妄想,必导致意志的衰颓,成为社会上的垃圾!”(25)残雪在这里用“很大的字”让我们联想起“大字报”这种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政治攻击形式:一个关系密切的熟人往往利用“大字报”粗暴草率和牵强附会地批判某人的政治观点,或者突然揭发某人的私生活。诸如“好逸恶劳”、“痴心妄想”之类的成语是用来谴责“非无产阶级”倾向或“反动”观点的十分常用的贬义词。
虽然虚汝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躲避她的母亲,母亲仍然接连不断地给她写字条,“有时用字条包着石头压在她的房门外面,有时又贴在楮树的树干上。有一回她还躲在树背后,趁她一开门就将包着石头的字条扔进屋里”(26)。这样的骚扰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过去经验中的历史暴力的扭曲再现。小说一开始,虚汝华从窗口捡到一个小纸团,扔纸团的大概是她的邻居更善无,他警告虚汝华不要“窥视人家的私生活”(27)。在怀疑虚汝华窥视别人私生活的同时,更善无自己的行为却侵犯了虚汝华的私生活。如此这般的背后相互攻击而不是正面冲突,构成了小说中驱使每个人物的神秘动力。更有意义的是,这里的言语骚扰,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话语骚扰,就是长期以来让残雪和她那一代人饱受惊吓和恐惧的无形政治力量。
尽管如此,话语威胁并不是心理震惊的唯一根源。在《苍老的浮云》里,除了互相猜疑之外,虚汝华与更善无之间还有过暧昧的婚外关系,他们彼此需要、互相警戒,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他们恐惧地相互搂紧了,然后又嫌恶地分开来。”(28)残雪对这样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冲动进行了挖掘。摇摆于历史暴力与主流话语之间的痛苦与色情诱惑或感情依赖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况(虚汝华的丈夫)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况的母亲根本就不爱虚汝华和老况,她经常带着“长统防雨胶鞋”或“一根铁棍”来到他们家,“一来立刻用眼光将两间屋子搜索一遍,甚至门背后都要仔细看”(29)。除此之外,她还不断差人给他们送字条:“要警惕周围的密探!”“在枕头底下放三块鹅卵石”,“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尤其不能望左边”(30)。
这些字条的风格多少是对那些目的在于为理性化的历史剧本制定规则的宣传话语的戏仿。尽管这些只能带来骚扰的字条并没有意义,但是“理论”教导的尖刻风格依然如故。老况被刻画成一个内心依赖母亲的不成熟男人,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对他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相矛盾的过激反应。一方面,他深受母亲的影响,老是担心会发生谋杀或者抢掠,“简直没法在这种恐怖气氛中生存下去了”(31)。另一方面,他“接到母亲的字条总要激动不安,身上奇痒难熬,东抓西抓,然后在椅子上扭过来扭过去的搞好半天”(32)。他也写过诸如此类的回复:“立即执行。前项已大见成效。”(33)
老况无疑是他母亲的同谋,他们一起“舞着铁棍在干那种‘驱邪’的勾当”(34)。小说出色地描写了老况对他所处的环境的自我矛盾的反应,他的挑衅举止和话语中表现出来的激动,以及他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的身份。老况在母亲的巨大阴影底下失去了他的主体完整性。后来,他的母亲要“搜集名人语录”以便“进行灵魂上的清洗工作”,老况“和母亲到街上去散步,手挽着手,趾高气扬,他心中升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感和自豪感”(35)。在帮助虚汝华给门窗钉上铁条之后,他的这种傲慢或自豪就转变为对母亲的彻底依附。他不断地小声叫着“妈妈”,“声音细弱得如同婴儿”,恳求母亲不要将他抛弃(36)。这种自大与自卑的心理交替注定了不稳定的主体错综复杂的感情走向。俄狄浦斯情结似乎不是对老况与他母亲之间关系的唯一解释,因为这里的母亲形象巫婆的成分多于母性(比如在挥舞铁棍驱邪的场面中)。老况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因此成为对母亲的依附,那是他向幼年堕落的结果,然而母性在他母亲身上已经不复存在。
象征着情感和温暖的母亲怎么会被描绘成絮絮叨叨的碎嘴女人?在残雪的许多作品中,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似乎被颠倒了过来,以表现儿子与母亲之间的变态关系。这样的母亲形象堪与经典的中国现代小说相比拟,如叶圣陶的《伊和他》中的所谓“‘阳具型的’母亲”,“作为主人的母亲”或“掩盖下的父亲权力”(37)。如果说叶圣陶的颂歌是献给即将破茧而出(一个现代隐喻)的“掩盖下的父亲权力”,那么残雪则揭露了“‘阳具型的’母亲”的独断专制。引起这种转变的是主流文学、艺术和电影,正如王斑指出的那样,“女性/母亲的形象常常与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38)。母亲的形象与“祖国”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表现实际上是毫不留情的政治势力的关爱性。事实上,在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被当作神话符号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下面这首“流行”歌曲(当然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39)母亲的形象因此被视为亲切和蔼的象征,然而它在残雪小说中所代表的却与此相去甚远。
这就是她噩梦般的小说的本质之所在:正面的形象或象征变成了超越主体理解力的含混暧昧和多义性。甚至自然景观往往也被降格为文化神话。通常被传统文人用来悲叹逝去青春象征的落花让更善无感到恐惧,他也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葬花。然而,更善无的葬花与黛玉的葬花只有表面上的可比性。更善无与多愁善感的黛玉不同,他无视“黛玉葬花”的抒情意义,“生气地踏倒了一朵目中无人的小东西,用足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拨着泥巴将那朵花埋起来”(40)。依此类推,残雪的“月光”也不再是美丽动人的形象,而是“像铺在地上的一长条尸布”(41)。
在这篇小说所有的凶兆中,太阳大概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小说一开始,更善无“在他的脑袋里搜寻着夸张的字眼”,好让他自己相信,“太阳一出来,什么都两样了,那就像是一种新生,一个崭新的开始”(42)。同样是太阳,除了在“夸张的字眼”中象征地位之外,它还是女主人公虚汝华心中的恐怖形象,“在林子边挂着一轮血红的太阳,红得很恐怖”,太阳让她的“太阳穴胀痛”(43)。红太阳是古今统治者专用的主要象征,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血红的太阳”是暴力和野蛮的隐喻。尽管这里的太阳仍然象征着一种“新生”或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个宏伟壮丽的形象却“红得很恐怖”,因为充满象征功能的太阳形象令人畏惧。这就是导致精神创伤的话语暴力和肉体暴力的主要根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雪的写作体现了返回本原(原初的事件、符号、神话等等)的不懈努力,然而这样的本原却因为受到病态经验的不断影响而不可避免地得到了病态的表现。
从象征的层面上看,太阳对应的是同时带来显赫与灾难的男人形象:在虚汝华的梦境中,“总有一个穿粗呢大衣的成年男子,一会儿慷慨,一会儿温柔地说出一些动人的话语来,一直说得她的耳朵嗡嗡地叫起来……在这一切的后面,是那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毁灭的临近”(44)。显而易见,如果说这个“成年男子”代表了弗洛伊德“诱惑场景”中的原初形象,那么“动人的话语”注定就是既诱惑(“一会儿慷慨,一会儿温柔”)又骚扰(“她的耳朵嗡嗡地叫起来”)的话语。毁灭正是以这样一种间断的而不是逻辑的方式出乎意料地降临在虚汝华(或残雪)的梦境当中。毁灭的凶兆可以被看作是分崩瓦解的主体对扭曲和错位的客观世界的感受。
《苍老的浮云》的主题就是萦绕着每个人物的持久不散的精神骚扰。有时,焦虑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东西,但焦虑的根源和对象却又无法把握。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回忆起所有的悲惨不幸。对虚汝华的母亲来说,她过去的精神创伤只是以一种幻影的视觉形象在她的头脑里出现:“她忘不了她失去头发的那件事,那个湿漉漉的秋天,树上的枯叶红得像要滴血,墙壁上渗出黑水,她坐在摇椅里,惶惶不可终日……”(45)原文中的省略号留下的是当时那件事无法追忆同时又是难以忘却的真实细节。归根结底,在难以忘却与无法追忆之间,在可以辨认与不可把握之间留下的只有“惶惶不可终日”。
残雪小说人物的焦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妄想狂幻觉,因为残雪的焦虑针对的不是某个单独完整的事件,而是随机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后果,在她的人物看来,焦虑是不可确定的。在小说开头的一个片段,更善无半夜里大呼小叫:“墙角蹲着一个贼!”(46)他醒来才发现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梦。另一方面,焦虑不只是幻觉或幻影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来自既可怕又可笑的真实事件。有一次,虚汝华的父亲怀疑她的母亲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吃他的肉,他看见她半夜里吮吸他的腿,他还发现自己的整个身体变得越来越瘦。他责问虚汝华的母亲:“你,干吗老吃我的肉?”她却更加凶狠地咆哮道:“呸!”“势利小人!算计者!我的天呀!”(47)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在老况与虚汝华之间,虚汝华继承了她母亲的习惯,变成了吸血鬼,她也在夜里咬丈夫的肩膀,吸他的血。在这里,即使连吃人与吸血都成为焦虑的根源,这样的表现模式也没有任何现实感。换句话说,那只能被看作噩梦,噩梦中的吃人与吸血是对社会或家庭中的恐惧的极端隐喻。
问题在于作者残雪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同一于虚汝华,那个最终把自己关在铁笼子般的屋子里的幽闭爱恋者。残雪在探讨自己写作的一篇短文中的自我描述暴露了她与虚汝华的相同个性:“一个人,生性懦弱乖张,不讨人喜欢,时时处在被他人侵犯的恐惧中,而偏偏又一贯用着一种别人看来是奇诡的、刻薄的眼光看这世界。”(48)对外部世界同样的心理敏感或者脆弱也导致了虚汝华的幽闭爱恋症,尽管那并不像是天生的禀性。事实上,正如我先前说明的那样,对骚扰的过度焦虑来自心理震惊的精神创伤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虚汝华睡着的时候觉得窗外的树枝在抽打她的脸。她让丈夫老况给所有的门窗钉上铁条,“这样一来屋子就像个铁笼子”,她也许只有“在铁笼子里”“才睡得着觉”(49)。
“铁笼子”的形象自然令人联想起鲁迅的著名隐喻“铁屋”,他希望(尽管不无犹豫)以此唤醒沉睡的人们(50)。相反,残雪的女主人公宁愿把自己关在被铁条钉死的房子里安心睡觉。这两个时代的两种形象之间的对立意味深长。这就是“五四”知识分子热切带入历史的革命,以继续革命的名义,引向了持续灾难对个人产生了震惊暴力,这样的精神创伤体验成为如今萦绕他们记忆的噩梦。虚汝华用来抵御外部骚扰的幽闭爱恋症就是“解放”话语底下的历史暴力带来的后果。这种话语正是从鲁迅与他的知识分子同伴的“五四”现代性话语发展而来的。
小说结尾的场面悲惨凄凉,虚汝华变成了一个干瘪的女人——令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著名诗句“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51)——她的身体填满了芦杆,弹上去会发出空洞的响声。“铁笼子”里现在铺满了死蟋蟀的尸体,破烂的线毯,被粉虫啃咬的藤椅,这是死亡和万物俱废的结局的绝佳写照。虚汝华的变形并非意味着启蒙后的蜕变,反而意味着再次出现和同时出现的精神创伤体验把残雪带入的生存困境。归根到底,那个干瘪的形象不是虚汝华,而是残雪的对象化自我。具有讽喻意味的是,外部世界不断增长的危险耗干了她的肉体。对虚汝华干瘪的身体的最早描写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她还是一个少女时,也曾有过做母亲的梦想的。自从门口的楮树结出红的浆果来以后,她的体内便渐渐干枯了。她时常拍一拍肚子,开玩笑地说:‘在这面长着一些芦杆嘛。’”(52)实际上,红色的浆果在这里表示唤醒精神创伤记忆以及使人反常的那种现时的和外在的刺激或者兴奋。因此,虚汝华悲剧性的形体变化只能用作者残雪的心理动机来解释,她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她自己的情意特征。
三、心理意象的毁形
卡夫卡式的变形寓言曾经出现在残雪最早发表的作品、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当中,小说的第一句开门见山:“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53)像这样以故事梗概开头的做法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大多数读者看来非同寻常,因为它无视理性的表现主体性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的基础。然而,这样的事实也许泄露了残雪自己对母亲的抵触态度(如果不是弑母情结的话),母亲的形象再次被塑造成一个妄想狂暴君,“铁一般的女人”(54),她不断地喊叫、自寻烦恼,抱怨儿子虐待她的“阴谋”。尽管如此,要是残雪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原型,她塑造的母亲形象就不会那么有趣。在残雪的小说中,母亲也确实关心儿子,只不过她采用了骚扰而不是启迪式的暴力和强制方法。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她安排儿子与科长的女儿、一个丑陋无比的老处女相亲,以此讨好她的上司。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残雪更倾向于表现儿子对母亲感情上矛盾的(如果不是敌意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母亲不断责备儿子的忤逆不孝。像这样沉重的声音不断造成了“我”的肉体痛苦,让“我”实际上成为杀害母亲的凶手。看到母亲脸上冒出的肥皂泡,她擦拭脸上的茶水的动作让他感到空虚,他“像受了鬼的差使”(55),建议她去洗澡,把滚烫的水倒在澡盆里。支配他的“鬼”显然就是阴暗的无意识以及遭到他否定的那个隐藏的自我。当他听见母亲微弱窒息的叫喊的时候,出于摆脱母亲的无意识愿望,他并没有在一切都变得寂静之前伸出援手。他撞开门,只看见澡盆里肮脏的肥皂泡,肥皂泡依然在意味深长地瞪着他,从澡盆底下传来母亲的声音。除了他明显的弑母倾向,主体爱恨交加的情感使小说的情节没有沦为平淡乏味的愿想成真。作为伦理原则的审查功能在这里被叙事者用来否定或者隐瞒他看着母亲消失的那种满足。这就是普遍的伦理道德——他害怕人们指控他有杀人企图——与他难以忍受母亲的不断骚扰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在母亲将她的卧床挪进厨房时提醒母亲防止煤气中毒。他遭到否定的弑母冲动后来超越了维系着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正常关系的伦理意识。
《污水上的肥皂泡》蕴含了残雪后来的短篇小说中的大部分特点:心理攻击和扭曲、多义的叙事、对变形的描写以及令人困窘的表述。她最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山上的小屋》侧重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对所有想象中或者潜在的危险与威胁的微妙恐惧。在山上的小屋里,有人在“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周围是呼啸的北风与嚎叫的狼群(56),那好像是“我”挥之不去的不祥之兆。小屋里的人与《苍老的浮云》中把自己关闭在密封的房间里与世隔绝的人物虚汝华相比,只不过这里的封闭并非出于自愿。有一次,“我”回到小屋里,看见自己在镜子里变成了那个人,“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57),那个人“蹲在”小屋里,“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58)。由此,这个形象可以被视为“我”的精神投射或者想象的反映。然而,尽管小屋里想象中的那个人物可能就是镜子里反射出来的那个影像,这样的视觉形象谜一般高深莫测,意味着“我”再也找不到小屋了,那也许是一种幻觉或者幻想。
残雪的神秘叙事呈现的心理意象可以被理解为真实的、同时又是以不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意象。然而,这种心理视像无法现实化,并不意味着心理压力是非现实的,而是说,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处理这样的心理压力和历史压抑是不可行的。小屋不仅是真实情形的一个象征,而且还是可以理解或不可理解的心理世界的寓言化形象。这让人再次联想起鲁迅的铁屋比喻。对鲁迅来说,铁屋是社会历史限制的明确象征,它或许可以被另一种历史力量打破,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希望。虽然如此,鲁迅却敏锐地质疑他那承载着历史承诺的写作的纯洁性,他认为一旦沉睡者醒来并且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悲惨处境,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残雪则更多是心怀疑虑地将问题局限于幻觉的精神领域。换句话说,残雪并不打算打破这样的框架——因为逃离小屋几乎没有希望——她更热衷于用声音和意象表现焦虑紧张、压抑强制和攻击挑衅的感觉。然而,将这些感觉概念化进而消除并非易事。
主体对概念化的无能为力符合“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氛围。这样的恐惧来自“我”想象中那些无法解释的心理骚扰。《山上的小屋》出现了残雪的另一组重要意象:刺穿或者钻孔。例如,“我”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59),狼群“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60),母亲的相貌被描写为“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61)。对家的刺穿是对强暴的隐喻,正如对童贞的强暴是无意识中对精神创伤的隐喻。总而言之,这样的情景并非如实照搬个人的过去经验。确切地说,在这里被唤起的刺穿意象,其本质必须被理解为心理骚扰无法追踪的、创伤化的历史经验的意象复活,残雪本人就像所有经历过专政的人那样深受其害。
在这里也能见出鲁迅的影响。《狂人日记》中的叙事者怀疑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等着吃他,并且为此备受折磨,《山上的小屋》中的“我”也对家里(一个相互威胁的群体)的人过分敏感。然而,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的恐惧不同,残雪的叙事者的焦虑和恐惧都没有明确的来源和对象。骚扰《山上的小屋》叙事者的不是有计划的谋杀(如鲁迅的狂人假设的那样),因此骚扰的真正原因无从找寻。虽然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发现她的父母翻过她的抽屉,把她心爱的死蛾子、死蜻蜒扔到地上。尽管如此,这件事很难被看作是她焦虑的来源或关键(更不用说这样的震惊通常而言不够强烈)。在整个叙事中,这件事并不是“我”关注的中心,而只是暴露了对暴力的敏感、却又隐瞒或偏离了仍然不为人知的原初事件的隐喻片段之一。除了这样确凿的事件之外,“我”实际上还遭受着任何感知或者感觉的骚扰。父母亲的鼾声震动了厨房碗柜里的餐具;一旦感觉到母亲盯着“我”的背后看,“我”的头部就会发麻和肿起来;父亲扫了“我”一眼的目光像是来自狼的眼睛。古怪离奇的一切分明来自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感知,或不如说是认知,贯穿在许多片断当中的这种感知或认知使得主体偏离了任何中心事物。
为此,《山上的小屋》的叙事者与鲁迅的狂人不同,她非但没有而且不能把重点放在她不得不面对的某件事。这样的事实意味深长,因为假设没有任何危险,她要面对的就是无处不在而又无法确定的对危险的猜疑。《山上的小屋》中的危险与威胁就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遭受他人压迫的受害者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也同样遭受到“我”或者其他人的骚扰之苦。“我”母亲声称,“我”每次走进她的房里找东西,她都会因为害怕而哆嗦;小妹偷偷告诉“我”,“我”开关抽屉的声音让她发狂;几十年来,父亲总是怀疑他把剪刀掉在了井里,他一直为此苦恼和牵挂,一天,他没有捞到剪刀,他看见自己左边的鬓发全白了。整个叙事不是对集体压迫的个人抗议,而是在酝酿一种恐惧的气氛:人人都在给对方制造莫名其妙的痛苦以及心怀叵测的威胁。
《公牛》是残雪的另一篇被大量编选的小说,其中的中心意象就是一头公牛用牛角捅穿了“我”卧房的板壁。根据叙事蒙太奇,当她试着抚摸牛角时,“我”触摸到的却是她丈夫的后脑勺。我们可以依此推断,公牛就是“我”丈夫老关的隐喻意象,老关对她的威胁被形象化为公牛的幻觉意象。当她再次发现丈夫的脑袋与牛角的相似之处的时候(她触摸丈夫脑袋的手被他坚硬的额发扎痛),她注意到他“滑稽的威胁神态”(62),他朝她呲出他的蛀牙。“滑稽的威胁神态”在这里变成了对复杂或混乱的威胁情形的矛盾修辞,因为滑稽可笑之事在于他们的折磨不是源于任何折磨的情境,而是来自另一种受折磨的情境。小说的另一个关键是老关始终担心他的蛀牙会不断加剧他的焦虑或折磨。更有甚者,在小说的末尾,老关高举大锤向一面镜子砸去,镜子里反射出来的老关就是折磨他的那头野蛮焦躁的公牛。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场面,公牛被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而不是袭击者:“庞大的动物的身躯倒在水里,‘啪嗒啪嗒’地作垂死挣扎,鼻子里喷出浓黑的烟雾,喉咙里涌出鲜红的血浆。”(63)
在残雪的小说中,骚扰的来源和对象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可以互相置换。因此,叙事者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原初的单一声音可以传递给众多他者,并且因此可以轻易地自我播散。实际上,直接援引老关游离于原来叙事声音之外的道白占据了小说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身为叙事核心象征的公牛是高深莫测和不能确定的,它体现了抵达表现终极真实的主体限度。许多年前,公牛的第一次出现(在一个诱惑的场面)几乎令人难以察觉,人们只能看见闪亮的紫光和公牛缓慢移动的屁股。听到公牛的敲门声,“我”怀疑那只是一个幻觉。公牛仅仅被当作不被理性感知理解的一种难以捉摸的危险,因为将公牛同一于老关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这篇小说中的公牛至少应该被诠释为难以归类的、同时是性诱惑与性威胁的巨大震惊的隐喻原型。进而言之,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这样的原型不仅是多义的,因为它(既动人又骇人)的双重攻击性,而且还是悖反的,因为它既卑鄙又脆弱。这种主导了残雪所有作品的双重性产生了作为精神创伤效应的终极不可确定性。这里便出现了反讽的概念,具体表现在不可调和的原型裂隙之中。
注释:
①萧元主编《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这个回答和余华在他的《虚伪的作品》一文中所作的陈述大致相同。余华说:“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虽然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由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同时存在现在之中,所以现在往往是无法确定和变幻莫测的。”(《余华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②③④⑤⑥残雪:《美丽南方之夏日》,载《中国》1986年第10期。
⑦⑧⑨(25)(26)(27)(28)(29)(30)(31)(32)(33)(34)(35)(36)(40)(41)(42)(43)(44)(45)(46)(47)(49)(52)(56)(57)(58)(59)(60)(61)(62)(63)残雪:《天堂里的对话》,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第289页,第310页,第205页,第205页,第181页,第250页,第205页,第199页,第198—199页,第199页,第199页,第198页,第230页,第261—263页,第178页,第237页,第178页,第249页,第254页,第272—273页,第178页,第241—242页,第197页,第180页,第287—288页,第288页,第290页,第287页,第288页,第291页,第285页,第286页。
⑩事实上,许多批评家对重复出现在她的不同作品中的这种意象感到被骚扰:因为“残雪迷恋的物象、隐喻,不断重复的事件模式”,“胃口的败坏部分地是要由作家本人负责的,她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与唠叨使人不胜厌烦”(张新颖:《恐惧与恐惧的消解》,载《人民文学》1989年第1期)。
(11)残雪:《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载《钟山》1987年第6期。原文中“脚”字误写作“肿”,这两个中文字的偏旁相同,那也许是残雪迷恋“肿”字的另一个标志。
(12)(13)(15)(16)(17)(18)(19)(20)(21)(22)残雪:《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
(14)陈凯歌导演并且获得戛纳大奖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悲剧场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影片中的两位京剧演员在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相互攻击并非是完全被迫的。
(23)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8,pp.463-464.
(24)Cathy Caruth(ed.),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53.
(37)Sally Taylor Lieberman,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8,pp.39-40.
(38)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50.
(39)《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48)残雪:《我是怎样开始创作起来的》,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2期。
(50)《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51)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53)(54)(55)残雪:《污水上的肥皂泡》,黄子平、李陀编《中国小说一九八八》,(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5页,第406页,第4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