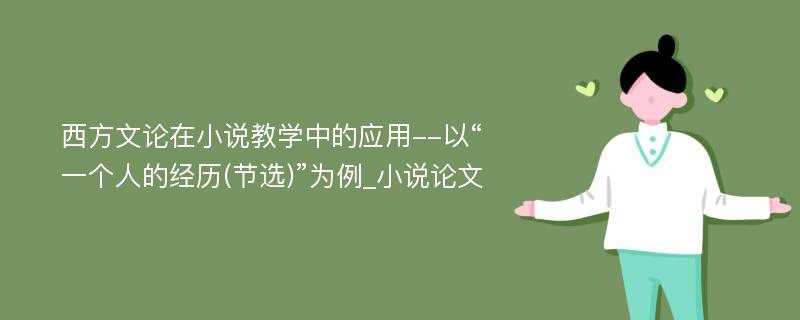
西方文学理论在小说教学中的运用——以《一个人的遭遇(节选)》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为例论文,教学中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高中语文课程的设置中,小说是举足轻重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以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见长。但在实际教学中,小说的教学状况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始终没有有力地介入过语文课程与教学,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红红火火的同时,文学鉴赏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含量却相当的贫乏”。[1]一方面是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稳定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知识总是停留在关于小说内容的“人物、情节、环境”上。教学内容的陈旧单一,有价值的教学知识的严重缺席,使小说课堂教学呈现出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倾向。 为此,笔者有选择地引进一些西方文学理论,以苏教版必修二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节选)》为例,尝试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拓展小说教学的内容,增强学生阅读小说的文本意识,提升小说教学的有效性,以期培养学生阅读小说的兴趣和提升鉴赏小说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学教育。 一、应用叙事学理论走进小说“套盒”式结构 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确,“说故事”是小说的基础,但故事由谁来讲、怎么讲却大有学问。叙事学理论认为,小说的美学价值往往并不是小说故事的本身,而在于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叙述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对某人讲的一个故事”,而且“由讲述者、故事、情节、读者、目的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在大多数叙事中至少是双重的:首先是叙述者向他的读者讲述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的叙述者的讲述”。[2]由此,小说形成了一个有多种声音建构和传递,多重故事彼此镶嵌、并置的“中国套盒”式结构。 课文选取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索科洛夫讲述了战争初期被俘并经受数次死亡威胁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得知自己家被德军炸毁妻儿惨死时,他才体会到最初离别时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而这一切却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俘虏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林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之后第二叙事者的叙述中断了,小说插入了第一叙事者“我”看到的春天景象:“和煦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语的悲怆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3]这段写景似乎是在提醒读者: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重回“过去”,“过去”和“现在”之间造成了许多需要弥补的裂缝。因而,我们不仅要关注战争本身,还要关注战后百姓的生活,更要关注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这一点正是肖洛霍夫战争题材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一个人的遭遇》这种“中国套盒”式结构采用双层叙事手法,两个叙事者在文本中呈现出不同层次并体现出不同功能。第一叙事者“我”充当叙事引入者,同时也对第二叙事者“我”——索科洛夫的叙述进行补充和评价;第二叙事者既是故事叙述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由于第二叙事者本身角色的限制而无法完全敞开叙事空间,所以,作者将第二叙事者的部分叙述功能分解给第一叙事者,从而减轻了第二叙事者的叙述压力;而第二叙事者叙述所呈现的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由第一叙事者进行补充和说明,这使整个故事叙述趋于舒缓,并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同时,两个叙事者之间的一系列对话以及整个小说的主观叙事视角,又增强了作品的主观感情色彩,从而把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的个人遭遇上升为一个时代现象。因此,小说文本教学内容直指人物心灵世界,读者体验到的不仅有主人公索科洛夫家破人亡的痛苦,更有他在痛苦中越来越坚强的意志,小说的叙事张力让读者领悟到了作品的深层含义。 二、应用“互文性”理论探究作者理性思考 “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性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因而,解读一部文学作品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所提供的帮助,正如布鲁姆说的:“为了解释一首诗,你必须解释它与别的诗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该诗生气勃勃的创造意义的地方。”在布鲁姆看来,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就像单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意义分工一样,单个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它和其他文本的区别与联系中,文本之间的“异”正是单个文本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将“文本间性”理论引入高中小说教学领域,就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发现文本中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精彩。因而,应用“互文性”理论进行小说教学,就必须考虑到此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提供一些必不可少的互文性文本。 《祝福》是学生非常熟悉的小说,文章采用的也是双层叙事,区别在于《祝福》的主体——祥林嫂的故事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吻叙述出来的,并且叙事者“我”在小说文本的开始部分还参与到祥林嫂的故事之中,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其实,在“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的关联中,寄寓着作者的深意。在“我”看来,祥林嫂最后在祝福中悲惨地死去,与“我”对她“灵魂有无”含糊其辞的回答脱不了干系。因而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中,这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层关注和思考。而在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第一叙事者“我”虽也是故事的介入者、评价者,但主要身份还是故事的倾听者、感受者。而这种感受对读者阅读小说又起到了一种“陌生化”(间离化)的效果,这种陌生化效果要求读者用一种探讨的、批判的态度对待第二叙事者所叙述的故事。小说文本中,第二叙事者索科洛夫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促使读者进入故事的情感体验状态,但由于第一叙事者“我”不时地站出来对第二叙事者的叙述进行评价,客观上又迫使读者对索科洛夫遭遇由情感体验转入理性思考,并进行深刻反思:“苏联的卫国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胜利后的人们,是否就能够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笔者认为,这正是作者未说出来的理性思考。 通过《一个人的遭遇(节选)》和《祝福》的“互文性”解读,我们发现鲁迅让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承担着他自己对社会的思考,而肖洛霍夫却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承担着他自己对现实的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呢?笔者认为,肖洛霍夫创作时的社会环境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说鲁迅写作《祝福》时的社会环境有多好。)因此,用“互文性”理论解读《一个人的遭遇(节选)》,读者会感受到小说文本的巨大叙事张力和间离化效果,而这种张力和效果又促使读者能够超越第二叙事者的叙述束缚,对作者的理性思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挖掘文本隐喻象征意义 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早就存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确定性和空白正是促成这种相互作用的桥梁,它们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深层的隐喻和象征意义。 在《一个人的遭遇(节选)》中,作者肖洛霍夫有意识地营造了德国另一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所说的文本“召唤结构”,他是在期待有经验读者的参与,这经验就是对20世纪上半叶苏联历史的掌握。作家通过对书名和主人公姓名提供隐喻性的文字,诱惑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激发自己的想象去完成作品的象征结构。 小说的题目是隐喻性的。在俄语中,题目中的“一个人”既可以指一个普普通通的、具体的、单个的人,也可以指更为抽象的人,甚至指人类,如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遭遇”这个词既可译为“遭遇”,指一生的遭遇,也可译为“命运”。由此看来,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像一道半开着的幽暗神秘的门,诱使读者去猜想:主人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命运,因而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小说人物的遭遇是隐喻性的,尽管它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它通过表现一个人几乎一生的经历表达了更为深刻的内容。 肖洛霍夫通过索科洛夫一生的命运激发读者的这种联想,在作品之外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外在隐喻文本。小说在展示“人”的“命运”时,有明显的生活轨迹的曲线,形成了一个倒U型结构。战争前,索科洛夫虽生活贫困,但家庭美满、生活充满希望。战争爆发了,他走上前线,经历了受伤、被俘的种种折磨,但他挺过来了。可是敌人的一颗炸弹夷平了他的家,夺走了他的妻子和一双女儿。当兵的儿子在攻入柏林时牺牲了,他再次孑然一身。他收养了父母双亡的凡尼亚,艰难地活在世上。他甚至怀疑:“我这悲惨的一生会不会是一场梦呢?” 在实际教学中,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赋予小说中“一个人”“遭遇”等词语以象征意义,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索科洛夫的生活道路是小说的“字面意思”,那么,苏联人民20世纪上半叶的道路则是没有出场的被隐喻的文本。索科洛夫的生活道路,就是以一个人的生平来象征一个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他和它的“生活曲线”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而且具有编年史的叠合关系,并且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一个人的遭遇》与苏联历史有着编年史的平行性。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小说结尾处第一叙事者“我”的独白涉及凡尼亚的有一句话:“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这表明第一叙事者“我”在聆听索科洛夫所述故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尽量不表露自己的态度。可是当“我”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以对小说中具体人物凡尼亚命运的预测,道出了“我”对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人民历史道路的谶语!作家肖洛霍夫无意中竟成了国家命运不幸的预言家。由此可见,主人公索科洛夫的遭遇不正象征着苏联人民在整个20世纪几乎所有的悲剧吗?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思想芜杂。限于篇幅,本文只略谈其中三种西方文学理论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本身无法解释的领域,西方文学理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如果我们能有选择地将一些成熟的、经典的西方文学理论引入小说教学领域,应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高中语文课程中的小说教学不同于大学的小说文学课,它学习的对象既不是小说理论,也不是小说文学史,所以,我们如果把西方文学理论引入小说教学中来,还需要设计一个教学程序:从西方文学理论中选择可以进入小说教学的知识,就像曹文轩主编的人教版选修教材《外国文学欣赏》那样,形成一个体系——讨论这些被选入的知识在语文教材中应如何呈现——在小说教学中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标签:小说论文; 一个人的遭遇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祝福论文; 肖洛霍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