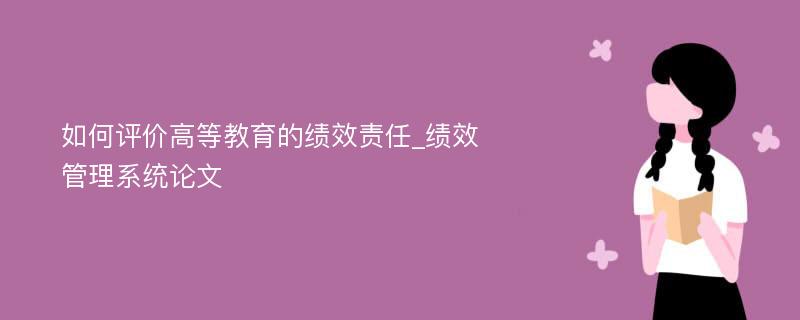
如何考核高等教育的绩效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绩效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绩效责任”是近期国会立法会议中有关高等教育议题的争论焦点之一。当联邦议会的最高立法者试图重新授权《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失败后,他们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诸多疑问,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机构是否对其教学质量和绩效承担了足够的责任?他们是否能够承担这类责任?如何承担?是否需要制定一套衡量绩效的标准?对未达到标准的机构如何进行惩罚?
与此同时,由于预算紧张,开销不断增加,各州政府也不断要求公立大学向世人展示他们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在为高等教育拨款之前,各州立法者想要了解这些经费是否有助于达成关键目标。由各州高等教育行政首脑(State Higher Education Executive Officers)组成的全国高等教育绩效责任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将为此提供政策性建议。
而各私立大专院校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承担更大的责任问题:随着学费的不断上涨,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也迫切需要这些教育机构证明他们所交的学费物有所值,而学生们也正在学习需要掌握的知识。
联邦议会将于2005年早些时候就高等教育中绩效责任的重新授权问题进行再次辩论。由于高等教育院校的数量庞大、专业领域相异,因而很难定义绩效责任,更不用说考核其是否达到标准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决策者应该从何入手以使各院校对公众更加负责等。针对这类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八位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克拉拉·洛维特(Clara M.Lovett)与罗伯特·蒙德汉克(Robert T.Mundhenk)——我们需要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
国会领导人决定2004年暂不对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案》进行重新授权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相关利益方仍有机会挽回颜面并重新考虑他们的处境。我们需要一次全新的对话——一次摆脱刚刚过去的空谈和毫无建树的对抗性交流的对话。这比那个无处不在的绩效责任话题更为必要。
必须明确国会议员及其选民想要了解高等教育的哪些方面:首先,为何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一直比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以及其他相关指标的上涨速度快?其次,为何各大专院校的利润投资比率(新生在6年内取得大学学士学位的百分比)通常很低?第三,为何这一比率在低收入家庭或某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学生中最低?
这类问题的提出是很合理的,尤其是在大学文凭已经取代中学毕业证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入场券的今天,这些问题的解决更是迫在眉睫。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可以熟练地运用拖延战术避开公众的指责,继续坚持他们自己的说辞;或者参加一次坦诚的对话,开诚布公地讨论那些他们不甚喜欢的话题。
比如,为准备一次全新的对话,各院校的领导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下那个大胆但却毫无说服力的断言——区域认证体系足以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认证是杜绝不合格教师与保护学生和公众免受学位欺诈的一种证明方式,也可促使各院校互相帮助改进教学计划和管理体制的质量,但它不能解释高等教育招生减少与学生成功率低的问题。
各院校的领导们也不能兑现诸如高等教育协会于2003年5月递交国会的“高等教育法案重新授权建议”信函中所定下的承诺。他们曾提议“公众可以轻易获得有关教学计划和成果的信息,但各院校可视自身专业领域而定”,这其中的限制性条款(斜体部分)明确地将各院校的自主权置于透明度和可比性之上。立法者和公众清楚地意识到国内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多样化与分权特征。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毕业于不同专业院校的学生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会相互影响,有很多共同点,因而在确定大学的教育成果时,他们对区分彼此学院的学习经验并不太感兴趣。
对他们而言,国会和各州立法机关的领导出面召开全新的非正式会谈有助于他们心甘情愿地重新思考绩效责任的含义。比如,一些国会要求的劳动力投资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规定的资料,如毕业生工作持久性、毕业后首次参加工作满一年时的年收入等数据,会因为雇员地址的变换以及雇主担心这些数据可能违反联邦隐私法而难以获得。其他数据如珀金斯法案(Perkins Act)最近重申的核心指标——“学位或获奖证书”也不能作为评定各院校是否成功的标准。
决策者们提出的某些指标,比如学生毕业率,并不能准确地衡量高等教育的绩效,因为他们忽视了转学到其他院校或在业余时间学习的学生的数量。此外,如果毕业率成为一个体制的主要奖惩触发器,那么早就应该关闭大部分中学,直接创造出所要求的毕业生数量就行了,而无需注意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
幸好公众还可以通过其他数据了解高等教育的绩效责任。数百个大专院校已经通过学习成果信息的运用改进教学计划以满足认证要求。个别院校可以用不同方式评价教学成果,除了肩负非常专业任务的院校外,多数院校可以共享众多相同的学习目标。
因此在行业协会的范围内制订出跨院校的类似“思辩能力”和“分析资产负债表能力”等通用核心成果的协议是可能的。然后各院校可以运用自身的评估体系证明他们是否已经取得了那些成果。这类文件可以向公众提供明确的、具有可比性的绩效责任资料,而无需各州或联邦政府颁布强制性标准,同时这也是高等教育对此全新对话所做的贡献。
为确保此类资料得到持续、广泛的使用,各院校还需不断努力。但显而易见他们可以为公众提供其所关心的相关信息,尽管他们总是埋头于术语堆砌的内部报告之中。现在该是各院校发布外行可以理解的数据资料、揭开秘密的时候了。
克拉拉·洛维特为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席,罗伯特·蒙德汉克为该协会评估董事兼高级学者
南茜·舒洛克(Nancy Shulock)——一次文化变迁
使公立高等教育更负责任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未能将绩效责任的确定提上公共议程。正如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罗伯特·贝恩(Robert D.Behn)在《反思民主制度中的绩效责任》(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布鲁克林研究中心新闻,2001)一文中谈到的:我们对“绩效责任”一词的定义通常都是处罚性的,其中“绩效责任担当者”只是单向的权力关系。罗伯特认为尽管这样的定义包含了广泛的民众参与,但并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管理分配和共享。
他的论述特别适合如今的高等教育。决策者们常常为了不引起各院校的“困扰”而要求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数据资料,或相反地强迫他们立刻拿出成熟的数据;决策者们热衷于对各大专院校进行比较,而对了解为何各院校间不具可比性不感兴趣。州政府官员们应监控各个院校是否正在尽职尽责地帮助政府解决相关问题,而非比较其毕业率、每位学生的花费或取得学位的时间(随院校专业设置和学生类型不同而各异)。
比如,为促进经济发展,各研究型院校有责任寻求外部研究机构的支持,同时促进商业发展。而各综合性院校则有义务将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类的毕业生安排进当地的相关产业中。社区学院则可以通过与当地工商业签订教育合同、或进行某个特殊领域的认证等工作,负责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与此类似,为增加学生录取人数,研究型和综合性院校有责任接收一定比例的社区学院转学学生,而州政府也可以要求社区学院招收更多居住在某些服务水平较低的特殊地区的学生。
此外,当这一体制开始向社会输送受过教育的公民和劳动力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院校和教育部门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跨越传统界线的新方式:在中学、高等院校、中等学院(向各大学输送中学生)、虚拟配置课程研究院、以及其他“P-16”教育改革(连接基础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公立教育体制)中进行双重招生。我们都了解高等教育中的管理共享与权力分散状况,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不论是各大院校、大学校园、教育体系,还是各州政府机关。
遗憾的是,尽管这一问题已经提上各州教育目标和公共议事日程,但大部分州政府的绩效责任管理体系仍未能提供充分、明确的有利于市民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教育成果证据。他们未能治理不良假定并制定出一系列可能为整个州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有效的院校管理体系,而是设计了很多数据资料用以监控个别院校的绩效。
请认真考虑下面三个谬误:
各院校可能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毕业率,然而这对州政府保持健康的民众与经济生活仍然太少了;
社区学院可能正准备将学生输送到四年制的大专院校,同时各综合大学也可能正高速地向社会输送毕业生,但由于学校学生人数过多或地理位置限制,大量准备送入各大院校的学生可能永远都没有被录取的机会;
参与教师培训计划的毕业生可能在相关认证考试中取得很高的通过率,但州政府仍有可能面临严重的教师短缺问题。
绩效责任必须是针对各州政府的成果,而不是各大院校的。因为决策者只熟悉旧有的以院校为核心的模式,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如何将完备的绩效数据用于更广泛的决策制定至关重要。管理者们应该作出可读性报告,用绩效数据考核该州的实力、不足与需要。之后决策者们可以根据这些报告组织关于绩效关键问题的讨论,制定适宜的目标,并敦促各院校达成这些目标。比如,如果数据显示某个州的经济发展中缺乏技术领域的毕业生,那么州政府就可以增加该科系的学生录取经费。
目前所需的是一次文化变迁。我们需要的是集体的绩效责任,通过它,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可以理解每个州的教育健康状况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各院校与中小学的努力,各大院校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计划、维持并支持其教育体制的决策者选择等。我们不需要那种组织管理严密、目光聚集在各大院校身上的绩效责任。各大院校必须保持达成绩效的责任感,其结果必须符合该州的总体发展需要。
南茜·舒洛克是高等教育领导协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立力学萨克拉门托分校政策研究所的执行董事
查尔斯·里德(Charles B.Reed)和爱德华·拉斯特·季尔(Edward B.Rust Jr.)——一种更为有条不紊的方式
各大院校怎样才能真正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评估体系,但那些评估与政府和公众对教育机构绩效理解之间的差距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法。
高等教育中大部分的绩效责任机制由个别院校以及对其进行授权的协会制定,并将其作为准绳衡量该院校的教学进步。从定义可以看出:这类评估标准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而很难解释给公众或用于进行各院校间的比较。此外,学生学习品质与联邦和各州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之间的联系也很难确定。因此,在政府与各院校领导人努力评估绩效责任时,通常不是采用真实反映学生实际掌握内容的评估方式,而是采用“生产率”式评估方式,比如入学人数、毕业年限、毕业率等,并据此确定需要提供的各种资源。
既然各大院校间千差万别,那么单一的全国性绩效责任管理体系应该是既不适用也不实际的。目前已经到了必须设计一套更为有条不紊的方式以衡量绩效责任的时候了。在近期企业与高等教育论坛(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发表的一篇题为《高等教育中的公众责任:问题与选择》(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Student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Issues and Options)的报告中,我们作为共同董事提出一个框架,明确了各大院校、联邦及各州政府以及全国性调研组织的特定角色。每位参与者都必须理解如何适应一个庞大、公开学生学习的绩效责任管理体系,该体系植根于必须要做什么、作用的对象、达成任务所需的时间等广泛的共享价值之上。
各大院校可以先确定并明确通报他们制定的有关学生学习的目标,然后再提供已经达到该目标的证据。各大院校在准备认证审核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学习评估问题。现在是该扩大他们的内部议程、接纳公众的时候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管理系统(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每年进行一次教师培训计划年度回顾,该计划通过对该州各校校长的查访,评估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的质量和准备程度。该体制每年都将回顾结果公之于众,并将其作为鉴别成功与尚需改进地区的依据。
地区性认证机构需要继续充当个别院校评估与公开绩效责任之间的桥梁。
他们应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与高等教育鉴定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合作,发掘出更好的、能够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并将其工作展示给公众的方法。他们应特别留意美国学生人数的变化,包括在职学生以及参加非传统授课方式(比如远程教学)学习的学生人数的增加。
各州政府应该建立绩效责任管理体系,以区分各院校绩效与全州范围的绩效。各院校承担制定绩效目标和提供成果证明等主要责任,州政府则应监督院校间学生的流动状况(包括学生从中学升入大学)、学生的转学趋势以及成人学生的入学和毕业的特点等。
联邦政府应一如既往地将重点放在维持高等教育的公平与经济机遇上。国家承诺为所有学生提供通过联邦需要补助金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而不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同样,联邦政府也应继续从事跨州的学生流动状况的研究与数据收集工作。
最后,全国性研究组织应该承担以类似于临床试验研究的方式研究高等教育中学生学习状况的任务。这类尝试要求一个更为持续、集中以及训练有素的约定,而非如今的由一系列不同研究方式组成的综合性纵向研究。从当前全国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学生的入学情况或“座位时间”(seat time),这可以通过学生的累计贷款得知,同时也可以了解这些贷款的消费模式,至于学生都学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更为强大的、包括每个主要参与者明确角色的公众责任框架将有可能提高绩效,同时增强公众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信心。
查尔斯·里德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管理系统的名誉校长,爱德华·拉斯特·季尔为国有农场保险公司的主席与首席执行官
托马斯·莱赛(Thomas Layzell)——放宽眼界
如今在各州及地方盛行的最有趣和最富挑战性的讨论是关于绩效责任的,这主要是受到当地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各相关部门不得不为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而共同努力。各州及其辖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他们要求所有人有计划、同步调地响应,这包括公务员、高等教育、商业以及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
无论这类讨论名为圆桌会议、高峰会议,还是相关“公众参与”、“责任管理”,它们全都建立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与共同努力基础上——但却明显不同。这类讨论涉及的观点多样,问题复杂,协调性和所需资源的分担均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这要求所有参加者放宽眼界,而非紧盯自己的责任和问题。
尽管有关绩效责任的讨论仍将继续着重于毕业率及毕业人数等传统问题,但新的矛头已经指向了高等教育本身,这将不断要求各大院校将重点放在如何取得更广泛的公共目标上,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公共卫生等。
正当各州致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解决经济发展等问题时,各大院校也面临持续增加的帮助政府开发并达到公共目标的压力。因而,高等教育绩效责任的讨论仅仅是各大院校面临的问题之一,他们还应考虑如何使公共议程发挥最大效应。一个成功的公共议程将会:
鼓励广泛的参与。公共与私营领域领导人对自然资源配置与议程支持的提高至关重要。在肯塔基,公立学校与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劳动力培训组织一样,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着重于为公众提供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经济地位的机会的广泛战略性目标。目标过于狭隘则用处不大。比如1997年的《肯塔基中学后教育促进法案》(Kentucky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六个目标中的两个呼吁大众支持肯塔基大学和路易斯维尔大学,希望公众理解经济发展领域内研究型学院的重要性。
采用长期战略。促使公共议程产生的问题通常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解决这类问题欲速则不达,因此必须设计一个组织框架和发展约定以维持长期的议程要求。其存在与否不能听天由命,也不能因某个特殊时刻某些特殊领导存在而存在。
我们在肯塔基的做法是:将议程与法律相结合。事实证明这是鼓励长期措施的有效方式。按法律规定,该州的中学后教育委员会负责设计议程,为其提出修正案,同时负责监督该目标的进程并公开报告。执行委员与立法分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提醒上层决策人有关公共议程的疏漏。这类措施虽不能确保长期执行,但却鼓励了相关行为。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明确、现实、可以考核监督与修正的优先权。在肯塔基,最初的优先权设定为增加各大院校的录取人数和提高出勤率。现在它仍为一项优先权,但在成功地提高入学人数后,我们已经将重点转向其他目标,比如增加不同级别与特殊领域的学位数量。
协调政策并实践目标。比如,管理与议程相关的教职员工行为——如与公立学校教职员工一同工作以改进教师质量;或与州和地方经济发展机构合作,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吸引公众参与等,均应被视为促进该议程的重要活动。
定期分析如何达成各项目标。这不仅包括所需资金的数量,还应包含如何有效、高效地组织和执行相关决议。
在进行绩效责任管理体系设计时,各州政府和各大院校应就公共议程及达成该议程的关键评估行动采取一致步调。各州实际情况不同,教育水平滞后的州可将重点放在录取人数和毕业人数上,其他州则可将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活动上。
绩效责任管理体系也可生成易于转换为答案的数据(实际上,应该是问题)。根据对这类信息的分析,确定出现了何种新问题以及决定如何解决等至关重要。若疏忽此类问题则可能导致毫无根据的评断或解答并不存在的问题的危险。学生保持率和毕业率便是很好的例子。当深究这些比率背后的真相时,公众往往会得到该院校有关绩效的答案。
此外,必须随环境的改变改善、校正绩效责任管理措施,修改或摒弃那些不再适用的部分,避免数据超载。比如,州政府所面临的支持监狱或医疗补助制度的压力与学生、院校以及州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等措施毫不相关,这时就应该删掉这类内容。我们需要新的、适合当前财政环境的评估措施。
任何一个绩效责任管理体系的主要目的都应是提高各大院校的绩效,而非攻击或保护它。这符合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托马斯·莱塞任肯塔基中学后教育委员会主席
约瑟夫·伯克(Joseph C.Burke)——“公开”一词是关键
若要承担重任,各大院校就必须平衡学术、公众和市场需求。但各院校、公众和商业文化的需求通常互相竞争。学院文化迫切需要教职员工参与的职业责任,这可能导致决策制定时的高压封锁。公众文化强调了服务公众用途的政治责任,这可能会为当前执政党所利用。市场责任则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可能将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转变为短暂的流行风尚。
缺乏有关公众需求的协议可能导致更多的不同团体间的对抗性。高等教育人士抱怨他们常常被政府和商业领导人批评为态度冷淡,这些领导人不了解其优先权,或根据选举、市场循环需要希望他们改变行事步调。州长、立法者和商业领导们不断要求各大院校开始新的计划和服务,但却仍谴责他们试图插手所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的局外人则指责他们缺乏绩效责任,但却未能对建立有效的绩效责任管理体系承担任何责任。
华盛顿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爱德华·韦伯(Edward P.Weber)1999年就绩效责任议题在《管理与社会》(Administration & Society)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中肯的问题:“处于管理分散、权力共享、合作决策、以结果作为导向、有广泛的民众参与其中的一个管理体制如何才能做到高效?”而且,必须加上一点,在一个充满市场压力的世界中,该体制至少需具备下列特征:
公共议程。一个由学院、商业及政府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小组应确定议程内容,详细说明各州对高等教育院校的需求,以及达到那些目标所需要的财政资源。该小组应为此宗旨设定指标、目的以及时间表,如不断增加的大专院校与公立学校的合作,提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支付能力,保证足量的毕业率与就业率,促进经济和公共发展的研究与服务计划。现有的代表所有利益相关团体的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应同心协力完成该任务。
比如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支持圆桌会议,而各大学与学院管理委员会则主办了高峰会议。其中,政府、企业、公众和教育界领导们确定了他们急需从公立和私立院校中获得的优先权。比如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峰会中,这些领导们制定了一系列目标,包括培养更好的师资力量,增加各大院校的录取率,提高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毕业生数量,扩大劳动力培训,以及鼓励各大学拓展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等。目前评估这类高峰会的建议的影响为时尚早,但这类会议或许可以为未来提供一种参考模式。
公开报告。某些人士认为高等教育报告太多。一个由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全国中心出具的每两年一次的“考核标准”报告对全国50个州的高等教育绩效进行评级。大部分公立和许多私立学院也呈报了他们的结果。然而院校的报告很少在所在州、校园决策者或公众之间传阅。
另一个问题是,这类报告只代表个别成果,并不能回答关键性问题。如该州高等教育体系运作状况如何?各大院校对公众需求有何反应?这类报告缺乏将其结果与州高等教育体系和各院校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指标明细,而决策者本可以依据该明细确定成功与不足。这类指标应可以评估各大院校与中学间的协作、学位完成与就业、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支付能力的尝试,以及服务于该州的研究和服务计划等。
公开质量保证。绩效报告展示了对公共需求的响应、校园计划的执行水平质量保证评估和质量控制。高等教育与其他行业相比已经有许多质量检测方式:认证、评估、学术审核,学生、校友以及雇主的满意度调查等诸如此类。但其致命的缺点是:这类结果通常被秘密保存,很少公开报道。绩效责任考核要求各大院校公布其认证、学术审核及满意度调查结果,至少是这类结果的总结,以满足公众了解的需求和同行公开批评的学术需要。
对民主制度下的绩效责任考核而言,“公开”一词是关键。具备此类特征的绩效责任考核将平衡学术、公众和市场需求。这也许会使一个古老的信仰复苏:高等教育对所有的美国人而言是一种不朽的公益事业,而不是一个只针对大学毕业生个人的短暂利益。
约瑟夫·伯克是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纳尔逊·洛克菲勒研究院政府高等教育计划部董事,同时也是《达成高等教育绩效责任:平衡公众、学术和市场需求》(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Balancing Public Academic,and Market demands)一书的编辑,该书于2004年9月由Jossey-Bass出版。
卡罗尔,克里斯(Carol T.Christ)——力求开放
当读到有关高等教育绩效责任这一标题时,有人可能会认为当今的高等院校未能肩负起应负的职责。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人对高等教育有着极强的信心。高等教育周刊连续两年的观点调查发现:公众对各大院校的信任排名接近各类机构之首;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约有93%的受访者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是美国最有价值的资源。那究竟为什么还要呼吁绩效责任呢?
结果很可能是公众赋予高等教育极高价值这一答案是假的。如今大学教育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由大学学位导致的终生工资差额在不断上升。如今一位男性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比一位男性中学毕业生的工资高出81%,而在1973年这一比例为33%,但相对而言,读大学的费用也显著增加。当人们看见一个至关重要、非常昂贵且品质很好的产品时,他们会非常关注谁有权使用它、如何对其进行分配、为什么如此昂贵等问题。因此,立法机构也呼吁高等教育在上述三个方面肩负起更为重大的绩效责任。
身处高等教育中的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学术界内部人士敦促我们更加积极响应政府对于绩效责任的呼吁,而他们则将重点放在学习成果的考核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除了未抓住重点以外。学习成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绩效责任的争论中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家长和立法者们都担心考试分数下滑以及孩子们是否具有读写和计算能力等问题。
但当政府、新闻媒体或公众呼吁我们的高等院校担负更为艰巨的绩效责任时,他们很少抱怨学生学习不足。他们心里真正关心的是哪些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花费多少、他们能否毕业以及何时毕业。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学生们在职场上的成功,而不是他们学到了多少文学、天文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许多高等教育人士在看到这类不合时宜的干涉(呼吁绩效责任)时怒发冲冠。毕竟,我们的院校原本已经充斥了各种水平和体系的考核。我们鉴定录取的学生;我们对学生评级,考核他们每一学科的成绩;我们评估教职员工,对其进行留任和升迁:我们审核需要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给予财政支持;我们评估不同的部门和计划;我们授权职业水平计划和教学机构;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但却还要遭受所有抱怨我们未能尽职尽责的侮辱。
显然,只对我们自己负责是不够的,这并不能完全履行绩效责任约定中规定的条款。公共议程的核心是入学机会和支付能力的保证。高等教育中的绩效责任与这些目标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绩效责任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就取决于一种更为伟大的透明度理念。高等教育围城中的我们必须更多地公开我们的业务惯例;必须更多地公开有关入学、财政援助政策及其实践;必须更多地公开预算和资金,提供更多信息,以便让公众对成本和定价有更加充分的了解。最终将帮助我们取得制胜的关键——基本的社会信任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的经久不衰。
哈佛大学前任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经过长期观察提出,“知道真相的权利”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特别是和公众形象和公共实体相关的部分。大专院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均被视为公共资产。这一观点折射出我们教育机构当今的向心力,它肩负不可推卸的重担和责任。
卡罗尔·克里斯为现任史密斯学院院长,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院长
资料来源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3,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