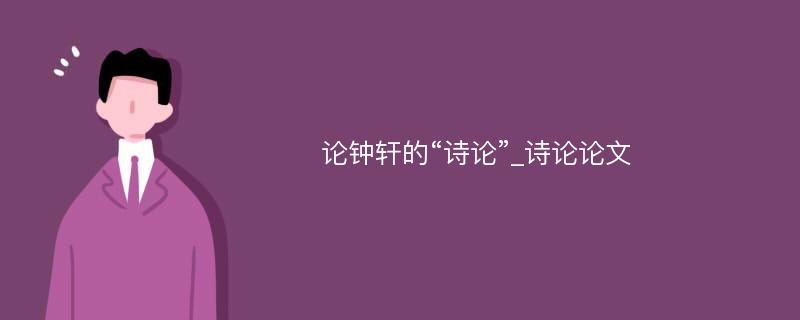
论钟惺《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论论文,论钟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钟惺在《诗论》中提出的“诗乃活物”的卓越见解,使读者的阅读活动直接进入诗学的研究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向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创作美学提出挑战,同时使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和把握途径。因而,重新评价钟惺的《诗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文艺理论,古代文论,诗论
中图分类号 I206·2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曾任行人,工部主事,福建提学佥事等职,后归隐故里,著有《隐秀轩集》三十二卷,还著有《周文归》、《古诗归》、《唐诗归》、《宋文归》以及《毛诗解》、《钟评左传》等。钟惺主要是与同里谭元寿共编《古诗归》、《唐诗归》而著名于世,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是评诗和论诗的,但终因其推崇“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故他的诗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没有特别的影响。这篇《诗论》原见于《钟惺批点〈诗经〉》一书的卷首,实际上为该书的序言,文末署写作年代为“明泰昌纪元岁庚申”,亦即公元1620年,后收入在《隐秀轩集》列集。较其他诗论而言,此《诗论》可以说是代表了钟惺论诗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诗论》中,钟惺提出了“诗乃活物”的卓越见解,使读者的阅读活动直接进入诗学的研究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向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创作美学提出挑战,同时使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和把握途径。因而,重新认识和评价钟惺的《论诗》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诗学中,人们对于诗的认识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诗是传达情感认识现实的一种方式。诗的本体生成就是作者的情志(思想感情),而诗作品则成为传达本体的唯一途径,也就是传达“情志”的媒介。孔子早就说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1〕言是传达志的手段,没有言和文, 志也就不能传达。这种诗学观认为诗作品的内容意义就是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情志,也即作者的原义、本义,因而读诗就必须研究作者(包括生活经历,情感态度,审美现想等),然后再进入作品去寻找作者寄寓的原义,正如刘勰所说的“沿波讨源”,“披文以入情”〔2〕这是一种保证诗作理解的客观性的最普遍的解读方式。长期以来,阅读诗歌就是领悟和理解作者情志的观点是天地经义的,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由此而导致的误区就是把诗作品当成说教读者的一种工具:譬如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论,荀子的文章“应合先王,应顺礼义”的文章观和“美善相乐”的美学观,《毛诗序》的“经善惩恶”的观点,班固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观点,姚思廉的“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的观点,孔颖达的“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的观点,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以及“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性情”的观点,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的观点,朱熹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观点,一直到顾炎武的“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的观点,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其实质都是把诗作品作为宣传儒家礼教的工具,强调诗歌对于读者的“教化功能”。在这里,读者永远只能是接受教育的对象。
因此,古代诗学批评和理论最关注的自然是作家——作品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这成为历代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构建自己理论的基本支撑点,于是,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则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
但是,钟惺在《诗论》中却把理论关注的视点对准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并对传统的诗歌本体论和解读方式进行重新认识和发出诘难。他首先指出:“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3〕对于诗作品的阅读和解释,不一定都要切合作品的原义。他认为,孔子删编《诗经》、其七十二子弟学《诗》引《诗》,春秋列国大夫在盟会、聘问等外交场合赋《诗》,以至韩婴传《诗》等,他们都不一定完全切合《诗》的本文本义,便又都觉得和《诗》的意义没有什么不相符的地方。因此“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凡是对《诗》的理解和解释,都没有必要去追寻作品中作者的原义。
何以如此?钟惺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看法:“《诗》,活物也,”“《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所谓的“活物”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第一,钟惺首先指出诗作品为“物”、就是把诗作品看成是一种物理存在。它一方面产生于作者的艺术创造行为,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物理的实体存在(物化为语言文字)。只有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它才有可能使作者的创作活动在结束之后具有某种继续存在的形式,使审美接受者可以重续作者的创作活动。第二,诗作品为“物”并非是游离于读者阅读之外的僵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具有“活”的性质,也就是说具有开放性和召唤性的特征。正是这种“活”的性质,为读者的理解创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钟惺提出的“活物”实际上就是指作者所创造的“文本”。按照当代接受理论的观点,文学作品被作者创作出来以后,其内容意义还处于晦暗的未明状态,作者的原义也只能是“可确定的X”, 〔4〕其本身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而只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 包含了许多潜在因素的意向性客体。这是因为作者一旦完成了其作品的写作,随同作品创作产生的一系列审美心态、情感活动、艺术想象等所构成的“力场”便立即消失,除了有限的部分物化为文字留诸纸面以外,作家创作作品时完整的心境绝大部分已逝去而不可复返,留下来的文字已全部消失了作家创作时的鲜活灵动的形态,成为需要再度阐释的符码。再者,语言文字本身传达的困难往往造成言不及意的窘迫。作家肖乾在《经验的汇兑》一文中曾说: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是天然含蓄的东西,无论多么明显地写出,后面总还跟着一点别的东西,也许是一种种口气,也许是一片情感,即就字面说,它们也是一根根的线,后面牵着无穷的经验。”〔5〕这就为作品留下许多“意义不确定”和“意义空白”,这些“意义不确定”和“意义空白”要依靠读者的想象加以补充,使其成为仿佛是确实存在的和充分确定的实在客体。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作为具有文字构架的文本只是处于向多种解读开放的未定之域,它在等待作为读者理解和解释的阅读活动。当代德国美学家伊塞尔曾对文学作品作了“艺术的”和“审美的”两极的区分,“艺术的极点是作者的本文,审美的极点则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现”,而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本身“既有别于本文,又不同于本文现实化,而必须被置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6〕也就是说“作品”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相遇和交流过程中,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因此,它既不纯粹是文本中原现实,也不是作者主观态度的产物,在伊塞尔看来,由文本到作品的过程,需要读者的能动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钟惺所提出的“活物”的见解和当代接受美学理论中所提出的“文本”的概念完全是一致的。
由于诗作品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活物”,它在等待和召唤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只能在读者的解读和阐释中才显现其内容意义,因而,诗作品的内容意义不是先于阅读行为而本有,而是在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生成的,读者的阅读活动进入了诗的本体层次。于是,诗的创作活动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合作而完成,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也成为一种创造,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重现作者的原义,只能和作品中作者的原义部分重叠,交叉或者错位,因此,“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钟惺批评了汉代人说《诗》,是“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他非常推崇朱熹的做法,认为朱熹注《诗》是“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传疑”。朱熹自己也曾说过:“《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7〕指出欣赏和阅读作品,可以根据读者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去思而得之,不必囿于诗中的原事原义。综上所说,“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
钟惺又指出:“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用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读者对《诗》的解释,人人各异,代代不同,而《诗》本身是不知道的,但《诗》却在不同的理解之中自然流布发明,其生命恒久不竭。唯其如此,《诗》才称为经典。这也就是说:《诗》之永恒的生命,并不表现在它本身所具有的固定的、作者所寄寓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它能容许不同环境,不同时代的人从各自的主观条件出发,对它的意义进行不断地重新赋予不断地充实扩展之中。
在这里,钟惺进一步强调了诗作品的内容意义在其实现过程中的历史性和永恒性。诗作品是“活物”其内容会随着读者的阅读而不断发生变化,阐释中因历史的增删和群体的叠加会对作品不断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意义,因此,其意义的生成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而永远指向未来,如此这样,诗作品才能长期存在,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德国当代著名学者伽达默尔说:“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至直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距离,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8〕如果说诗作品是“活物”, 如前所述主要是指它在有限的文字中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未定性,如何把这种意义的未定变为确定,使作品成为它想成为的东西:一个审美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有权怀有某种骄傲,因为他把作品提升到了它的真正存在。”〔9〕然而,读者群体是个能动多变的因素, 每一个体的独特的生存体验、情绪、思维以及其知识结构都可以在与有限的文字文本的际遇中,开拓、创造、增益或发展作品的意蕴和内涵。这种解读的创造本质和创造品格,使阅读活动中作品的内容永远不可穷尽。德国另一名美学家姚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10〕钟惺正是从诗的本体存在关系上强调读者阅读活动的重要意义,因而把对读者在诗歌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
诗作品的内容意义只有在读者的解读中才能实现,读者作为诗创作的重要因素起作用,这样读者理所当然成为诗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那么,读者如何去阅读和理解作品呢?读者怎样跟作者合作,共同创造并实现作品的内言意义呢?钟惺认为:“分章句,明训诂”是读者阅读的必要阶段。在诗的创作中,语言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每个读者进入阅读之前,他所面对的作品世界是一些冷冰冰的文字,这时,读者需要运用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对作品中的语言文字进行阐释。而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可能是与作品的语言同一时代,也可能是与作品的语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尤其是后一种情形,读者所使用的语言与作品语言会形成差异和矛盾,也构成一种张力,这给读者的解读带来复杂性和阻碍性,同时也为读者的理解带来无限丰富性。因此,对诗的字义进行分章句和训诂,是帮助读者进入作品语言的重要前提。但分章句,明训诂这只是阅读诗作品的初步阶段:“凡以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因为这时作品本文的潜在意义还未得到读者心灵的感应,只有其潜在意义得到读者心灵的交流,融合变成了鲜活、现实的实体之后,才成为实在的美学对象,因此钟惺指出,对于诗的进一步理解则在于“神而明之,引而伸之。”
笔者以为,钟惺所说的“神而明之,引而伸之”实际上是指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层次:“神而明之”是读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条件去灵活领会,“引而伸之”是读者在领会的基础上自由引申。这里,“神而明之”是基础,它是引导读者按作品原有的潜在意义来解释和理解。这种作品的潜在意义作为一种影响力,对读者施加影响,使读者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去随意解释作品,无论读者如何解释,都含有作品潜在意义的某种因素,并不能完全脱离作品的实际。因而“神而明之”的过程也就是作品本文功能的影响过程,而“引而伸之”则是读者的再创造过程,读者可以在“神而明之”的基础上去想象创造,在想象中把作品的潜在的未定的东西化为确定的有血有肉的艺术世界。读者的阅读理解就是这两个方面在某一点上的统一。
“神而明之,引而伸之”是读者阅读活动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创作活动和读者的接受活动融合为一了,作者在作品中寄托的意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但同时又丧失了独立自在的地位,读者可以在理解创造中不断获得它先前不曾拥有的成分。这是一种双向作用,是二者间的建构活动。于是,诗作品的内容意义就在这种活动中实现了。
无论是“神而明之”还是“引而伸之”,都不能忽视读者先有的主观条件的因素。在当代阐释学那里,读者的这种主观条件被称为“先结构”或“前理解”。钟惺虽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显然他是意识到了读者的主观条件对于阅读的重要作用。他引用朱熹的话说:“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者也。”朱熹的意思是:不敢以自己对《诗》的注解来充当和代替天下所有读者的理解。在明代,学子们的《诗经》读本,是以朱熹的《诗集传》为准的,“国家立于学官,以考亭注为主”。〔11〕朱熹却以为不敢以自己的理解来代替天下所有读者的理解,这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因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而对作品的理解有差异,没有任何个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会与他人完全一致。所谓个人的主观条件就是读者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全部个人因素,包括生活经验,思想感情,文化水平,艺术修养,审美能力,心境注意,兴趣爱好等等。所有这一切个人的因素,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读者的理解。其中审美经验在个人因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审美经验是不可重复的。真正的经验总是由“我”在“此刻”实行的,它是不可完全替代,也不能完整重复的。“人不可能两次趟进同一条河流”,因此,这种个体的不可重复的经验就只能是有限的,给审美经验带来了有限性的特点。审美经验的有限性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体对作品的理解,每一个体读者因此不可能完整重现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原义,也不可能理解和领会作品的全部意义,由此而产生了理解阐释的差异性以及多样性的结果。所以,朱熹认为不敢以自己有限的理解来代替天下所有读者的理解实在是明智的。钟惺也因此批评了有些人固执已见:“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是已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已说也,”这样的话“岂不隘且固哉!”坚持一种说法,以为这种说法能够竭尽《诗》的全部意义,这是非常狭隘并且固执的。
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也会因个人主观条件发生变化而对作品的理解随时而异。钟惺描述了自己的审美经验:“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浏览之,意有所得,……再取搜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徒,已觉有异于前者。”所谓“趣以境生,情由日徒”也就是指读者读《诗》所获得的情趣随着环境(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有所更新,这是由于人的审美经验有限性也使读者不可能完全重复自己已有的体验。人类的生命体验总是在人生旅途的不同时刻装载一些东西,也卸掉一些东西,它依据记忆而存在。记忆的变化,影响着审美对象、审美趣味的变化。因此,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体验中,即使是同一读者阅读同一作品,每一次都会与前一次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郭沫若说:“同是一部《离骚》,在童稚时我们不曾感得什么,然而目前我们能称道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天才的作者。”〔12〕郭沫若说的是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其生活经验,艺术修养乃至兴趣爱好发生很大的变化则更不用言说了,由此钟惺指出:“夫以予一人之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以一个读者而言,其阅读可以获得前后不同的情趣内容,而天下所有读者的阅读则是一个不断在历史中延继的过程,因此诗作品内容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就具有向再理解、解释或再创造永远开放的能力,对一代代阅读者来说则是每读每新,常读常新,诗作品的内容也因其永远不可能被完成而激发着,召唤着一代代读者,拥有永恒的魅力。钟惺最后说:“故说《诗》者散为万,而《诗》之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对于《诗》的解释有千千万万,而《诗》只有一部,一部《诗》可以为千千万万的读者所阅读,理解和解释,这就是《诗》之所以称为经典的真正原因。
三
应该承认而且看到,我国古代诗学中对于读者的阅读欣赏也是非常重视的。例如孟子就曾提出过“以意逆志”之说。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言辞,不以辞言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3〕这里的“意”是指读者的意,“志”是指作者的志,意思是,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诗的时候,要想透过外在言辞得到作者的本心,就要设身处地用自己的心灵去领会作者当时的心,从而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与作者相契。“以意逆志”说在古代的诗论中影响较为广泛,后人如姜夔论读诗:“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故当以心会心,”(《白石道人诗说》)谢榛说欣赏作品:“尔心非我心,焉知我心这有得也?以我之心置于尔心,俾其得我之得,虽两而一矣”(《四溟诗话》)汤显祖说自己读《西厢记》的体会:“董(解元)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董解元〈西厢记〉题辞》);焦循说阅读古人作品是“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以精汲精(《与孙渊如观察书》)。”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以意逆志”的绍述。由此可见,“以意逆志”的根本思想就是要求读者深入到作品世界作者所提供的特定意境之中,去寻找作者原来的情志,设身处地去体验他在此时此地的感受。
在古代诗论中,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庄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里他指出,正如筌蹄为得到鱼兔的工具,语言也是传达意的工具,但正因为语言作为物质媒介本身并不等意,所以必须利用语言而又最终超越语言去把握其中作者的寄寓的东西。所谓“得意”就是要得到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
“意境”在古代诗论中通常作为诗词的最高美学范畴,读者读诗就是要体会诗作品的意境。而这意境则是他在语言符号的指示下充分发挥想象的结果,清人对读者读诗时想象活动曾作十分细致的描绘,如叶燮谓阅读杜甫诗句:“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原诗》),黄子云《野鸿的诗》:“当于吟咏时,行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然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读者对词的欣赏:“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如此等等,都是指读者阅读诗作品时所获得的意境是读者想象的结果。“意境”说重视读者的想象作用,强调读者阅读时的主观能动性,但这只仅仅是是一种精神主体的活动,并未进入诗的本体层次。在“意境”说中,诗的本体就是作者的情志,作者通过诗的作品世界所描述的意境,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产生心灵勃勃的情境,读者的阅读只是通过想象的情境来进入作品获得诗的本体。杜甫说:“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又说“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所谓“有余”“混茫”,皆指耐人玩味的情志本体而言,而他说这本体是在“诗罢”和“篇终”,可见它在诗作品之外,读者必须超越作品去进入“有余”与“混茫”之中,所以杜甫认为读诗的极致是“篇终接混茫”也就是透过作品世界去寻找作者本义。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诗论中对读者阅读活动论述的共同点都是认为诗的本体是传达作者的情志,诗作品只是作者传达情志的语言形式,因此是作者创作了作品而与读者无关,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只是为了去体验和再现作者寄寓在作品中的情志。因而,读者世界及其阅读活动实质上并未进入诗学范畴,读者只是作家——作品这一理论核心的附庸,在由创作论原理推及阅读论的各种关系中,读者只有具备再现作者原义的认识能力,所有这些,当然有别于钟在《诗论》中对读者阅读活动的见解和阐述。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钟惺《诗论》的突出成就就在于创立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尽管他在《诗论》中没有提出一整套与此相关的概念术语,但其分析的视角和把握的途径完全是从读者的阐释和接受入手,把读者的阅读活动看成是诗创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接受阐释理论其关键所在。钟惺的《诗论》对后来的诗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袁枚所说:“作诗者以诗传,说读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不必尽合于作者也。”(《程绵庄诗说序》)王夫之指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沈德潜认为:“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评点笺释,皆后之方隅之见。”(《唐诗别裁·凡例》)这些论述中读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很显然在钟惺以前的诗论中是较少涉及的。如此,钟惺及其《诗论》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理应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3〕这里的诗指《诗经》,但可泛指一般的诗歌作品。
〔4〕〔9〕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158页。
〔5〕〔12〕转引自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280页。
〔6〕伊塞尔:《本文中的读者》, 蒋孔阳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
〔7〕朱熹《诗序辩论》
〔8〕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10〕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24页。
〔11〕:考亭指朱熹。《明会要》卷四十一《弇山集》:“洪武十七年,颁科举定试,初场试《四书》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诗》主朱子《集传》。”(参见李壮鹰编《中华古文论选注》(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13〕《孟子·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