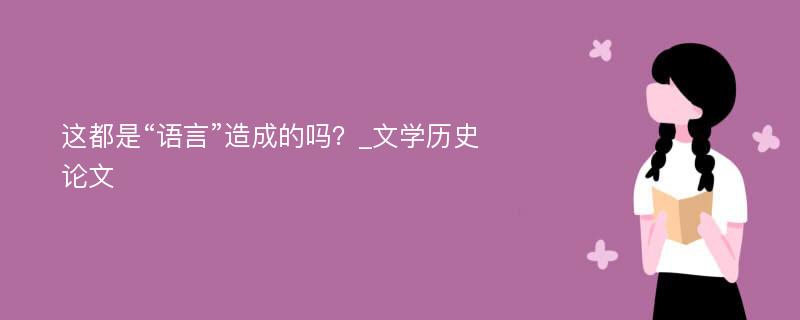
都是“语种”惹的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是论文,语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状况的不满和忧虑,无论圈内还是圈外人士都感觉到。因此, 同样作为“忝列于这一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十分理解吴亦锜、彭志恒、赵 顺宏、刘俊峰提出他们思考时的“两难”心境,也充分意识到《存在》一文,对开阔我 们思考空间的意义。我们愿意借此契机,就《存在》的话题,也谈一点我们蕴蓄已久的 想法。
否定了“语种”也就否定了“华文”
“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重 新命名而被肯认的。它主要是针对前一时期这一领域研究,把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澳 文学”和不属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并列一起所可能引起(事实上已经引起)的 不必要误解而提出的。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赋予这一领域研究新的性质和范畴。因为 作为世界性语种的华文文学,体现的是以语种进行整合研究的意图,而原来的“台港澳 文学”所对应的是大陆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所对应的是“海内”华文文学与海 外华文作家居住国的其他语种文学。二者逻辑对应关系的不同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必 然带来诠释范式的变化。人们将更多关注不同语种之间文学的文化内蕴、审美思维以及 艺术方式等等的差异与变化。在研究范畴上,作为语种的世界华文文学应当包括华文母 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大陆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两大 序列:尤其是使用华语人口最多,队伍也最庞大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学,应当成为研究 的主体。然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名实不副地用华文文学这一大的概念,来“命名”和研 究大概念下的局部文学现象。丢弃了应当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主体的中国大陆地区文 学,“世界华文文学”便不能成为完整意义的世界华文文学。这或许正是一部分学者对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至今尚存异议的原因。
《存在》所论及的华文文学,也是狭义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暨海外华 文文学’”。不过在进入具体讨论时,又抛却了台港澳文学,而专指海外华文文学。因 此该文所批评的“语种的华文文学”也非概念的本义,而只是“语种”这一“民族主义 的合谋”带给海外华文文学的灾难。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语种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同 义反复,“语种”已经包括在“华文文学”的命名之中。否定了“语种”,也即否定了 “华文”,那么“文学”将何以存身?概念的前后矛盾和对象的游移不定,套用一句话 ,莫非也是“命名”惹出的祸?
为了契合《存在》的本义,我们的讨论便也集中在海外华文文学上。
华文书写不只是一种操作工具
撇开一些情感色彩激烈的语言,《存在》对“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批评,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语种的华文文学”只关注文学的表象,没有进入文学的内面世界,它已经 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思维障碍;二、“语种的华文文学”导致文化民族主义,使华文文 学异化为文化民族主义梦想膨胀的工具或符号。
这个判断的偏颇是明显的,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辩析清楚。
首先,语言果真只是文学的操作工具和外部表象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看似简单,但深 入分析却要复杂得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不该回避,但恰恰是最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是:海外华人为什么要用华文写作?如何理解海外华人文学书写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一问 题追问的深度直接规约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向和旨趣。概而言之,圈内学人对此问 题有三种模糊的态度:或者存而不论,只专注于对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鉴赏;或者过分 强调华文创作对文化承传的意义,由于对华文作家在艰难处境中坚持华文写作的同情, 把应有的学理研究和批评变成廉价的“赞美修辞学”;或者以海外华文文学缺乏直接的 读者群为由,认为只生产不消费,这种“生产”有何意义?朱大可从“燃烧的迷津”泅 渡到澳洲以后,就提出过这种疑问。他以惯常的大胆隐喻的方式称海外华文作家为“盲 肠作家”,就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海外作家的华文书写何为?如果我们从海外华人文化属性建构的维度上看,华文书写的 意义与价值或能凸显出来。对于移民少数族群而言,文学书写是肯定自我存在的一种重 要方式。在海外华人,文学想象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建构行为,他们透过想象努力建构一 种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生命共同体。说故事或文学叙述则具有建构少数族群弱势自我的历 史整合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华文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抵抗失语、治疗失忆症,重新拾 回一个族群历史记忆的文化行为;而不是如《存在》所言,只是一种操作工具,或者一 种文学外部的表象。
今天,新世代的海外华文作家越来越倾向于把华文写作视为一种族性记忆的方式。现 旅居香港的马华作家林幸谦,就坚持把华文写作定位在抵抗失语与建构集体记忆之间; 北美华文女作家裴在美直接视写作为记忆的方式,记忆的图像,以及围绕记忆的方式打 转的各种阐述或各种话语。一个族群也包括个人的文化身份与属性受制于历史、文化与 权力的持续角力,对过去历史的挖掘将有助于稳固族群与个体自我的主体感。因此,文 化记忆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族性记忆的丧失或文化失忆,事实上是把自我 历史的诠释权拱手出让,人们将不再拥有自我的历史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华文书写不 再是如朱大可所讽喻的可有可无的“盲肠”了。马来西亚女作家钟怡雯的作品《可能的 地图》和《我的神州》等,就是一些典型的抵抗文化失忆的追忆文本,透过回溯、书写 和重构,使历史的缝隙及断裂处的真相浮出水面。这种细致甚至有些琐碎的追溯,如同 普罗斯特寻找逝水流年,即个体绵延的生命之流。从这个层面看,海外华文文学具有在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意义与功能。华文书写正是海外华 人言说存在并进而拥有整合自我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我们有必要对海外华文文学此 一向度给予更充分更细致的关注。
“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
《存在》对“语种的华文文学”另一个最尖锐的指责是“文化民族主义”,甚至认为 所谓“语种的华文文学”,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这大概是因为“ 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而它的外延则是一个被幻想出来的 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象,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一种 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辉煌。”这种未加论证的判断,使我们想起几年前引起外国文学界 热烈争论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观点。二者的逻辑推论方法几无二 致:因为是外国的,所以是殖民的;因为是语种的,所以是民族主义的。其感觉和演绎 的成分,显然多于理性与实证的分析。
民族主义是晚近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明华文文学研究已经 产生与学术思想界对话的意识。对民族主义,我们不必推崇它,也无须回避它,关键是 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它。在前些年的华文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部分研究过度强调 海外华文文学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向度,这种倾向与部分海外华文作家大量的乡愁书写 和研究者过度泛滥的乡愁诠释同步同构。这种过度强调传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 无一利。但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 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海外 华文文学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 国文学与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把海外华文文学先天具有的汉语美学传统视 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显然是不妥当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 、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不能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 在迅速来到的全球化语境中,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 存的历史趋势中,已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形态、质态和价值。对“世 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 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对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象 ,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这一命名,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 供了可能。
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象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 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 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 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 ,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 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 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 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 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 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 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 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 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 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 这一领域研究缺乏学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 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 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 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不足: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
《存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文化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用以 代替“语种的华文文学”的语言学种族属性和理论建构。从语义学上看,“文化的”和 “语言的”似乎很难完全界分并形成对抗。文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语言似乎也包含 其中。不过细读《存在》就会发现,其所说的“文化的华文文学”,指的是一种“生存 形态”、“生命自我展开的形式”,或曰“人生形式”。这一立论自有其合理的内核。 把文学视为一种生命的表现,这是文学的普遍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把华文文学作为一 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也就有据可依。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而言,这个命题的提出仍然 富有意义。因为以往的研究,确实存在着忽视对个体生命存在形式进行探索的倾向。从 早期“边缘与中心”的争论,到晚近“文化身份”的追寻,人们在热衷某种具有普泛性 和一体性的文学理念、概念系统和文学史视域时,相对而言,文学的生命个体性反而被 遮蔽了。因此,重新回到对文学普遍本质的生命关照与人文关怀,对推进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是,“文化的华文文学”立论的基础是生命哲 学,而不是文化的,讲的是“生命”而不是“文化”,将其易名为“生命的华文文学” 或许更为准确。它只揭示文学的普遍本质,而忽略了不同文学的特殊性。就华文文学而 言,它只肯认了普遍的“文学”的生命意义,却丢掉了特殊的“华文”的文化品性。尽 管《存在》在“生命表现”前面加上了“海外华人”这个限定词,但仍然只停留在海外 华人的生命形态上,而未能体现海外华文文学特殊的华文品性。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 不能不是《存在》所界定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不足之处。
如果把强调文学本质的生命体现看作是回到文学自身,而把文学的文化特殊品性看作 是文学外部研究,那么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不仅对文学自身关注不足,对文学的外部 研究也同样欠缺。圈外甚至圈内的一些人士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一个逐年形成的印象,认 为海外华文文学缺乏经典,艺术水平极为参差不齐。姑且不论这一印象准确与否,就晚 近活跃的文化研究而言,其兴趣更多地从形而上学的超验、本体,永恒的普遍性话题中 转向更微观、具体的日常世俗生活。经典并非一定是文化研究的前提,不是经典的各种 文化现象,诸如电视肥皂剧、广告、MTV以及种种可以纳入时尚的躯体书写、美女书写 等等,以其更贴近大众的世俗生活和更能体现大众一个时候的文化趣味,成为文化研究 更多关注的对象。海外华文文学本来就可以有多种读法,它的文本价值也是多重的,可 以作为一种历史文本来读,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文本来读,当然它主要是一种文学文本 ,在审美的选择中进入审美的分析。前几年一些学者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着意倡导的 文化批评,正是这样地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空间,也逐步逼进海外华文文学 的精神内核。《存在》把这类研究也视为“多半是文化民族主义心情渗透”,而予“彻 底地否定和弃绝”,表示要在“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下进行“修改”。不过《存在 》并没有提出他们的“修改”方案,只要求“修改”以后的文化批评,“按照所属理论 范畴的内在要求,对华文文学的各种叙事现象进行客观、稳妥的理论描述”,这话等于 没说。实际上“文化批评”与《存在》倡导的生命本义的华文文学研究恰恰相反。文化 批评并不主张回到文学自身来研究文学,而更偏向于所谓的外部研究。在文化批评的视 野中,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文学只是一种社会文本,美学也只是一种 特殊的意识形态。所以文化批评对意识形态、权力、种族、性别、族群、快感、政治、 大众传播等等问题更感兴趣。其实,从审美的文学批评到文化的批评的转换,为华文文 学的学术化/学理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华文文学研究将从那里获取更丰富的理论 资源、学术方法和分析工具;人们也可能从对某些华文文学作品纯粹鉴赏的审美尴尬中 ,获取其作为社会文本蕴藏的否定信息和价值。我们相信,文化批评将打破华文文学研 究的目前困局,为华文文学研究拓展一个新生面。果能如此,那么,回到真正意义上来 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研究,也就不再遥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