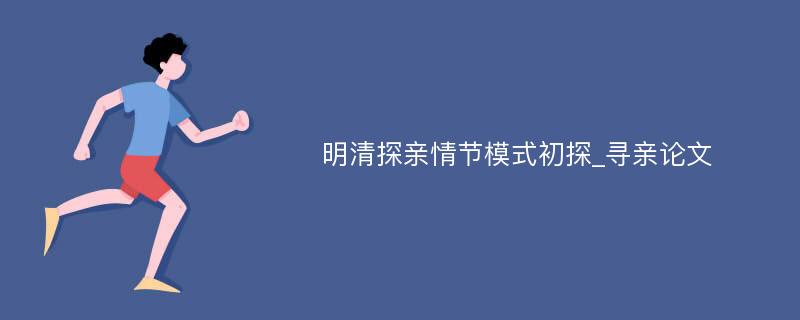
明清寻亲戏曲情节模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明清论文,情节论文,模式论文,寻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3-0107-06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孝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不只是一种伦理观念与规范,也包含了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精神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政治法律、历史记载、文学艺术、民间俗讲等,都围绕“孝”之主题进行了丰富的文化创造,拥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其中,戏曲文化是重要的一环,在此,笔者把以表彰孝行、劝孝教孝的戏曲作品称为“孝义戏”,而“万里寻亲”则是孝义戏曲中一个重要的类型。
所谓寻亲故事是指寻觅失散已久之父母的故事。寻亲之事在正史、野史中常常可以见到,逐渐成为一种孝行典范,这一孝行在文献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元代郭居敬辑《二十四孝》,其中有宋代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万里寻亲孝行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此后这类实例逐渐增多,明清两代数量激增,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①。而以“万里寻亲”为题材的戏曲创作也很早就开始出现。唐代变文中,就已有描写目连不辞千辛万苦、救其母出地狱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作为中国戏剧准形态的宋杂剧中,有可连演数天的《目连救母》杂剧;而元杂剧中除了《沉香太子辟华山》外,还有《认金梳孤儿寻母》,也是自幼和母亲失散的孤儿成人后找寻亲生母亲的故事。明清两代,此类题材的戏曲作品开始增多。在目前以“孝子寻亲”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中,笔者特选取其中有完整剧本流传者以资考察和比较。按照时间排序:《黄孝子千里寻亲记》(元代,明人改编,简称《黄孝子》);《目连救母劝善记》(明万历七年,简称《劝善记》);《周羽教子寻亲记》(明万历,简称《寻亲记》);《万里圆》(清顺治)。
明清戏曲中孝子寻亲故事大都有一个近似的情节模型:失散—决心—寻亲—重逢—归家。而从决心开始,到重逢为止,是寻亲的主要过程,也是全剧的重头戏,可以合并观之。因此,可以把寻亲戏曲的情节模式简化为失散—寻亲—归家三步过程。由“失”到“归”,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失而复得的,即是人伦感情,也是人伦秩序和人伦道德。这也体现出孝的复杂性。
让我们先从失散开始。
历史上,亲子相失的原因有很多种,包括:战乱、匪寇、穷困避役、外出经商、出游求佛等,母子相失的原因,还有一种比较常见,就是身为妾侍的生母“为嫡母所逐”。综而论之,亲子离散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则是出于自愿。历史上甚至还有自愿离家的父亲,在外已经重组家庭,或者早已皈依佛门,因此不愿意跟随千里迢迢追寻而来的孝子回家的例子。[1](P119)而在戏曲中,亲子相失则无一例外地是出于被迫。显然作者是要在戏曲舞台上树立道德典范,通过艰苦寻找后团圆的喜乐和人生意义的满足来完成戏曲的教化任务,这样的失而复得才显出其宝贵的道德价值。那些自愿性质的离散现象则被有意识地规避了,因为自愿的动机构成了对“失而复得”的反讽,作者的道德教化意向也就无处措置了。
失散中有两例是因为战乱(《黄孝子》和《万里圆》),这和明清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寻亲记》则是出于豪强的欺压。《劝善记》比较特殊,生母是因为罪愆而被罚,因此目连的寻母行为则还包含着“救赎”的涵义。其实,所有的寻亲故事中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救赎”之义。因为,父母的远离,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意味着为人父母责任的丧失,而孝子不远万里的追寻,除了把流离失所的父母,在身体和名分上回归到他们“应该”的位置,更意味着原谅和弥补父母所亏欠的一切,隐含着孝可以弥补一切过失的讯息,显示出“孝”在传统伦理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有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意思。可见儒家的孝道和家庭伦常往往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
无论是战乱,还是避祸和救赎,失散都应该是一段极其值得展开的故事,提供了广泛的情境和可能性。但这显然并非戏曲作者的兴趣所在。在大部分的寻亲故事中,“失散”都只是作为寻亲的序幕存在,关目相对较少,如在《万里圆》中只有六出,《黄孝子》也是六出,在整体篇幅中占了不到四分之一。而且《黄孝子》还利用这短暂的六出,叙写了黄觉经父母黄普之忠和陈氏之贞,力图挖掘其中的道德资源。目连则由于纳入了一个佛教故事的框架里,佛教的罪与罚自然也成为关注的重点。这和《黄孝子》的创作出发点是一样的。
《万里圆》叙写的时代正是明清交替时期,这一时期是清初文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戏曲中也不乏表达(如《桃花扇》)。因此《万里圆》也有意识地涉及了清初动荡的社会现实,还安排了专门的关目来展现史可法、黄得功的抗清行为。不过史可法和黄得功都是忠臣,是可以和孝子之孝参照对看的,其道德劝谏意义不言自明。只有《寻亲记》以较多的篇幅表现了周羽饱受官府、胥吏和豪绅的欺凌和榨取,以至于有家不能归,也只有在这出戏里,“寻亲”不仅仅是孝的表现,也是对苦难的一种纾解。
寻亲是戏曲的重头戏,包括决心、寻亲和重逢三个段落。以孝子为叙事的焦点,敷演孝子在“孝”的召唤下,远离家园,抛妻弃子,割舍所有的牵挂和情义,决心踏上渺茫而艰苦的寻找旅程。并在经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后,最终骨肉重逢。这其中的几个段落的发生,关涉到当时戏曲文化对孝道内涵的诠释。
明清时期,交通和通讯都极不发达,要找到长期失去联系的父母绝非易事。其中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饥寒危险等艰苦的条件,更需要面对茫然求索时几近绝望的心理压力。过程的艰巨性对戏曲家来说反而成了有利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用来衬托孝子强大的意志力。因此,在寻亲历程的起点,孝子们在踏上寻亲旅程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心:
《万里圆》:“若不得父母同归也,宁死他乡誓不回。”(第八出)
《黄孝子》:“为儿不得奉慈颜,日夜悲号何足道,此身愿做他乡思,誓不见亲应不返。”(第七出)
是他们对寻亲的艰苦和渺茫估计不足吗?显然不是。《万里圆》第八出,黄向坚决定出发寻父时,其妻就列举了此行面临的重重阻力:“只恐相公弱质,不堪跋涉长途”、“念风霜切肌……兵戈满地……饥寒难济”。《黄孝子》中老仆陈容也劝阻黄觉经出外寻母:“只是东人年幼,未曾历练,岂堪途路跋涉。乡井既殊,风土自异。况老夫人在兵戈相失,又无定居,四海之路甚广,岂能遍历。”(第七出)这些劝阻之词,既出于亲人们对孝子的真切关怀,也有非常实际的顾虑,出于人之常情。其实,寻亲也不只是孤身外出一种方法,戏曲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更为极端的寻亲方式来表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奇节”式的行为更符合“非奇不传”的艺术表现的需要,更透露出作者树立道德典范的创作意图。剧中,列举这些困难与其说是为了挽留孝子,莫若说是对孝子决心的反衬。困难越是巨大,孝子的超人意志力和坚韧的精神力量便越是得到放大和强调,“孝”道的超越性力量才能够充分展示出来。
是孝子们对家乡、家园、家人毫无留恋吗?似乎也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孝子在出行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矛盾中的痛苦煎熬,也可以看到孝子两难的抉择,在人伦关系的坐标系中,孝子往往处在各种关系的交叉点上:既是儿子,同时也是丈夫和父亲。在“孝”伦理的体系内部,孝子不仅仅承担一种义务。《万里圆》中的黄向坚,出门寻亲时已经娶妻生子,孝道义务的履行意味着背弃抚养照顾妻儿的义务,他面对的是不同义务的矛盾。《黄孝子》中黄觉经,取消婚约前去寻亲,就无法履行繁衍后代的义务;《寻亲记》中周瑞隆出门寻父,就无法照顾在家的母亲,他们面对的是孝道体系内部的矛盾。同时,黄觉经还欠下含辛茹苦抚育他成人的陈容夫妇的恩情无法报答;周瑞隆为了寻父不得已刺血写经,毁伤了受之父母的身体;傅罗卜辞官,忠孝难以两全;傅罗卜和黄觉经辞亲,给女方带来了命运的困厄……种种矛盾纠缠在一起,使孝子在决心出行时也难免牵挂和痛苦。但是,这一样动摇不了他们寻亲的决心:
《万里圆》:“事关父母,这些家事小事也顾不得了。”
《劝善记》:“我未报亲恩,焉敢受妻儿奉养。
《黄孝子》:“有母流落,不能寻访,何瑕言及亲事。”
各种社会关系的纠缠,使寻亲不仅要孝子个人付出金钱、体力和精神痛苦的代价,和他相依为生的亲人们也要被迫一起牺牲。在“孝”的巨大道德召唤下,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可见“孝”在封建道德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小说中的类似情节。如《石点头·王本立天涯求父》中,王原向母亲表达了不见父亲誓不回家的决心后,母亲质问道:
好决心,好志气,只是你既晓得有爹,可晓得有娘么?……父母总是一般,我现在此,你还未曾孝养一日,反想去寻不识面的父亲!这些道理尚不明白,还读什么书?讲什么孝?[2](P189)
这些诘问王原是无法回答的。小说在这里并没有回避孝道德内在的冲突,在今人看来更加合情合理。但这样的矛盾很显然会削弱寻亲孝行的道德意义,因此在戏曲中没有得到展开——和小说比起来,戏曲更倾向于道德劝谏意义,只有回避寻亲孝行背后的伦理悖论,才能砌筑一座孝道德的完美大厦。
综而论之,在戏曲中,作者关注的并非孝子所面临的困境本身,也不是着意于展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生二律背反。作者设置这些困境只是为了衬托孝子寻亲的至诚至坚,和列举旅程的种种艰难困苦一样,同样是为了显示孝道德的巨大力量。
为什么孝道德的力量如此强大?因为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孝”有着人伦本原的地位。《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百行之本,是道德伦理的总纲,人类的道德教化不但要从孝道开始。“孝”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它不是区别人的社会身份、年龄、能力、资赋的标志,而是区别人和禽兽的标志。如杨起元就说过:“然则人之所以贵者以能育物也,人之所以能育物者,以有孝思也。”[3](P490)
“孝”的内容无非是“养生送死”。若父母渺茫不知所在,不但使为人子者失去了养生送死尽孝心的可能,更使人子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价值。所以孝子们在出门寻亲之前,大都办妥了后事,这不仅仅是显示出“誓不见亲应不返”的决心,更是无法面对自我的表现。在找到父母之前,孝子的灵魂是完全无法安顿的,这也体现出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孝”的“人伦本原”、“孝为德本”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孝子们为什么要为寻找一个甚至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而踏上漫长的寻亲旅程,即使这个旅程充满着已知或者未知的各种艰苦,即使付出巨大代价结果却极其渺茫。孝子们的义无反顾来自于“良心”的驱动,如果不能完成,孝子的良心是无法安顿的。
良心是每个人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按照伦理学的说法,良心虽然是对人的某些自由和欲望的压抑、阻遏和侵犯,但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的一切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给的,因此,就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防止更大的害和恶(社会和他人的唾弃、惩罚),是净余额为善的恶。对孝子来说,他在寻亲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如肉体所经受的各种艰辛痛苦,精神所遭受的骨肉分离之痛等,当然是一种害和恶。而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充满艰辛和未知的旅程,恰是因为这种痛苦能够换取他所想要的善。包括灵魂的安顿、自我价值的实现、理想的生命观都是良心所获得的净余值。
决心既定,孝子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亲的艰险旅程。前面说过,在交通和通信都极不发达,社会治安也存在许多问题的时代,孝子在寻亲过程中必然经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种种阻力成为阻挠寻亲的直接障碍,同时也构成对孝子诚心的重重考验。相对于历史记载,戏曲可以有更多的篇幅和更从容的空间进行细腻的表现,同时也是令情节跌宕起伏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段落成为寻亲戏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部分,常常在舞台上搬演。如清代刊行的,收录剧场经常演出的昆曲和花部乱弹零折戏的戏曲剧本选集《缀白裘》中,就收录有《万里圆》“跌雪”一出,可见讲述黄向坚如何遭遇强盗的这段戏,在当时的戏曲舞台上,演出相当频繁。
孝子历经艰难困苦,经受着包括来自自然、社会和心理的多重考验,既有精神层面的顽强拼搏,也有生存层面的拼力挣扎。有的孝子虽然在神灵的护佑之下经历万险,最终性命无虞,但其中的苦楚惨痛还需要孝子遍历亲尝。
自然环境的恶劣是孝子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路途的险阻、恶劣的天气、还有到处出没的豺狼虎豹,处处构成对孝子生命的威胁。剧中有的通过第三者之口,极尽铺陈:
《黄孝子》:“那猛兽生一副兀兀突突迎山峰撞石壁折灌木披荆棘的磕脑头,撑一双团团圆圆绚绿艳射金辉闪燐光烈炬火的突爆眼,开一张了了义义耸银枪攒玉笋排戈戟晃锋刃的巨牙齿,竖一条矗矗巍巍排百州撑四极撼天摇地轴的铁棒尾。布窝弓永不能伤,穿罗洞何曾得隘,吼一吼山岳动摇魑魅丛中皆震踏,啸一啸波涛汹涌蛟龙渊衣尽翻腾……”(第十四出)
有的则直写孝子的真情苦况,刻画出恶劣环境给孝子们带来的无尽痛楚:
《万里圆》:“我手抖手癵蜷、形如距,足趔趄、行还仆。战战牙关气咽饥喉。生寒栗冻裂残躯。嶙峋山谷,白茫茫认不出高低路。鬼门关打个盘旋,奈何桥恁般苦楚。”(第二十三出)
《劝善记》:“冰光璨,冰气团,隐隐蛟龙驻此间,令人心胆寒,身既单,衣又单,雁不到来至此间。”(过寒冰池)
孝子寻亲所遇到的自然阻力有:高山大池(《万里圆》、《劝善记》);沼泽(《黄孝子》);虎(《黄孝子》、《劝善记》、《万里圆》);蛇(《黄孝子》)等。《劝善记》因为有佛经故事的框架,一路上还遇到了诸如乌龙精(“过寒冰池”),赤蛇精(“过火焰山”),沙和尚(“过烂沙河”)等妖魔鬼怪,其实一样可以视之为各种自然力量的化身。
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陷阱凶险也在时时考验着孝子们,有骗子(《黄孝子》),有强盗(《万里圆》),有兵匪(《万里圆》),还有美色的诱惑(《劝善记》)。主角处处生死交关,频涉险境,令人望而生畏。这也是作者希望带给观众的效果,透过移情的作用而能感受数千里、数十年寻亲过程的艰难,进而起到感化孝思的作用。
百转千回的历程是寻亲戏曲中不可或缺的情节单元,它既是考验孝子心志的历程,也是开启希望的关键通道,因此不可或缺。这段路程越艰辛、越危险,也就愈发考验出孝子寻亲意志的坚定不移。孝子身体的单弱和精神世界的强大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更加显示出“孝道德”无坚不摧的力量。
道德力量的强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孝感”现象的出现。“至孝格天”本来就是中国孝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万里寻亲故事本身就具备的传奇色彩又为各种“孝感”情节的书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劝善记》因为其佛经故事的框架,有观音菩萨一路保护救助。《节孝记》中也有土地、山神的庇护。这样一来,种种困厄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考验。这在《劝善记》中表现最为突出,因为观音菩萨还专门安排了两次色诱的魔障,以考验孝子的诚心。所以,决胜的唯一武器是孝子坚定的意志,也就是人的道德力量,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孝感神应”的信心和心理期望。
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之下,至诚至坚的寻亲孝行,既然能够感动天地鬼神,自然也就能够感动众生万物。所以在寻亲的艰苦历程中,不乏人情的温暖,但凡听说是孝子寻亲的,无不给予无私的帮助。如《黄孝子》,黄孝子被骗走盘缠后,获老汉赠银;《万里圆》黄向坚宿店时得到同行人的指点,遇盗时被老僧所救,并获赠衣物;《寻亲记》中李员外转送《台卿集》甚至成为父子重逢的关键……孝子踽踽独行的寻亲身影,其背后交织着富含道德意味的人情网络,孝子寻亲的最终成功,人情网络的互助与帮补是必不可少的后援力量。
鬼神相助加上人情的帮补,最终使孝子寻亲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外部环境对寻亲的促成作用。对于鬼神相助之类的“孝感”情节,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荒诞,但在当时,孝乃百行之原,伦理之本,深受国家和社会的推崇和提倡。孝是人之至性,必能感动上苍,受到天神的赐福——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联系。既然深信不疑,自然会受到激励和感化,正所谓“孝心感格神天助,好与人间做样看”(《石点头》)。而各方人情的帮助扶持则表现出当时文化对这种孝行的肯定。无往而不利的背后,是社会文化对这一孝行的认可和赞赏,由是在观众心目中也强化了这样的评判体系。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作为有所回报,或为物质上的报酬,或是精神上的褒奖等“符号资本”,从而使自己得到各不相同的认可。孝子寻亲固然需要付出艰辛的代价,但其可以因此获得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奖赏。其对观众的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历代孝子寻亲事迹对主人公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甚至看到戏曲作品中主人公寻亲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模仿前代的孝子们,如“刺血写经”(《寻亲记》)、“茹素断荤”(《节孝记》)、“弃官寻亲”(《劝善记》、《寻亲记》)、都是模仿朱寿昌,写广告的方法(《节孝记》)则是复制明代赵重华寻父事。而主人公的寻亲故事又成为激励观赏者的教科书,最终形成交互影响的网络,起到了强大的文化动员作用。
孝子寻亲的案例在明清时代的历史记载中相当集中地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寻亲事件最后都有着完美的结局。仅《明史·孝义传》中就有崔敏、史五常等四人并没能有亲子团圆的幸运,而只把父亲的骨殖带回了家。在《清史稿》中,这样的记载同样历历可见。史书的严肃性和正统性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但这显然令相关的道德宣传与舆论期待落到了比较尴尬的境地:不是“至孝格天”吗?怎么天意不帮助这些孝子实现心愿?这样的困惑当然是道德宣传者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时候,戏曲就显示出其作为虚构性文艺作品的优势来。
寻亲戏曲无一例外获得了完满的结局,孝子在历尽艰苦后终于找到了魂牵梦绕的亲人,由离到合,由散而聚,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父母对家庭的回归,就是对孝道为他们所安排的位置的回归,孝子的生命价值也终于得到实现。因此,归家这一情节在不同的戏曲作品中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旌表、封赏、登仙……概莫能外。孝子们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伤感体验,最终也证明只是过程,只有孝道是永恒的。
结局的完满还不仅仅表现在画出了“失而复得”的完美圆圈,整个家庭的道德无亏是更深层的完美。史书中有的是道德有亏的父母,如有的父亲逃债、逃役造成父辈抚养义务的空置;有的母亲改嫁造成妇德受损②。在戏曲中父母则都是忠臣烈妇(《劝善记》略有不同,但母亲的污点最终被孝子的虔诚清洗干净,举家登仙),忠孝萃于一门。从《黄孝子》朝廷旌表的圣旨中我们就可见一斑:
黄大人为国鏊兵,殁于王事,此乃忠也;令郎立誓寻亲,终得会合,此乃孝也;李夫人身遭俘掳,守志坚贞,此乃节也;陈管家善保遗孤,能全抚养,此乃义也。忠孝节义出于一门,世间少有……
这种“捆绑”式的复合型情节凸显出“孝”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孝无疑处于起点和核心的地位,对其他道德规范有统摄和指导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把忠、节、义、悌等看作是孝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实施。正如《劝善记》所说:“臣子之道,忠孝一理……为子而孝可格天,为臣必忠能报主。”(《罗卜辞官》)当然了,封赏和旌表也是针对全家进行,如《寻亲记》:“周瑞隆升苏州府知府,父周羽封封丘县尹,郭氏封贞洁宜人。”(第三十四回)虽然是虚构的封赏和旌表,但一样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如减免徭租,赐予绢帛等),还有“心理收入”(如声誉、名望、面子等),对受众的激励作用显而易见。这样的情节使“孝”道德一方面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约束力量,另一方面也内化为人们行动的力量。
比起割股疗亲、为亲殉身这类代价惨重而于事无补的行为,万里寻亲不但能够得到法律的通融,而且也容易得到社会舆论的赞赏。从《黄孝子寻亲纪程》的序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国家的旌表和封赏,使寻亲孝行更加得到了权利话语的认可。它准确折射着古代社会的道德精神,有效地指示着社会文化的导向。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作为收束,戏曲敦励教化、移风易俗的作用才能得到完美的实现。
从以上情节模式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道德劝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是戏曲设置情节的主要动机,表现出极其浓厚的社会功用意识。本来,作为“万里寻亲”的旅程情节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情节之一,其广阔的时空背景本可以容纳丰富的社会内涵[4],但寻亲戏曲却只在人伦关系和孝道宣传上恋恋不去。因此,情节大多在道德意义的支配下生成,有的由剧中人直接发出议论,有的则在情节进程中诱发道德含蕴。创作者虽然也在讲述一个震绝人寰的亲子故事,不乏以情动人之处,但其终极目的,还是要树立一个道德典范,以理服人。这从寻亲戏曲情节模式中对历史材料的取舍、重点段落的发挥、矛盾纠葛的解决等都可以看出端倪。
第二,情节模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失散—寻亲—归家”式的情节模式在寻亲戏曲中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孝子们历尽艰辛、千辛万苦地成全了他们的孝道,而最终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既有升官发财等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有表彰宣扬等心理收入,正所谓“子行大孝诸神佑,永播芳名万古传”,寻亲戏曲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样的情节模式。它首先反映出了一种稳定性的民族心理结构,即孝敬父母的人最终一定会得到好报。同时亦可见寻亲戏曲的创作意旨,不在追新求奇,也不在作者自我情感意愿的表达、或个人才华的呈露,而在于提供一个孝行的标准和其可资施行的理论上,既然是标准,当然比较整齐划一。戏曲作者倾注其中的功能关注要远远大于艺术关注,与其说它们是艺术作品,毋宁说是孝道理念的通俗讲本,来得更贴切些。
第三,这样的情节模式体现出明清孝义类戏曲独特的书写策略。其书写策略的中心目的就是“树立榜样”,围绕这一中心,对史料或者民间故事进行各种适用性改造,以使舞台上的孝行故事显得更加光整完美。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并力图通过道德来维系天下和统治秩序的国家。故而,作为道德承载体的榜样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古往今来,每一个时代,榜样都层出不穷。这些榜样既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担负着时代的需要。万里寻亲的孝子作为榜样既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非完全的真实生活的体现,而是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宣传需要以及书写者主观意图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持续加工甚至说“造假”的过程。他们的意义可能主要并不在于让普通大众全面地模仿,而是在社会上造成某种氛围,以便国家更广泛深入地向普通民众灌输和推行“主流”的思想文化观念。
注释:
①根据《明史》,明洪武年间的旌表已经明确标出“万里寻亲”为一种孝行范畴。
②前者如王原之父,见《明史·孝义》;后者如朱寿昌之母,见《宋史》卷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