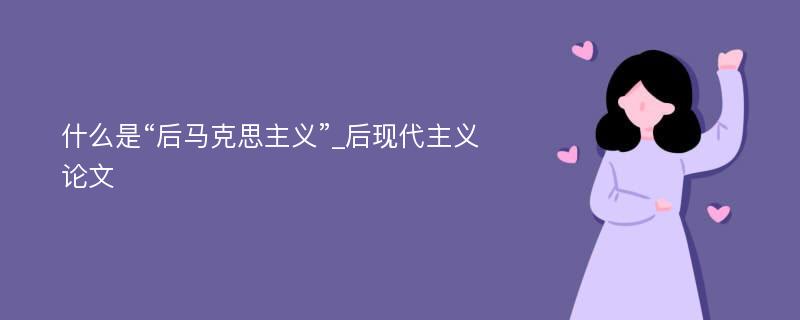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045-06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思潮在西方的出现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如今它已在各个学术领域渐成气候。鉴于国外部分学者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作无限的拔高和追捧,而国内学者对这一思潮的解读又各取所需,因此,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方法论上的“后”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源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看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解读“后”(post)以及“后”(post)与“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关系。
从本质上说,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后”(post),更多的是指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当然,由于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进行取舍上的立场不同,从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曾经给过一个经典的解说。他将后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另一种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所做的工作是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它虽然还在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但不再信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彻头彻尾地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所以,西姆将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标示成“post- Marxism”——正体的“后”(post)表明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斜体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指示它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而“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则相反,他们一开始好像是要用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来超越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始终无法遣散,因此这些人只是表面上的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骨子里却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西姆用“post- Marxism”来指认这类后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斯图亚特·西姆这种区分背后的深层含义,有人做过精到的概括: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立场(post- Marxist)和“后—马克思主义”立场(post- Marxist)之间做了一个区分。一方面,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洞见嫁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上,比如拉克劳和墨菲(1985)。这一融合貌似扩张马克思主义,实质是认为我们只要关注新的文化气候而无须再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一努力固然值得同情,但鲍德里亚对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扩张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它只是具体细节的重新组装。另外,“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看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置之不理,但在德里达(1994)和利奥塔(1993)看来,他们其实始终为马克思所笼罩。鲍德里亚就是这样的角色,他看来好像与马克思决裂了,但对马克思始终保持一种乡愁。鲍德里亚的整个学说始终对“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冲动。①
从中可以看出,在西方,尽管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判然有别。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维护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实“后”假“马”;有些人声称自己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其实却对马克思主义难以释怀。然而,不管怎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紧密勾连是一个显明的事实。
因此,如果要对后马克思主义下一个简单定义的话,可以这样来表述: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借用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替换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一种思潮。离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语境来界定和看待后马克思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研究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触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旨趣。正如《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一书的作者菲利普·戈德斯坦(Philip Goldstein)所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总体主义等观点的削弱,以及福柯通过研究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而对苏联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揭露,从此而开创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得益于阿尔都塞和福柯天才式的理论贡献,使得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等领域都有了各自的版本——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或学派,但他们都重申和援用阿尔都塞和福柯的理论。”② 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从来不忌讳谈论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对自己的重大影响。
正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运用的是“后”主义的方法,所以它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给出的诊断书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术语:本质主义、功能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自然主义、总体主义、极权主义、阶级主义、中心主义、经济主义、形而上学、宏大叙事、还原论、一元论、决定论、二元论、目的论、先验论、机械论、实体论、实在论、封闭性、凝固性,等等。与之相反,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秉承了以下原则和精神:多元主义、非目的论、非确定性、对等逻辑、非决定论、非还原论、语境主义、话语性、差异性、异质性、开放性、模糊性、复杂性、非锁合,等等。显然,这种批判理路延续的是“后”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这些看似天花乱坠的后马克思主义术语,其内在逻辑理路不过是“后”主义。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鉴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丑化,撰文批评道:“我的观点是,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学术真空,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才选用的一个词语:既是一个理论的真空,也是一个标准的真空。围绕它的不过是一些非常陈旧的论点、偏见和漫画般的扭曲。”③
二、性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
或许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代表性思潮。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挂起钩来,这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其实,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多的瓜葛,两者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阵营。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还保持或多或少尊重的话,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却表现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后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或否定态度,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观点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后马克思主义当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形态纯属一厢情愿,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一条判然有别的鸿沟。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从各种“后”主义那里借取资源,目的不是要阐扬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整体上解构马克思主义。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庸俗化理解就是这种总体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出于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几乎所有的概念都进行了批判,即使是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最有价值的概念也未能幸免。概括起来说,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在社会发展动力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反映,并且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有负面效应,因为它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规律所保证的、自动来临的东西,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是社会行动者建构的产物。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消解“生产力”这一概念。
其二,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异化现象,正是这种非人的异化,导致了无产阶级共同体的产生,从而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孕育了革命的主体;而后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异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虚构,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有着适当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不会导致异化现象的产生,反而导致了工人内部的分化,使得具有共同立场的无产阶级主体不可能产生,因而革命的主体不可能是单一的无产阶级。
其三,在对资本主义的取缔方式上,马克思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革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颠覆资本主义社会;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政治的表现,这种宏大政治不可能会产生实质效果,因而后马克思主义转而诉诸文化抵制、话语宣泄等边缘性的所谓的微观政治和斗争。
其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阶级斗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则根本反对用革命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而主张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其五,在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一个消除了剥削和压迫、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理想社会;后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透明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依然存在对抗,尽管这种对抗也许不是阶级对抗,但依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思想差异的对立等等,并且认为这种对抗和对立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因此,必须始终葆有对抗的因素,否则共产主义社会谈不上是一个民主社会。
其六,在社会主义的存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赞成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则反对任何“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主张抵制科层化、官僚化的所谓激进民主和激进政治。
其七,在社会发展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主张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决裂;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这种完成体现在民主的延伸上,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更民主化。
另外,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刻意夸大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分离,认为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没有联系,只是单纯地为争夺话语权力的斗争,是民主话语的冲突和对抗。这样的立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同时,后马克思主义也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只是一种理论虚构,而非是真实状况的描述,并且认为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要求,工人阶级压迫性意识的产生是通过民主话语的建构而实现的。
所有这些分歧表明,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左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二次方。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的话,那么,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则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自己的努力是为了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从其现实作为来看,他们却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他们毫不忌讳地说:“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④ 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打着挽救马克思主义旗号实则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因此,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说:“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⑤
三、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主义
之所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因为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和引导力,进而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想阵营去寻求理论资源。正如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政治的回归》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社会主义策略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恩斯特·拉克劳也宣称,“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⑥。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借取民主理念注入社会主义,并将民主的理念在社会主义中全面铺展和彻底化,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治目标就是他们所谓的“激进民主”。
激进民主,通俗地说就是民主的激进化,即要将自由民主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化。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要提出“激进民主政治”的目标?是因为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是如何把民主、自由的精神嫁接到社会主义当中去,或者说,将社会主义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的轨道。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民主革命,所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缺乏民主的维度。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缺失,原因在于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隐含着反民主的东西;现实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总是会一再走向极权主义,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就隐含着极权主义的因子。既然马克思主义那里不存在民主思想的存身之所,那么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民主的理念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面前转身离去,全身心地投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怀抱,也就不难理解了。
将民主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剥离出去,并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反民主思想或极权主义,这恰恰是自由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手法。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两者在精神上本来就是息息相通的,难怪学者诺曼·杰拉斯坦率地指出:“拉克劳和墨菲在可能的限度内向我们表达了对自由主义最温和的看法。”⑦ 艾伦·伍德也反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可被说成是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⑧。
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极权主义现象,这种极权主义的出现显然与时代的险恶政治环境,特别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围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后马克思主义却全然不顾这些背景,反而把社会主义产生极权主义现象的根源完全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尽管声称自己是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确切地说,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披着葛兰西主义的外衣以达到自己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已⑨,因此,它对马克思主义所有经典概念的全面解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必然走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敌对阵营加以打击这一步。后马克思主义反复念叨着自己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障眼法。后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此,两位西方学者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实质。丹尼尔·麦吉(Daniel T.Mc Gee)说:“后马克思主义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让我们不能专心于改善活人的状况。通过让我们关注不朽性的希望,后马克思主义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理论形式的误解政治学的技术,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⑩ 诺曼·杰拉斯也说,后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好像是激进的民主人士,但其表述民主的观点肤浅得令人失望,而且比肤浅更有害的是,它表现得很像冷战时反马克思主义标准的转喻”(11)。
四、行动上的“精神社会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范围广泛的群众运动,不仅群众运动的名目繁多,有学生起义、女权主义运动、生态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运动等,而且斗争的形式也多样,如占领课堂、袭击警察、街头静坐、实施爆炸、抵制兵役、断路、吸毒、性滥交等等。这些运动或斗争形式,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这些斗争现象在马克思的设想中都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被马克思排除在自己的社会主义斗争策略之外的。因为马克思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剥削的加重,社会最终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必然会发生对抗。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言外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认为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有资格充当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不认为阶级斗争之外的其他斗争形式会有重要的历史效果。
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张是根本不认同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想法是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它忽视了真实的社会现实,看不到工人阶级之外群体的真实利益和真实想法,更看不到这些群体抗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基于20世纪6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新社会运动现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围攻。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从新社会运动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伊萨克(Jeffrey C.Isaac)作了总结: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关键挑战不仅仅是关于中央集权主义和好斗性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政治的相对稳定中,各种新社会运动纷纷涌现——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虽然从历史上来讲并不是全新的,但是,它们所表达的特殊的不平、它们独特的组织形式,无不带上战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印迹:由于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主义,小家庭出现瓦解,对女权主义而言,劳动市场上妇女的大批出现;就公民权而言,民族的及国际的人口变换;就和平运动而言,社会的好战性及核武竞赛;就生态而言,无计划的地区经济发展、化学工业、药用工业、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并不是阶级对抗,它指向非阶级的权力关系。就这一点是真实的而言,它们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不把它们还原为阶级关系的派生物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些现象。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回应了这一挑战。(12)
后马克思主义由此认为,西方国家发生的“新社会运动”表明,任何一类主体(学生、工人、妇女、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者、性偏好主义者、反核主义者、反体制主义者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变化的领导中坚。至于如何实现激进民主,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所谓的“领导权”(hegemony)的构造。在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当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具有领导权的资格。但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激进民主政治的领导者不可能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更何况无产阶级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在现实社会面前,没有哪一类主体比其他主体更优越。因此,不能把未来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某类主体身上,更不能将这类主体的地位永恒化。
后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这样一种立场:社会变革的领导者是一种联合力量。在这种联合力量里面,各类主体是平等的,同时也是异质的;他们的联合是偶然的、暂时的,而非固定的、永恒的;他们的联合并不是出于固有的阶级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外在的话语“接合”(articulation)。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实现就依靠这种联合的领导权力量,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就是努力去思考——如何才能将这种领导权建构起来。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将研究重心转到“话语”分析上来,到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那里去寻求理论支持,是有原因的。
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提法看似有一定的新颖性,但实质是用理论上所谓的翻新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斗争性。而当他们以“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13) 的理由来弱化无产阶级的作用时,其目的貌似是要进行一场对资本主义的“全民运动”、“大众运动”、“大拒绝”,其实质则是要将斗争的力量和斗争的目标泛化,最终使资本主义处在打击不到的安全地带。因此,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策略不过是对社会主义追求的放弃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委婉维护,从而将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推至于遥遥无期。
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节节失利的失望,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斗争面前转身离去,而投入智力工作上的向壁虚构,不再对“回到阶级斗争”有任何的兴趣。正如拉克劳在2001年为其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回答“左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说的那样:“答案是不放弃‘文化’斗争,回到‘真实’政治。”(14) 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用“激进民主”政治置换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并将这种政治转换成“话语政治”,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所极力倡导的通达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然而这种“激进民主”没有任何激进可言,它充其量是另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15)
总之,不管后马克思主义提出多少种替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策略的方案,不管后马克思主义主张谁来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的社会力量,由于后马克思主义首先认同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16),因此,他们所有的社会主义方案及主张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体制内的人或认同自身体制的人不可能“内爆”或推翻自己的体制。针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张,艾伦·伍德指出,“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者是处于绝望中的幻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17) 用达纳·克劳德的话来说: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策略,充其量只是新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社会主义”(18)。
注释:
① Richard G Smith & Marcus A Doel.“Baudrillard unwound:the duplicity of post-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2001,volume 19,pages 137-159.
② Philip Goldstein.Post-Marxist Theo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2-5.
③ Norman Geras.“Post-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63,May-June 1987.
④⑥ [英]恩斯特·拉克劳、[美]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第4、198页,尹树广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⑤⑧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再版导言”第2、5页,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⑦⑨ Norman Geras.“Post-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63,May-June 1987.
⑩ Daniel T.McGee.“Post-Marxism: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58:2,June 1997.
(11) Norman Geras.“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New Left Review,No.169,May-June 1988.
(12) Jeffrey C.Isaac.Power and Marxist Theory:a realist View,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artⅡ,6,p.208,1987.
(13) Ernesto Laclau.“Class War And After”.Marxism Today,April 1987,p.32.
(14) [英]恩斯特·拉克劳、[美]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第14页。
(15)(16)(17)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第7页、“再版导言”第5、15页。
(18) Herbert W.Simons & Michael Billig (Edt.).After Postmodernism: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Sage Publications Ltd,p.251.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