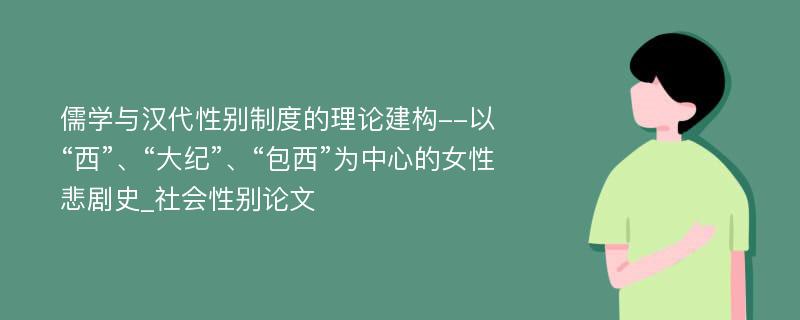
儒学与汉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建构——以“女祸史观”下末喜、妲己和褒姒的史事撰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儒学论文,汉代论文,妲己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2)04-0094-07
一般认为,在夏商时代,还存在母权制的孑遗,女性尚保有广泛的权利,体现在政治、军事、祭祀、农业等方面,她们有独立的财产权,有主持祭祀和指挥作战的权力[1]7-10。但周的兴起,使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文化发展发生重大转折。周代制度的创设,为强化父权奠定了基础[2]53,从此,女性的地位开始降低。王国维曾提出:“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3]473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周代政治和文化延续和强化的结果,它为后世不断对社会性别制度进行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女性在涉政问题上的被排斥。在传统上,学界一般认为,越向前追溯,女性的地位就越高,故夏商高于周秦,汉魏高于唐宋明清。这种线性逻辑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先秦时代,女性涉入政治的机会略多,但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理论建构的重要时期。本文试从末喜、妲己和褒姒三人历史形象的变迁入手,探讨卷入政治中的女性是如何被“污名化”的,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在女性涉政问题上“厌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①。
在古代社会,夏、商和西周三代皆亡于女宠,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早在春秋时期,这种观念就初步形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之母曰:“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晋杜预注《左传》,即曰:“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骊姬废。”“是物”即指美色,女宠被认为是三代灭亡的原因。这种看法也反映在《国语》中。《国语·晋语一》载史苏之言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周于是乎亡。”这也是三名女性的名字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史籍之中。自此,使三代灭亡之人,遂作实为末喜、妲己和褒姒。但三人形迹如何,春秋以至战国之史籍并未明言。为了让这种“女祸史观”或言“女宠史观”成为定谳,继先秦之后,汉代人对三代史实进行了重新建构,重点突出了末喜、妲己和褒姒在三代灭亡中的作用。对这一历史建构过程,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古史“层累构成”说,仍然表示出强大的解释力②[4]59-60。“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5]273,因此他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历史理念。比如,顾颉刚先生本人也曾就妲己做过简单考证,认为妲己的事迹不过是后人追加到她身上而已[6]82。也就是说,末喜、妲己和褒姒的历史形象,以及她们被当成三代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先秦秦汉时期社会、文化对其进行建构的结果,其史事是不断积累增益的,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理论建构,而欲建立起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
一、对末喜的史事建构
末喜,在古代史籍中又作妹喜、末嬉、妹嬉。在较早完整叙述夏代历史的《史记·夏本纪》中,并未提及末喜③;而详细讲述末喜事迹的,是刘向的《列女传》。刘向在该书末章专辟“孽嬖传”。《列女传》本是讲妇女之德,以为广大女性的榜样的,然而在此章也列举了很多“反面教材”,末喜居其首位。
在此章中,刘向把很多与末喜无关的“史实”附加到了末喜身上。末喜的形象被彻底固定化,后人述及末喜与夏亡之关系,多据于此。在传统的历史撰述中,桀作为亡国之君,必然是荒淫无道、道德败坏的④,而末喜则是他“堕落”的重要原因和帮凶。刘向总结出末喜的几个特征,其一,美而无德;其二以美色蛊惑夏桀,致使夏政不治。
那么,夏末乱政果真是末喜造成的吗?早于《列女传》的典籍并不简单地这样认为。前举《国语》即是如此,而汉初的《韩诗外传》同样如此。《韩诗外传》卷二载:“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其卷四又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可见,《韩诗外传》虽云夏桀无道,但却与末喜无关。
《淮南子》也述夏、商末世政象之乱,但只及于桀、纣而已。其《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疲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
《史记·外戚世家》序云:“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亵姒。”此段虽指言末喜、妲己和褒姒三位女性与夏、商和西周的灭亡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指明其间的必然联系,而只是从外戚的角度上进行了解读:“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太史公认为,夫妇之道和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定要谨循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既定秩序,否则就会发生变乱。所以他说:“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惟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汉书·外戚传上》序基本袭自《史记》,大意与此同。也就是,《史记》和《汉书》的著者尚没有简单地把三代的灭亡归结到末喜、妲己和褒姒个人身上。
就连西汉后期刘向自己编辑的另一本书《新序》中的相关篇章也持此立场。其《刺奢》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节士》又云:“桀为酒池,足以铉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是刘向对战国史料的汇编,体现的是先秦一部分人的立场和态度。《竹书纪年》云“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又云:“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7]32。《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亦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琼室、玉门”。两书所列先秦资料,似为《新序》所本。
然则,从何时起末喜才被与有夏灭亡联系起来了呢?前举《国语》已将末喜与夏亡连书,但并未肯定她与国运有关。较早地把末喜将有夏国政败坏联系起来的,是荀子。《萄子·解蔽》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荀子认为,夏桀、殷纣为末喜和妲己所“蔽”,她们要为夏商之亡负责任。这肯定不是荀子的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一个学术派别的性别立场。
同样在刘向《新序》中,其《杂事一》亦曰:“禹之兴也,以涂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汤之兴也,以有莘;纣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此段虽记述与史汉相近,但思路却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从外戚和婚姻的角度上讲述这段历史,而是将夏、商和西周的灭亡归结于三位女性,从此,这种观点在汉代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一种历史观。成书于东汉的《吴越春秋》在述及吴王夫差接纳西施时,称遭到伍子胥的反对,伍子胥认为,“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差不听,结果亡国⑤。汉晋以后,此种历史观遂成为中国正统的历史观,一直延续近两千年。然而,汉代之后,对末喜的史事附会仍没有停止,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即云:“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8]26至于《宋书·乐志三》:“末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更明言良臣关龙逢为末喜所杀,这则是其中的极致了;当然末喜形象的建构此时基本上也处于末流,之后,关于末喜本身再没有新的史事增益,因为南北朝以后,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已初步成型,无需末喜等人的历史形象为其做注脚。
那么,末喜到底与夏亡有无关系呢?虽史料不足征,但仍有踪迹可寻。《韩非子·说难》曰:“是以桀索缗山之女……而天下离。”具体何故,却并未明言。而《吕氏春秋·慎大览》则载:“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商汤“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
这一记载表明,虽夏桀迷恋于女色以致政治败坏,然而在伊尹被商汤派遣入夏以后,末喜却与伊尹合作,起了指路人的作用。正是如此,遂有末喜为商汤间谍一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本《孙子·用间篇》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而《国语》亦曰“与伊尹比而亡夏”,似可以坐实此说。但末喜为何要与伊尹联手呢?《吕氏春秋·慎大览》提到夏桀“好彼琬、琰”。琬、琰为何?《竹书纪年》云:“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7]29此亦见于屈原之《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嬉何肆,汤何殛焉”。原来,琬、琰是另外两个美女,末喜应该是出于嫉妒,才与伊尹联合,助商汤灭夏的。这么说,按这一史料体系提供的线索,夏亡同样与末喜有关,但不能再说美色祸国,而是末喜因失宠而嫉恨才“倒戈”。把嫉妒归于女性的天性,本来就是对女性性格的一种误读;而且这种说法在社会性别理论方面不如“美女祸水论”更有利于支持父权制,所以,此说也许更近于真相,但并未为主流历史观所接纳。
但无论如何,就历史观而言,先秦秦汉对女性是持一种“厌女”的倾向和立场的,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的价值观的基础。比如《诗经·大雅·瞻卬》云:“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刘向《列女传》认为,此诗说的就是末喜乱夏的情形。
二、对妲己和褒姒的史实建构
至于妲己,历史记载则简单得多,基本上是按《史记·殷本纪》的叙述,其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但同样并未明言妲己具体有什么恶行。而早在屈原《楚辞·天问》,则开始给妲己贴上“惑”的标签。其曰:“殷有惑妇何所讥?”汉王逸注曰:“惑妇,妲己也。”前引《荀子·解蔽》则曰:“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意即君主之败政乃是女性“惑”、“蔽”所致。同时,《吕氏春秋·先识》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则已经把妲己推向政治的前台,明言她操持政权,祸国乱世。虽然如此,上述诸篇对妲己之恶行的指责也均非具体。
直到西汉后期,刘向《列女传》才大大加以补充,其曰:“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并把商纣所有的恶政都归结为“妲己乐之”。按《列女传》的说法,纣王造“炮烙之刑”也是为了博妲己一笑;比干之死也是因谏妲己而起。周武王“以亡纣者,是女也”,在伐纣成功以后,遂“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⑥。因此,在刘向看来,商的灭亡完全是因为妲己一人所致,较之《史记》的记载,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性别歧视的影子。刘向的偏见不是从他自己开始的。《尚书·牧誓》提及武王伐纣的檄文,就曾经提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命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云云。《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誓师,“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妇女涉政——尽管可能子虚乌有——竟然成为“革命”的正当理由。汉代人在解释《诗经·小雅·巧言》时,认为“君子信盗,乱世用暴”、“匪其止共,维王之邛”两句,都是民间在讲述妲己亡殷之事。由于西汉儒学地位的提高,《尚书》越来越取得经典的地位,其对妲己的态度和立场必须影响到汉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刘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之下,完成对妲己的史事建构的。妲己于是也成为祸国的典型,也成了统治阶层要吸引的历史经验教训。《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也,(孔)融与太祖(曹操)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此条亦见《后汉书·孔融传》,其云“(孔)融乃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妲己赐周公”之说,仅见于此,似为孔融伪造史实,可能是影射甄氏之事,但很明显,他是把妲己作为不祥和亡国之征来对待的。
同样的遭遇也落到褒姒的头上。在《史记·周本纪》中,褒姒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存在诸多硬伤的传说而已。夏朝的龙涎化为玄鼋,“童妾既龀而遭之”而生褒姒,固已荒诞不经。虽然《史记》所述基本袭自《国语·郑语》,但此记述有悖《史记》一贯撰述风格不言,其硬伤也难使其成为信史。按《史记·周本纪》,“童妾既龀而遭之(龙涎)”在“厉王之末”,龀即换乳牙,当六七岁。而“既笄而孕”,则是说15岁怀孕。如此,褒姒当生于周宣王初年。周宣王在位46年,那么,“当幽王三年,王入后宫而爱之,生子伯服”,其时褒姒至少40岁。幽王年龄几何并不可知,但按常理,一个男性,无论他多大,爱上一个40岁的女性可能性似较小⑦。
另一硬伤则出在褒姒之子伯服身上。据传统记载,幽王本已有太子,即姜后之子宜臼,亦即后来东迁之周平王。从周平王继位的情况看,此时他至少已成年⑧。而据《竹书纪年》,周幽王八年伯服被立为太子,时仅约5岁。在民意汹汹和内忧外患之下,幽王废长立幼,破坏西周宗法制的政治基石嫡长子继承制,是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的⑨,此举殊难理解。
再一硬伤则为广为人知的“烽火戏诸侯”,遭受愚弄的众诸侯不再履行从征的封建义务,这是幽王被杀和西周灭亡的最直接原因。然而,一般认为烽燧制度在秦汉时期才广泛应用于边境,其出现最早不早于战国后期。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中国还没有烽火告警一说⑩。
到底有无褒姒其人?《诗经·大雅·正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诗经·大雅·瞻卬》又曰:“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把西周灭亡的责任都指向了褒姒。因此,褒姒可能确有其人,但至少《史记·周本纪》对她的记载是不成立的(11)。尽管其不成立,太史公仍然没有交代褒姒的恶行。褒姒的恶行,还是出现在刘向《列女传》。
汉代及以后学者在注《诗经》时,也对褒姒之事进行了附会。《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曰:“《十月之交》诗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橜维趣马,维师氏,艳妻煽方处。’……美色曰艳。艳妻,褒姒也……诗人刺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宠而处职位,不以德选也。”另,《汉书·谷永传》“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颜师古注曰:“《诗·小雅·白华》之篇也。幽王惑于褒姒而黜申后,故国人作诗此以刺之。”这些都是在《诗经》对褒姒祸国定调基础上的扩大化。《列女传》记载褒姒,内容与《史记》略同。但是,仍突出了褒姒至政治败坏的作用。其云:“褒姒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又云:“忠谏者诛,唯褒姒之言是从,上下相谀,百姓乖离。”褒姒的形象、行为与前述妲己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先秦秦汉时期,在对末喜、妲己和褒姒祸国的史事建构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特点,即:暴君皆因女宠而沉湎酒色,荒怠政事;因女宠而大兴土木,劳苦百姓;听妇人之言,拒良谏,杀忠臣。每一个朝代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涌现很多的问题,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痼疾,如果这个政权不能进行自我调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一旦有适当的突破口,崩溃之势就不可阻止。以西周为例,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作为政治基础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瓦解,使得西周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内忧未平,外患又不止,同四周少数民族的战争,已经给西周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幽王时期,西周在对外战争中接连遭到失败,这同时也让它在诸侯面前丧失了权威。恰在此时,王位继承出现问题,成为压断西周政权的最后一棵稻草。褒姒不过是在这一系列政治危机背景下被突出了出来而已,成为政权崩溃的替罪羊,其根本原因在于女性被当成政治的祸乱之源。
三、“厌女症”与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建构
“厌女症”(misogyny),又称“仇女症”、“厌女主义”和女性贬抑,是指一种对女性的仇恨或强烈偏见,它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女性身上;而且,作为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的体现,它又把对女性的“物化”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9];然后再通过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12),维持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并使之合理化,从而建立起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广义的范畴里,“厌女症”包括了“憎恶女人”的所有形式,比如有关性的、对母亲的恐惧、政治的、结构性的、美学的和道德的,等等[10]229-232。
对末喜、妲己和褒姒祸国的史事建构,就是“厌女症”在政治和历史观上的体现。由于先秦秦汉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使厌女症成为中国传统性别制度和文化的重要特征。从这些历史的建构中,在社会性别制度方面,除了宣扬女性乃祸害之源、不祥之兆,主要树立的是女性处于卑弱地位的观念。西周时代奠定了男公外、女私内和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这一直是传统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的主流和经典模式,体现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上,即一夫多妇和主夫属妇,体现在家族关系上则是女性不确定的从属关系[11]99-128;而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女性不能涉政的政治禁忌。
在制度创设的同时,自周代起,就在思想和价值系统上对女性在社会、政治中的身份限定作出了理论性的阐释。孔子的思想中有明显的重德抑色的倾向,他贬低女性的地位,并把女性与小人并列,极端不赞成女性涉政,这已为学界共知[12]23-27。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荀子,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荀子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女色会导致亡国的思想家[1]38。《荀子·女乐》曰:“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把女色与男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荀子认为,女色足以败坏政治,足以令国家衰亡,“桀蔽于末喜、斯观……纣蔽于妲己、飞廉……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对此前已出现的“女祸论”进行了理论论证。
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易传》对女性卑下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易·坤卦·文言》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而《易·家人·彖》亦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由于《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的性别哲学深刻嵌入到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性别对立被当成是将事物分成二元对立面的普遍趋势的根源,而且这是“自然的”,合乎“天理”的[12]119。
同时,儒家经典《礼记》又专门规定了女性的行为准则。《礼记·昏义》提倡女子出嫁前三月,就要“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礼记·内则》则更加明细地规定了女性在家和出嫁后的行为要求,严格要求男女两性的内外隔离,其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出嫁到夫家,要使自己在家族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行同于奴隶。“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舅姑若使介妇,毋敢敌耦于冢妇,不敢并行,不敢并命,不敢并坐。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自《易传》至《礼记》,规定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生存秩序”,强化了女性“主内”的社会观念。中国儒学社会形成以后,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就成为一种性别的社会规范,长期以来,维系着妇女名分和两性隔离的社会性别制度[13]289。
在先秦思想的基础上,汉代董仲舒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论证了男主女从的“合法”观念,集中体现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其《循天之道》曰:“男女之法,法阴与阳”;《阳尊阴卑》曰:“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天辨在人》则曰:“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就为人间的夫妇主从关系找到天理的依据,天使之弱下,天的秩序,无可违抗,是一种“自然秩序”。所以,《春秋繁露·基义》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政治制度必须依从于天意和天所规定的秩序,董仲舒为把男尊女卑纳入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中奠定了基础。
而到了汉代儒学价值观的集大成者《白虎通义》,就全面形成了“三从四德”的社会性别理论,使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建构最终完成。《白虎通·三纲六纪》曰:“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又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爵》曰:“妇人……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五行》曰:“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自此,传统的纲常理论对女性卑下地位的规定成为不可改易的社会律条和基本道德准则。
除了制度和文化上的理论建构,汉代社会也开始了对女性人身的“驯化”,把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的价值观在社会中进行传播、灌输,其中最典型的即刘向《列女传》。刘向辑录古代女性的盛德懿行,表章“母仪”、“女范”,为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女性提供学习的榜样。该书通篇贯彻的即是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社会性别理念,认为“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14]39;“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14]123。
如果说《列女传》是男性对女性的服从要求,而班昭《女诫》却是女性对女性自身的“驯服”化。《女诫》共七章,分别是《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和叔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礼记》已经提出“妇德”理念,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女性的“卑弱”,而且要求女性自己维系这个“卑弱”地位。这是女性对男性提出的社会规范亦即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理论的内化,使女性放弃了对自己个性的追求而曲从于男性。
也正是汉代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把末喜、妲己和褒姒三人列为下等,不仅是因为她们“祸国”,还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如果不服从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安排,就会受到各种的规训和惩罚,虽被视为“妖孽”亦可。《列女传》总结出末喜祸国的一大特征,即是她“丈夫心,佩剑带冠”。末喜本系女性,竟然“僭越”到男性的领域,不仅有男性的思想,还穿戴如男人,这已经打破了天地、阴阳的秩序,是不祥之兆。《晋书·五行志上》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若内外不殊第,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随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正是此理念的现实化。不独于此,《宋书·五行志一》亦曰:“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这都是从历史方面为此理论提供论证,从而也成为为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传统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的产生、定型和衍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社会模式变迁的原因,有生产方式转换的原因,也有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但不能否认当时知识界对这种社会性别制度进行的理论建构,除了从哲学上进行思想的合理性阐发和论证之外,也从历史上寻找事例做具体注脚,以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彰显现行社会性别制度的合法性。先秦秦汉时代对末喜、妲己和褒姒史事的历史建构,正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收稿日期:2012-01-20
注释:
①本文不使用“干政”,是因为干政在传统的表述中隐含有贬义;也不使用“参政”一词,是因为参政的概念过于现代,对女性而言,女性参政在古代并没有出现过。
②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他举例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他认为,“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③但在本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则注引《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查今本《淮南子》,并无此句。该句与《刘向列女传》所述相近。
④其实也未必尽然,《论语·子张篇》孔子弟子子贡就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不是刻意为夏桀翻案,而是道出了一种历史观而已。
⑤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此记载亦见于《越绝书·内经九术》,内容大致相同。
⑥此亦见于《逸周书·克殷》:“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
⑦晁福林认为幽王为太子时既已娶褒姒,但也只是一种推理,缺乏史料支撑,见氏著《论平王东迁》,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4页。
⑧宜臼出走申国,申侯等曾拥立其为王,因此西周末年,曾出现“二王并立”,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见晁福林:《论平王东迁》,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⑨当然,幽王利令智昏,更立一个婴儿为太子也不是不可能。但据晁福林先生的研究,伯服此时应该也已成年。他认为伯服长于宜臼,且伯服为长子,见《论平王东迁》,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3-14页。此是《史记》矛盾之处。
⑩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8页;另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3页。按《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则不是烽火而击鼓。其云:“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於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後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史记》亦有“幽王为烽燧大鼓”之句,但击鼓征调诸侯勤王一说似更不可行,因此亦不可信。
(11)崔述《丰镐考信录》亦从关中形势的角度否定相关史事。
(12)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天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标签:社会性别论文; 史记论文; 褒姒论文; 妲己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国语论文; 列女传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淮南子论文; 竹书纪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