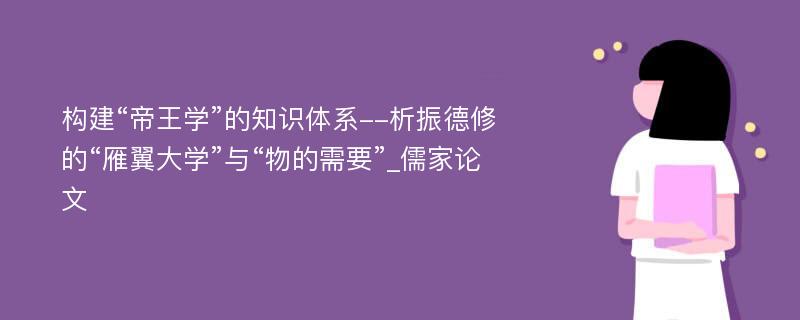
建构“帝王之学”的知识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物致知论文,帝王论文,之学论文,体系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向被称为“帝王之学”。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中说:“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其实,历史上被称为“帝王之学”的,不只是《大学衍义》,如唐太宗所撰的《帝范》、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范祖禹所撰的《帝学》等也属于“帝王之学”。《大学衍义》一书同其它讲“帝王之学”的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在我们看来,《大学衍义》一书讲“帝王之学”更具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大学衍义》是以《大学》“八条目”中的“六条目”为理论框架的。其六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六条目本身有一个递进的逻辑次序。而历史上有关“帝王之学”的内容,便可以分类放进这些条目之下。而以往属于“帝王之学”的书,如《帝范》、《贞观政要》、《帝学》的内容,因为缺少这样一个逻辑架构,许多内容的排列给人以平列而松散的印象,而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不只如此,自二程以后,学界关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讨论,层层展开,深入底里,扶而使得《大学衍义》有关“格物致知”的讨论变得深刻起来。 但是,《大学衍义》毕竟不是一部纯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经验性、实用性很强的著作,且它是专门为当时帝王“量身定做”的一部专书。所以,如何从大量史料中遴选出适合的材料,将其纳入到《大学》“格物”、“致知”等条目的框架中,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五为“格物致知之要”,作者解释说:“人君之学,必知其要,然后有以为用力之地。盖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 这里,真德秀没有刻意讨论什么是“格物”,什么是“致知”,因为要讨论这类问题,便会陷入无休止的理论纠葛之中,而是将“格物”、“致知”并作一项说。虽然他没有刻意讨论,但他还是对“格物”、“致知”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中说:“大学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开明其心术,使既有以识夫善恶之所在。”将“格物致知”落实在“识夫善恶之所在”上。这个倾向性的看法并不是真德秀的独创,而是建立在朱熹的四书学之上。朱熹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朱熹《四书或问》卷一)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建立在“事物”上的一种学习。这个“事物”,可以是历史的经验,也可以是自身的历练。那么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所要学习的首先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真德秀将其具体分为四件事: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认为这是“格物致知之要”,而关于这四件事,每件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和类项。这些便构成了统治者必须学习的知识。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首要的任务必须学习。而学习的具体内容,已经是设计、规定好了的。真德秀由此而扮演了“帝王之师”的角色。 那么,真德秀设计和规定了哪些帝王所必须学习的知识呢? 一、明道术 真德秀所说的“道术”颇有“务虚”的味道,这实际是告诉统治者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度,应该用什么“道术”来统治和治理国家。而所谓“道术”是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它实际包含今人所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内容在其中。当时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传统儒家看来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而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这在传统儒家看来也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所谓“明道术”就是要明确地认识和坚守这些基本原则。但是这样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几句口号,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思想体系: (一)要懂得和认同“天理人心之善” 真德秀要人君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即世上存在一种原始的、根本的善的力量,人君的首要职责就是开发、扶持这种善的力量。这种原始的、根本的善的力量,就是“天理人心之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真德秀援引儒家经典作为理论根据。首先他援引成汤之语:“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尚书·商书·汤诰》)所谓“上帝”即指“天”而言。“衷”即是“中”,“自天所降而言,则谓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则谓之‘性’,非有二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谓‘顺’。若其本恶,而强教以善,则是‘逆’之而非‘顺’之也。”(《大学衍义》卷五,下文凡引此书,只注明卷数)在真德秀看来,后世孔子、孟子之所以能阐发“性善之理”,而“开万世性学之源”,皆导源于成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的话。真德秀同时认为子思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就是成汤的所谓“降衷”。 真德秀又引《易传》之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依他的理解,道与阴阳的关系,就是理与气的关系。“理之与气,未尝相离,继继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则曰性焉。理无不善,性岂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虽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实出乎此。”天命与性的关系、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学的基本问题。真德秀将其作为“人君致知之首”,这是为什么呢?真德秀回答说:“人君之于道,所当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盖不知己性之善,则无以知己之可为尧舜;不知人性之善,则无以知人之可为尧舜。”(卷五)在真德秀看来,只有承认人性本善,人君才能尊任“德教”。反之,如果像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流行于社会,便会有“严法峻刑毒天下”,人君不可不慎也。 (二)要懂得什么是“天理人伦之正” 真德秀所谓“天理人伦之正”,即是指“三纲五常”。他论“五常”引孟子之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然后指出此五者“皆人性所自有……经传论人伦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尽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呜呼,旨哉!”(卷六)他认为孟子对“五常”之道的概括,高度凝练,得天理人伦之要旨。 真德秀论“三纲”引班固之言:“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班固《白虎通义》卷下《三纲六纪》)然后评论说:“三纲之名,始见于此,非汉儒之言,古之遗言也。……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由古至今,未有三纲正于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纲紊于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计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卷六)依真德秀的意见,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牢牢抓住“三纲五常”这个法宝。 真德秀还通过一些细目进一步论述“天理人伦之正”,这些细目包括:通言人子之孝;帝王事亲之孝;长幼之序;夫妇之别;君使臣之礼;臣事君之忠等等,兹不赘述。 (三)要弄清“吾道源流之正” 真德秀这里所谓的“道”乃是儒家所谓的“中道”。他所谓的“源流”,就是程朱理学的所谓“道统”。他引《论语·尧曰》篇,认为尧传给舜的“统治秘诀”是“允执其中”,舜传给禹的“统治秘诀”也是“允执其中”,这就是后世所谓的“道统”。所以真德秀说:“其体则极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则酌时措之宜,是名‘时中’。圣贤传授道统,此其首见于经者。”(卷十一)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尧、舜、禹之“道统”,一脉相传而至孔子,所以上引《论语》才载有那段话。孔子又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为之专作《中庸》一篇。此篇为二程和朱熹所特别看重。程颐说:“‘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如初寒时,则薄裘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则非中。”(《二程遗书》卷十七)真德秀评论说:“程颐之论‘时中’,至矣!……此人君抚世应物之大权,然必以‘致知’为本,惟圣明深体焉。”(卷十一)就是说,人君通过“格物致知”的手段,掌握万事万物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抚世应物”处置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中”。简言之,所谓“中”就是处理事物恰到好处。 (四)要弄清“异端学术之差” “异端”一词,首见于《论语》。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真德秀诠释说:“‘异端’之名,始见于此。谓其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也。”这里所谓的“攻”,是攻读的意思,不是攻击的意思。孔子认为,学者攻读“异端之学”是有害的。孔子为诸子百家之首,孔子所说的“异端”,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呢?按照真德秀的说法,老聃、杨朱、墨翟,皆与孔子同时。以今日观点看,此观点或值得商榷。不过,孔子应该不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少正卯之流也未可知。但真德秀所要讨论的不是“异端”一词的提出及其历史背景,而是要告诉人君都有哪些学术属于“异端之学”而预加防范。真德秀提出: 1.认清杨朱、墨翟学术之弊害。墨翟主张“兼爱”,将自己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同等看待,杨朱主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儒家孟子批判墨翟“兼爱”是“无父”,杨朱“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2.认清法家之学、纵横家之学之弊害。法家倡导“刑名之学”,以苛法治国,杀人无数,刻薄少恩。而纵横家之学逞口舌之辩,纵横捭阖,倾乱人国。二家之学皆非正道。 3.认清道家老聃、庄周之学之弊害。老子讲“慈”、“俭”等为近理之言,其“无为而治”思想对汉初休养生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学以事物为糟粕,以空虚为妙用,庄周因之,为后世清谈家所仿效,乃至误人家国。 4.认清神仙之说之弊害。神仙之说,谓人服食长生不死之药,可以成为神仙。秦始皇、汉武帝皆一世英杰,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药,虚耗国力,而一无所得。当以为戒。 5.认清不可以佛教治中国。汉代,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学大抵以空为宗,以为人死精神不灭,轮回转生,其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梁武帝三次舍身事佛,以致国事日非。其后侯景作乱,梁武帝竟被逼饿死台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此一大历史教训。 二、辨人材 帝王之学的主旨在治理天下国家,君主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需要选拔、委任众多官吏一同来治理天下,而所选拔的人才或忠或奸、或贤或愚,则关系国家的政治的清明与否。所以真德秀将“辨人材”作为帝王之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个道理,其实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虽然古今时代不同,但其道理是相通的。那么,真德秀所说的“辨人材”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一)学习圣贤观人之法 在真德秀看来,人才的选拔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良臣辅政,其国必兴;奸邪用事,其国必衰。作为君主,军国大事虽有许多,但识人、用人则是人君的重要权柄,只有恰当地用好这个权柄,方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选拔人材的前提在能识别人材,这里有一个“君子小人之辨”的问题。那么,究竟怎样分辨君子和小人呢?真德秀提出,看人首先应该看其道德如何,其次再看他的才能。如果一个人很有才能,但在道德上有缺陷,那这个人便不堪大用。他说:“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古之论人者必贵于有德。后世人主或以才能取人,而不稽诸德行,故有才无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败事者几希!”(卷十五) 真德秀进一步提出识别人材的基本方法如下: 1.知德必观其行。“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见之事,则德为虚言矣。”(卷十五)一个人是否有德,主要不在于他一时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在长期的行事中如何表现。从其待人处事的长期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是真有德还是假有德。 2.德无偏颇之弊。“德”通过性格来体现。如果一个人性格刚躁,即使有德,也可能做错事。反之,一个人性格柔懦,即使有德,也做不成大事。所以真正有德者在性格上要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这就是所谓“成德”,“成与否,而人材之优劣判矣。”(同上) 3.行德当持之以恒。有德者贵乎守常,“有常者为君子,不能常者为小人。”(同上)一个人若只一时行德,而不能持久,也不足以言德。这个道理拿到现代来讲也是对的,正像毛主席所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4.观察行善动机。一个人行善之时,要观察他做这件事是出于道义之心,还是出于谋利之心,“若其本心实主于义,则其善出于诚,可以为善矣。若其本心实主于利,则其善也非出于诚,安得为善乎?”(同上) 5.正确看待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有可能犯过错误,不能因为他有过什么过错,便将他全盘否定。不能只看错误本身,还要看犯错的原因。如某人因爱民而违命,其用心为仁,那么可以取其仁而略其过。 (二)了解古代帝王知人用人之事迹 真德秀指出,掌握知人的原则和方法固然很重要,而知人者的主观因素也很重要。所以他特设“帝王知人之事”之目,以史为鉴,总结历代帝王知人用人的经验和教训。 1.勤勉政事,了解群臣。真德秀认为,人主只有自己亲身参与政务处理的实践之中,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能有知人的智慧。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援引了汉高祖知人的故事:汉高祖临终之时,吕后问他:“萧相国死后,谁可代替他?”高祖说:“曹参可以。”吕后又问其次,高祖说:“王陵可以,但他愚而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单独难以担当大任。周勃厚重少文,然而安刘氏者必是周勃,可令其为太尉。”高祖的知人之明在他去世后一一得到了应验,所以后世史家以“知人善任”誉之。汉高祖知人为何如此精准呢?真德秀概括说:“帝之性既明达,而又更事履变之久,至于群臣之才行皆尝斟酌而剂量之,故所以为后人计者几无遗策。”(卷十六)在他看来,汉高祖知人有其天性“明达”的因素,加上他“更尝之多”,即实践经验丰富,并亲自处理实际政务,洞晓事情之利害,每日接触群臣,观察其才能特点。有了这种种因素,才能做到“知人善任”。这也是汉高祖在历代帝王之中的过人之处。 2.度量阔大,不怀私念。真德秀认为,关于知人之事,帝王本人若胸怀宽广,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就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若气量狭小,出以私心,感情用事,就会得出不切实际的判断。真德秀举西汉周亚夫为例:汉文帝时,周亚夫为将,严于治军。汉文帝到细柳营地劳军,见周亚夫“持军之严,虽人主无所屈”,遂赞他“真将军也”,委以重任,并告诫太子说,如有大事,周亚夫可以任将。汉景帝时,起用周亚夫为丞相,景帝认为他好直谏傲上,“非少主臣”,因而疏远他,最后让他屈死狱中。对同一个人为什么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呢?故真德秀评论道:“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为忤,景帝专以适己为悦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贤否,其必自去私意始。”(卷十六) 3.思想端正,谄利不动。汉武帝末,霍光、上官桀、桑弘羊等受诏辅佐少主。其后,上官桀、桑弘羊等为泄私愤,以重罪诬陷霍光。幸亏昭帝明辨是非,才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对此真德秀评论道:“武帝托孤于霍光,善矣。而又参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于高帝也。”武帝为何让上官桀、桑弘羊参与托孤呢?真德秀解释道:“桀以谄进,弘羊以利合故也。”故他告诫人君:“必先正其心,不为谄惑,不为利动,然后可以辨群臣之邪正矣。”(卷十六) (三)了解奸雄窃国之术 任何朝代,社会政治的坏乱不关天意,只关人事。政治坏乱往往来自于坏人当道。传统上称这样的坏人叫“奸雄”。这些“奸雄”之所以能窃据高位,多由于最高统治者识人不明,以奸作忠。常言说:“大奸似忠。”奸臣的脸上并没有特殊标记,因此如何分辨忠奸,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德秀总结历史上奸雄窃国之术,就是给帝王提供一种历史的镜鉴。 所谓“奸雄”,即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窃取高位之人。此类人有着极大的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使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谓“窃国”,即暗中篡夺国家政治的领导权。窃不同于抢,抢是公开进行的,是看得见的,被抢者可以防备;窃是暗中进行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奸雄窃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手法隐蔽,人主如果麻痹大意,无形之中便江山易主了。所以真德秀将奸雄窃国者的种种卑劣手段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供帝王防窃之用。真德秀总结奸雄窃国的手法有以下几种: 1.内外勾结。真德秀指出:“自古奸臣欲盗其君之国,非挟宫闱之助,合左右之交,则不能独为。”如夏代寒浞欲篡后羿之位,一方面引诱后羿沉溺于田猎,使之不理朝政;一方面勾结后宫,贿赂朝臣,与之狼狈为奸。寒浞愚弄朝廷上下,为所欲为,最终取代了后羿政权。其实,如果帝王能直接处理朝政,是很容易觉察权臣弄权,内外勾结的。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往往是由于帝王耽于逸乐,不理朝政。所以真德秀借虞、周君臣互相告诫的话说:“无逸游,无耽乐,以此为防。”(卷十七) 2.收买人心。齐景公时,厚敛于民。而田乞为大夫,收税用小斗,出贷用大斗,厚施于民,以收买人心,民心尽归田乞。晏子谏景公,景公不听,坐使田乞威权日重。景公死后,田乞擅行废立之权,国家大政尽在其掌握之中。及至子孙辈,齐国政权遂为田氏所有。真德秀指出,田氏之祸,推原本末,由不能早辨其心。如果景公能纳晏子之谏,及时采取措施,齐政焉为田氏所有? 3.以色为饵。真德秀举吕不韦篡秦为例:吕不韦篡秦使的是美人计。他先结交在赵国为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并用贿赂的手段达到了使子楚为太子的目的,然后选一绝色美女与己同居,使之怀孕,又将此女献与子楚。后来子楚为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死后,其子嬴政为王。秦国政权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落入吕氏后人之手。真德秀举此例的目的,是希望人君知奸臣用智之可畏,谨毋以色而倾其国。 4.饰伪乱真。真德秀举王莽篡汉为例,王莽称得上窃国之术的集大成者。他的窃国,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而最显著的则是饰伪。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事事显出君子的形象,其奸伪足以欺天。真德秀告诫人主,对于像王莽这样的奸臣,防备的方法就是“防其渐”,即在他的窃国之心刚冒头的时候就要能识别和制止,不使其发展,他借鉴《易经·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的思想说:“履霜之不戒,则其渐必至于坚冰”。 (四)了解谗臣、佞臣的罔上之情 所谓“罔上”,就是欺蒙皇帝的意思。真德秀设“愉邪罔上之情”的子目,而愉邪之人包括奸臣、谗臣、佞幸之臣和聚敛之臣。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仅简介其所论谗臣、佞臣的罔上之情。 1.认识谗臣的罔上之情。谗臣,就是背后说人坏话,以达损人利己之目的的臣子。这种人,表面和颜悦色,内里包藏祸心;当面甜言蜜语,背后暗箭伤人。《诗经》把这种人比作“鬼蜮”,鬼蜮害人而不可见,谗臣害人藏形匿迹,两者极为相似。(参见《诗经·小雅·何人斯》)《诗经》又把这种人比作苍蝇,苍蝇尽往污秽的地方飞,嘤嘤嗡嗡叫个不停,逐利而败物;谗臣多与小人勾结,凭借花言巧语,逐利而伤人。(参见《诗经·小雅·青蝇》)谗臣手段如此阴险毒辣,故真德秀指出,“谗人之情志在伤善无有穷已,故家有谗则家乱,国有谗则国乱”;“谗邪之人宜屏之于外,毋在朝廷以伤人”。(卷二十一) 谗臣害人,须欺骗人主,使人主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然后借人主之刀以杀人。所以谗臣害人之阴谋能否得逞,关键在人主。人主若不信谗,谗臣自然不敢进谗;人主若是信谗,谗臣就会大售其奸。 杜绝谗邪的前提是能辨谗,果断去谗。真德秀引《诗经》中的思想说,小人进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试探,如果人主对谗言既不拒绝,又不辨别,就会再进。再进如果又不辨别,就会相信。(参见《诗经·小雅·巧言》)如果“闻谗则怒,闻善而喜,好恶明白,断决不疑则乱为之止矣。故人君杜绝谗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断’”。(卷二十一) 2.认识佞臣的罔上之情。佞幸之臣,指巧言谄媚而受宠之臣。这种人,受宠前专以卑贱的态度和花言巧语讨好人主,以求宠爱。为了求宠,除了生命之外,他们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例如,齐桓公的三个大臣易牙、竖刁和开方:易牙杀子以适君,开方背亲以适君,竖刁白宫以适君。而一旦受宠,他们便放肆其恶,为所欲为。齐桓公死后,易牙与竖刁杀诸大夫,立桓公不想立之子无诡;开方杀孝公之子,而立其不当立之弟潘。几番折腾,使齐国大乱近三十年。齐桓公为何宠爱这三个人呢?真德秀分析:在齐桓公看来,易牙杀子是不私其子,开方背亲是不私其亲,竖刁自宫是不私其身,他们必能忠于自己。殊不知他们这样做并非真情,而是想得到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受宠。所以真德秀感叹道:“前日之适己者,乃所以为贼君之地与?”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德秀警告人主:“齐桓能服劲楚,卒之乱齐者三孺而非楚也。”(卷二十四)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太深刻了!人主能不警醒吗? 三、审治体 所谓“治体”,即治国方略,治国的大政方针,主要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和人民?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主要依靠德教治国呢,还是依靠刑法来治国?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主体而言,显然不能单纯依靠德治或刑治来治理国家,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但其中还是有主辅先后之分的。由此而提出“德刑先后之分”的问题,这是国家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即单从“德治”方面而言,也要加以细分,而不能大而化之笼统地来谈“德治”,比如说,一个社会注重道义,固然是“德治”的内容,而一个社会重视满足人民的利益,显然也属于“德治”的内容。问题是:道义与利益二者之间,也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由此而提出“义利重轻之别”的问题。因此,“审治体”,就必然包括了“德刑先后之分”与“义利重轻之别”这两方面的内容。下面分别论之。 (一)明确德、刑先后之分 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真德秀主张以德政为主为先,以刑法为辅为后。他这种主张首先是以经典为根据,其次是以历史经验来印证。 在经典的根据方面,他以《尚书·舜典》为根据,认为“舜之命官也,先播谷,次敷教,而后及于刑。”在真德秀看来,帝王命官用事,首先要考虑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无衣食之忧、冻馁之虞,就会遵纪守法;如果老百姓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可能铤而走险。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再施行德教,引人向善,民心就会良善,社会风气随之敦厚淳朴。至于使用刑罚,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真德秀又说:“舜之制刑也,特以辅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于无刑。”(卷二十五)舜设置刑法,乃是为了补教化之不足。舜使用刑法,目的是为了最终消除刑罚。 在历史经验方面,周朝以德治国,享国八百余年,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二世而亡。明效大验如此。有人曾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法。真德秀反问,这些人为什么不以周、秦之事来作鉴戒呢?真德秀又以隋文帝和唐太宗作对比:隋文帝时代多盗贼,文帝下令:“贼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偷一瓜,事发即死。”(《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真德秀指出,隋文帝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来惩罚盗贼,终不能使盗贼减少。唐太宗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无忧,数年之间,外户不闭,路不拾遗,隋朝存在不到四十年,而唐朝国祚达三百余年。其失、其得也可以作为鉴戒。 所以,真德秀赞赏董仲舒的政治理念,并借以阐释德、刑二者的关系,他说:“仲舒以《春秋》之学,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谓善矣!”(卷二十五) (二)明确义、利重轻之别 “重义轻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重义或重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晦庵集》卷二十四《与延平李先生书》)朱熹之所以将义利关系作为儒学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它是社会人人时时面对的问题。“义”是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利”是维持和增进人们生活的物质资财。那么,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义利关系呢?思想家们曾经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张岱年先生总结说:“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共分三派。孔子、孟子、朱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与利为一。荀子、董子、张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在历史上,此三派中,以第一派势力最大。”(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张先生所言甚是。这里,我们不拟对之详加讨论,只是要指出,真德秀的观点属于第一派。他在“义利重轻之别”的题目下,首引孟子见梁惠王“王何必曰利”的一段话并对它大加肯定:“为国者当躬行仁义于上,而不可以利为心。”为什么对“利”要如此防范呢?他认为如果在社会上鼓吹“利益至上”,只要“利端一开,君臣、父子、兄弟将惟利是趋,《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见利而动。”(卷二十六) 荀子在义利观上有兼重义利的倾向,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篇》)真德秀反对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的观点,他认为人性中只有“义”,“利”是“物我角立”的产物,是后起的。“夫利者人心之蟊贼,不可有也,圣贤之教学者,必使尽去此心,而后可与为善。其化民必使尽革此心,而后可与为治。”(卷二十六)他指出,荀子持“性恶”论,才有这样的观点。 真德秀告诫帝王,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作为人君,当倡导仁义,奉行仁义,不谋私利。历史上也有一些重义轻利的明君,唐太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真德秀讲述了关于唐太宗这样一件事: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宣、饶二州在大量开采银矿石,皇上若派人去收税,一年可以得到数百万两银子。而唐太宗却说:“我贵为天子,所缺少的不是钱财,而是可以利民的好言论。与其多得到数百万两银子,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贤才。你未举荐一个贤才,也未罢免一个不肖小人,却专说收税牟利的话!”(吴兢《贞观政要》论贪鄙第二十六)当天就黜退了权万纪。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讲述此事,就是要为国君树立一个榜样,希望国君能像唐太宗一样,成为“重义轻利”的明君。 四、察民情 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据有一国,或据有天下,其实质在于据有其土地以及居住在此土地上的人民。土地没有情感和意志,而人民是有情感和意志的。古人将实施统治视为“临民”,这里便有一个君与民的关系问题。《荀子·哀公》篇引述孔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最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君与民的关系。得民心则得天下,民心是执政者合法性的基础。所以,真德秀将“察民情”作为帝王之学“格物致知之要”的重要内容。而要“察民情”,就要把民心向背问题当作重要课题来探讨。 (一)懂得人心向背之由 执政者高高在上,凭什么具有各种权力和权威,对人民发号施令,要人民服从你的统治呢?如果执政者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还能保有那些权力和权威吗?这就提出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而人心无论是向是背,总是有其道理,有其理由的。总结历史规律,探讨“生灵向背之由”,便是统治者所应必修的功课。真德秀是怎么论述的呢? 真德秀首先引古人言:“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尚书·周书·泰誓》)意思是说,抚养、爱护我的就是我的国君,残害、虐待我的就是我的仇敌。这是民本主义思想观念下的“君王观”。这种“君王观”不是由君主们自己来定义的,而是由人民来定义的。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可以套改这句话说:“人民是君王的尺度。”就是说,君王的长短好坏是要人民来衡量的。人君如果有这种意识,自然就会尊重人民。 真德秀又引古人之语说:“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尚书·周书·康诰》)意思是说,由民心向背可以见天命所在,小民单个看虽然地位很低,但整体看却代表了天命。而且小民的心是很容易变的。如果他们对君王由失望到绝望,那此君王将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君王要好自为之,远离逸乐游豫,致力于治国安邦、抚恤人民之事,人民才会拥戴你。 真德秀又引孟子之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只有与民同休共戚,才能得到民心,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有自己的地位。晁错说:“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晁错《贤良对策》,见《汉书》卷四十九)真德秀对晁错这番话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如下数条,作为民心向背的根由,使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这数条是:一、“不穷兵,不黩武,所以全其生也。”二、“不急征,不横敛,所以厚其财也。”三、“不为苛扰之政,所以安其居也。”四、“不兴长久之役,所以养其力也。”(卷二十七)人君能做好这几条,则在争取民心上稳操胜券矣。 (二)清楚田里休戚之实 实行“仁政”、“王道”,是儒者千百年来的政治理念。真德秀同样保持这样的政治理念。但在专制君主“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如何让人君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政治理念呢?在历史上,创业之君主往往起自民间,知道民间疾苦,以及创业之艰难。后世继体之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呵护有加,全不知民间饥寒与困苦。作为“帝王之师”,有责任让人君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当时的体制,不可能让人君亲自到社会底层“访贫问苦”,于是这些帝师们便想尽办法,让人君知道这一点。所以,真德秀于《大学衍义》的“格物致知之要”四个基本问题中,特设“察民情”一项,作为“帝王之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科目。真德秀是怎样让人君知道底层人民的疾苦的呢?最主要的途径还是经典的学习,特别是通过学习《诗经》来潜移默化地来诱导人君。 真德秀引《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小雅·采薇》)然后评论说:“此商之末造,纣为无道,夷狄交侵,文王时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戌役以卫中国,非可已而弗已也。……采薇,采薇,以薇为遣戍之期也。”此诗相传为文王所作,文王作为仁者,体谅戍边者之辛劳悲苦,“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文王乃先其未发,歌咏以劳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卷二十七)按照儒者的解释,这是先王“以人道使人”的范例,不像后世统治者那样,把底层人民当作牛马来奴役。 真德秀引《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经·豳风·七月》)然后引朱熹之语评论说:“周家以农事开国,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惧其未知稼穑之艰难也,故作此诗,使瞽矇歌之宫中,庶几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宁。”(卷二十七)此诗相传为周公所作。当初,周公辅佐成王,充当师傅之任,怕成王不知“稼穑之艰难”,通过《七月》一诗来描写农夫一年各节气的辛苦,并谱以曲调,让乐师歌于宫廷之中,可见周公之良苦用心。 真德秀不仅援引《诗经》,也引用历史上反映农民疾苦的诗作。真德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时,后唐明宗曾问宰相冯道说:“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冯道回答:“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后唐明宗听此言后,命左右写录此诗,时常吟诵。真德秀接着评论说:“唐明宗,五季之君,而俭约爱民……因冯道之对诵夷中之诗,恻然若有所感,然未闻当时有所施行,则亦徒言而已尔。”(卷二十七)孟子曰:“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圣之君可不念哉!”(《孟子·离娄》)真德秀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不仅要有仁民爱民之心,关键还在于要能落实于政治实践,制定出体恤底层人民的政策出来。以上真德秀从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个方面阐述了“人君格物致知之要”,由此勾勒出帝王之学知识体系的大致轮廓。自古以来,虽然有所谓“人君南面之术”或“帝王之学”的说法,但从未有人讲出“人君南面之术”或“帝王之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其知识体系应该是怎样的。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第一次涉及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以后偶或有学者对此问题有所补充或修正,但真德秀建构“帝王之学”知识体系的首创性,是应该给予积极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