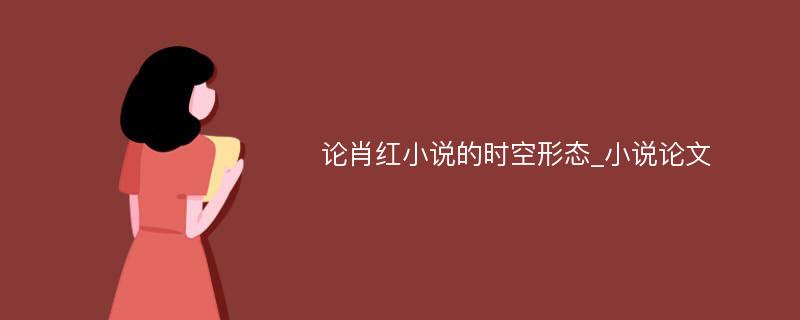
简论萧红小说的时空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时空论文,小说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义称萧红的小说是“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1] (P.570)萧红作品的魅力不仅仅来自内容,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叙述形式。而她的小说恰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闲散的结构、稚拙的叙述都构成了独特的“萧红体”,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莱辛在《拉奥孔》中曾说:“时间上的先后承继属于诗人的领域”,“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2] (P.46)恰巧,萧红可以说是集诗人与画家于一体,甚或她更偏重于画家。萧红小说结构的散漫、零碎化、片断化是和其小说中特殊的时空处理相联系的。萧红小说中的散点透视终止了时间的延续性,把一幅幅散漫独立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空间结构摒弃了时间结构,从而形成了小说结构的散化。
一、时空与作品结构、主题
时间与空间是构成一部小说的主要因素,而决定了小说结构最根本的依据只能是时间和空间。巴赫金在《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中指出:研究长篇小说的时空关系在于它们的情节意义,造型意义——小说的全部抽象因素;哲学和社会概括、思想、因果分析等,趋向时空关系并获得丰满血肉,获得艺术形象性。[3] (P.275)传统小说往往是情节结构模式占统治地位,时间大都沿“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空间变化随人物位移、情节推进而更进,呈顺序性时空结构特点。这类小说线索分明,人物鲜明,故事性强,容易吸引读者阅读。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缺乏时间的间断性,且利用因果必然律取舍材料,常常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传统情节小说的局限性与传统的时空观以及时空处理是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译介使得近现代作家对传统章回小说进行了突破,时空艺术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变化。1903年,周桂笙在《毒蛇圈·译者语》中指出,西方小说与中国小说时空结构不同。与此同时,一批小说家开始探索新的时空建构方式,如徐卓禾《入场券》、《卖路钱》(1907)、吴趼人《平步青云》、《查功课》(1907)。他们改变传统直线型静态叙述模式以事件推移为主,以“时间一致”为原则,改变情节发展的自然流程。而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则采用了全新的时空结构,突破了传统情节小说的框架,淡化情节,以“狂人”心态来安排时空。萧红在谈到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时就认为:“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像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4] (P.2)萧红的小说则是在其导师的引导下走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萧红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风就曾批评《生死场》:“对于题材的组织力度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5] (P.147)萧红的小说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形象,小说的情节主要由叙述者所感受的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段组合,时常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时间断裂,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多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出现,每一个场景都可以独立成篇,形成并置的状态,这与萧红对于时空的独特处理是密切相关的。
二、个体时间与生存的状态
传统艺术认为,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传统小说多是依照线性时间的发展来组织故事情节,而萧红则常会忽略叙事时间的连续性,终止具体时间的流动,造成时间的中断与碎片化。葛浩文认为:“由于萧红的作品没有时间性,所以她的作品也就产生了‘持久力’和‘亲切感’。”[6] (P.184)
《生死场》叙事时间跨度在十年以上,作者却只写了大约一年半的六个季节的更替,这里似乎有着一个连续的时间线索,但实际上这里的六个季节完全是不相关的,它们依附于具体的场景方式独立存在。《呼兰河传》表现得更为明显,小说的第一章完全是概述,各章节之间完全不存在时间的连续性,时间在这里已不存在组织文章结构的功能而变成一个个碎片。时间的碎片化又是与瞬间的强化相关联的,作者将一个个瞬间拉长凸显,让时间以碎片的方式呈现在时间长河的瞬间里,人物的生死苦痛得以放大,令人触目惊心。《生死场》十年更替,作者以一年半的时间来表现,而这一年半中又分为几个时令,作者在时间刻度上通过截取一个又一个瞬间进行放大,用放大镜来张显瞬间的意义。
这种时间的断裂造成了小说结构的不连贯性,“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5] (P.147)人们常认为《生死场》的中心是人民的抗日,但以传统思维却不能理解为何后七章与前十章造成了明显的情节上的断裂。其实,小说后七章的抗日情节只不过是萧红时间刻度上一个被截取放大的图像,它与前面各章应是并列的,只不过从内容上讲它是人生苦痛的一个应激状态,战争将人生的苦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的愚昧与挣扎也达到了顶峰。用抗日的主题来套《生死场》是偏颇的,萧红更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萧红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普泛性的愚昧而苦痛的生活,这里有女人的生殖痛苦;有小团圆媳妇被受折磨却无力发声的无奈;有冯二成子追求爱情而不得,不得不回到自己孤独而丧失意识的生活中去的悲凉……等等。
萧红的作品回忆色彩浓郁,萧红许多篇小说都是以童年视角进行叙述的,回忆对于萧红来说,首先是小说叙事技巧和形式,同时也与萧红对时间的感受有关。回忆的形式也给故事带来了时间的模糊与空间清晰的特点。这些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但具体的时间却是模糊不清的。霍布斯认为:“(回忆)是找出一个固定而局限的时间和地点来寻找,然后他的思想便从这儿起,循着上面那些时间和地点追寻,以便找出动作或其他情况可能使他丢掉了这件东西。”[7] (P.15)回忆是一个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双维度进行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心有一个时间差的存在,即“固定而局限”的时间和被追寻的时间的时间差。萧红这里分别是小说文本的叙事时间和小说文本的故事发生时间。《呼兰河传》现时和往事之间的鸿沟,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剩下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断片,对这些断片的审视,由于距离的生成,时间的淡化,从而超越了利害感,保持着对人和事的静观。
同时,徐岱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故事中的时间如果在向度上属于‘过去’,便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色彩。”[8] 怀旧是用过去某一瞬间来取代现实,对现实的一种挪移。不过在萧红那里“旧”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怀旧范畴所能描述的。萧红那里过去性时间具有一种穿透性,这种过去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现实。同时这种时间也具有一种想象性,是作者对下层历史经验的想象。如《牛车上》,“我”在朦胧之中听五云嫂讲述她丈夫的故事,这里折射出的是兵年、荒年人的苦痛;《家族以外的人》,以“我”的眼写出了有二伯的辛酸苦辣,回忆所造成的时间距离,不仅仅沟通了叙述者与作者,也沟通了萧红与下层民众的体验。因而可以说这种回忆中既往的时间具有想象性、虚拟性的特点。萧红不仅在回忆,也在想象,以寻找一种反映下层民众生命体验的方式,以童年回忆进入叙事,这种方式中作者不是高于人物的,而是平等的,甚至是低于故事中的人物的。这种方式与当时主流所持有的高高在上的启蒙与拯救的姿态是完全不一样。萧红认为:“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至高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4] (P.4)回忆性时间所造成的萧红的观照姿态也正是萧红作品的意义所在。
同时,萧红小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明确的指示性,萧红作品中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泛化的时间,年年如是。萧红的时间是不具体的,“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口了”,“每当我到祖母屋去……”,“一到了冬天,冯歪嘴子差不多天天出去卖一锅黏糕的。”这些叙事中,具体的时间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假定性的时间,时间对事件的发生无关紧要,人物周而复始得重复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呼兰河城的人们年年保持着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亘古不变,呼兰河城的不幸又在遗忘中发生,发生后又遗忘。人们在千百年的传统的思维习惯地支配下生活着。萧红笔下的人生是循环的:“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生死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东边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呼兰河传》)循环的时间里有着宿命的暗示,也暗示着人类的愚昧。时间的循环固化了人生的艰辛,人便在这种永远无法改变的循环中在命运的旋涡中挣扎,这便是萧红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认识与思考,同时这种时间的处理也造成了人的生存状态的普遍性,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方式,只要你生活在这一空间中,你便会依循这样的方式生存下去,永远无法改变。循环的时间里,时间的流逝无法带来事物的发展,一切都是固定的,静态的时间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它根本无力推动叙事的发展。
萧红作品中的社会性时间基本是缺席的。以往评论者总要将萧红与抗日文学、左翼文学相联系,每每在赞叹之余又批评其作品的消极性,不能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反映抗日的时代主流。其实,萧红作品与民族主义的叙述不同,作者摒弃了被强权化的民族大时间,淡化作品的时代性,以自然化的时间为背景,突显了个人的时间。
历史化的大叙事通常都是线性历史,李科尔认为,历史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但由于线性历史本身的困境,杜赞奇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一概念,指出了线性历史所不能涵盖的复线历史下的各种事件与状态。萧红她对时间的理解便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有偏差,她写的不是全民族共有的时间,而是一种寂寞的个体时间,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萧红自身,而且是另一种视野下的大众。
萧红的作品很少有直接描写抗日的,为此她也常常受到诟病。萧红很少正面描写,她对抗日的描写都是从侧面:如《北中国》,作者没有写耿家大少爷是如何离家出走参加抗日,而是写了耿大先生在儿子出走后对儿子的想念、生病以及最后被炭烟熏死;《旷野的呼唤》没有正面描写出陈公公的儿子如何弄翻了日本人的火车,而是写陈公公在儿子失踪后担心焦虑以及儿子被抓后急于救儿子的迫切,以及他在旷野上的奔走与呼喊;《朦胧的期待》写的是李妈在金立上前线前的焦躁与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孩子的演讲》写的是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王根在欢迎演讲时的心理与演讲失败后的害怕……萧红关注的不是抗日的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的真实情感。萧红当年曾极力反对萧军参加抗日义勇军,她认为以萧军的年龄以及他的写作才能实在不值得去战场牺牲自己。[9] (P.8)
到了《呼兰河传》,这更是一个缺乏历史时间的文本,评论者们因为无法再从中找到符合他们的宏大叙事,而将其斥为萧红创作的重大退步。茅盾也不得不说:“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枷锁,在呼兰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0] (P.705)在呼兰河城里,人们所遵循的时间秩序完全是源于季节与生命的兴衰更替。
恰如萧红所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1] (P.343)这或许正是萧红超越那个时代的表现。
三、空间结构与人生隐喻
从小说结构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传统小说偏重时间的连续,现代小说开始更加关注空间的跨越。早期的叙事文学往往偏重时间的连续性,甚至莱辛曾片面地认为,文学要是表现事物的并列,就是对时间艺术的背叛和对空间艺术的侵犯。[12] (P.48)而在萧红的作品中,空间往往超越了时间而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
时间的模糊使得萧红作品的空间结构更为重要,萧红小说基本上是以空间变换来组织小说结构的。她的小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有不断变换的场景,这些独立的场景的并置建构了整部小说,而这些独立的场景都依附于一个作为大背景的空间。
《生死场》的大背景便是一个村庄,故事的镜头按场景来转移:麦场—菜圃—屠场—荒山—坟场—都市—乡村。十年的变迁,作者也是依靠场景的描写来实现的:“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一下子镜头便到了十年之后:“屋顶的麻雀仍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山下有牧童在唱歌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
《呼兰河传》的空间特色更为明显,人们甚至认为这部小说的大背景呼兰河城便是小说的主角,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是对呼兰河城作全景式的描绘。小说在呼兰河城的大背景下又细致描绘了一个属于“我”的小空间,“我”家的后花园;后几章对人物的描写也是以“我”家的院子作为空间背景的。这部小说基本上是以呼兰河城这一空间环境为结构中心来组织全篇。小城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可以说,弱化时间因素而以环境为结构中心来组织全篇是萧红小说的一个特色。
前文已经提到萧红小说中对瞬间的强调,而空间意识小说理论家则认为瞬间不能是真正的时间,而是空间。取消了时间顺序即暂时终止了时间流程而截取了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里,多个线索被置放在一个相对的平面上,场景的转化是要再现空间的存在。
可见,曾经学过绘画的萧红似乎对空间更加敏感,她常以空间塑形来打破时间的连续性。萧红小说由单纯的时间艺术转向对空间的描绘的重视,从单求情节的曲折而寻找奇特的性格转向了在场面的充分展开中让人物去推动情节的发展。普鲁斯特在他的《驳圣·伯夫》一文中谈到盖尔芒特城堡时有一句话:“时间在其中采用了空间的形式,这事实上可以作为小说特点的一种概括:叙事艺术的时间性不在于像音乐那样直接采取时间的形式,恰恰相反,它只能通过突出空间来表达时间。”这一点上,萧红小说具有了某种现代性的意味。
萧红小说的章节不依靠情节,不依靠时间来组织,而是依靠空间上的相对参照来结构,在萧红小说中,对场景的描写显得十分重要。空间在作品中总是被具体化为景物,与人物的活动相结合而构成运动着的场景。萧红对她的场景常常不遗余力地进行描绘,对于空间背景进行细致描写是萧红的一大特色。《呼兰河传》第一章便按方位顺序对小城进行概述式的描写。从十字街到东二道街,再到西二道街,小胡同,逐一进行点的描述。萧红几乎每一篇小说中都有大量的场景描写,甚至在对人物进行描写时,也如场景一样进行转移与连接。《呼兰河传》中写到有二伯,萧红分别各用一节写到:“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有二伯的鞋子,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在《马伯乐》中,对人物的描写也随着人物的辗转而逐步深入。作者的写法与常人不同,她没有去虚构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按照不严格的时空顺序,这里她以镜头追踪的方法,以人物性格表现的需要任意调整结构。
在传统或同时代其他小说中,场景虽然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在这类作品中却是依附时代存在的,都已经时间化了。萧军在《八月的乡村》的重版前言中便直说:“任何一种文艺作品就其性质和职能来说,全属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显示生活的反映或升华,这《八月的乡村》当然也没例外——时代反映而已。”[13] (P.1)而萧红笔下的空间都失去时代特征,静态场景、画面成为具有超越时代的无限性与永恒性的空间存在。萧红小说中多自然环境的描写,很少有社会环境的描写,这与她小说社会性时间的消失也有关系。
对于萧红而言,一种空间就代表一种生活,如后花园、桥。萧红小说多以空间命名,如《生死场》、《清晨的马路上》、《桥》、《马房之夜》、《牛车上》、《山下》、《莲花池》、《北中国》、《小城三月》……空间成为了人的生存的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表达,空间在萧红的世界里往往具有主体性格。
“后花园”在萧红小说中是自由与多彩生活的象征,是童年“我”的天地,而在短篇小说《后花园》中,作者将它与磨倌的磨房形成了对比,并让后花园做了磨倌冯二成的活动背景,后花园像是一个隐喻:“后花园经过了几度繁华,经过了几次凋零,但那大菽茨花它好像世世代代要存在下去的样子,经冬夏为春,年年照样的在园子里边开着。”最后冯二成与时间的挣扎失败,他仍然回到了磨房,也许磨房中的生活也是世世代代无法改变。
《呼兰河传》中萧红用了大量的笔墨渲染了一个“大泥坑”。这个“大泥坑”似乎是整个呼兰河城的隐喻,在呼兰河城的空间里有着种种的不幸,染缸房淹死过人,豆腐房里曾打断了小驴的腿,造纸房饿死过一个私生子……,而这些不幸只是人们闲时的谈资,不久便会被遗忘。《莲花池》中“莲花池”是一个充满敌意,蕴涵危机而又充满诱惑的空间,它既承载了人生幻想,又有拳脚的惊悸。“小豆一天天地望着莲花池。莲花池里的莲花开了,……那不大健康的小豆,从未离开过他的窗口到池边去脚踏实地去看过一次。只让那意想诱惑着他把那莲花池夸大了,相同一个小世界,相同一个小城。”
对于萧红而言,人与空间是密切相关的,人既创造了空间,又受到空间的制约,萧红的空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它与民族的大空间又是有区别的。在萧红的笔下,空间比人物更能传情达意,更能体现人的生存悲剧。
四、开放式结构与小说的散文化
萧红小说时间的弱化,空间场景的切换使得其小说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它使作者能够在自由放纵的创作心理状态下,摒弃情节结构(时间结构),把世界的诸多形态,人生的诸多滋味同时呈现出来,进而传达出一个整合的境界。小说的情节结构,也就是一种时间结构,它往往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推进故事的发展。一般的小说讲究故事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却有意淡化情节,完全摒弃了偶然性、传奇性,也不倚重故事性。时间在萧红小说中没有构成情节的自然程序,没有成为推动情节的活跃因素。萧红的时间意识弱化了情节、弱化了“小说性”,有助于形成某种散文化特征。一个场景,一个片断,一个瞬间的感悟,萧红便抓住这样一个具有空间性质的点作横向的开掘。萧红小说中还随处可见类似散文的“闲笔”。这样使得她的小说失去了一个“中心”而成为了淡化情节、淡化人物的散文化的诗化小说。
早期评论者多认为萧红的作品不能算是小说:“我觉得不能说它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因为,它没有严谨而贯串的小说结构。但它确是一篇优美的抒情诗,它由好多篇可以独立的散文连缀起来的,这些散文表现着呼兰河这个中国北方的小城的实际生活及世态,以及作者童年时代生中所接触到的某些人物。”[14] (P.170)而萧红却不只一次地谈到自己对小说体式的理解:“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4] (P.2)
打碎时间连续性,不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逻辑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风景画、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通过这些片段和场面的细腻描写,从某一侧面去揭示事物的社会意义,表现人物的命运,这种写法在取材和结构上都与散文类似。这种艺术风格使得萧红的小说与散文的界线十分模糊,这可以看作是萧红打破小说与散文界线的一种努力,这或许就是她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小说”中的属于“她”的小说。
萧红小说时间的弱化,空间场景的切换使得其小说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它使作者能够在自由放纵的创作心理状态下,摒弃情节结构(时间结构),把世界的诸多形态,人生的诸多滋味同时呈现出来,进而传达出一个整合的境界。萧红作品的结构方式恰如“桔瓣式”的结构,“是像一个桔子来建构的。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毗邻——莱辛的术语),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15] (P.142)开放式的结构总归会凝聚在意义的茎干上,萧红的小说“不是萝卜,日积月累,长得绿意流泻;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许多相似的瓣组成的桔子,它们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15] (P.142)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16] (P.489)萧红无意于精心组织结构和情节,反而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自然天成,风行水上的韵味。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闲散的结构、稚拙的叙述都构成了独特的“萧红体”,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萧红的小说看似散漫无章法,表面体现出无限的诗情与宁静,文本的背后却蕴涵着作者对于生命的深刻思考,萧红也正是从“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