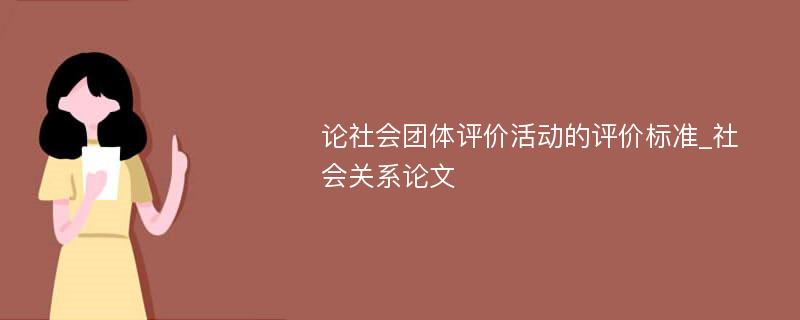
论社会群体评价活动的评价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评价标准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群体评价活动就是主体为社会群体的评价活动。研究社会群体评价活动就必须研究作为其主要环节的评价标准机制。
一、价值标准和社会评价标准
价值就是客体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主体需要是价值关系的一端,客体属性是价值关系的另一端。主体需要是主客体之间是否形成价值关系,或者说是客体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由此决定了社会群体需要与社会群体主体相对应的客体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即社会群体需要是价值标准。
需要不同于对需要的意识,没有被主体意识到了的需要不能成为主体进行评价活动的出发点,意识到了的主体需要才是评价活动的标准。因此,意识到了的社会群体需要就成为社会群体主体进行评价活动的标准。在个体评价活动中,需要的主体与具体评价活动的现实主体同一,主体需要容易被主体意识到。社会群体的实际主体作用,或者通过处于社会群体组织和结构最高位置上的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现实地体现出来,或者通过社会群体内众多个体的评价活动现实地体现出来。(注:关于社会群体主体评价活动中的两种现实形式问题,参见拙作《论社会评价活动的主本》,载《学术月刊》,1997(7)。 )社会评价活动中的现实评价主体与社会群体主体不直接同一,社会群体需要要通过较为曲折的途径为具体进行评价活动的现实主体所意识。因此,社会评价标准的获得要比个体评价标准的获得困难。
社会群体需要作为价值标准是社会群体需要作为评价活动出发点的根据;社会群体需要作为社会评价活动的出发点以社会群体需要被作为主体的社会群体意识到为前提;被社会群体意识到了的社会群体需要也就成为社会评价活动的评价标准。因此,价值标准、评价活动的出发点、评价标准三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不能由此认为,价值标准就是评价标准。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群体需要是客观的,本身无所谓真假。作为评价标准的被意识到了的社会群体需要是主观的。具体进行社会评价活动的现实主体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群体的需要,也可能歪曲地反映社会群体的需要,因此被意识到了的社会群体需要作为评价标准就有了真假之分。虽然社会群体需要的意识要以社会群体需要为基础,但作为社会群体需要的观念反映毕竟与作为观念反映对象的社会群体需要不是一回事。
二、社会群体评价标准的显意识形态和潜意识形态
社会群体需要必须在社会群体主体的意识中才能成为社会评价活动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然而,它既可以以显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群体主体意识中,也可以以潜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群体主体意识中。
显意识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思想、有意识。潜意识是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显意识犹如一座冰川浮在海面上的那一部分,更大的部分还浸在海水中,这便是潜意识。潜意识与本能有深刻的联系,但它不等于本能,而属于意识。马斯洛在谈到主体需要处于潜意识状态时说,这些基本需要不是有意识的,“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经常是无意识的”(注:马斯洛:《动机和人格》,62~6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这里所谓的无意识,不是说这些基本需要没有进入主体意识之中,而是说主体的这些基本需要总是存在于主体意识之中,以至于主体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由此从显意识转化为潜意识。
作为人的社会群体意识同个体意识一样,有显意识和潜意识之分。存在于社会群体意识中的作为评价标准的社会群体需要既可以以显意识状态存在,也可以以潜意识状态存在。社会群体的一些需要为权威机构或众多个体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需要就处于社会群体的显意识状态。显意识状态的社会评价标准一般通过规范和规则、契约、条约、政策、法律等理性形式表现出来。人们自觉地用规范和规则等作为评价人与事的标准,或者赞赏之或者谴责之。当然,显意识状态的社会评价标准也可以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但理性形式是其典型形式。社会群体的另一些需要在社会群体意识中经过长期的积淀,表现为社会群体的一些传统、习俗、禁忌等非理性规范形式。社会群体内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中遵循着这些传统规范并自然而然地用它们作为评价人与事的标准,虽然他们并不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传统规范与社会群体的一些需要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评价标准就呈现为潜意识状态。
社会评价标准的理性形式是经过社会群体主体理性思考后表现出来的,一般说来比较严密,能比较正确地反映社会群体需要。但理性标准决不等于正确标准。社会评价标准的非理性规范形式是没有经过主体理性思考表现出来的,由于它们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因此也往往具有合理性,然而盲目性比较大。但非理性规范标准决不等于错误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潜意识状态的社会评价标准是较低历史时期的社会评价活动常常运用的社会评价标准形式,显意识状态的社会评价标准是较高历史时期的社会评价活动常常运用的社会评价标准形式。社会评价标准的显意识状态可以通过积淀转化为潜意识;社会评价标准的潜意识状态可以通过激发转化为显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提高社会评价活动的自觉性,人们比较重视对于显意识状态的评价标准的运用。但是,在现实的社会评价活动中,潜意识评价标准的运用也不少。由于潜意识评价标准往往是显意识评价标准的一种历史积淀,人们一般是在不自觉状态下运用这类评价标准的,因而潜意识评价标准在社会评价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更大。同时,正由于人们一般是在不自觉状态下运用这类评价标准的,因而其在社会评价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也就更大。这两点都说明,人们应该而且必须重视潜意识状态的评价标准,研究它在社会评价活动中运行的机制和规律。
三、社会群体评价标准体系
同一社会群体主体对于同一社会现象往往可以用很多评价标准进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标准反映了同一社会群体主体的不同需要和利益。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评价标准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主体的评价标准体系。社会群体主体的评价标准体系与评价标准系统是不同的,前者是主体的不同需要即不同评价标准的统一,后者是主体的需要即评价标准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具体表现的综合;后者是前者的载体,前者总要通过后者具体地、现实地表现出来。
社会群体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决定了社会群体的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多层次的。这些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相互从属,形成以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主线的一个需要体系。社会群体的需要体系使社会群体主体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即利益,即评价标准,具有体系性。
社会群体评价标准的体系性表现在评价标准是多样性的统一,即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对于任何一个客体,社会群体主体往往可以从几个方面或几个层次去评价之,也就是说,社会群体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标准。这些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标准相互区别,但又不是完全离散的、无序的、毫无联系的,恰恰相反,它们好似从一个光源发出的多道光线,即都是社会群体的最基本标准的不同表现或显现。
社会群体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评价标准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社会群体内评价标准的矛盾可分为有学者所指出的两种性质,即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
所谓内在矛盾是指,反映在社会群体意识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需要之间的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是由它们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人们同时用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来评价历史或社会现实时,常常会陷入内在矛盾之中。所谓外在矛盾是指,反映在社会群体意识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需要,其内在规定并不使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甚至要求它们之间相互补充,但由于种种外部原因,社会群体只能满足其中的一种或几种需要,而不能同时满足全部需要。
社会群体评价标准体系是多样性的统一。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在评价一个客体时,可以运用的评价标准很贫乏,那么,这只能说明,或者这个社会群体的内在规定性很贫乏,因而主体的自身需要很贫乏;或者这个社会群体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很贫乏。这两方面都说明,这个社会群体发展不成熟。一个社会群体主体对自身需要的意识贫乏,还常常表现在会用自相矛盾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客体,而不能统一之。一个社会群体主体所运用的评价标准处于离散无序状态,并不能说明一个社会群体的评价标准没有统一性,而是说明这个社会群体的主体性的统一意识尚没有很好地形成,这也只能由这个社会群体发展的不成熟来予以解释。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群体,其内在的个体充分地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层次,具有丰富的内在规定性。因而,它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就会产生丰富的主体需要体系。这种主体需要体系所形成的社会评价标准体系,既有丰富的多样性,又有明确的统一性。因此,一个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明确的统一性的社会群体评价标准体系,对于社会群体意识来说,是一个社会群体成熟的主观标志。
四、社会群体评价标准的选择
社会群体主体在对客体进行评价时,总要从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评价标准体系中选择一个或几个评价标准。社会群体主体选择评价标准的实质,就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形成的或可能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选择与主体的某种需要相联系的价值关系作为评价活动的反映对象。
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群体的最根本的需要,相应地,关于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意识就成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对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利,就成为各种评价标准可以进行比较的最根本的根据。这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或其他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如此。
主体在比较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必须由自己来决定选择用何种主体需要作为现实的评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康德早就注意了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问题。康德认为,在道德领域,具有理性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决,“如果自由不是自决,它是什么呢?所谓自由就是作自己的规律,乃是意志的属性”。(注:《康德哲学原著选读》,2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主体选择评价标准是自由的,这不仅对于个体来说是如此,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如此。社会群体主体对于评价标准的选择虽然总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但必须由社会群体的意志自己作出决定。当然,社会群体没有超人格的意志,社会群体主体对社会评价标准的选择,或通过社会群体内大多数个体的决定体现出来,或通过社会群体的权威机构和代表人物的决定体现出来。离开具体人或机构对社会评价标准选择的意志自由,也就没有社会群体主体对社会评价标准选择的自由。
选择评价标准的自由决定了社会群体主体应该对由此所产生的后果负责,虽然有时这种负责是需要说明或解释的。对于社会群体的集体责任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国家是恶劣的,但是“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应有的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1页。)在这里,恩格斯的本意显然不是为封建统治者的恶劣开脱责任,而是在探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责任。
从主体方面来分析,社会群体主体正确地评价标准涉及到三方面因素。
其一,社会群体的存在及其需要是否合理。社会评价活动总是从一定社会群体的需要出发进行评价活动,正确地选择评价标准就必然要涉及到社会群体的存在及其需要是否合理的问题。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正确选择社会评价标准的前提。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由这个生存和发展最基本需要派生出来的基本需要,应该说,都具有合理性。基本需要往往要转化为许多具体需要才能表现出来,而具体需要并不是基本需要的简单分解。具体需要的产生与社会群体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因此,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能说明这个社会群体的所有具体需要都是合理的。社会群体具体需要的不合理,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本身就不合理。这种情况比较简单。一是一社会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就其本身而言,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这种需要放到社会群体的需要体系之中,这种需要就与其他需要发生了内在矛盾或外在矛盾,这种需要就会成为不合理的需要。
其二,社会群体的需要是否被社会群体主体所正确地意识到。社会群体主体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包括两个环节:
第一,社会群体的各种具体需要必须全面地反映到社会群体的意识中来,以形成完整的社会群体的评价标准体系。社会群体的有些需要可能没有被社会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或权威机构认识到,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于社会群体的意识之中;社会群体的有些需要可能以潜意识的形态为众多个体或权威机构所接收,因而也就以潜意识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群体的意识之中。没有进入社会群体意识中的社会群体需要,社会群体主体不能用它来作为评价标准;以潜意识形态进入社会群体意识的社会群体需要,社会群体主体只能不自觉地用它来作为评价标准,因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群体需要要完整地反映到社会群体意识中,社会群体的众多个体和权威机构必须对社会群体需要进行自觉的调查和研究。
第二,社会群体的各种具体需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客观关系必须正确地反映到社会群体意识中来。马斯洛指出,“人类机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当机体受到某种需要支配时,对未来的看法也会改变”(注: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16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这里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确实一种当下的紧迫需要会实际地改变各种需要与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另一种情况是,一种当下的紧迫需要会影响主体的判断力,使主体不能正确地认识各种需要与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这类情况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存在的。并且,由于社会群体主体对社会群体需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客观关系的认识途径更为曲折,从而使关于这种客观关系的认识任务更为艰巨。这种客观关系认识不清楚,影响社会群体主体正确地选择评价标准,会对社会群体带来十分严重的危害。
其三,社会群体主体必须对反映在主体意识中的各种主体需要及其与主体所形成的各种客观关系,正确地进行比较和权衡。前面,我们曾从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的角度对社会群体的评价标准体系作过分析。为正确地选择社会群体的评价标准,我们还可以对由社会群体的各种需要转化而来的利益体系作如下分析,即完整的社会群体利益体系中,包含有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等等。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有的时候,我们则要注意到首先保证眼前利益,才有可能谈得上长远利益。无论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长远利益还是眼前利益,都必须通过众多的具体个体和权威机构来认识之、比较之。而权威机构归根到底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个人利益是不可能不在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长远利益、眼前利益的比较和权衡中体现出来的。为了正确地处理好社会群体中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处理好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与社会群体内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中,既不能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集体利益,也不能离开个人利益、抹杀个人利益而奢谈集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