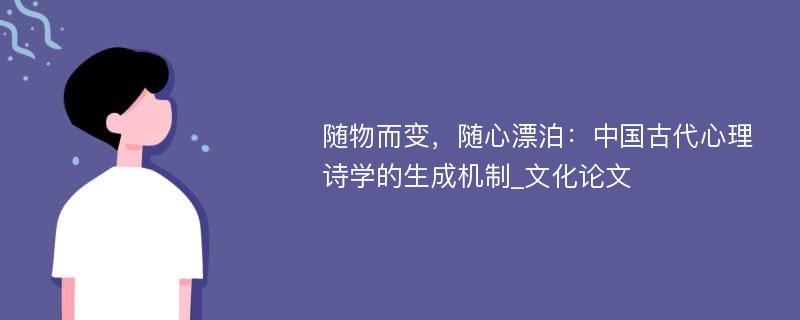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诗的生成机制——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机制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心理诗学关于诗的生成的“物感”论里,“物感”作为诗的本源,是以因物所感而生成诗为根据的,但是,诗的生成却极为复杂玄妙,它是心物交融互化的结果。解剖“感”是完整把握物感作为诗之生成本源的根本途径。
(一)
感,即感受,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拥抱、交合和把握,是集合了客体刺激诸因素和主体心理诸因素的神奇的创化运动。没有这一运动,就物归物,心还心,诗无从以生。苏东坡那首《琴诗》喻此最恰:“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的真正所在是创造者用指在琴上的弹拨,“感”便是诗创作中的创造性弹拨。它是由物心对峙分立而到心物浑化再生的中介,或者枢纽。一切“物”都需经过它的整合,才能再生,心也需它的发生才变得生气勃勃、源流不尽。因此,古代诗学理论无不以“感”作为重心,而且,可以说历代诗论家异口同声,认识基本一致,宛若灵犀之通。
早在《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中就有言:“凡音者生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于内。”音乐生于人心,是感化而成的。《乐记》说得更具体明确些:“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这段话不仅揭示了诗由物感而生的逻辑过程,还暗示了那“感”的内在运动的神秘。不同的心态便有不同的声,而这心态又不是固定于心的,而是“感于物而后动”。其“感”远比“物”、“心”本身要神秘复杂得多。
荀子论心有征知,“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同时又讲“缘天官之意物”,实际也是在讲“感”,讲主客体的沟通。
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南北朝无疑是文论诗论的重大发展时期,关于“感”的论述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刘勰推出的命题直截切要:“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彩》)人之七情,在于去感应万物,去实现心物的交合运动。这一切是自然而必然的。与刘勰同时代的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开篇即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值得玩索之处,不仅提到“感”,而且以“摇荡”状“感”,形象传达出“感”的心理运动特征。
唐及以后的诗论一直未逸出以上思路,既可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更显示出“感”的显著存在。如唐梁肃云:“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周公瑾墓下诗序》)元稹云:“凡所为文,多因感激。”(《进诗状》)
宋杨万里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诗之生成感悟曰:“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答建康大军库监门徐达书》)因物生感,感而生诗,人类最复杂的精神劳动——诗创作就这样简约地表述出来了。可见对“感”的体验之深和感悟之明。朱熹也认为,“诗乃人心感物而形于言”,与杨万里的表述差不多。而宋濂的表述依然是此一模式。其曰:“及夫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则沛然发之为文。”(《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叶夷仲文集序》)
清代叶燮云:“原夫作诗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原诗·内篇》)王闿运《论诗法》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这里不仅讲不能缺少“感”,而且“感”的质量不够,也不能成诗。
诸般论述,无不把“感”作为客观物通向艺术世界的唯一通道。用明代著名诗论家谢榛的话说,便是“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而二者酵化再生的过程便是“感”。不过,“感”又是极难把握和说清道明的,从上面列举的论述来看,也还没有对其运动作出具体的富有力度的说明,但诗文论家从没有放弃过这种说明。如果我们不怀疑这种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那些谈“感”的论述中同样能寻索到一条并行的悠长逶迤的地脉。可以说,在谈“感”里已经包含了对这种运动的暗示。如《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所说:“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于内”,音之所成是因心感物并在内心化生而成,虽片言,却能明意。又《乐记》说有什么样的心就可感生什么样的音。但是这又不是心中本来就是这样,而是“感于物而后动”,是在物的触感下引起的心物化生运动。其他的论述,皆可作如是观。
另外,还可以从“感”论的思想体系来认识这个问题。古代诗学的“感”源出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源头《周易》,源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置身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理论框架中,“感”便是“感而化生”,而“感而化生”运动是“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两极皆向对方生成,至阳出于至阴,至阴出于至阳,两极交合而成于一体。有此框架作底景,对于诗论中的“感”字所包括的物与心的化生运动就不难认识了。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隆重推出两位著名理论家的描述。
一位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表述: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刘勰把“感物”的心理运动过程,概括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的过程。其中以“宛转”、“徘徊”词下得至妙。在感物过程中,一方面是主体心灵随着外物唤情特征的“宛转”,另一方面又是外物在主体心理场内“徘徊”,二者相互生发,耦合交媾。刘勰还用另外的形式具体化这种宛转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心物之间亲和自然,在不断的交流互生中化生出新质。所以当代著名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总结和赞赏这一过程把心物矛盾有机统一起来了:“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1](P75)
另一位是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他在《艺慨·赋慨》中指出: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
应该说,刘熙载晚于刘勰那么多年,其论应有所突破,而此段论述不仅未突破,且表述极为相似,与刘勰之说如出一辙。但,此处我们勿需去评价他们在文论史上的地位,我们只想说,刘勰抑或刘熙载找到了隔世知音,他们所见略同,都摸到真理的脉搏。刘熙载用得好者,在“相摩相荡”。“摩”、“荡”与“宛转”、“徘徊”何其相似?不独“摩”、“荡”好,“相”字亦下得妙。在他们看来,心物如具灵性,似有神助,在主体的“感”的机制里,亲和赠答,“相摩相荡”,化生新质。西方哲人黑格尔曾说过:“在艺术创造里心灵的方面和感性的方面必须统一起来。”[2](P49) “艺术家须用从外界吸收来的各种现象的图形, 去把他心理活动着和酝酿着的东西表现出来。”[2](P359) 刘熙载的物我相摩相荡以及刘勰的宛转徘徊,便传达了这种意思。创作实践表明,在感物过程中,客观之物与主观之心是互相交流的,客观物象作为触媒,亦作为对象,引发主体心灵的拥抱,接受其情感、灵性和生命的灌注。而主体心灵,也是因此得到触发和寄托表现的。
刘氏的论述不仅在于阐述了这种相互运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揭示出这一运动的复杂性。既然有“心”参与,而且需要“宛转”、“徘徊”,反复摩荡,那就表明,这个过程是不平常的,是一个反复的曲折深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发的自组织过程,虽是耦合,虽是瞬间生成,却有着深长的感物背景。陈子昂一登上幽州台,便吐发出千古绝唱;陶渊明不经意间便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朽佳句。原来他们在这一瞬间已融进了漫长的人生底景,已灌注了他们漫长人生所酿成的情感、灵气和生命。惟其如此,其所感成果,才不是生涩的原生物或抽象无着的镜中花,而是奇妙的创造物,是凝聚了自然的精华与主体的精血的鲜活的生命体。
让我们看看西方人对此的思考。
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为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法国著名传记文学家安·莫洛亚说:“艺术的对象是现实的图画……同时这现实又是由人的理智安排的。我们可以援引培根的不朽公式:‘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的大自然。’(注:莫洛亚1928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传记的各方面》。)作为艺术大师的梵高也同样认为:“艺术,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被他解放出来的。”[3](P439) 古典美学家黑格尔指出,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2](P201)。现代美学大师桑塔耶那在《美成》中则认为一切美都可以从心物遇合中寻求:“美乃是灵魂与自然一致所产生的结果。”
这里的“相乘”、“解放”、“产生”等等词语,无不是从一个科学角度表述主体感物的宛转徘徊的复杂过程和创造结果,与刘勰等的论述相通。
在当代中国,也可找到类似的精彩论述。如我国的著名作家兼理论家的王蒙认为:“写作的过程,最难解决的也是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时候这个问题不像哲学上的问题那么容易说得清楚,那么单纯。在文学创作上,文学作品往往是非常纠缠不清的一种关系。文学作品,它既是非常客观的又是非常主观的。”[4](P98) 王蒙把艺术活动中及映射于作品中的主客体纠缠媾合说得复杂难解,不分明是在强调感物的“宛转徘徊”及其所带来的作品的新质特性吗?
综观上述诸论,可以把古代诗学“感物”的实质内涵这样梗述:诗人感物是一个由对峙走向交融的漫漫长途,表征上可以表现为瞬间浑融或其他形态,但心理运动却无异于经历了万水千山。整个过程是主体显在的和潜在的心理要素与客体“物”不断聚合分解进而化合的运动。其新体是主客体双向互动的不同组合形态所凝结成的自足感性形式。从这种浑融一体又分明可以看出,是一个由心化物而成诗的过程,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即有主观精神的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因此,主体的心灵观照是“感物”之根本了,它担负着从对峙走向融合的重要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古典文论研究专家吴调公先生一口气用了一组排比句来急切表达对心灵观照主导作用的赞赏和兴奋:
没有心灵观照,诗人便不可能根据一定的精神需要从客观现实中选取那烙印着自己心灵中意蕴最深的东西。
没有心灵观照,诗人便不可能从个性心理特征出发,发现最能适应作为主导意识的审美对象的精神内涵和恰如其分的审美意识的语言载体。
没有心灵观照,诗人便不可能从虚静走进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促成诗人之“神”与客观之“神”经过二者的互为作用,互相渗透,由“中间变量”所形成的珍贵境界:从有限到无限,从诗人的直观背后看出诗人的高水平思维,从以物观物深化到以心观物[5]。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感物”而实现主客观契合的心灵运动便有了一个层次进化过程,才是一个充满神奇性的创造过程。
(二)
在“感”的心理长征中,其层进过程是明显的。郑板桥的“三竹”境界可以移喻。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根据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论述了艺术创造过程中“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区别和转化。他有这样一段画跋: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技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画》)
这是对感而化生的层进层次的生动描述。“眼中之竹”,是指作为客观之竹对主体心的触动之竹;“胸中之竹”是眼中之竹触发的心内潜存之竹;“手中之竹”是心物交融而再生之竹。三者有层次之别,但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是一种主客体双向互动由浅入深的感而化生的心理运动。不独郑板桥已经点明,并非只有画画如此,其他艺术创作与此相通,就是从诗论中,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对应描述,如“即景会心”(《姜斋诗话》)、“心源为炉”(《董氏武陵集记》)、“相为融浃”(《姜斋诗话》)。试以此分别述及。
“即景会心”,是感物的第一个层次,是指主体对外物的初级感受。“即景”是当下所得,感觉器官直接觅取,然后形成感觉内化、演化,产生“会心”。但此时的“会心”仍是浅层次的,还主要是“随物以宛转”,或者说还主要在物理场运动,也就是在对客观之物的追逐与顺从。这是萍水相逢的感受,其交合是肤浅的,主体的心灵还未得到自由的释放和超越。
“物理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冯特提出来的,他的学生、构造主义学派心理学家铁钦纳对此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物理世界;另一个是心理世界。两个世界的本质不同。物理世界是客观事物的原初存在,心理世界则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物理世界是对于外物的真实的阐释,心理世界是对内心真诚的体验。两个世界的价值也是不等的。对于科学来说,物理世界能定性定量,是真实的;而心理世界,任意变形,缺乏科学特征。但对艺术来说,恰恰相反,物理世界表现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而只有准确的心理世界,才令人奉为真实。如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诵读此诗句,谁也不能用物理的时空观念责难怀疑李白所营造的情感淋漓的艺术世界的构成要素,破坏它们的和谐。在物理学意义上,一粒尘埃落在肌肤几乎浑然不觉,微不足道,而在心理意义上则可能力沉千钧,叫人食寝难安。两个世界各有其不同的本质和价值观,而艺术追求后者。
在“即景会心”层次,还主要是皈依于物理的逻辑规律。主体感受主要是寻求和拓展更深层的突破口,将客体信息的分离特征系统化,即对不同层级的刺激信息进行选择,从中筛选和过滤出最能表征客体意义的一定量的信息。同时,当客体信息不足时,主体想法使客体信息尽可能充分释放出来,以利用主体原有的知识经验,适当猜想补充,使不完整的信息系统化起来,以适应主体的心理的同向运动。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层次,其深进层次是在它的基础上展开。郑板桥之“竹”、李白之“月”等,虽然成为艺术作品时早已超越这个层次,但是,显然是深植于此的。它是创作的第一个环节。没有“物理境”中的“宛转”发现,自我便无法得到寄寓释放和表现。故古代诗学理论一致强调作者感物之前的身历目到,以便获得对“物”的敏感和把握能力。如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宋画院郭熙语也。金许古《行香子》过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晓山高,郭能写山之貌,许尤传山之神。非入山甚深,知山之真者,未易道得。’”强调的是“入山深”、“知山真”。王夫之明确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到,是铁门限。”(《姜斋诗话》)金圣叹则断言:“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十年的辛苦体认,才有做“物”的主人的自信。同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认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要能以奴仆命风月,使外物能随心(主体)所欲地被把玩和摩挲,就必须首先“与花鸟共忧乐”。这也正是歌德所讲的做自然的奴隶。做奴隶是为更好地做主人,因此仅停留于这个层次,还不能完满体现人类与客观事物的深刻关系,不足以显示出“万物之灵”的权威,于是有更深进的层次。
“心源为炉”是感物的第二个层次,相当于郑氏的“胸中之竹”。
刘禹锡曰:“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纷纠对错,逐意奔走。”(《董氏武陵集》)这就是讲用心灵去体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不是役于物,而是驭于物,由物态特征的有限性走向心理世界的无限性。在这里,一切“与心而徘徊”。主体心灵以其汹涌的情感外渗和经验模式的自由伸展,支配着客观之“物”,使“物”成为主体的附庸,完全脱失自身的逻辑。也就是从“物理境”完全进入“心理场”。这时的“心”会强制性地发泄,任意跃如,对客观之“物”全然超越。只有在这里,人才无拘无束,觉出了自己的伟大,成了大自然的造物主、万物之灵。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用自豪的语句概括这种情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主体心灵达到了无拘超越的至境。也就是说,“心”的思维机制和方式表现为“吐滂沛于方寸”,只要主体体认是心灵的自然表达,就具备了真实性品格,不受自然物结构的绳墨和验证。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写过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是一首公认的情感浓烈、意味隽永的名词,其中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感物的第二个层次特征。词人浓睡醒来,惦记着风雨中的帘外海棠,便问卷帘人。卷帘人通过实地亲勘,据实回答:“海棠依旧”,仍是花红叶绿。这是明确的客观物质信息,但在词人跃动的愁绪满怀的心理场中,这种客体特征被极度地淡化解构,而代之以情感的热烈拥抱和溶化,于是有对卷帘人的“无理”反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客体特征的把握则变得微不足道了。也正是如此,才使本词不致成为海棠的说明书,而具有一种深沉的感情力度,洋溢着醉人的艺术魅力。
清人龚自珍在北京对戴醇士说过这样一番话:“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席前,不关风雨晴晦也。”[6](P158) 西山之远近有无,完全凭心调遣,“不关风雨晴晦”。这是对感物内在运动规律的最好说明。在主体心的能动作用下,要么是极大限度地对物象变形,要么干脆是无中生有。而成熟的古代诗论对此肯定有加、津津乐道。如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王维诗句,‘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廓、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辽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用歌德的话说,这是成了“大自然的主人”,以强烈的呼号、赤诚的抒发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超越,实现对自我的体认。这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一层次,就无法进入主客体神契妙合的层次,不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其情景交融的诗核也无法成功凝结。这是对“役于物”的成功否定。不过,仍不能到此为止。在经历了主体的无拘超越后还必须回归,在更高的层面上达致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正如现代文学大师鲁迅所论:“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颈子二三尺而已。”[7](P175) 鲁迅先生的话,归结到一点,便是主体超越必定受其客观规律所制约,以客观规律为依据。只有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有效达到第三个层次:心物深层次双向互动、融洽和谐。
“相为融浃”,情景融洽和谐,是感物的最高层次,是经历了两重否定之后获得的一个必然归结,是更高层次上的双向互动。在这里,凛然的客观世界不再造成主体心灵的被动和疲软,自由的主体心灵也不再造成客观世界的破碎和消遁,两相保全又融洽和谐,也就是古人屡屡盛赞和倡导的心物神契、情景交融。王安石《登宝公塔》以最凝练的诗句表述了这一特征:“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诗文理论家们也如斯表述。王国维说,诗“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这里,无论“有我”“无我”,其所构成之“境”皆已心物浑然了。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诗中论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客观之竹不仅为主体心灵所包容,而且为之所浑化;既是一种美不胜收的客观物象,又是感发人世挚情的审美对象;同时还是一种深潜自居的自我形象。斯竹,既有鲜明的物态表征,又有创造者炙手可感的体温和律动。这是心灵与外物在双向互动中的深度的综合。古人称此为“至境”、“高格”,当代学者赞为“艺之至”、“无技巧境界”、“人艺即天工”。
可以说,成功的感物或完美的感物,必须经历这三个层次,而最高层次是一种境界——出神入化的境界,又不是轻易可臻的。刘禹锡讲的“心源为炉”的“逐意奔走”,形象生动。这不是一般的“奔走”,而是从目即心受开始而臻至心物浑然融洽的心理长征。在这条征途上,有的是呕心沥血、灵魂阵痛之苦,也有心灵自由释放、天人合一的审美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