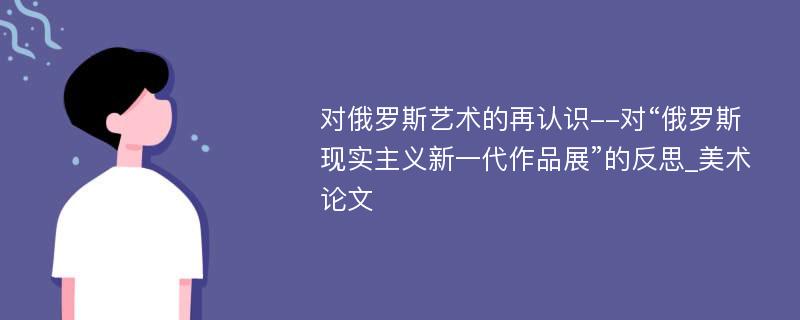
俄罗斯美术再认识——《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观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再认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新生代论文,作品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11·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2)03-0065-(05)
当我审视来自远方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时,一系列的问题油然而生:如何以一个开放式的语境去剖析俄罗斯美术?新的俄罗斯美术形式如何体现绵延至今的历史“现实主义”精神?究竟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才能真正切入当代?如果俄罗斯造型艺术仅以民族本土性(如俄罗斯传统中的圣经、神话内容)来应对当代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造型艺术的形式本身与时代性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由此引出的种种思考,将是本文论述的主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对于我国美术的影响是否能达到1957年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展出巡回画派巨匠们的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我国众多艺术创作者能否从中把握俄罗斯以及世界当代艺术的脉搏并加以发挥?换句话说,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究竟获得了多少“展览”的实质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作此阐述的动机和目的所在。
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历史位置
俄罗斯还在十世纪基辅公国时代,就与欧洲发达的拜占庭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基辅公国在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通过宗教影响,拜占庭的圣像画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这为十七世纪后肖像画发展打下了基础,画面开始重视透视和质感的表达。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俄国从封建农奴制迅速向资本主义过渡,在俄罗斯全面“欧化”过程中,肖像绘画在这一时期色彩仍然比较单调,构图也缺乏变化。至十八世纪中期后叶卡德琳娜即位,大量艺术家出国学习,国内缺乏教师,遂请来法国、意大利、英国艺术家来俄教授,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艺术及肖像绘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构图开始变得宏伟,画面表现无疑也受到了当时欧洲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崇尚文学绘画的习俗颇为风行,俄罗斯艺术开始升华。文学方面,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等大文豪降生,他们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畸型的人际关系,尖锐而敏感地揭示了生活现象的本质,是十九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后又出现了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倡导的“现代人”杂志。音乐界也出现了由穆索尔斯基等组成的为俄国民族音乐而奋斗的“强力集团”。美术界也紧跟文艺界动态和思潮,参与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六十年代具有民主主义思潮的艺术家们发展了菲多托夫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中记录了俄国社会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彼罗夫(1833-1882)的“送葬”、“复活节的宗教行列”、“沙漠中的基督”等表现出了人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其抒情的画面、凄凉的意境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有着密切的关联。列宾(1844-1930)是巡回展览画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描写了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现实生活形态。苏里柯夫(1848-1916)在历史题材的绘画领域内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在《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这幅名作中,他把近卫军、莫洛卓娃、米西柯夫放置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以此揭示他们复杂而微妙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深度和力量。这一时期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
期待新艺术样式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期,巡回展览画派已失去了昔日“批判现实主义”的动力,创作上也日渐趋于保守,缺乏新意。这一时期的整个社会背景是俄罗斯处于动荡时期,艺术风格也一直受到谢洛夫等绘画的影响,巡回展览画派已不再能左右俄罗斯画坛。然而,同期欧洲的艺术运动却极为活跃,从而再一次影响了当时俄国境内的青年艺术家们,彼得堡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名为“艺术世界”的社团,亚历山大·贝诺斯开始号召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们有计划地向欧洲(特别是法国、德国)学习,“艺术世界”杂志开始传播外国艺术信息,给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艺术思潮带来了活力。“艺术世界”在俄国的出现,对二十世纪前期俄罗斯绘画起到了冲击作用,直至对后来苏联时期的绘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次大震动,它震撼了俄罗斯艺术家的心灵(也暗示着前卫艺术活动的接近终止)。他们开始在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寻觅人民所需要的艺术样式,并创造出一批歌唱祖国、颂扬人民、保卫和平的作品:如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雕塑《铸剑为犁》,油画《末日》(注:《末日》的作者名是三人的联合署名,那个时期有许多这样的创作小组,并不全是自发的,艺术创作的功用可见一斑。),莫依钦柯的《红樱桃》、《红军来了》、《通讯兵》,雅勃隆斯卡娅的《春天》等。亦有一些艺术批评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美术领域所显现的“实利主义”、“生产本位主义”比一般纯粹美学的探索更为重要。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以及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对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美术领域的走向有着相当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仍然是目前我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同样,俄罗斯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不会在“休克疗法”中瞬间消亡,基础扎实、讲究功力的学院派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把此次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注: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于2002年4月4日——5月5日在上海金茂大厦展出。)和一九七七年巴黎的六十年来苏联绘画展作一系统考察,再联想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土地上所发生的文学艺术转型的中途夭折,我们是忧喜参半:令人扼腕的是今日俄罗斯艺术多样式多流派终究没能像当年那样辉煌于世,而令人欣慰的是其“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至今仍在这块土地上熠熠生辉!
来自欧洲艺术运动的影响
与十月革命时期相并行的巴黎画坛则延续着艺术变革的火种,艺术展览一个接一个,出现了“蓝骑士”、“红方块牌中的仆人”、“驴尾”、“靶子”、“军人”和“维纳斯”等艺术展览与团体,风格也从“新原始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新朴素派”、“极限主义”演变至“结构主义”,这些画派又倾向于“未来主义”,追求表现四维空间的“黑色方块”、“绘画上的零度”以及“绝对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几何抽象”等理论。与此同时的康定斯基是俄罗斯该时期活跃在欧洲画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世界现代美术史记录的先驱之一。同时,俄罗斯的塔特林在1920年完成的《第三国际纪念模型》——这是一件以木质为主的螺旋形塔梯,使当时苏联的造型工艺在现代具有领先地位(指当时欧洲的现代艺术及工艺设计运动)。塔特林的各种物质材料的文化理论影响了“结构主义的诞生”。此时左倾形式主义运动也逐渐高涨。虽然俄罗斯没能继续与欧洲共同上演现代美术史上的精彩剧目,但在人类艺术追求本质的过程中,俄罗斯绘画艺术在美术史上也以它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到苏俄“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历史功绩,都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足迹。那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结,那种深情、挚爱,那种鞭挞丑恶、崇尚人性为本的精神力量为以后的“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绘画的几个问题
仅从几件作品来评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艺术风貌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与技能的审视,同时也不宜仅从某一理论或者固定的审美观来评判这一展览。尤其是因为近十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处于一种极其动荡不安的状态,就更应从作品与社会现实、作品与人互动的角度来评判艺术。换句话说,评判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批评、一种哲学。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美术所展现的当代美术精神。
1、人文关怀。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了,岁月的更替、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与冲击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和思维模式。“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是指沙俄时期批判现实主义至苏联现实主义传统之后近十年间的“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们,他们自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画派的延续。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现实主义新生代在主题与形式上作为一个画派的演化过程与延续,是否还具有当代“现实”意义;在技术与形态上,他们好像从未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未放弃艺术的真诚追求,但是历史、现实生活、民族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是否依然在他们的作品里得到“人文”的关注?
从这几位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学院派崇尚经典的始终如一的创作理念,古典的样式、前辈的表现语言在不经意中表露无疑,他们的基本功无疑是扎实的。尤里·戈留塔,笔触豪放不羁,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情绪,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拉长的人体、线面相互交错的处理手法,无不流露出前辈画家巴巴(注: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2001年被选为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莫依钦柯的程式,他对前辈的技术传承几乎到了不折不扣的地步。但是,其众多的肖像画神情如一的漠然样子被一些评论者渲染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笔者对此则不敢苟同;亚历山大·巴戈香追求深度和力度感,确实凝重而厚实,其压扁的人形与布满画面的构图及简化的色彩关系似乎在述说着某种压力下的不快,其样式延续着八十年代一些作品的风貌。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类作品,画家在自己的色彩世界里诠释着古老的信念,似乎当下俄罗斯掀起的宗教热使画家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把历史上以神话为体裁的传统观念在历史的范围内用于重塑历史画的格局,其以圣经、神话的一贯认知为基础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否具有真实的当代“现实”内涵就不得而知了,他的作品是形式变化最多的,但在个人风格上似乎没有找到合理的承继形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把握能力堪称一流,也是笔者最为欣赏的一位。作为大师,他可以让授予他荣誉的人们感到自豪,作为一代艺术家的典范,他应在时代与艺术的坐标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总而言之,在充分领略俄当代画作赏心悦目的景象的同时,可以发现上述几位画家似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缺少对当下问题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的参与。
当然,展览是值得一看的,毕竟多少年没有一个像样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画展在我们这块曾经对其顶礼膜拜的土地上展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们的了解也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审视。
2、时代特征。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确实有着很大的探索勇气和创作精神,试图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情趣的艺术样式,他们好似同样坚守着伟大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底线,捍卫着伟大的“现实主义”旗帜。但是,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的画中亦可以看到某些其它艺术样式的运用,这得益于八十年代开放语境的熏陶(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政策,也促使了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眼前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却只能通过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搪塞时代,哪有当年列宾、苏里柯夫的睿智与气慨。这种远离现实的“现实主义”不再是真正的当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实主义”艺术仍然在那些“新生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每一代“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群体,从绘画传承角度为我们揭示了从帝俄“时代”到苏维埃时期一直到俄国“现实主义”艺术演化的历程,在秉承先辈写实主义画法的同时揉进其它的绘画样式,以求在新的视觉刺激框架中与受众共鸣,在这一点上,他们总能做到恰如其分。
当然,他们的作品虽然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又吸取了一些其他艺术样式成分,但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视角,是假视的、游离于现实社会背景之外的——传统的永恒生活主题是否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以及社会职责,宗教的宣扬是否真正缔造出了现代社会大众的意识所在,习作式的肖像是否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消极的人生观,等等。在创造性语言的表达形式与技术的造型能力与形式美感上,还留有苏联时期的表面表现形式,这种“述而不作”式的传递也许正好是一种常态。然而作为“浸润于规模空前的对百年前的文化转型期精神氛围的体验与思索”(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的俄罗斯文化人,其作品理应给人以更多的对当今的理解与思考。“画展”作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典型表现是否具有代表性?在质疑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新生代”群体的回避现实与失落状态寻找一种解释:“他们尚处在苏联解体、苏联文化解构的余震之中,他们正面临着‘一切都翻了身’、‘一切尚未安顿下来’的又一次转型关口”(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假如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标签将在往后的作品中,以不亚于当年巡回展览画派对世人的震撼来揭示一个艺术新时代——一个自信、开放并有民族凝聚力的、为复兴俄罗斯而创作的艺术时代。然而,从新生代的画展中人们恐怕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启示
毋庸置疑,充当人类重新认识“真、善、美”的社会良知和灵魂仍然是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就像相当多的题材是关于“环保”和“恐怖主义”等当今世界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样,它们深入到了人的内心深处,刻画了人的复杂而又微妙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新生代”艺术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否真正具有深厚的民族精神和人道主义审美亲切感的那种魅力呢?假如让我们再一次游历莫斯科特列采恰可夫斯基国家画廊,穿梭于七十七间硕大的展厅,崇敬之情即油然而起。那里悬挂着俄罗斯与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画家的作品:毕加索、梵高、康定斯基、莫奈、库尔贝、鲁本斯、苏里柯夫、列宾、赛罗夫等等等等,这样的陈列与观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参照,它至少告诉我们,在宣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俄罗斯艺术曾经与世界水乳交融、并驾齐驱。如果俄罗斯艺术曾经如此,那么俄罗斯绘画大师善于与同时代的世界沟通的高超本领,理当亦应是传统继承的重要特征,因为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怀有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在封闭环境中培育起来的情感往往是盲目的、偏执的。俄罗斯学者指出:“‘苏联范式’无法从民族意识中排挤出去,因此在今后的年代中,俄罗斯民族意识仍会保留‘苏联基调’,这个基调现在和将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人自我认同的性质”(注:李英男:《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新生代”画家的意识是否能独立其外,真正“新”起来,看来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前景。
重新回顾一下俄罗斯美术,将会使我们对我国当代美术发展态势进行新的思考与认知,同时我们也将思考如下问题,即当今俄罗斯美术的状态和发展态势是否还存有诸多问题,那个曾经辉煌于世的俄罗斯美术,还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它的深厚的潜力吗?作品存在的价值自是毋庸置疑。但平心而论,若要回顾与审视当下作品的内在意蕴和成熟度,看来也有欠火候。绘画展所反映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倘若缺乏对现代艺术的深度了解,就会屈服于只是表面技法的艺术样式。至于强调现代精神、现代艺术的原则性,则理应包含对艺术本质的说明,而不能像一些俄新生代画家那样只在感性的漩涡里打转。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艺术对我们的重大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与洗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再来关注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画派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起源、表现、性质和命运。通过研究解体后的俄罗斯艺术动态,重新认识俄罗斯美术,不光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正在转型中的俄罗斯的精神界面,而且从中俄美术交往的相互观照中去体味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大概这就是我从所观看的展览会中得出的一点感悟吧。尽管这可能已经超出展览举办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