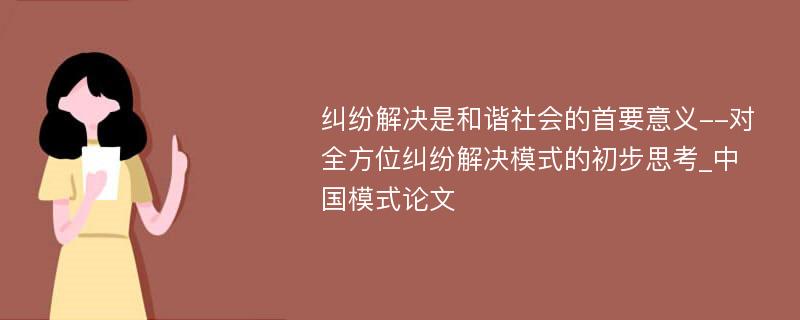
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和谐社会论文,纠纷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6-0045-07
当今中国应当建设的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致力追求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不完全一样的。如何建设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路径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仅从纠纷解决的主体和路径分析出发,探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尤其是反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纠纷解决思路的日益狭隘化的问题,以期为中国未来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一、和谐的要义是纠纷的解决
纠纷是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任何社会都难免有纠纷。人类不同的个体之间,永远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不一致的利益,必然导致冲突或纠纷。社会和谐的程度,端看其纠纷解决的成效如何。纠纷越多的社会,纠纷越难以解决的社会,纠纷越易于被恶化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越低。反之,纠纷越少或者纠纷解决得越顺畅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越高。纠纷被有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或者程度以内,纠纷被及时解决或即时理顺不使其恶化,怨恨暴戾之气难以郁积,这种状况,就是所谓和谐社会的内涵。
纠纷的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一个社会的任何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都是以恢复社会和谐为目标。因此,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如何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推论,纠纷解决不一定以达到通常所谓“天理昭彰”、“正义弘扬”、“申冤雪恨”、“皂白分明”、“权利义务厘清”的状态为标准。在更多的情形下,“纠纷了结”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纠纷不再进行下去”这一目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好多纠纷实际上是以一个大家公认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来“了结”的,有时甚至是以牺牲某些法定正当权益的方式了结的。比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戈尔诉布什案,最后是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投票表决解决的;2004年台湾大选中的“国亲联盟”诉民进党选举舞弊案,也是通过司法机关驳回起诉的方式解决的。所以,用那种虽然不太完善、达成的结果不太令人满意的,且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来讲好像有缺陷的方式了结纠纷,总比让纠纷恶化或扩大化要好。
我们国家法律设定的很多规则,实际上都有尽快解决纠纷、使纠纷不再恶化或扩大的用意,比如司法终审制。并不是说只有二审才一定能够保证兑现正义,而是说必须有终审制,使官司不至于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西方国家规定三审终审,我们规定二审终审,我们比西方国家更希望官司早些了结。比如民法上设置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制度,也是为了使与被宣告人有关的权益纠纷早日了结或稳定下来,不然因无法查明生死而使有关权利义务长期悬空的状态会恶化民事纠纷,造成更大的损害。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设计理念就是,用“虽不理想,但没有更好的办法”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纠纷,恢复和谐。此即先秦法家慎到所言“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严格地说,都是“不善”的,但是总比什么办法都没有要好。不善的办法也能“一人心”,统一认识,了结纠纷。
清人汪辉祖对此一道理作过十分精当的阐发:“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之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1]
我们过去在立法上过分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就尽量推迟立法的进度,使得很多问题长期无法可依;在司法上,长期格外追求在个案处理结果上的“尽善尽美”,过分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宁可牺牲法律的一般规则也要“曲当”个案的事实。如是久之,严重损害了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这种作法,不断没有解决纠纷,实际上恶化或扩大了纠纷。
二、国家首要任务是解决纠纷而不是制造斗争
任何政府当局都应当以消除纠纷(斗争)为首要任务,不可反而挑动纠纷或斗争。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曾经犯过根本性的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党运用阶级斗争工具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战争年代,斗争是作为革命造反的重要手段。要造反,要夺权,就得搞乱敌人的阵脚。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我们党还在一段时间继续讲阶级斗争和革命造反的合法性、正当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向人民解释我们党得到政权的正当理由。但我们党现在已经执政快60年了,如果执政党仍旧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把自己的政权叫做革命政权,这是相当不恰当的。在当了执政党近60年之后,我们党应该改弦更张,把自己定位为“民主政党”,因为我们党是在代表人民实行人民民主,我们党是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如果一定要说还要斗争,不过是要以法律机制与违反社会和谐、民主法制的现象斗争而已,这不是人民群体的阶级斗争或革命运动。
第二,在夺取政权之初,自50年代至70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指导之下,继续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是为了“斗”掉潜在的旧制度、旧思想,斗得人们思想升华,斗得大家灵魂深处闹革命,最后实现最高层次的和谐——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种为了未来遥远的天堂般的和谐而牺牲眼下的和谐,以互相斗争的手段去争取未来和谐的思路,与迫使人民牺牲眼下的实实在在的自由、权益去争取遥远的“人类未来解放”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一致的。这种“斗争”思路也是不可取的。
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纠纷,调和矛盾。过去,我们党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严重的误解,所以党试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追求社会和谐,这实在是南辕北辙的选择。我们党过去对国家的理解,可能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名言:“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2]236也可能因为我们党过分夸大理解了列宁的论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3]175仅仅这样理解国家,当然就把国家仅仅当成了斗争工具,所以要不停地煽动人们相互斗争,不停地用国家的暴力进行压迫。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恩格斯也说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4]166恩格斯在这里道出了国家的更高更长久的使命:维护秩序,使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保持在秩序(即可以互容)的范围内,让阶级冲突或斗争不至于使大家同归于尽。这就是说,国家的存在,主要使命是调和矛盾,是解决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所谓“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和谐。
三、纠纷解决是多主体、多途径(形式)的
纠纷解决绝对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事情。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本身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建设起来的。有了国家这种纠纷解决机制以后,从前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未因此而消亡,很多都在继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把纠纷解决仅仅视为国家的专门事务。过分把纠纷解决视为国家的专门事务,只会贬低社会、淡化社会,忽视社会的作用,这必将使纠纷的解决更加艰难。
近年来,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大有“国家单边主义”或“片面抗战”的趋势。“找领导去”、“找公安去”、“找法院去”,是人们在纠纷发生后的第一反应。中国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民间秩序权威几乎全部被视为“封建宗法势力”、“家长制残余”、“土豪劣绅”、“黑恶势力”、“讼师讼棍”加以扫荡,社会力量在纠纷解决中已经没有任何正当权威,即使在有些案件中参与纠纷解决,也大多是以“妾身未明”的可怜姿态出现,随时可以被官方一句话加以否定。虽然名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还存在,虽然治保会、调解会还有一些活动,但他们很少积极主动地主持民间纠纷的解决,即使主动主持解决,也更多地是在代表国家,而不是社会的自治权力的行使。
这一趋势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人们对国家寄予的期望越多,呈交国家解决的纠纷越多,国家越是力不从心,不能解决时纠纷也就越多,国家越发显示出“无能”的形象,国家的威信越是贬低;另一方面,社会越不参与纠纷解决,社会的作用越被贬低,社会就越是不成熟,越是不能承担起应有的作用,人民的自治力就越差,人民的自治力越差,就越是为专制提供理由和土壤,人民越是远离民主和自治。国家解决纠纷权威的下降,社会陌生于民主自治并依赖专制,都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大失败。
(一)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性
1.国家作为纠纷解决者 国家作为纠纷解决者,其要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是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是说,她不是社会中任何一个团体或者力量的代表,不能表现出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是担当起超然于所有阶级或团体之上的中立、公正的角色。国家在解决纠纷中的角色,大致是两个方面的或两种形态的:一是直接作为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上的中立的协调人和裁判人,这主要体现在各类行政事务的决定和实施中,体现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中;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这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以及对政党或国家机关局部违宪的追究事务中。国家公诉人向刑事法庭或宪法法庭提起公诉,实际上是代表全社会利益。这时,国家是一方,犯罪嫌疑人或有违宪嫌疑的党派、机关是一方,法庭是被打扮成在国家与他们对抗中的第三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公诉案件中国家公诉人只能与个体被告人诉讼权利平等,也就是为什么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要说成是“女王诉汤姆斯”、“合众国诉辛普森”等等。
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要么是超然于冲突双方的利益之上,要么是自居代表社会所有阶级或集团利益,绝对不能公然说自己就是某一个或两个阶级的助威者,这就如裁判员绝对不能同时又是比赛某一方的拉拉队或代言人。因此,国家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作用,是要尽可能阐释和昭彰正义,使自己尽可能被冲突各方所信任,同时,尽可能把自己对犯罪和违宪集团的追究,说成不是一己之意的产物,不是国家的一己之私,而是听命于更客观中立的机构——法庭来裁决。这样的冲突解决思路,才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思路,才使国家不至于轻易成为冲突双方的怨恨对象。国家如果在纠纷解决中把握不好自己的角色或者角度,就容易成为社会冲突双方怨恨的对象,或者把自己卷入纠纷的旋涡,那么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就要受到怀疑了。
2.社会作为纠纷解决者 对于“社会”(society),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理解,不能把社会仅仅理解为“客观的社会”。“社会”的要义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人民在国家安排以外自发组织起来满足自身特定需要的组织形态。社会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其实有多种表现形态。实际上,能够参与纠纷解决的社会组织,可能包括多种形态:(1)血缘社会,指宗族、宗亲会等等。他们其实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如中国古代的宗族通过族长、宗祠自行裁决纠纷[5]97~102;[6]90~92,如旧中国民法中正式规定过“亲属会议”的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2)地缘社会,指乡约、乡党、村社、同乡会、保甲邻伍以及现在的村组、社区等等。他们在中国古代一直发挥着纠纷解决的作用,如明朝王阳明推行的“乡约制度”,就有直接参与社会纠纷解决的[7]228~232。(3)江湖社会,指会党、帮派、山头草寇团伙等等。他们也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内部纠纷的解决机制,以及他们参与帮助附近百姓之间的纠纷解决。今日仍有借助乡间强势力乃至黑社会之力解决民间纠纷之事。(4)宗教社会,即寺院、教友会等等。中国古代寺院内部的法律权益纠纷一般是由寺院长老自己解决的,寺院也经常参与解决僧人与百姓之间的纠纷,或直接参与调解民间冲突。如北魏时允许寺院内部自行裁决一般犯罪:“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统(寺院执法)以内律僧制治之”(魏书·释老老)。(5)职业社会,指工会、农会、会计师协会等等。这些职业社会组织也可以自行解决内部纠纷和协助政府解决他们与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纠纷。如台湾《工会法》第五条规定“工会之任务”包括“劳资间纠纷事件之调处”、“工会或会员纠纷事件之调处”[8]1173。其《农会法》第四条亦规定农会任务之首是“保障农民权益,调解农事纠纷”[8]1181。(6)商业社会,指行会、会馆、金融互助会等等。在旧中国,商人会馆、行会在纠纷解决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帮助解决商人群体与官府之间的纠纷。我国今日的商事仲裁机构进行的仲裁调解,就是这类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现。(7)政治社会,指政党、政治社团等等。近代以来,政治党派社团参加纠纷解决,主要指其对其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处,亦包括它参与其他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8)学术社会,指各类学会、作家协会等等。他们实际上也能参与某些纠纷的解决,比如参与有关知识产权侵害事件(如学术抄袭)相关纠纷的解决。
3.个人作为纠纷解决者 除国家和社会外,个人也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主体之一。这包括个人以自己的力量直接解决纠纷,也包括个人借助其他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纠纷等两种情形。个人也是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说,社会上的很多纠纷,实际上是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的。如果没有个人的力量作为随时随地参与私人间纠纷解决的保证,我们的社会恐怕会因为纠纷多得不可开交,政府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而完全瓦解。
(二)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除了认识到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性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解决解决纠纷的途径(或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1.从国家而言 国家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通常只注意纠纷的司法解决,很少注意到在司法之外还有很多可以解决纠纷的途径,如政治解决、经济解决、文化解决等等。所谓政治解决,就是国家通过政治策略的变化来解决纠纷,比如这些年国家通过城乡居民一体参加公务员考试、各类人员就业考试的政策,解决了过去多年城乡居民之间因为“户口”差别产生的许多纠纷。所谓经济解决,就是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来解决某些纠纷,如国家近十几年间依靠市场经济杠杆作用解决了许多由计划经济造成的国营企业债务纠纷。所谓文化解决,就是国家通过文化引导来解决纠纷,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注重培育“敬老”文化氛围,如周代为弘扬“敬老”文化,实行“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礼品点心)从”的制度。国家推行这种关于老人使用拐杖的范式,实际上就是想培育“敬老”文化环境,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敬老养老,以助于解决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养老纠纷。
2.从社会组织而言 社会组织解决纠纷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社会组织有自己的预防纠纷机制。中国古代的宗族自治过程中,有着典型的纠纷预防机制。比如为了预防婚姻纠纷,中国古代的婚姻一般是以两个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为保障的。我们今天无法理解,为什么古人一定要把男女之间的婚姻之事搞得那么隆重,为什么一定要三父八母、七姑八姨都参加到里面来,其实用契约法的眼光来看很好理解:两个家族的“要人”都出来做这件婚姻契约的见证人和保证人,那么如果有一方要毁约、要翻脸不认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再比如说,中国古代有所谓“乡饮酒”之礼,这就是一种由社会操作的纠纷预防机制。“(乡)饮酒之义,君子可以相接,尊让洁敬之道行焉,是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悌)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就是说,这种礼仪,是为了教导敬老尊贤的风尚,预防人们产生“凌上僭贵”之心,预防“争斗之狱”。
其次,社会组织有自己的调解(劝解)和仲裁机制。大凡纠纷发生之际,在社会中有一定身份名望的成员会自动站出来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和仲裁。即使是不同社会组织(体)之间的纠纷,各自社会组织内有身份的成员一般也会主动站出来代表本方与对方团体中“主事的人”进行交涉以解决纠纷。费孝通先生曾描述乡村调解,“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9]56除了调解之外,社会组织还以自己的权威直接仲裁案件,如近代上海的商会直接仲裁商人之间的纠纷案件。仲裁与调解的最大不同大概就在于,调解至少要在拿出纠纷解决方案之前先获得双方同意(至少口头表示同意)然后再正式做成调解协议,仲裁则无需事先一定获得双方同意,完全可以凭仲裁者的权威直接作出民间“判决”,且纠纷双方有义务接受。
再次,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制裁机制,以保证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比如在中国古代宗族内部,对于违反宗规族法的人,其制裁方式是多样化的。据朱勇兄的考察,安徽南部地区各宗族的制裁措施大致有训斥、罚跪、记过、锁禁、罚银、革胙、鞭笞、不许入祠、出族、处死等11种[6]99,都成为族内纠纷解决的有力保障。在工商业行会内部,也有制裁机制,如北京剃头业行会对于违反行规者“将其理发工具掷于街巷”。还有的行会的制裁方式是“给行业祖师出香火钱”、“罚请吃一次盛宴”、“出钱请戏班给行会同人唱大戏”、“开除出会馆”、“大家联合抵制他”等等[10]116。
此外,为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社会自治组织通常还设计有与国家联接的机制。比如,在中国古代的宗族,有“聚族鸣官”的“告官”模式和“受官命调处”的解纷模式。关于前者,如安徽太平县《李氏家法》第十条规定:如有子媳忤逆不孝,屡教不改,经族内“捆送入祠杖责”后仍“凶狠不服”,则“送官究办”。这种“鸣官”,通常是宗族首长以家长名义将犯者送交官府,又作为证人向官府提供有罪证言,还运用自己的势力影响官府,总之是要求官府按照宗族的意见惩治[6]100,218;[7]123~128。关于后者,就是所谓“官批民调”模式,就是州县官在告状上批“着族长调处,勿使滋讼”,然后把案件发回诉讼双方所在的宗族首领,由他们调解处理。这时的宗族,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实际上已经与国家有机连接了。
最后,我们甚至可以说,非法社会进行的某些非法制裁,也可以视为某种纠纷解决途径。比如吴思在《隐蔽的秩序》中所列举的盗匪组织通过自己的某种制裁措施来解决纠纷、收取保护费[11]409~411;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兔子不吃窝边草”帮助保护当地百姓利益和解决纠纷,又如当今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措施,也可以视为某种纠纷解决的模式或途径。
3.从个人而言 个人也是社会纠纷的解决主体,有自己丰富的纠纷解决途径或者模式。个人解决纠纷,总的来讲,就是“自力救济”。其自力救济的方式,应该包括以下多方面:
(1)个人自力报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制止纠纷扩大化的最常见办法。孟子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促使很多人不敢作出杀伤别人举动的原因,正是别人会反过来杀之,这种对他人报复的恐惧当然制止了很多行将发生的纠纷。
(2)当众指斥,制造舆论,挑起道德审判。我们通常看到,在发生纠纷争吵的场合,为何自认为有理的一方一般会调门很高,这正是为了制造舆论,将在场之人引入裁判员角色,或吸引人们围过来当裁判员。当众获得同情支持是他的最大追求,这最有利于按照他认识的道理来解决纠纷。
(3)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是由个人进行的纠纷解决模式。个人在紧急情形下,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以可能对别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手段,或者用对他人财物加以毁损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解决纠纷。特别是正当防卫,实为国家授权“现场报复”以“制止不法侵害”,正是为了快速解决纠纷。
(4)自助行为。中国早在唐代法律中即有规定,债务人如逃避债务,债权人可以“牵掣”或“强牵”其财物并告官(如牵掣过契又不告官,则“坐赃论”)。今日台湾的《民法》仍有类似规定,曰“自助行为”。
(5)决斗和神判。决斗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进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历史上,通过决斗解决纠纷,特别是名誉纠纷、权力纠纷、情色纠纷,是常见之事。中国过去的江湖社会也盛行决斗解决地盘或势力范围纠纷。不过,有时双方同意借助神明裁判来解决纠纷,比如捞油锅、过刀山之类,这与决斗比较相似。
(6)个人被国家特别授权以私力来解决纠纷,如中国古代允许复仇,就是这种逻辑。如三国曹魏时立法:“贼斗杀人,以(已)劾(告发)而亡,得听(受害人)子弟追杀之。”这是国家立法公然授权受害人的子弟代表国家行使对(私斗)杀人犯的追捕惩罚权,以图解决日益严重的杀人案件蔓延问题。我们1997年《刑法》规定了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无限防卫权”,旨在借人民之手制止犯罪、减少纠纷,实际上是将国家的一部分执法权或行刑权授予了特殊环境下的受害人。前几年好几个大城市搞地方立法,规定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撞了白撞”,实际上也是这种思路,也是把制裁交通违规的行人,减少交通纠纷的部分权力授予了机动车驾驶人。
四、传统纠纷解决模式反省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纠纷解决途径方式等作一个宏观的反省,以揭示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思路的狭隘性。通过这样的反省,我发现,我们过去对于纠纷解决,有很多致命的认识错误。这些错误认识妨碍了我们有效地解决纠纷。要为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更好的思路,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认识,建立新的认识体系。
第一,个人、社会自力解决是纠纷的最主要解决途径。很多人认为,国家是解决纠纷的第一主体,民间纠纷的国家解决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其实,只要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的纠纷,层出不穷,无以数计,如果按照解决途径来分,应该说事实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个人自力解决的纠纷,占全部纠纷的最大部分;社会以团体力解决的纠纷,占全部纠纷的较大部分;国家参与或主持解决的纠纷,只占全部社会纠纷的最少部分。在国家产生以后,个人自力解决的纠纷越多,社会自治解决的纠纷比重越大,越说明一个国家的国民程度高,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程度高。反之,一切纠纷都依赖国家解决,即使也能达到某种安定或稳定,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第二,国家纠纷解决途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途径。纠纷解决首先应该是社会之事。只有在社会途径解决不了之时,才可以诉诸国家。除了严重刑事犯罪以外,所有违法和违反习惯引起的纠纷,都可以看成是民间有权参与解决之事,不可看成首先是国家之事。纠纷的国家解决机制,其要义或本质是:它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伤感情的选择,是会造成不可改变的结局的选择,因而有着对社会和谐之篱笆进行“最后修补”的属性。古人云“一年官司十年仇”,《重订增广贤文》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两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大概都是讲诉讼或曰国家纠纷解决模式的这种属性。为什么经过国家就必然有这种“绝感情”、“伤和气”的效果呢?我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异己性、外在性。对于长久习惯于在自己的“亲和圈”即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后产生的拥有军队、警察、法庭的国家的确是一种异己之物,是一种外在之物,让它来“耀武扬威”地解决纠纷,是很让纠纷双方都没有面子的,因此必然产生隔膜感。这就如家内兄弟间有纠纷,如果叫叔叔伯伯来调解,大家都不会觉得伤感情太多,但是,一旦兄弟中一方找外人来帮忙解决纠纷,那么这对兄弟的情感算是破裂到顶了。对于百姓来说,国家暴力“耀武扬威”地强加于他的纠纷解决方案,与他们通过社会自治力达成的带有“道德自省”、“顾大局、明大义”、“从善退让”性质的纠纷解决方案,其价值和效力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对纠纷的社会或个人解决途径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尊重社会的自治权利,实际上就等于承认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承认国家的局限性。而承认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要义。承认国家权力和作用有限,就必然要承认个人权利的神圣性、无条件性、不可剥夺性,这就必然要导致民主和自由观念发达。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不承认它们有天赋的自治权利,我们就无法理解民主和法治。我们过去在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上,出于对个人和社会的不信任,建立了国家“家长制”主义的无所不管的纠纷解决体系,现在该是对这一体系进行总清算的时候了。我们的法制对人民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处处有体现。比如在民间调解问题上,台湾的《乡镇市调解条例》只规定了体现“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的“合意原则”,认为调解协议归根结底是私人契约,应该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愿;但是我们大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则在“自愿”原则之外还规定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及“合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仅是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还不够,调解协议的内容还必须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调解协议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公权力(国家司法权)明确可以介入民间调解这类私权事务,并且国家对私权利的效力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同时,该法还规定,行政主管机关有权主动审查复核人民调解协议,有权予以撤销。与国外和台湾的调解制度相比,这体现了国家权力过分使用的倾向,反映了对民间社会自治的极度不信任。此外,台湾“法律”规定民间调解可以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但我们的法律规定调解只能对“民事案件”进行,这也同样反映了对社会自治的不信任。国家对社会生活参与、干预的范围太大,程度太深,是我们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最大弊端之所在。国家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对国家利益的破坏、对统治秩序的破坏,一定要把很多私法问题公法化,这种情形是与民主法治追求背道而驰的[12]。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应当包括政府给予社会更多的纠纷解决权的含义在内。
第四,不尊重社会,就无从言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是社会自治比较成功的社会,不是国家暴力张扬使民众胆怯的“(法家)商韩式社会”。社会组织以自己的途径方式,运用不靠国家力量自然形成的权威,解决自己社会内部的纠纷,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既然要追求和谐社会,就要先同意社会有更多的自治权自主权。如果不然,我们追求和谐社会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叶公好龙。我们过去老是说中国古代是“有国家无社会”,其实中国古代总算比较尊重血缘社会(家庭、家族、宗族)的自治权,总比我们今天连血缘社会都不尊重要好。我们只需看看今天的中国哪一个民间团体能够不挂靠“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而成立或存在,就可以知道:真正“有国家无社会”的国度是不可以真正解决纠纷和建成和谐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