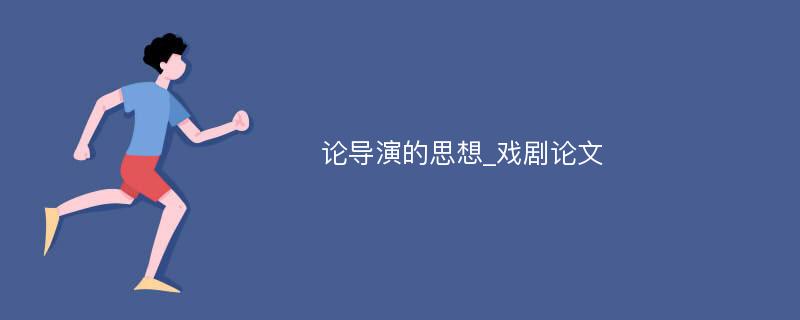
论导演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演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导演则是作为一个将各部门进行综合运用者出现在戏剧的排演之中。因此,他的创作思维必须是全方位的。某种程度上来讲,导演应该是一个熟悉舞台演出各个部门的全能指挥,他的思维将决定着未来的演出显现。那么,又是什么来启动导演思维,影响导演思维的呢?我想就此浅谈几点认识:
一、戏剧观决定导演的思维模式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什么是戏剧”没有足够认识的人会导演出一台好戏,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局限在对戏剧本质的起码认识基础上也还是很不够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导演对戏剧的本质作不断的探求,在戏剧观念上作不断的更新、发展。由此,我们联想到前几年对戏剧观展开的讨论,以及对戏剧假定性本质所进行的探讨和实践,使人们对戏剧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在观念上有了更广泛的突破,才有了后来的舞台演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舞台时空的灵活性。就拿话剧《中国梦》来说吧,导演黄佐临如果没有对写意戏剧观念及舞台假定性的充分研究和认识,就不可能在话剧表演中运用那么多的虚拟表演,舞台时空转换也不可能表现得那么自如而得心应手。新的戏剧观念,带来了新的戏剧形式,一些传统话剧里的“不可能”,在这里却是浑然天成,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表现形式作为内容的承载体,与传统的表现形式相比,无疑更增强了承载力。而这一切恰恰得之于佐临先生多年来对戏剧本质的潜心研究。我们从他的《漫谈戏剧观》中也可以很充分地认识到,新的舞台呈现样式,一定先是建立在导演对戏剧本质特性的充分把握和认识基础之上的,这是前提。导演所有的构思,都是首先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二、导演思维中的预成构想
所谓预成构想,就是没有成为实际主体呈现的,只是存在于导演脑子里的未来舞台演出。之所以称作“预成”是因为它必须是导演切合实际地运用经验,先期达到一个想象构成,也就是预测到未来演出。那么,导演在构思活动中所进行的想象构成是以什么为基础或依据的呢?我以为除了对导演技法的熟练掌握之外,还必须有以下三点:
1.艺术眼光。我们通常把它叫作切入口。那么所谓艺术的眼光,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简单说来,艺术眼光就是为主体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的眼光。而这种客观对应物,大多是蕴含着社会精神潜流的感性生命体。艺术家所要做的是要将自身的个体情感与总体的社会精神潜流,协调在一个感性生命体之中。艺术眼光的特殊性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这种感性生命体的敏感性。比如,我们看待一对离婚夫妻,社会学家可能是偏重于离婚对社会稳定或对第二代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考虑;法学家则可能侧重于离婚者是否符合法律中的条款或是离婚后的财产分配;而艺术家呢?他更关心的则可能是属于这对离婚夫妻精神世界的东西。只有个体生命意义的,也许是让很多人能够感知但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它交汇着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和有普遍价值的社会精神。艺术家如果能够在这一区域里作些停留,往往就能够上升到哲理的天地。应该承认,艺术家拥有着自己的天地和自己的权利,在另一个层次上掌握着自己的评判标准,这也是导演在思维活动中首先必须具备的艺术眼光。
2.给作品定位。定位,不是要给作品划上硬框框,而是指对作品所蕴含的精神气质散发出来的个性特征的张扬,是导演在宏观的总体把握上和微观的具体细节上对作品的个性和特色的统筹。给作品定位实际上也是使作品走向风格化的前提。我们知道,我国话剧中有所谓“京派”和“海派”风格之分。应该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各树一帜,无疑是由一大批剧作家、导演及演员们在实际创作中不断地进行某些带有特别意义的取舍而逐步形成的。同样,一种主张、一种取向,落实在一部作品中,往往是通过总体的展示和细节的刻划才得以展现自身的个性和风格化特征的。而实现这一切的有效途径恰恰离不开给作品进行定位。定位,如同有了一个座标、一种流向,使整部作品能够顺着导演所指定的轨迹延伸。当然,它必须是导演对一种精神气质和文化状态的深切体认和追寻。这种体认和追寻越是深入,作品的个性就越是鲜明,风格化的效果就越浓郁。
3.对舞台演出各部门的充分掌握,即演员表演、舞美、灯光、服装、道具、音响效果等特性的掌握。这一切都必须能够在导演脑子里深化为表现手段中的元素成份,变为导演语汇,贯穿在对未来演出的构思活动中,并随时能够开口说话,成为表现手段。
4.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也就没了戏剧,戏剧的完整体现是由观众的不断参与共同完成的。因此,导演思维必须依附在观众的观赏视点之上。对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势、欣赏习惯以及文化心理层面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在他的思维活动中不断地用观众的眼光来衡量判断,预测到自己的预成构想是否可能被观众所接受,为观众所认同,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演出效果的吻合。
三、剧本内涵与形式表现
关于这一点,使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有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过去曾经作过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讨论,但是现代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已经认识到,只有深刻地体会内容和形式之间无分彼此的有机统一关系,才能正确地把握艺术创作方法。著名的牛津大学教授柏拉德莱曾经说过:在绘画里,根本没有在“意义”上敷设颜料的事,有的只是在颜料中的意义,或有意义的颜料。在其他艺术中也是同样,内容是美学中的元素,形式是元素间的关系。这对我们认识剧本可提供的内容与导演所建构的表现形式间的关系是很有启发性的。
剧本在未被上演之前,只能算是案头之作,还不能算作一出戏。只有当导演赋予它演出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时才算是一台完整的戏剧。那么,导演又是怎样运用结构思维将剧本内容用主体的表现形式呈现在舞台上的呢?关于这一点,每个导演都具有自己个性思维的呈现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某些带有共性的东西。比如中戏院长徐晓钟导演认为,导演在进行舞台显现的构思中,必须确定全剧演出形象的“种子”,这形象的种子实际就是一种未来舞台演出形象化了的具有哲理性意蕴的立意,一种意象,它并非很具体,往往是具有象征性和暗示性,是一种力的暗示,力的结构。比如他在排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过程中,对全剧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他说:麦克白是一个巨人在一条血河上,并且逐步地往下沉,这往下沉实质就是一种下降的力;麦克白被权欲所诱惑,这是一种权欲的诱惑力,不惜弑君篡位,逐步走向不可自拔的深渊,这又代表着一种力。徐晓钟正是根据这不断牵引着麦克白“下降”的力建构导演思维的。与他不同,胡伟民在对桂剧《泥马泪》的构思中,首先出现在他脑子里的则是出现在全剧最后的一个场面,一个众人匍伏在地顶礼膜拜的仪式,以至他认为“全剧不过是升腾的载体,在最后一霎那,在辉煌的仪式中,悲剧情境将会达到顶点。”这最后一个场面、一种仪式,成了他全剧构思的灵魂,全剧深刻的内涵和哲理意蕴将是通过这样一个仪式场面得以显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徐晓钟对《麦克白》中一种往下沉的“下降”的力的构思,还是胡伟民《泥马泪》中的仪式性场面,尽管他们的切入口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在寻找某种能承载剧本内涵和导演立意的载体,或某种体现出立意的样式,这种载体或样式是导演思维的关键。成功的演出,正是导演找到了能够恰当地体现全剧内在精神的载体和样式。当然不可否认,一个好的导演构思,一个完美的演出形式,一定是导演与剧作者在思想上的一种交融,他往往是导演与作者在精神世界里的某个交叉点迸发出来的火花。只是导演的思维更注重直观效果,更加地形象化。
以上三点,只是导演在构思舞台显现的思维活动中最简单和基本的特征。其实,导演的思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特别是随着现代戏剧观念的不断更新,导演主体意识在不断加强。过去那种导演主要依靠演员表演,着力帮助演员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间的冲突和思想感情,以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思维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现代导演从过去追求表象的逼真,走向了提示对象的本质和意蕴,并常常运用新的视听语汇对人物内在心理作外化表现。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性,而内容则趋于简括,往往是让内容直接凝结在形式之中,使观众在欣赏形式美上作一定的停留,欣赏形式美的同时就在体会内容。当然,真正做到这些也是极其不容易的,这需要导演在观念上不断地开拓与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