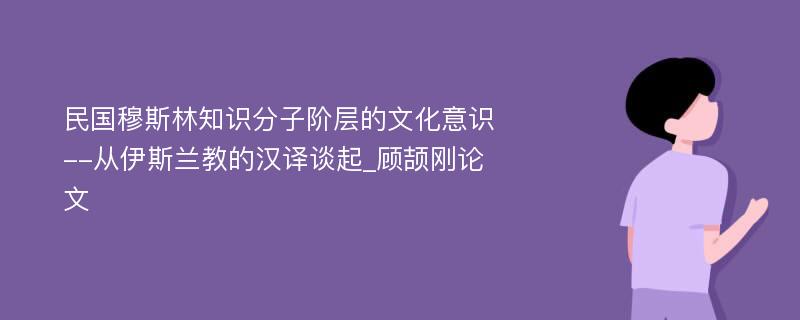
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从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穆斯林论文,译著论文,汉文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4)04-0082-06 一、问题的提出 每当谈及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及文化活动时,当代的学术界总会提到顾颉刚在《回教的文化运动》①一文中提到的“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1]。仔细考究发现,这个提法是针对北京知名阿訇王宽倡办新式教育而言。事实上,文化活动不仅包括教育,而且还涉及其他方面。正如同期的穆斯林学者赵振武所言,“中国回教文化”包括“回教的学校、著作及翻译、报纸、杂志、学术团体、图书馆及画报阅览室,以及书店印刷诸事业而言”[2]。一直以来,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穆斯林教育和伊斯兰教报刊的研究持续升温。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相继影印出版了《清真大典》、《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回族典藏全书》等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不仅有学术界熟悉的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而且还有反映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作及翻译”。关于前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很多,关于后者,迄今既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适当的学术定位,这不得不引起关注和思考。本文拟以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为例,初步探讨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 二、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与文化自觉 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振兴宗教 晚清以来,受科技革命和进化论的影响,各大宗教纷纷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以便适应新的时代。民国成立后,新政府颁布实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民的信教和出版等自由首次得到法律的保障,此举得到各大宗教信仰者的拥护与赞同。伊斯兰教界的代表张子文阿訇撰文指出:“从前专制时代,欲编译一部汉‘其他部’,政府就来禁止你出版;欲合一个者莫尔提(即聚礼)官厅就取缔你演说。”[3]他特别强调“历代专制国不准人民著作出版,未能将清真经史,早用中国文字语言,翻译成帖,坐是以亘古正教,卒不免庸俗之人訾议,良可悲也”[4]。信教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穆斯林的创作激情,在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基础上,他们继续著述立说,以此达到振兴伊斯兰教的目的。 张子文阿訇在《清真正史》中表达了希望振兴宗教的迫切愿望:“自海禁大开而后,中国人士,由外洋书籍,译其双爪片鳞,既失经传之真诠,且鲁鱼亥豕,毫厘千里,非特骇人听闻,重贻吾教之污点,亦为世道人心之隐忧。”因此他“久欲将吾教经传,译供众览,奈机遇不逢,徒切愿大难酬之虑。迨共和改建,平权自由之说,中于人心,其注重道德,保持公安者虽不乏人,而徒逞强权,不念公理者,亦数见不鲜,人心不古,习染其速,若不以宗教道德之学,急为引起人民之良心,使之祛妄归真,崇尚人道,将恐机械变诈,相习成风,国家既受影响,宗教岂能无虞”。[5] 民国五年(1916),王友三、王宽、张子文、王静斋、孙绳武等人在北京创办《清真学理译著》,在该刊发刊词中,孙绳武指出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存在的六个方面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措施。第一,教理晦秘;第二,学术废弛;第三,教师弱职;第四,教民蔽陋;第五,外侮频来;第六,生计日促。针对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孙绳武承认出版《天方学理译著》就是为了“倡扬蕴奥之教理,发挥宏博之学术”,“指导教师尽职之方法与表示教民守教之标准”,“倡明”学理,“使人无指摘(指责)之余地”。[6]尽管《天方学理译著》只出版了一期,但是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民国时期穆斯林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六个问题而努力改变自身的现状。 马健之阿訇在给弟子许子斌《回民常识课本》的序言中强调振兴宗教的必要性,他指出:“夫我伊斯兰者,真主所建设,圣人所保守之宗教也。故其兴衰,匹夫有责焉。当兹科学昌明,文化蓬勃之秋,举凡宗教事业,莫不奋起直追,以谋其兴盛与巩固。我人何能因循以闭关自守乎?基此,振兴宗教,乃刻不容缓之要图。振兴之策,不外发展教育与宣传教理。欲发展教育,非设规模完善之学校不为功;欲宣传教理,非有显明造宜之课本不济事。子斌同志最近所编之常识课本,既明且显,适合初学用作教材,读者当受益不少也。”[7] 总之,在清末民国时期,振兴宗教成为各大宗教界的共识,这不仅是由时代决定的,而且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然而,宗教本身是静态的,是不变的,人作为宗教的信仰者,是动态的,是可变的,宗教昌盛与发展和宗教群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民国的穆斯林学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要达到宗教的发展目的,首先要解决穆斯林的宗教学识问题。穆斯林对宗教的认识和实践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宗教的发展程度。 (二)关注教内缺乏宗教常识的群体 明清以来,普通穆斯林大众对伊斯兰教缺乏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已经是普遍现象。民国以来,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接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中出现怀疑宗教的现象。为了消除这种现象,一批穆斯林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 山西政界的穆斯林官员马骏在给河北宣化马耀庭《教典辑要》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近世以还,日渐陵替,本教同人除少数深明经典外,余皆惟知身属回教中,人问以教中精义,则茫然莫解,斯皆由于读圣经者仅明条规,读儒书者不识经文所致,他如不识经文,不读儒书者更不足论也。……上谷马君耀庭,幼娴熟经义,长读儒书,慨我教之式微,乃译经汇说,著教典辑要一书,为初学作指南,冀正教之日上。”[8] 固原的虎嵩山阿訇在《伊斯兰教三字经》自序中指出了撰述的缘起:“我国教胞率能自幼入塾读经,然每因文字之隔阂,教授之陈腐,或家庭环境之变迁,往往不能克竞学业,半途而废者,在所多有。此种读经而未明其意之人,既无阅读阿文经典之能力,即其终身亦无由知其所当知之机会,以致信教有心,奉行无本,甚者以讹传讹,乖谬百出,派别纷歧,团体涣散,教将不教,遑问其用。”[9] 北京穆斯林学人杨少圃创作《伊斯兰教义概说》也是为了解决教内穆斯林缺乏宗教常识的问题。他指出:“嗟夫,晚近以来,世风日下,教势颓废,濒危于淘汰,教民愚昧,彷徨于歧途,乘真理而不究,背正路而奔驰,遵经圣谕,置若罔闻。人情风俗,视为急务,前途渺茫,何堪设想,尤有甚者,厥为青年,幼而失教于小学,继而失教于中学,辄被基督化及无教派之教师所熏染,或被异端左道似是而非之谬说所阻挠,扑朔迷离,罔知所皈,或竟烟嫖博饮,或竟谗簧谤教,固非教义之不真,教道之不正也。”[10] 另外,《清真必读》、《开礼麦讲解》、《穆明学要》、《宗教正基》的作者也都非常关注教内穆斯林失学的情况。以上著作大都是为缺乏宗教常识的穆斯林而准备。从民国伊斯兰教发展史来看,这种教内自救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广大中下层穆斯林的认可,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发展。在解决缺乏宗教常识群体的问题后,对宗教略知一二,但又囿于宗教内部细节或者礼俗的穆斯林也不在少数,如何化解穆斯林内部的分歧,强化内部的团结,是民国穆斯林知识分子探讨的话题。 (三)消除教内的弊端或纷争 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权的更替,而且民俗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新旧文化交错冲撞,而且中西文化也开始融合互相影响,整个中华文化都处于剧烈的变革和演化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穆斯林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主动承担起阐扬伊斯兰文化的角色,及时剔除了伊斯兰教内部的一些礼俗或者陋习,有效地维护了穆斯林内部的团结。 王静斋阿訇在《选译详解伟嘎业》中表达了消除教内积弊的愿望。他指出:“自海禁大开以后,印版可靠的大经充满华夏,参考有据,正是学者藉资猛进之良机。然实地考查,在我华北,并末见显著之发展。有的讳病忌医,依然展转敷衍,以为不如此,不足以维持旧观,有的立志较坚且有系统的宣传,但因处于四面楚歌地步,苦于无从着手。今天,鄙人遍观潮流所趋,拟作一个空前的大揭审,志在扫除多年积弊,故有《伟嘎业》之译。”[11] 河南穆斯林学人王象贤对教内“流风遗俗”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为洪宝泉阿訇《明真释疑》所作的序言中他指出:“后世学者遗本逐末,徒以才华相尚,矜奇立异,自以传说为是,谬解学说,不明真传,卒使古圣贤之大经大法,尽败坏于浅学误解之下,良可慨也。开封洪宝泉阿衡者,心焉忧之。慨然以阐明教道为己任,殚精竭虑,丛集前贤百十卷之著作,以资考证,翻译成帖,批阅了然,俾皆知我教之真传,既非宥于风俗,亦非从乎于习惯,世代遵守,垂鉴永远,则亦我教道之幸也夫。”[12] 湖南张春三阿訇等编著《回文读本》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消除教内的误解或者容易引发误解的一些教法问题,他强调:“吾国地处东土,当夫海禁未开,教律经之来者鲜,大道真谛,无由阐扬,市虎杯蛇,教民互以谬说相传,而其子孙替袭,尤视为金科玉律,行久成习,遂坚不易改。迩者,文明进化,东西各以学术相磨砺,吾教律经,亦涉重洋,远莅华地,海内明达,群起讨论,同人等研究之余,则有无任惊惶且惊惧者。盖教律经之所载,劝诫悉据主圣之谕,而东土所行多流风遗俗,为后人之误会者,如是南辕北辙,大与正道背驰,而教人奉之若主命圣行,似此能不令人惊惶惊惧!同人等既幸觉其谬,敢不公诸世人,促其省悟,尚冀海内明达诸公。各抒己见,共挽狂澜,则大道幸甚,同人幸甚。”[13] 河南的马广庆阿訇通过《答王殿辅阿衡书》,希望消除伊赫瓦尼和格迪目之间的分歧,并且呼吁格迪目派的阿訇将有争议的教法问题刊登在穆斯林报刊上,“请四海学者指示”,他们“定有公判”,这样“尤可增进”两派学人的“见闻学识”。另外,马广庆也指出,王殿辅阿訇撰写的劝告书中“含有危险言词,教胞贤明者,一视即明,不至于误会,而教胞重,恐有知识薄弱者,倘发生教祸事端,殿辅应负其责。儆吾为慎重防范计及地方治安起见,拟将殿辅劝告书呈请现地长官备查,以明责任,而防不测也”[14]11。 的确,中国穆斯林关于伊斯兰教大原则方面的遵守是一致的,然而,在礼俗、葬俗和婚俗以及部分教法方面的分歧较大,社会影响也很大,民国穆斯林学人试图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对这些有争议的话题作公开的探讨和说明,以达到强化内部团结的目的。事实表明,礼俗文化具有相应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或者消解,但能达到相互的谅解,在“各干各得”的原则下,穆斯林内部仍然能形成团结的氛围。然而,教外的误解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消除外界的误解 民国时期发生了许多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有关的教案,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甚至出现打砸出版机构或者报社的事件。对于穆斯林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并未将这种误解归咎于教外人士或出版机构,而是归于穆斯林自身,他们认为外界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大量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翻译伊斯兰教的经典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为此他们主动承担起这种文化自觉的重任。 北京的追求学会成员对“侮教案”进行了反思,将责任归咎于穆斯林自己身上。在他们看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性的著作太少也是导致人们误解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尽管中国有“几千万”穆斯林,但汉语的伊斯兰教研究性著作只有“十数本”,不仅如此,就连《古兰经》“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华文译本问世”[15]。为了避免“侮教”事件的再度发生,他们希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研究学术的团体”,将“研究教义或译读宗教书籍,作为全体会员必作的工作”[16]。 政界穆斯林官员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是因侮教案而作,其目的“使教内外之人,一读此书,即能瞭解伊斯兰义谛,而益坚其信仰之念或自拔于迷误之途,一在消除群疑,使凡轻视伊斯兰及诋毁伊斯兰者,一读此书即爽然自悔前日之非,并肃然而起终身之敬”[17]。 青年时期的纳忠翻译《伊斯兰教》一书主要缘于早年非穆斯林同学在他的“干粮中偷偷地放了一些猪油”,使他“怒火中烧”,于是相约两个同好,在放学的路上“教训这几个肇事者”,校长追究此事,他们三人中的一个“被判了主动的罪名,悬牌斥革”,他和另外“被罚了二十个手掌”,施放猪油的几个“也被罚了十个手掌”,学校还书面责令家长“从严管束”,他回到家里又“挨了一顿”打。他这样写道当时的心境:“我的心上好像被锋利的雪刃刺了一下,留下了不能复原的一道创痕了。”[18]他后来不断从事翻译,就是为了消除国人的误解,避免更多的穆斯林学生重蹈他当年的覆辙。 历史的发展表明,民国学者出版了多部介绍伊斯兰教的著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不仅消除了教外的误解,避免了教案的再度发生,而且推动了民国教外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穆斯林知识阶层在应对教外误解的同时,他们还面对来自基督教界的批评与指责。 (五)回应基督教界的批评与指责 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扩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成为基督教传教士关注的重要群体之一,除了直接向穆斯林宣传以外,传教士还以基督教的视角,或与穆斯林辩论,或著书立说。基督教界对伊斯兰教的诠释给穆斯林知识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各种攻击和歪曲面前,他们不得不被动出击,或辩论,或著书立说予以回应。从被动到主动,反映了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 为了回应《回教考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上海穆斯林委托安徽怀宁穆斯林学者马介泉撰文予以回击,他在《回教考略书后》的文章中指出:“日者沪上吾教同人,以英人季理斐所著《回教考略》一册见示,并约共参其得失。介泉于阿拉伯文字,未尝学问,宗教思想,又极浅薄,是何足与言宗教哉。无已,请就昔日趋庭时,侧闻先君所言之余绪,一正其异同,而为之书后。第废书已二十年矣,文词杂糅,自知不免,尚祈阅者谅之。”[19]154 河南淮阳穆斯林范槐堂是晚清的贡生,在《回教辨真》序中,写道:“道不讲不明,教不阐不张。吾教学者,多抱闭关主义,深恐旁人瞻我门墙,窥我堂奥也。无如天主、耶稣等教,树帆挑战,或著《回教考略》,或著《回教求真记》,要皆本臆说,以蛊惑人心。许阿衡友义,素具卫教热忱,复批阅稣教典籍,遂指其误而辟其谬,著为此编,词虽简而指颇明,事虽略而理甚畅。”[20] 在《回耶辨真》的译文序中王静斋阿訇同样表示:“余尝批阅彼教公会所出之《回教考略》、《诸教参考》等书,其诬我诋我之言,读之不禁扼腕,咨嗟唏嘘。” 《真道溯源》的作者四川穆斯林马叶飞②同样表达了写作的原因和目的,以示人以真理,消除谬误。 由于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反面宣传和歪曲论述,引发了穆斯林大规模的回应,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比较的著作。虽然民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辩论比较激烈,但是通过关于宗教间的相互阐释和互动回应,客观上推动了民国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在解决了内外交困的问题后,民国穆斯林试图通过汉文译著活动,发挥宗教在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六)挽救世道人心 民国时期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潮在中国社会都有存在的影子。在这样的转型时期,宗教界极力宣扬自身宗教的道德教化,试图在新的生活条件下发挥宗教的作用。中国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积极阐扬宗教教义,试图通过道德教化,挽救世道人心。 马骏在《清真要义》中表达了挽救世道人心的看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人不可须臾离,教也者,世不可一日无。虽然世界之教不一而足,教中宗旨各异,岂可概论哉,如孔教注重伦常,天耶颇重慈善,惟传教士之来华多含有政治之意味,乃为美中不足耳。道佛二教在中国已流为一种烧香、祷告、募缘、度生之状况,犹太教仅一少数,他如拜火、拜木、拜石、拜牛蛇等教可不置议。我回教本真一之精神,包平民之宗旨,适合共和之潮流,可惜者教中人多不学无术,不惟不能推阐教旨,使世人了然我教之美善,而一般顽固者抱固守主义愈行愈狭,几使本教人亦不知其所以然,误我回教殊非浅鲜,此有心者甚以为忧焉。余对宗教素乏研究,所知者不过天经之大义,教规之常行,或得之汉译各书,或闻之教中阿衡要旨,皆有益于世道人心者。”[21] 张子文在《清真学理译著》序言中强调翻译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迫切性:“近观我国一般狂士,咸以宗教为障碍物,故妄倡改良社会,不尚宗教。意在败坏道德,扰乱伦常,呜呼,人心日浇而日漓,社会愈趋而愈下,舍我宗教何以维持世界之颓风,惟我清真教人,历居中国,论婚丧礼祭,风俗习惯,与汉人无甚差异,但因信仰之不同。与夫教旨之相殊,自不能不略有区别,察清真教经典纯系阿拉伯文,而汉译典章尚付阙如,不惟教外人士多难谙其底蕴,即本教同人茫然于教理者,亦实繁有徒,是我教所有不能扩张之一大原因也。”[6] 马善亭在《说回教》一书中特别强调宗教能弥补法律之不足。他说:“盖法律,偏重行为证据方面,而不能杜绝生恶之源,宗教乃行为意念兼重者也。无证据之恶念,法律不能处罚之……法律惟能裁判人身,但不能限制其心,法律仅治其表,而不能限制其心。人民若有宗教之信仰,其念必正,其思无邪,有正念,无邪思者,断不能起恶意,而有不正常之行为也。是宗教包括法律,而法律不能替代宗教也。再者,宗教是领导潮流的,包括人类行为,应付社会变化,思想进步的。故宗教无时或穷,况其命令禁止之中,皆有当然及所以然。而法律是追随潮流的,故其增删无定。”[22]8 自清末以来,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否定自身文化传统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地位发生动摇,一批知识分子号召以新文化运动代替旧有的文化。在这种思潮和意识的影响下,一批学者在反思儒家传统的同时,并未抛弃中国文化的价值,而是在新的时期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取舍、补充和诠释,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缔造了一批具有民国社会文化特色的新一代穆斯林学人。他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去“以儒诠经”文化套路,他们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自身所面临的内外交困问题,主动对伊斯兰教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表述,出版问世了一批有影响的汉文译著。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并未因清朝统治的结束而停止,到了民国时期有了新的内容、变化和特色,扮演了新的角色,发挥了新的作用。这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研究。 ①自从1992年以来,关于《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的署名问题引发很大的争议,白寿彝先生将该文收在同年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以及后来出版的《白寿彝文集:民族宗教论集》,特别强调该文系“代顾颉刚先生作”。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将该文收入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中,认为该文系其父所作。查阅历史发现,该文最初是白寿彝草拟,经顾颉刚修润,最后以顾颉刚的名义发表。对此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3月2日,将寿彝文另作,成《回教的文化运动》,二千五百言,即寄《大公报》。”民国三十三年,顾颉刚将该文收入其打算出版的《顾颉刚文集》中,特别强调该文“承白君(白寿彝,引者注)供给好些材料,作于二十六年三月二日,发表于同月七日天津、上海两处《大公报.星期论文》,转载于《禹贡半月刊》。”可惜该文集未能出版,直到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事实上,该文在当时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师校刊》不仅对顾颉刚的学术活动作了重要介绍和评价,特别强调该文为顾颉刚先生所作,而且将该文翻译成阿拉伯语,在该刊连载。顾颉刚很重视这个评价,曾将该杂志的介绍短文剪贴下来,附在日记后面。同样,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白寿彝在桂林主编《月华》时,曾公开提到“去年三月间,顾颉刚先生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该文。 ②清真书报社民国十四年出版的《真道溯源》没有作者的署名及相关信息。而在该报社主办的《正道》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中有该书及作者的信息,署名作者是马叶飞。关于马叶飞的籍贯、生平事略,详见《四川安县属之回民概况》,《月华》第七卷第三十期。余振贵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一书中认为《真道溯源》的作者是马宏道。2008年出版的《回族典藏全书》第四十五册收录了清真书报社的《真道溯源》版本,在总目录中,沿袭了余先生的说法,将作者署为马宏道。标签:顾颉刚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穆斯林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文化自觉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