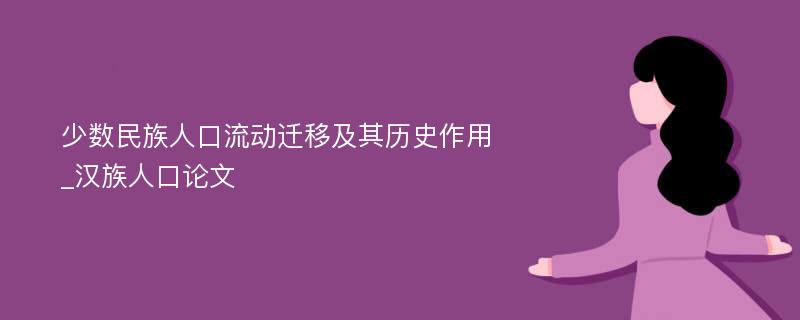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人口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与民族众多。古往今来,人口的流动与迁徙纷繁庞杂,并对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发展乃至整个的历史进程,都有着十分重要而又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对我国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的总体趋势与历史脉络、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的现实状况与时代特征,特别是由此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略作讨论与探索。
一、我国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的总体趋势和历史脉络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若撇开先秦之世暂且不说,仅以纪元前后秦汉“大一统”时期中原华夏诸族与南方江汉平原的楚人、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四川盆地的巴人和蜀人、以及关陇一带的秦人及部分古羌人相融合,汉民族最终形成并确立主体民族地位以来而言,总体上呈现出两大历史趋势:一是汉民族从以黄河中下游一带为核心区的东部地区,呈放射状向包括东南沿海台湾、海南诸岛在内的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二是周边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其中又以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并推动汉族向南迁徙为主导形式。两大历史趋势的形成,都有其极为深厚的自然地理根源、社会历史背景和诸多错综复杂的其他因素,共同构成了2000多年来我国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的基本格局和主旋律。
纵观我国自秦汉以来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仅人数较多、规模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的便达上百次。其中,汉族人口向周边地区的流动迁徙,主要有秦朝年间为“北击匈奴、南开五岭”而向北方河套地区和东南岭南一带遣发的数十万汉族将士,西汉中叶汉武帝“开三边”时向西北、西南、东南、东北等周边地区组织的大规模“徙民实边”,唐朝初年重新开疆拓土设置安西、安东、安北、安南四大都护府时前往屯垦戍边的汉族军民,明初“洪武开滇”时在今云贵两省布置的大面积军民屯田,清初康、雍、乾三朝历时100多年的汉族移民潮“湖广填四川”,近代以来北方汉族农民自发性的“闯关东”、“走西口”,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军民向川、滇、黔西南三省的大撤退,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向大西南、大西北及海南岛的胜利进军和就地驻防等等。
相形之下,周边少数民族向靠内地区的迁徙流动更为频繁。其中最主要的有:东汉至三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内乱分为两部后,南匈奴的“内附入塞”和鲜卑、羌、氐、羯诸族的接踵而来,两晋之世上举“五胡”诸族的进一步南迁和“十六国”的建立,南北朝时鲜卑拓跋氏建北魏、东魏、西魏和宇文氏建北周,隋唐时突厥、回纥、吐蕃三大强族的南下与东进,两宋时期北方契丹、东北女真、西北党项等族的相继南下和辽、金、夏三朝的崛起,以及后世蒙古族、女真后裔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和元、清两大王朝的建立等等。其间,由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推动,汉族人口向南方迁徙的则主要有两晋之际南迁匈奴人建立的北汉政权攻破洛阳、长安即“永嘉丧乱”时数百万北方汉族的第一次大南迁,唐代“安史之乱”时北方汉族的又一次大南迁,两宋之际金灭北宋即“靖康之难”前后中原汉族的再一次大南迁等等。
诚然,以上所叙仅仅只是粗线条的历史脉络。事实上,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上起先秦下迄当代,起伏跌宕而从未完全中断过。特别是守望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世代逐水草而居,四时往来游牧不定,虽历数千年时光而故俗不变。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的现实状况和时代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从此跨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坚持奉行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兄弟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基本政策,除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外,还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在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致说来,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在这一历史阶段内,党和政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国防和开发边疆,曾陆续向边疆民族地区组织了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支边活动。其中规模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的主要有:1952至1954年人民解放军部分驻新疆部队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就地“屯垦戍边”,60年代“三线建设”高潮时沿海部分大中型企业向西南、西北地区的战略转移,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期北京,上海等内地大中城市“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北大荒、内蒙古、新疆、云南、青海、海南等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屯垦戍边的“上山下乡运动”等等。而穿插其间的,还有通过历年来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分配、退役退伍军人安置、在职人员工作调动以及招工招干等多种方式,向边疆民族地区大批输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精壮劳动力。据有关资料显示,仅解放初期的1950至1956年,上海市便向以边疆民族地区为主的全国各地输送此类人员20余万人,[1]加上随行家属可达四五十万人。而在这一阶段内迁往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类“支边人员”,即使是扣除1979年“百万知青大返城”时回迁的数百万人,亦可达上千万之众。
而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束缚,致使这一时期我国的宏观人口布局,整体上陷入一种超稳定的僵滞状态。其间,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除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和边境沿线地带出现部分边民外流之外,主要是通过为数有限的招工招干、参军服役、外出上学和探亲访友等途径来实现。当然,其间也有个别特殊情况,如在1958至1960年间的“大跃进”运动中,因举国上下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而一度造成工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剧增,于是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农村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和工矿厂场。及至1961至1963年进行调整时,又有2600多万进城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1]当中不乏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
第二阶段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目前。
值此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流动迁徙也日趋活跃起来。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70年代末由农民进城而发端,以后迅速扩大蔓延,到90年代中期便已席卷全国并持续至今的人口流动大潮。据调查,当前我国的人口流动,流向上主要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由边疆民族地区流往内地,由中、西部地区流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但同时也存在反向对流的情况,展现出一幅波浪壮阔的宏大画面。另据调查,在现阶段的流动人口中,以来自农村的打工人员为主,足迹遍布三大产业的各个领域而以第二、三产业较为集中;年龄以16至40岁间的青壮年居多,性别则男性略多于女性;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一般为中、小学毕业,间有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者和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流动人口的整体数量,目前已突破一亿人大关,[2]其中少数民族约占5%左右即500余万人,族属上则揽括了我国现有的各少数民族。对于现阶段我国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的总体评价,因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而尚待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和讨论。其中仅就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而言,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在时间上,阶段性特征明显。具体说来,一是在前一阶段即新中国建立到三中全会前夕的近30年里,人口流动的主体,是内地汉族人口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而后一阶段则呈现为双向对流的格局。二是前一阶段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类“支边”人员,一旦抵达之后,通常便长期落籍定居下来,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而后一阶段则无论是汉族人口流往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流入内地,都缺乏相对的稳定性,基本上属于流动人口的范畴。三是前一阶段的人口流动,几乎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安排下按计划有序进行,后一阶段则多属在市场调节下的自发行为。究其所由,上列诸多不同点的产生,主要又与前后两个阶段国家分别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直接相关。
其次是在性质上,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不论其动因、形式、内涵、人数、流向如何,整体上都属于以经济为主要目的正常范畴。历史上那些由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引发的各种形式的非正常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基本不复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阶段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总体时代特征。
其三是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迁徙正呈逐渐趋缓之势,即使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相当一部分各民族群众正陆续放弃“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向定居、半定居过渡。与此相反,少数民族人口向城镇和内地的流动,则呈现出日益频繁的上升趋势。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的历史作用
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少数民族古往今来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不仅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人口与民族分布宏观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特定的社会功能。现分述如下。
其一,对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意识最终形成的促进作用与社会功能。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的总称,在内涵上既是一个民族族群体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共同体的综合概念。大量事实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对于中华民族族群体的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形成,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特定的社会功能。主要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相当一批古代民族特别是内部结构较为松散的原始游牧族群,在漫长的流动和迁徙过程中,由于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发生变化而引起生产生活方式变更后,内部出现分化而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成为不同的民族,促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得以不断增加,族群体不断发展壮大。较具代表性的实例,如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合计总人口超过1000万的彝、白、哈尼、拉祜、纳西、傈僳等同源近亲民族,据研究都出自远古时期活动在西北甘青高原上的古氐羌游牧族群,后因人畜繁衍等种种内外因素扩大游牧范围陆续向南迁徙抵达云南高原腹地及其邻近地区。再往后,又因地理环境的改变而陆续由游牧转化为农耕,并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或不同的地形层面上形成不同的民族集体。[3]
二是随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而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枝繁叶茂。主要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融合型民族的形成,即由来自异国他乡、五湖四海直至大洋彼岸的外来移民,进入我国境内后逐渐融合形成的新型民族集体,较典型的又当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回回民族。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较一致的意见,回族在族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陆续取道海、陆两路来华经商留居我国境内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及至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先后击灭西夏、金和南宋统一中国建立蒙元王朝的过程中,一批批蒙古铁骑西征时从西亚、中亚以及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西域等地带回的穆斯林,又随之移居我国各地。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这些分别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以至不同种族的穆斯林,因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并在风俗习惯上颇多一致而“居必聚族,行必结旅”,久而久之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之林中的又一新成员。类似的情况,还有西北地区的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也都是经长期迁徙流动和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年轻的民族集体。[4]
另一种是植入型民族,即通过人口的迁徙流动,从周边邻国植入的民族集体,如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朝鲜族,就属于这一类型。众所周知,朝鲜族是朝鲜半岛上我国近邻今朝、韩两国的主体民族,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后,大批不甘忍受奴役的朝鲜族人口纷纷越过中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与先期迁入的本民族同胞汇合后,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并从此在中华母亲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与朝鲜族相类似的植入型民族,还有来自越南的京族(旧称越族)和来自俄罗斯的俄罗斯族等等。[4]
三是在纷繁复杂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中,我国各民族在加强了交往联系的基础上,进而发展为相互之间的民族融合。其中,既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又有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同时还有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更为广泛频繁的相互融合。从而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自古便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兄弟关系,并在文化上产生诸多共同的基因、心理上具有相互的认同感。延至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东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之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最终形成,成为支撑我国各兄弟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又成为我国各兄弟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基本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得以不断强化深入人心。
总之,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无论是在中华民族族群体的发展壮大方面,还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方面,都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社会功能。
其二,对我国人口和民族分布宏观格局形成的影响和作用。众所周知,作为我国人口和民族分布格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呈现出相互穿插、交错杂居的局面。从较大程度上讲,这种“大杂居,小聚居”和“杂居中有聚居,聚居中有杂居”民族分布宏观格局的形成,乃是历史上和今天人口流动与民族迁徙的直接结果。其中,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位列第二的满族,便是一大实例。满族发祥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我国东北地区,其先祖曾于历史上建立过“渤海国”和金国两大地方民族政权,及至公元17世纪初又建立后金(后改清),并于明朝末年继金国之后再次入主中原建立满清王朝。据历史文献记载,清兵入关前满族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分布在东北,主要又集中在今辽宁一带。以后分为三部分,分别留守关外、驻守京师(北京)和驻防各省,后两者称“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由此,满族人口的分布也从以往多囿于东北一隅迅速扩散到全国大多数地区,而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远者甚至深入到西藏、新疆、云南等边远省区,其中不少后来还成为当地的世居民族传衍至今。[5]与满族相似的还有蒙古族,例如今天分布在远离蒙古大草原的一万多云南蒙古族,据研究就是元朝时期驻滇蒙古将士的直系后裔。[3]
至于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大潮,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多民族大杂居局面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大批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内地,大大拓展了相当一批少数民族的空间分布面。如在当今的中国,维吾尔族的踪迹早已不限于新疆一地而是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的还在不少城市中形成特定的聚居区,即被当地群众习称为“新疆街”的维吾尔族社区。这一新情况,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屡见不鲜,即便在偏居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及其他中小城市也同样存在。而另一方面,以往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边境沿线地带,也随着内地流动人口的陆续到来而出现多民族杂居的局面。据调查,在边境沿线地带的部分口岸、城镇和矿场,以汉族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已超过乃至若干倍于当地少数民族,如位于中缅边界上段高黎贡山深处的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片马口岸,当地居民傈僳族、景颇族仅一两千人,各类外来流动人口则高达五六千人。[6]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基础上,已在实际上改变了这一地区人口结构要素中的民族构成比重。
其三,对边疆开发建设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家园,古往今来,各兄弟民族都为开发建设这片辽阔而美好的土地立下过不朽的功勋。而在广大的边疆地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从遥远的古代起就为祖国边疆的开发建设作出过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其中,大多数的早期开发和建设,又都是伴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而进行的。
少数民族及其人口流动迁徙在祖国边疆开发建设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数藏族及其先民对我国西藏及邻近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研究,藏族与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属近亲民族,同样源于西北甘青高原上的古氐羌游牧族群,先秦时其中的“发羌”等几支陆续越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部分滞留藏北高地与“唐牦”等当地本土民族融合成为今羌塘地区藏族的先祖,其余的大部分仍继续向南迁徙抵达雅鲁藏布江沿岸的藏南谷地直至喜玛拉雅山北麓地带,经与当地本土民族融合后成为西藏腹地的主体民族,以后又向东部藏东川西高原、东南部滇西北迪庆高原,以及藏西阿里高原迁徙扩散,发展成为以当今西藏为主要聚居区,地跨相毗邻的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广大地区的藏民族集合体。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高原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多变,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但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先民,不仅于公元7至9世纪间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而且创造出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独具特色的藏民族文化,对西藏及邻近藏族分布区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另据记载,与藏族相类似的,还有起源于今黑龙江支流之一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族对蒙古大草原的早期开发,以及发祥于蒙古草原深处的维吾尔族及其先民对新疆的开发等等。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历史上和今天的人口流动与迁徙,不仅对于中华民族族群体的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及我国人口与民族分布宏观格局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同时,在流动与迁徙之中,少数民族还对祖国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不过,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对此要特别一提的是,人口的流动和民族的迁徙,并非总是蓝天白云、鲜花草地、风和日丽,更多的还是一路风尘、饱含艰辛,特别是历史上那些由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更是与饥寒相随、与苦难同行的亡命天涯之旅。而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大潮,在活跃经济、繁荣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对环境和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与冲击,造成城市拥挤、能源紧缺和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此,需要加以辩证地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