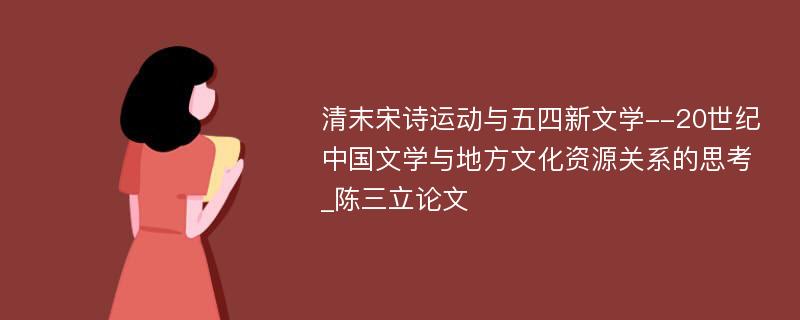
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本土文化资源关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晚清论文,本土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咸以降,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是宋诗运动。不仅当时文坛的主要人物在文学主张上都倾向于效法宋诗,如程春海、何绍基、祁春圃、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反对专事盛唐,强调学宋诗,特别是学黄庭坚;而且这一派的影响所及,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晚清文学(注: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有“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思(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如前有程、何、曾领衔的“宋诗派”,后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诗人。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前,宋诗运动是文学领域中最具影响的文学思潮。理所当然,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也最为直接,如文学革命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深受宋诗影响,胡适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指出:“说到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他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以说完全是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注:胡适:《阿独秀与文学革命》,参见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9页。)胡适自己也受到宋诗运动的影响,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他记叙晚清宋诗运动对他的思想影响时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如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注:参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98页。)然而,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很少注意到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更没有人愿意肯定晚清宋诗运动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研究状况,我以为直接的原因来自两方面。第一,受到胡适等人的思想观点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章中,侧重强调晚清宋诗运动的消极影响,甚至将它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来理解(注:胡适在留学日记、《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等文章中,反复批评陈三立、郑孝胥等人,认为他们一味模仿古人,缺少时代感。),这一观点流波所及,使得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无形中接受了胡适的影响,较少关注晚清宋诗运动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正面影响。第二,在对待晚清宋诗运动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上,研究者往往被这些宋诗运动代表人物主张宗宋,效法黄(山谷)、苏(轼)、王(安石)、陈(师道)的表面文字所眩惑,而忽略了晚清宋诗运动的真意所在。换句话说,研究者只注意到晚清宋诗运动代表人物师法宋诗的一面,而很少考虑清代诗人为什么一改明代崇尚盛唐诗的做法,偏偏去师法宋诗的原因。鉴于以往文学史研究对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误认,也鉴于晚清宋诗运动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关系,我以为有理由梳理这种文学史的影响关系。
一、如何看待晚清宋诗运动的产生及其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
宋诗运动尽管到道、咸年间才处于鼎盛时期,其实,从清代一开始,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便改变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师法唐诗的做法,而转向学习宋诗。黄宗羲在《诗历·题辞》中认为“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注:黄宗羲:《诗历·题辞》,见《四部备要》本《南雷诗历·题辞一》。)在《张心友诗序》中,他提出:“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其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诗也。于是搢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注:黄宗羲:《张心友诗序》,见《四部备要》本《南雷文定·卷一》。)黄宗羲经国朝之变,深切感受到明代诗风的空疏,遂反对前后七子将诗风定于一格的做法,力倡学习宋诗,强调“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莫非唐音”(注:黄宗羲:《张心友诗序》,见《四部备要》本《南雷文定·卷一》。)。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合辑《宋诗钞》,宋诗对清初文坛的影响由此逐渐扩大。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等倡导宋诗,一方面是强调宋诗的内容,要求“艺苑还从理学求”(注:黄宗羲:《与唐翼修广论文》,见《四部备要》本《南雷诗历·卷三》。),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将诗歌创作定于一格,认为学宋并不妨碍学唐诗,宋诗也是从唐诗演变而来的。到乾嘉之世,翁方纲以“肌理”之说,校王渔洋的“神韵”说之弊。在诗歌创作上,翁方纲师宗苏(轼)、黄(山谷),他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注:《石洲诗话》卷四第十三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123页。)。针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谓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注: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的观点,翁方纲强调“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注:翁方纲:《志言集序》,见《复初斋文集》卷四。),认为“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注:翁方纲:《蛾术编序》,见《复初斋文集》卷四。)所以,翁方纲尽管与清初黄宗羲等人一样,也要求师法宋诗,但明显的是黄宗羲等人的“经世致用”的内容减弱了,而考据训诂等学问内容增加了。故《晚晴簃诗汇序》称清诗“
爻核坟典,粉泽《仓》、《凡》,证经补史”(注: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这种诗论及诗歌创作内容上的变化,显然与翁方纲所处乾嘉之世学者文人崇尚朴学的风尚有关。
同、光时期,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为代表的诗人,对宋诗之法做了更自觉的宣传,使整个晚清诗坛笼罩在效法宋诗的气氛之中,形成了“同光体”诗派。这一诗歌流派的理论代表人物陈衍在《沈乙庵诗序》中对“同光体”作了具体说明:“‘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注:参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85页。)“同光体”诗人比师法宋诗的前代诗人更进一步扩大了对宋诗的学习范围。以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以陈衍、郑孝胥、陈宝琛为代表的闽派与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派诗人,在宗宋的同时,各人师法对象不完全相同。赣派以黄庭坚为宗师,兼学梅尧臣,代表诗人陈三立“恶俗恶熟”,化用黄庭坚的“点石成金”之法,力求在字句上翻新出奇。闽派溯源韩(愈)、孟(郊),于宋人偏重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姜夔。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有“三元”说,认为诗应推本唐宋的开元(杜甫)、元和(韩愈)及元祐(黄庭坚)(注: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认为:“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参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上)》,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代表诗人郑孝胥的诗风凄婉深沉,语言较为流畅,在答樊增祥的诗中,郑孝胥提出“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注:郑孝胥:《答樊云门冬雨剧谈之作》。)诗风与赣派陈三立诗的“生涩奥衍”形成对照。浙派代表诗人沈曾植论诗有“三关”之说(注: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说:“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参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上)》,第455页。),溯源六朝的颜(延之)、谢(灵运),要求经学、玄学、理学一起打通。由于沈曾植学问渊博,故诗中大量运用僻典奇字,使得诗风“雅尚险奥,聱牙钩棘”(注:陈衍《沈乙庵诗序》中语,参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385页。)。“同光体”诗派内部风格的差异以及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诗风上的差异,说明宋诗运动在晚清仍处在不断的探索、发展过程之中,作为晚清诗坛的主流,“同光体”诗人仍在努力表现外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扩大诗歌创作的表现力度。一般研究者在评价“同光体”时,往往强调“同光体”师法黄庭坚、梅尧臣、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雕章琢句,翻新求奇,力图化腐朽为神奇这一面,而对于“同光体”要求雕琢须从自然出这一面却注意较少
。我们看到,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三派诗人,论诗中都主张遵从自然情感。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中说:“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注:参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上)》,第521-522页。)在《近代诗钞·沈曾植》中,陈衍又说:“诗虽小道,然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足以发明哲理。”(注:陈衍编辑《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84页。)郑孝胥力主诗歌要平易畅达,他称颂江湜的诗“笔力精深语能浅,诗境尤难在逼真。”即便是以诗句“声涩奥衍”著称的陈三立,在“恶俗恶熟”的同时,还有追求自然平实的另一面。如,在《陶渊明》一诗中,他称颂陶“此士不在世,饮酒竟谁省?想见咏荆轲,了了漉巾影。”(注:陈三立:《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陶渊明》,参见陈衍编辑《近代诗钞》,第997-998页。)在《黄山谷》中,他又推崇黄诗“馋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注:陈三立:《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黄山谷》,参见陈衍编辑《近代诗钞》,第998页。)认为诗句的锤炼,终须以自然的面貌呈现。沈曾植作诗喜用僻典奇字,但也有字句极为平实的诗作,如《题赵吴兴〈鸥波亭图〉》、《简天琴》、《懊侬曲》,写得浅易平实、清言见骨。“同光体”诗人这些自然平和的诗句,较多反映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或体现他们对古往今来时事的感叹,如陈三立、沈曾植反映戊戌变法及外国列强危害中国的一些诗篇,不仅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诗句也较为浅易。至于“同光体”诗人的诗作大多字句深涩枯冷,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因为有些是属于个人的艺术风格问题。我们不应一味要求诗人都去作浅显平易的作品,更何况辞意朦胧、字句深涩的好诗妙句,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像陈三立的《江行杂感五首》、《由沪还金陵散原别墅杂诗》、《春晴步后园晚望五首》、《正月十九园望》等诗,沈曾植的《偕石遗渡江》、《西湖杂诗十七首》等诗,都有其充实的内容,并不因为字句深涩而失去其艺术价值。对于另一些属于形式技巧探索的诗句,也应有所肯定。“同光体”诗的深涩奥奇,在艺术上当然并不全都是成功的,但这些诗人用心良苦。应该说,“同光体”诗人在晚清诗人中,对社会政治的了解是较为深入的,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都直接介入过晚清政治活动。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戊戌变法时站在维新派一边,后因变法失败而遭迫害致死。陈三立参与了
父亲的维新活动,世道之变使陈三立较一般人更能体会到晚清政治的状况。陈衍、沈曾植都在张之洞手下任过职,郑孝胥在晚清政坛上更是一位极其活跃的政治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诗歌创作中最大的困难,倒不在于没有深切的感受,而在于既有的诗歌表现形式难以完全传达个人的感情。所以,陈三立等不断要求炼字炼句,翻陈出新,目的在于希望在诗歌表现形式上能有所突破。从“同光体”诗人的创作所反映的内容,到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有意识探索,体现了晚清时期中国文学自身是在努力寻找突破既有格局的途径。正因为“同光体”诗人有着这种追求,所以,在晚清文坛中能够引起广泛反响,流波所及,直至民国时期,如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及后来的钱钟书等,都受到“同光体”诗风的影响(注: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时,收入陈衍的文章;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教授宋诗,曾著文肯定陈衍所编《宋诗精华录》;郁达夫作诗,喜借用和化用宋诗诗句及意境;钱钟书早年问学陈衍,有《石语》详记之。)。
在“同光体”诗人的艺术探索中,所谓的“学人之诗”,也是他们的尝试之一。这一观点最早由陈衍提出。在《瘿庵诗序》中,他批评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观点:“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乐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隽绝乎丑夷也。”(注: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86页。)陈衍称“同光体”诗是“学人之诗”,固然有标榜自己,借“学人之诗”抬高自己声望之处,但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晚清诗歌的努力方向。我们看到,包括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在内的宋诗运动代表人物,都强调学问对于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正是晚清诗文发展的要求使然。可以说,晚清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人反对诗歌必须表现情感的观点,但他们对那种一味注重性灵,以致诗文内容空疏的文风持反对态度。故宋诗运动要求诗文须见根底,推崇黄庭坚所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援引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作为文学史的经验。到“同光体”时期,学问入诗的呼声更为高涨,因为晚清诗歌发展面临突破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鉴于当时人们所受的教育,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以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学创造的动力及参照对象,对大多数文化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使得“同光体”诗人在摒弃性灵一途之后,为翻新出奇,便只能强调“学问入诗”,以传统作为诗歌翻新的经验参照。我这样评价包括“同光体”在内的晚清宋诗运动,无非是想说明,一代人的经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对于晚清绝大部分文化人来说,应该承认他们是有文化危机感的,并且,试图在思想及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但他们长期接受到的教育,是传统的教育;生活的世界又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世界,即便他们对西洋文化有所涉历,也极为肤浅,还不足以构成新的文化经验,当然,更谈不上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有所认同了。所以,晚清宋诗运动取法宋诗,不能简单等同于复古运动,而是在复古名义下的变革,是对中国近代诗文新途的开掘。
在论述到晚清宋诗运动的诗文探索道路的同时,人们自然会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诗派”所探索的另一条诗歌发展道路作为对照。的确,这是晚清诗文发展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新诗派”的探索是唯一的思路。事实上,即便是“新诗派”的诗人,也并不完全否定宋诗运动,梁启超、黄遵宪等与包括“同光体”诗人在内的晚清宋诗运动代表人物有较密切的私人友谊,在诗歌主张上也彼此吸收。如梁启超曾从赵香宋(熙)学诗,赵便以郑珍的《巢经巢诗钞》相赠(注:参见白敦仁著《巢经巢诗钞笺注》(上),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页。)。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第十条中,称道陈三立:“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梁本人“中年后一意学宋人”(注:陈兼于《论诗》自注,见钱仲联《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1页。)。“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不囿于门户之见,对“新诗派”的黄遵宪有较高评价。陈三立有《赠黄公度》一首,陈衍《近代诗钞》中收有黄遵宪的诗作。而倡导“吾手写吾口”的新诗人黄遵宪尽管反对厚古薄今,但在《人境庐诗草》序言中,也还是强调作诗须有根底,讲究来历。并且,黄遵宪与“同光体”诗人有所往来,并有诗唱和,如《和沈子培同年韵》、《游仙词仍用沈乙庵韵》等。故钱萼孙在《人境庐诗草笺注发凡》中指出:“黄(公度)先生自序其诗,谓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无不采取而假借之。故其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今夕为拈出,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注:引自《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1949-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由上述可知,晚清宋诗运动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而不是相互遏制、相互敌对的。
二、“五四”新文学对晚清宋诗运动经验的总结及发展
如果说,晚清宋诗运动代表了晚清诗文探索的主要方面,那么,到了民国时期,随之兴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宋诗运动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总结了1872年(即《申报》创刊)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并谈到了宋诗运动的影响及其作用。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作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作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了这个毛病。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近代的作家之中,郑孝胥虽然也不脱模仿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还不全是模仿。”(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23页。)在胡适看来,继唐诗而起的宋诗,自有特色,可惜后来的“江西诗派”及“同光体”诗人都没有把握住宋诗的好处。事实上,胡适在这里只是为了论证新文学产生的需要,着眼于新文学与以往文学运动的差异。而在正面阐述他的新文学主张时,胡适对宋诗运动则有所肯定。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从肯定的方面入手,将“八不主义”概括为四点,即“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41页。)这四点内容的基本精神,与宋诗运动所强调的“以文入诗”有相似之处。早在美国时,胡适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强调了文学革命的要义所在:“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在30年代完成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胡适交代了“作诗如作文”的思想来源,正是他读宋诗的结果(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98页。)。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去读宋诗,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晚清文坛崇尚宋诗的风尚使然。这一看法,我们在胡适当时的论敌——胡先骕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胡先骕早年师从陈衍、沈曾植,对“同光体”一套诗学家法相当熟悉。在评价胡适白话文学主张及白话诗时,胡先骕首先就注意到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与宋诗运动的关系。不过,胡先骕认为,胡适只是强调宋诗“以文入诗”中,以白话入诗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宋诗的其他方面。所以,胡先骕评价胡适“对于中外诗人之精髓,从未有深刻之研究,徒为肤浅之改革谈而已”(注:参见胡先骕《评〈尝试集〉》,见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论衡——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在我看来,胡先骕的批评意见,倒是从反面说明了胡适在接受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发挥。晚清宋诗运动强调“以文入诗”,目的在于改变明代以来诗歌创作空疏的风气,代之以较为充实的内容,并且,在诗歌表现形式上,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基本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诗文范围之内,他们所谓的“变”,只是在传统范围内重新调整文化秩序,而不能像后来胡适这一辈人那样,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参照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变革的具体方案。所以,宋诗运动变来变去,不外乎在中国的诗文传统中兜圈子,而很少能见到其代表人物参照外国的文化经验,特别是欧美的近现代文化经验。这是一种时代局限。而胡适这一辈人,与晚清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相比,在文化经验上要丰富,这主要指胡适等人赴美留学,在已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中,增加了近现代欧美的文化经验。这里所说的文化经验的增加,并不是说胡适到了美国留学,自然而然便获得了一种新经验、新感受,而是指胡适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对比之后,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新视野。晚清以来,中国派至美国的留学生自不止胡适一人,但毕竟只有胡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这与胡适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比较,结合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需要,不失时机地提出变革要求,并提供具体的变革方案有直接的关系。从《胡适留学日记》中不难发现,在1916年以前,胡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学习、接受欧美文化;但胡适与其他留学生的区别在于,他很关注当时国内的文化动态,也注意不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能够在学习中渐渐积累心得,由少到多,逐步扩大到对整个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如他在美时,仍然看当时国内出版的《国粹学报》;对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等文章,用自己的经验尺度,加以评判(注:《胡适留学日记》下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美数年中,从未中断。而在经受
这种传统教育中,在诗文方面,胡适走的路子,很明显是受到了近代诗风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学习宋人的东西为主。在日记中,他自己说,自小学诗时,读的是白香山的东西。到美后,诗文方面读得最多的,是《王临川集》、《山谷诗》、黄黎洲《南雷诗历》等(注:《胡适留学日记》下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13、118、123、333页。),这些东西都与晚清宋诗运动有关。胡适除了接受浅显明了的诗风影响之外(对山谷诗主要选取浅显这一方面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面便是注意体现变革的要求,也就是“作诗如作文”的要求。不过,胡适结合自己的学习,对“作诗如作文”有不同于传统的理解,即这里的“做诗如作文”已不是传统文学风格学意义上的变化要求,而是从文学的根本价值需要,也就是从文学存在的根本目的、要求等最基本的价值角度入手,提出问题,并尝试着做出回答。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胡适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干、特长,这主要是利用自己出色的社会活动的特长,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注:《胡适留学日记》上册,第271页“理想贵有统系”列举三种方法,即谈话、演讲、著作,体现了胡适在美时的学习心得。)。在参加各种社教活动中,胡适体会到欧美的语言有很强的表音能力,对语言初学者来说,表音文字见到便能读出字音,容易学。中国文字以表意为主,虽说容易辨别意义,但在交流、表达方面,不及表意文字方便。对章太炎所说的表音文字容易读却不容易表意的观点,胡适在实践中进一步发现,美国社会中实际上很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人们常用的字不过一二千个,通过自小的学习记忆,一般人都能烂熟于胸,故在英美,一般的马车夫、农夫也能读报看书。相反,中国表意文字因地域差异、历史差异,各地发音不同,言义之间隔阂,久而久之,使得说话与书面表达之间形成了两种语言系统,而且使用文言的少数人根本不考虑普通读者的接受需要,不是从交流的便利需要出发,而是为了逞才遣性,在写作中一味追求古雅,使得文章诘屈聱牙,古色斑斓,既不便于文化传播,又缺乏时代感。所以,语言问题既是工具、手段问题,又是价值、观念问题。在与梅光迪、赵元任、任鸿隽等人的讨论中,由于多数人的反对,更促使胡适下决心思考这些问题。在大量阅读欧美文学作品时,胡适注意到近现代欧美文学中书面语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口语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中国的文言与日常生活口语之间的差异来得大,也就是说,语体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能够克服文言文所存在的与日常生活用语之
间的隔阂(注:《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139页“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条。)。语体文在欧美世界的成功,使胡适相信中国的白话同样可以取代文言,而达到文与言的统一。
为了让人信服,胡适又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从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发掘白话文学的资源;第二,是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在第一方面的工作中,胡适援引了《诗经》,乐府,唐宋诗、词,曲,话本小说中的实例,说明白话写作古已有之。如1916年4月5日,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标题下,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生在韵文领域的六次革命,他特别指出宋代语录体的影响,说明语录体到元代时,在词、曲、小说上的巨大成功,肯定“以俚语为之”的清代白话小说是“活文学”。对于晚清的唐宋诗之争及尊杜(甫)问题,胡适在日记中引录了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等文章,认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不必拘泥于师法唐或宋上。在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指出杜甫也写白话诗(注:《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209-212页;第256页;第287页“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条。)。对胡适所引的这部分材料,梅光迪等反对者只是认为胡适所见不全,而并不全盘否定。如果说,援引古代文学传统中白话文学的材料,证明了白话文在文学史上的确有存在的价值,那么,胡适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证明白话文学在表情达意上远胜于文言文而必须成为当今文学的主要表达形式。以白话作文,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在《竞业旬报》上已有实践,所以,他自信白话可以作文。但对于白话是否可以作诗,胡适在理论上相信,然而自己没有作白话诗的经验,因此从1916年起,胡适自觉尝试写作白话诗,较有代表的作品,如7月22日《答梅觐庄》等(注:《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1月29日记有“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同年9月15日,有“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叔永、觐庄皆极力反对。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刊发八首诗作,同年6月,在《新青年》刊发四首白话词。这些作品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热爱新文学的人士,肯定胡适诗的价值,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充分肯定胡适白话诗的尝试价值,社会上一些文学青年也接受胡适的白话诗。据废名所忆,胡适的白话诗,他差不多全能背下来(注:废名:《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另据胡适为第四版《尝试集》作的序文所记,《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后,两年里竟销出一万部(注:参见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所有这些都说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主张,顺应了当时文学发展的需要。晚清宋诗运动苦苦探索,力求给中国*
代文学打开一条出路,结果,这条通途被胡适打开了。从《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不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很好地总结了宋诗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肯定了宋诗运动“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但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批判:第一,宋诗运动的参照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学,而不是20世纪中国人的感受与经验,故“同光体”诗人脱不掉拟古的习气(注:胡适在留美日记中多次提到陈三立、郑孝胥等人缺乏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满脑子的杜、韩、苏、黄。参见《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227-228页、第286页。);第二,宋诗运动的艺术探索之所以不彻底,不为普通人所接受,表现在诗文写作上,主要是没有脱离以典代言的用典习惯,那些僻典奇语,不仅使今人的经验被束缚在传统的表达形式之中,脱离时代气息,而且,生僻的典故致使读者难以理会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注:胡适最初提出“八不主义”时,将“不用典”列为第一条。参见《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292页。)。前一个方面,显示了胡适的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后一个方面,体现了胡适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方式上超越了一般的言义之辨的水平,要求文学艺术应以现代人的经验及感受方式来写作,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写作方式。
三、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关系
胡适对宋诗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新文学运动在1917年后取得的巨大社会反响,的确证明了胡适等人的文学主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另一方面,宋诗运动的后继者在随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活动中,也并没有迅速消失其影响,他们仍活跃在文坛与大学讲坛上。如1922年《学衡》创办时,“文苑”一栏由胡先骕负责,而他刊发的诗评,都为宋诗派的文章(注: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4页。)。其他如陈三立、沈曾植、陈衍、李拔可、林学衡等人,在当时文坛仍有影响,他们仍不断写诗作文,并定时聚会。像《东方杂志》等当时最有影响的期刊,一直刊发他们的作品。林学衡在《今诗选自序》中对民国以来“同光体”诗人的影响做过描述:“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注:参见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辑,第195页。)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新文学运动以后宋诗派的文学史影响,特别是他们与新文学的相互关系呢?
我以为,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宋诗派的影响已远不如从前,换句话说,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已压倒其他各类传统文化人物而成为国内文坛及学术界的主角,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已取代了晚清宋诗运动的评价体系,而成为引导国内文学发展的主导因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宋诗派的影响基本限定在传统诗文的研究范围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学任教,如陈衍、林学衡、汪辟疆等,主讲的课程大都是中国古代诗文方面的内容。另一些人则转向学术研究,如沈曾植等(注:沈曾植1922年病逝。)。与此同时,宋诗派内部也有所变化,如林学衡后来转而反对“同光体”,他在《丽白楼诗话》中对“同光体”诗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注:参见林庚白著、周永珍编《丽白楼遗集》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7页。)。而新文学代表人物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对待宋诗派的态度也趋于和缓。20年代,郑振铎在为《小说月报》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时,收录了陈衍的《散体文正名》一文。商务印书馆自1915年邀陈衍在《东方杂志》续写诗话,一直刊发到第十八卷止,并于1929年出版《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本。30年代,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都肯定宋诗运动所强调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朱自清在40年代发表的《什么是宋诗的精华》及《论雅俗共赏》中,肯定晚清宋诗运动“以俗为雅”的诗歌探索路径,认为值得新诗借鉴(注: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直至50年代,郑振铎在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仍时常说到宋诗派对自己的影响,希望有人对宋诗能做深入的研究(注: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言中提到,编选《宋诗选注》是郑振铎交给的任务。参见《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第298-299页。)。在创作上,宋诗派所倡导的效法宋诗的风尚,在新文学人士的创作中留有明显的痕迹。陈独秀的诗作,带有宋诗的风格,喜欢议论,表现哲理。郁达夫的诗作常常化用宋诗的诗句、意境(注:郑子瑜有《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一文,系统论述了郁达夫借用、化用宋诗的情况。参见郑子瑜《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钱钟书早年曾向陈衍问学,其《石语》一书记录了问学的详情。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将唐宋诗视为两种诗歌风格,进而肯定宋诗有自己的独特地位。而吴宓在《赋赠钱君钟书(默存无锡)》中称道钱钟书“源深顾赵传家
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注:参见吕效祖主编《吴宓诗及其诗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以宋诗之苏黄作为钱钟书诗风的参照。尽管钱钟书自己并不认为受宋人的影响,但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智、冷静的风格,说明晚清宋诗派所倡导的诗风多少对其有所影响。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认定新文学在批判宋诗运动局限性的同时,仍然接受了宋诗运动的观点、主张的影响。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待这种影响关系,我认为,不是说新文学人士无条件地接受了宋诗派的影响,而是宋诗派的观点、主张已经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融入了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新文学人士在寻取文学史经验时,将宋诗派的观点、主张及其文学探索作为文学史上曾经出现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历史材料,加以利用和发挥。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受到过“同光体”影响的新文学人士身上便能发现,如钱钟书的文学趣味和文学风格明显留有宋人的影响,但同样,钱钟书的文学风格已不是宗宋一词可以包容。在《石语》中,钱对陈衍等“同光体”诗人的局限,有非常自觉的意识。这些变化说明,经过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文化眼光已经突破了传统诗文的范围,而以现实生活及世界文化的经验,作为新的文学的价值参照。这种变化,恰恰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选择。同样,宋诗运动留下的文学史影响以及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影响的接纳,也说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充实过程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过程,甚至像宋诗运动这样被人们长期认为是非常保守的文学运动的经验,也被吸纳到新文学中来。这种文学史现象提醒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在白话文学的单一经验支撑下完成的,而是在多种文学史经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新的观点、感受能够产生文化上的突破,但真正能够对文学史形成巨大影响的新观点、新感受,总是属于那些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发挥传统文化资源,并具有开阔的文化眼光的人。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宋诗运动的关系,仅仅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新的文学突破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新文学与其他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现出文学史应有的复杂性,人们还在被一种单一的研究视界所局限。因此,研究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只是我个人试图突破原来单一研究视界的一种尝试。
标签:陈三立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胡适留学日记论文; 晚清论文; 读书论文; 石遗室诗话论文; 胡适论文; 黄宗羲论文; 郑孝胥论文; 近代诗钞论文; 四部备要论文; 沈曾植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