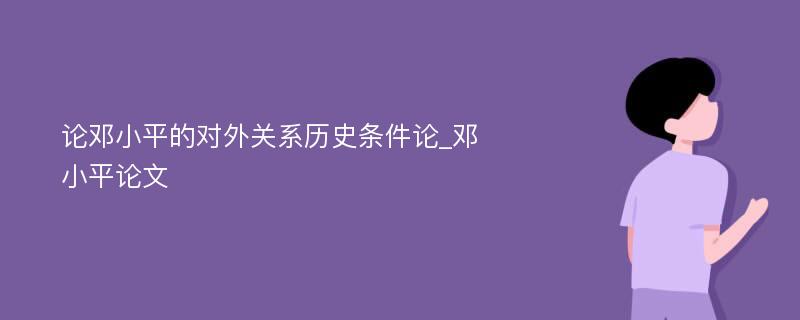
略论邓小平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历史条件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邓小平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的理论揭示了:对外交往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互动结构体。作为对外交往的客方是否有意地敌视、封锁己方,作为对外交往的己方是否自觉不自觉地与世界隔绝,再加上决策者是否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提出处理对外交往中一系列问题的正确决策,这三者是实现对外交往所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 交往 封锁 闭关 利益原则
邓小平在充分阐释其对外开放决策的同时,也深入地论述了对外交往的理论,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理论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深远意义。作为其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的揭示。
对外交往总是一种历史性的交往。也就是说,对外交往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总是来自一定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曾回忆:“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 〕对外交往是一个有机互动结构体。作为对外交往的客方是否有意地敌视封锁我们,作为对外交往的己方是否自觉不自觉地与世界隔绝,再加上决策者是否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提出处理对外交往中一系列问题的正确决策,这三者是实现对外交往所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
今日世界从整体态势上来讲,其人心所归的意识潜流于对外交往的历史条件的形成是十分有利的。但由此就能得出对外交往的历史条件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乐观无忧的结论么?答案恰恰相反:对外交往所涉及的双方不经过极其艰苦的相互反思、相互协调,不珍惜已经萌芽的机会,良好的对外交往的历史条件是很难建构成功的。邓小平站在中国以至世界的高度,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劝导、评价、解惑、决策的工作。
一
对于那些对外交往的客方而又恰恰是曾经长期封锁过中国、且对中国现今的对外交往仍存担心的某些发达国家,邓小平采取的是劝导方式。
首先,邓小平从这些国家自己所直接面临的问题谈起:“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在发达国家本身继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矛盾中,为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其主要矛盾是“出路”问题。资本、贸易、市场这一系列具体问题,归根到底是统帅到其发展如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发达国家的发展就很难避免停滞在裹足不前的区位。
其次,邓小平对这些发达国家如何找到自己发展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是发达国家毋须认真地考虑改变不发达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独自解决自己发展受到限制的问题。但这条一厢情愿的路走得通么?邓小平替他们算了一笔人口帐:“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他们走这条路的前景判断是:“不容易。”实际上,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走了几百年的发展老路,从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开始,他们的少数人的初始发展就是建立在多数人贫困的基础上的。尽管他们曾经由此获得过巨大的发展机遇,摘取过前所未有的发展果实,但是要再继续发展,恐怕是很难再借助这一发展老路而滑行下去了。世界绝对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武器战争征服下的赤裸裸的掠夺受到更普遍的反对,不发达国家愈来愈不甘于自身的贫困……在这一条件下,发达国家再走以前的发展老路,只会处处碰壁,处处“不容易”。
另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是发达国家明智地支持和鼓励、起码是不压制、不反对不发达国家改变自己贫困的现状,在促进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基础上,解决自己发展受到限制的问题。只有使不发达国家尽快地“脱贫”,具有更大更多地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能力,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冲破限制自己发展的既定囹圄,找到更为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邓小平以中国为例,替他们算了一笔贸易帐:“中国这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邓小平在这里揭示的“一进一出”原理,不仅对于发达国家,也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对外交往都具有现实普遍意义。绝对意义上的只出不进或者只进不出式的对外交往是不可能的。有进总会有出,有出总会有进。两者互为原因互为结果,互为基础互为提升。只许人家进,不准人家出,这一进的态势是很难保持长久的。因为作为进的一方如果不能在“一进一出”中使自身的发展得到增强,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实力去进,甚至原有的进的能力还会由于饱荷而不可避免地衰落。同样,肯定自己出,否决自己进,这一出的力度也将会越来越减弱。因为只出不进导致的只会是自身整体功能的退化,最终影响的固然是别人的发展受阻,更显性的还是自己的发展损失。所以,居住在地球村上的人们,只有大家都尽量力求平等一些地去交往,并按照规则游戏去“一进一出”,才有可能出现一荣俱荣、俱荣我荣的百舸争流的发展局面。
最后,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十分求实的战略家风度,很坦率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2〕一方面确实“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 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从前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担心并不是一丁点道理都没有的捕风捉影,中国在广泛的对外交往中发展起来了,不发达国家也在广泛的对外交往中发展起来了,是会对发达国家构成更激烈的竞争,这其实并非坏事。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么发达的一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竞争。只要这一竞争是建立在理性有序的基础上,竞争就会离所谓的威胁很远、很远。只要发达国家真正以诚信为本的姿态投入与不发达国家的交往竞争中去,这一交往竞争对他们自身的发展只会有促进作用,得到较大利益的仍然是他们,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发展中国家威胁论的担心或者是杞人之忧,或者是冷战思维惯性的偏见。从后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担心则完全显得是多余的了。“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邓小平替发达国家作出的这一判断毫无戏讽过言之嫌,而渗透推心置腹之义。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综合实力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几百年,他们早就处于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有利境界。在这种占优势的条件下,还“怕”后来发展的中国和其它国家什么!再“怕”,除了心理狭窄、缺少大度外,剩下的就是丧失机遇和没有出路。
当然,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怎么向他们说明双方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潜在的对方,仍然总是对中国的发展看不顺眼,总是企图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与己相互交往的行列之外。对此,邓小平一贯坚持国家、民族的尊严,给其以针锋相对的回答。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就指出过:“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3〕四十年以后,1989年10月,邓小平再次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4〕到1990年4月,邓小平满怀信心地总结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5〕邓小平这几段宣言式的论述, 闪烁着革命辩证法光芒:我们不赞成封锁,但我们不怕封锁;你们尽管可按你们的设想封锁,但你们并达不到你们封锁的目的;封锁本身无条件的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但封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由坏事转化为好事。一切企图封锁住中国及其发展中国家对外交往大门的人们,如果能多权衡一下具体表现在这里的主体与对象、手段与目的、动机与效果的矛盾冲突中的利弊得失,那么他们在反思和再择自己现实行为的方向时就会明智得多。
二
对于对外交往的己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艰难跋涉,邓小平一面客观地叙述事实,一面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欧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6〕
苦头,切肤之痛。在综观以明朝中叶为分界线的古代中国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对外交往状况,对比前段发展强大的辉煌和后段落伍贫弱的苦涩,更使人刻骨铭心。
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朝代都在对外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自信心。战国时期,连贯欧洲、亚洲、非洲三大陆相互交往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成果经由这条路向世界辐射,世界上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的经济文化精华经由这条路被中华民族西域的龟兹传递到中原腹地。此时秦国以丝绸交换牛马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贸易渐进兴旺;燕国、齐国从海上开始了对外交往。西汉时期,首先应征汉武帝诏书的张骞,作为中国历史记载上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往的直接通道;接踵而至的使节互访络绎不绝,仅汉使的足迹就遍布今中亚细亚及阿富汗、伊朗、印度,还有东部的朝鲜一带。东汉时期,班固的西进之行将交往的触角延伸到今地中海东岸;东汉晚期,实现了与罗马帝国(大秦)的官方交往。东晋南北朝时期,既有汉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后由海路回归,突遇飓风飘流数载的倍受艰辛,又有西僧鸠摩罗什来到后秦首都长安讲学大开译场、集聚学者三千的空前盛景。大唐时期,对外交往活动极盛,有来往关系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商人纷纷从陆、海两路涌入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中国使臣、商贾也远涉各国,成为时至今日仍被外域所称的“唐人街”、“唐物”、“唐文化”的最早血脉。宋朝时期,对外交往的通道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粤之广州、澳门,闽之漳州、月港,浙之宁波、定海,都成为对外交往的交汇点。其中,闽之漳州还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元朝时期,与欧洲的交往范围扩大到前人从未有过的疆域;原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整整居住、旅行了十七年,他口述下来的《马可·波罗行纪》(又名《东方闻见录》)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又一轮的交往热潮,使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这三大发明传到了欧洲,使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知识传到了中国。明朝永乐年间,随着明太祖登基后致力于以明王朝为主导的对外交往,导演了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九年,联络交接遍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沿岸、波斯阿拉伯沿岸、非洲东岸等三十六个国家的壮举,堪称当时世界第一。
此前后近两千多年的对外交往活动,主要是以我为中心,我即“天下第一”和“天朝无物不有”的富国强民性情绪一直牵引着统治者和老百姓的思维。对外交往战略的排列顺序是先政治,后文化,再次才是经济。政治交往上的扬威、怀柔主调,决定了其在文化交往上的宽容、兼收倾向和经济交往上的大度、厚赐特性。这种欲使“威德遍于四海”,“布德施惠”型的对外交往模式之是耶非耶,后人尽可多方评说,但起码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即对外交往者确实具有非常强的自信心,而不论这种自信心是来自于国家的实力还是来自于脑际的梦幻。自信心推动了对外交往,对外交往加强了自信心。另外,起码还有一点是可以明确得到答案的,即民族发展强大和国家对外交往两者之间的关系,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恐怕不宜只作单向直线的推论。两者之间客观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原因、互为结果,只要国家对外交往的政策基本得当和内外环境大体安定,就会形成两者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甚至更进一步应该看到,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容、相互内蕴的关系:民族发展强大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应有之义,国家对外交往是民族发展强大中的必备内容。
打断这一良性因果链条和冲破这一动态包容体系的可能行为,从理论的想象上可以列举出许多条,书面上也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历史上的确切事实是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民族从主要倾向上选择了闭关自守的行为,使得这一良性因果链条和动态包容体系毁之于一旦。明朝中叶以后,明、清两朝当政者先后两次的封关禁海令,令人遗憾地开创了一个闭关自守的时代。
就具体事件分析,这两次封关禁海行为并非全无道理,甚至在彼时彼地是很有道理。但这些都只是小道理,不是大道理。大道理就是邓小平归结出来的“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小道理被大道理管着,大道理错了,再对的小道理也都显得微不足道。从小道理上讲,是应该平息倭患,应该反对外来宗教强权,应该巩固国家的政权。但千应该万应该,却是不应该推出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决策作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这一实际行动虽然简单便捷,也得到当时中国民众的经验意识的直接支持,也似乎披上了“保家爱国”的绚丽的外衣,却导致了“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绝境。这一历史的事实作为大道理,反过来将那些小道理本有的光辉也遮掩殆尽,使得小道理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最终是大道理、小道理两败俱伤。
那么,难道就没有既能较好地解决诸如此类的小道理,其本身又是正确的大道理?邓小平解答这了这一困惑:“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7 〕这里的大道理就是反闭关自守之道而行之——开放、对外交往。坚持了这一大道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乐、文化的兴盛、公有制的主导等等这些相对而言的小道理就容易解决了。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是怎么也阻挡不住的。
当然,邓小平并没有否定开放、对外交往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而是相当清醒地承认这一点。但他更明确地强调这些消极因素对我们是“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这些消极因素是“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的”。就是说,我们有充分的把握以其自身的发展医治其自身发展中的疾病,在开放、对外交往中克服开放、对外交往中的消极因素。千万再不能因为其消极因素的客观存在,回返到前人曾有过的闭关自守的囹圄中去。老祖宗吃过的这个苦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吃了。
三
永远坚持对外交往不动摇的大道理确定了,接下来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为了更好地实践这一大道理的具体决策。邓小平为此精心策划了许多正确的原则。
“打破封锁之道”原则:对于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对外交往的客方对己方的封锁制裁,邓小平一方面认为客方不可能达到封锁的目的、己方不怕封锁、在一定条件下封锁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另一方面又认为“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切不可安于被封锁的状态而无所事事,要谙熟“打破封锁之道”。这“道”既言指“物质通道”,又蕴涵“谋略之道”。关于打破封锁的“物质通道”,邓小平早在1949年7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 就提出过“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8〕。在己方领土领海主权范围问题上不能有任何退让,不能让企图封锁自己的人封锁到自己家里或家门口来。我们从来没有企图去封锁人家,但我们要尽量扩大反封锁的防卫圈,这一防卫圈越大则反封锁的效果越好。关于打破封锁的“谋略之道”,邓小平指出:“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9〕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两极称霸的时代早已结束,一极称霸的时代将完全没有可能。今后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多极的时代,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还有南方。世界上的人们不可能都来封锁我们,除非我们确实完全悖了理,自己彻底地孤立了自己。只要善于捕捉矛盾、利用矛盾、发展矛盾、统帅矛盾,打破封锁的“谋略之道”就能驾驭得得心应手。
“不要当头”原则:“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为什么在世界范围的交往中“不要当头”?一是当不起,二是当了被动,三是不当更能有所作为。三条理由,言简意赅。其中既包含对一些总是企图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秩序中称王称霸的国家的间接批评,又包含对本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经济教训的直接总结。明朝中叶以前,历代对外交往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要当头”的思维定势,为了在政治上被拥戴为“头”,不惜以经济交往上多多付出为代价。明成祖一即位,就认为应该“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在,无不复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11〕为了使万国远来者承认大明王朝居中于世界的地位,宁愿以物安抚,安抚至满足其欲望的地步,这一交往代价可想而知。较早一些的明太祖说得似乎更通情理:“西间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12〕更早一些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的重要任务就是认为周围各国“欲贪汉财物”,所以“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使得各国“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甚至汉武帝还亲自下令:对“外国客”要“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13〕
如果说这种对外交往中为了“当头”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策略,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世界经济竞争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还能运行下去的话,那么在今日的中国经济相对较为落后、世界经济激烈竞争愈来愈关系到一国的命运的形势下,是绝对行不通的。在这一战略问题上,任何形式的头脑发热,都会使本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甚至是致命的损失,自己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到头来反而会造成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起的作用更小。其实,当年古代中国的那种经济交往中少进多出的长期积累,也为明朝中叶后中国在整个世界上屈辱性的落后悲剧的形成,埋下了一条深深的伏笔。
“越发展越要谦虚”原则:“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4〕国家交往如同朋友交往,谦虚中充分体现着一个“诚”字:“心中要有数”,是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要有个客观的分析,真心地用不同的分寸与不同类型的朋友进行交往;“不随便批评别人”,是指在相互交往中随便批评人家有时会显得主观、缺乏说服力,有时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导致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听得进,人家即定有缺点也让人家自己总结,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过头的事不要做”,是指相互交往中的具体行为准则,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宁可多稳妥一些,也不要无根据的激进,特别是关系到恩恩怨怨的事,多朝前看、多一些大度总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越发展越要谦虚”原则,是中国传统交往美德的继承和提升。它既保持了古人历来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君子谦谦的传统,又将这个传统的基础和目标进行了彻底改造。“谦虚”的基础不再是人生的自我禁锢,其目标也不再是人性的所谓内在省悟;它突破了单个人的蕃蓠,强调了发展主调——“谦虚”的基础是发展,“谦虚”的目标也是发展。这样就将德性上的“谦虚”放置于互相交往着的民族、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给它注入了勃勃生机。
“利益”原则:在相互交往中,“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5〕首先,邓小平很明确地指出了国与国相互交往中的最高准则,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之所以最高,就是高在它是一种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的局部利益;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多维利益,而不仅仅是单向性的某点利益。其次,既然最高原则都坚持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都必须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如果交往各方都努力同时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就会形成良性交往循环。如果各方都只顾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贬损别人的国家利益,一来一往相互抵消,结果是伤害了各人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此下去,就会出现一种互不信任、互相指责、互为怨敌的恶性交往循环,严重到极致带来的只会是交往的中断。这种爆炸式的局面,终归削弱的还是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时,问题的可能解决,只能是再回到尊重对方利益的轨道上来,重新迈开良性交往循环的步伐。早知今日难堪的妥协,何必当初骄横的强权,这是历史向人们作出的警示。最后,尊重对方的利益不是一句应景的空话,它有切切实实的内容。所谓尊重对方的利益,就是要尊重对方的历史传统、尊重对方的国体政体、尊重对方的人权尺度、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念等等。世界不可能是单色而只可能是多彩的,单色意味着退化的危险,多彩必定带来进步的繁荣。而多彩者之所以会被称为多彩,其最基本逻辑前提就是差别;差别并不等同于孰优孰劣,差别是形成多彩的最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在相互交往中,总是计较别人的差别,不仅是对别人利益的侵犯,而且还是浅薄无知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将“利益”原则贯彻到交往实践中去,邓小平率先在“利益”之最直观的方面即经济利益方面,采取了具体求实的行动——既心胸大度又聪慧精明的行动。
1986年9月2日,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邓小平时提问:“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邓小平回答:“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情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16〕这里的点睛之言是“投资者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需要西方的资金是为了发展经济,这是我们的利益,西方的资金愿意来也决不会白愿意来,它有它的利益,那就是资本增值,没有了这一利益冲动实现的可能,它的资金就不会来了。再则,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中国作为礼仪大国的一贯优良传统。所以邓小平明确强调:“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这里充分体现了一种心胸大度的气势。但是这又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有过的“厚往而薄来”模式的大度,而是聪慧地继承了其“厚往”的优点,精明地克服了其“薄来”的弱点,将“厚往而薄来”扬弃为“厚往而厚来”、甚至希望提高到“厚往而更加厚来”的境界。
邓小平为此指出:“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17〕要达到“厚来”,就必须将表面形式上对人家礼貌变为扎扎实实地向人家请教。要达到“厚来”,还必须走出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的误区:“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最终的“厚来”,已经从税收、工资、技术、管理、信息、市场的受益,提高到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再升华到对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推动。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化“寻常”为“神奇”的交往发展谋略。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2〕〔4〕〔5〕〔6〕〔7〕〔9〕〔10〕〔14〕〔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第329页,第357 页,第90~91页,第354页,第363页,第320页,第330页,第171页, 第32页,第372~373页。
〔3〕〔8〕《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4页。
〔11〕《明成祖实录》卷二三。
〔12〕《明太祖实录》卷七一。
〔13〕《史记·大宛传》,《二十五史》第1卷,第3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