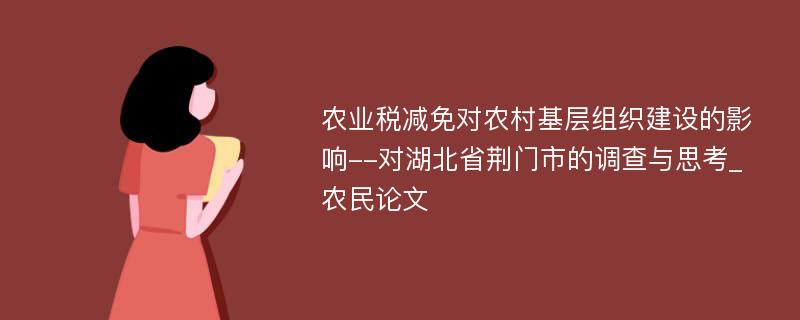
减免农业税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对湖北省荆门市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荆门市论文,湖北省论文,农业税论文,基层组织建设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自2000年开始“减轻、规范、稳定”农业税征收的试点起,至200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完全取消了农业税。中国政府曾在2004年宣布在5 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目标可提前在3年内实现。与此同时, 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2005年中央在2004年对产粮农民进行粮价、良种和农机直接补贴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对县乡财政的“三奖一补”政策。完全取消农业税,是一项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改革措施。它宣告了中国政府将彻底废除延续了几千年的按田亩、按人头平均赋税的封建税制;标志着农村居民将彻底告别实行了几十年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城乡区别税制。[1]
税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并不是单纯的“费改税”或减轻农民经济负担问题,它的实质内容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农村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它在减轻农民负担和规范财政分配的同时必然会对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农业税收(含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及其相应的三提五统或附加)在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大,减免农业税收对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影响较小;工业发达地区,农业税收在县乡村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不大,减免农业税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基层组织影响也不大;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税收一般占当地县乡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2] 减免农业税收乡村组织产生的影响将最大。本文将以湖北荆门市为个案考察减免农业税对中西部农村乡村组织的影响。
荆门市地处湖北省腹地中心,位于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北部。素有“地接江汉,门锁荆楚”之称,现辖1市2区和沙洋县、京山县,总人口近300万,版图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业人口210多万,耕地面积近400万亩。荆门市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和优质杂交油菜生产基地。常年粮食种植面积在400万亩左右, 产量20亿公斤上下;油料年产量26万吨以上,油菜双低化率达100%。粮食一直是荆门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全市约有60万劳动力直接从事粮食种植。荆门市还是湖北省重要的生猪、家禽和水产品生产基地。
农村税费改革前,荆门市乡村两级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民的各种上交款。其中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占乡镇财政预算收入的70%左右,乡镇统筹、集资、事业规费等面向农民的收费与乡镇财政预算收入大体相当;[3] 除极少数有集体企业的村组外,绝大多数村组收入全部来源于村三提、共同生产费和其他摊派;农民负担最高时曾有一些村组达到过亩均400元。
2000年,当国务院在安徽省试点时,京山县就作为湖北省的两个试点县之一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县合同内负担下降27.79%,亩均由112.74元下降到81.74元。与此同时,荆门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撤销管理区、合并乡镇、清退编外人员的配套改革。2002年,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省级试点单位,在全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荆门市农民负担下降到了亩均不超过100元,合村并组、 精简村组干部也同时进行。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入,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荆门市进行了旨在减少乡镇财政支出的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2004年,农业税率降到了4%,亩均负担在50元左右,进行了乡村综合配套改革。2005年, 农业税完全取消,荆门市准备进一步合村并组和精简乡镇政府的机构人员。
从荆门市5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情况来看, 减免农业税对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地区的乡村两级组织的主要影响有:
一、堵死了乡村组织向农民收费的口子,缓解了乡村干部与农民的矛盾,重建了乡村组织的合法性
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既要交皇粮国税,如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又要为乡村两级集体提供积累,如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等,并且要承担乡村现代化的大部分成本,如为各种达标升级集资。乡村两级组织也借收取各种税费的机会层层加码为自己捞取好处,致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如荆门市1998年仅被市批准列入合同内的负担就有50388万元,达到亩均147元、人均233元。沉重的负担, 引起了农民对乡村组织的不满,激化了乡村干部与农民的矛盾,致使涉农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大大降低了乡村组织的合法性。减轻并规范农民负担,减少了乡村组织搭车收费的机会;免除农业税,更是完全取消了乡村组织向农民收费的权力。这将从根本上消除乡村组织在收费上同农民产生的矛盾,缓和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
二、有助于乡村干部从繁重的税收任务中解放出来,为乡村组织转变职能和精简人员创造了条件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催粮派款要占用乡村干部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4](p64—72) 以至于乡镇的一些机构陷入了养人收费、 收费养人的怪圈。减轻并规范农业税收后,乡村干部收取农业税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例如,在税改前特别是1999年前后每年从5月开始直到春节, 荆门市乡村所有干部都要将税收作为第一任务,有时还从教师、职工和农民中抽人组成征收队,但许多村仍要靠借贷完成税收任务。2004年,荆门市农业税率降到了4%,亩均只有50元左右,而且,给予每亩10元早稻良种补贴、15元中稻良种补贴、30元左右的价格补贴,许多村在6月夏征时一个星期就完成全年80%以上的任务。取消农业税后, 乡村干部将完全从收钱收粮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使那些纯粹为收取农业税费而设立的机构和人员失去存在的理由,为精简这些机构和人员创造条件;也使那些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和人员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为群众谋利益、办好事。
三、提高了乡村改革的紧迫性,逼迫乡村通过裁减人员和合并机构来保运转,但同时也降低了乡村组织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无法安置剩余人员
农村税费改革前荆门市乡村两级的财力主要由农民负担。如沙洋县改革前由农民提供的乡镇财力仅合同内的就有6830.13万元,其中农业税2463.1万元、农业特产税878.59万元、屠宰税533.44万元、教育集资271万元、五项统筹2684万元,占整个乡级可用财力的85%以上;村级财力中的三提有3108万元,占村可用财力的95%左右。京山县在改革前由农民提供的乡级财力仅合同内的就有5476万元,占乡级可用财力的80%以上;村级财力中仅村三提就有2190万元,占村可用财力的90%。农村税费改革要逐渐减轻农民负担,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可能完全与被减免的农民负担相等,这必然导致乡村财力的大幅度的下降。乡村两级只能通过降低开支来保持收支平衡,而减人、并机构是最好的办法。荆门市在村一级的改革主要是合村并组、精简村组干部。如沙洋县合村11个、并组259个、精简村组干部2108个;京山县合村5个、并组343个、精简村组干部1692个。2004年,全市村均人口已近2000人,村均国土面积已近10平方公里,村干部数量每村都在3—7人,其村干部的报酬基本上能通过转移支付提供。乡镇一级改革主要有:2000年撤销了214个管理区,2001年通过合并使乡镇数由71个减为57个,2002 年乡镇党政内设机构由6个减为5个,2003年乡镇事业单位由20多个减为8—10个;同时进行了清退临时工和编外人员、核定领导职数和在编人员的工作,所有的临时工、编外人员和民办教师都被辞退。但由于2003年前大多数乡镇精简在编人员特别是财政编制人员时,都只是采取的提前内退和轮岗的办法,在岗财政供养人员(不含教师)名义上每个乡镇由200多人减到了100多人,财政总供养人员实际上并没减少多少,财政开支仍超出税改后乡镇的财力。2004年荆门市贯彻落实湖北省《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文件,每个乡镇只设“三办一所”或“一办一所”: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加挂综治办的牌子)、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财政所,每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不含教师和县直单位)在50—80之间。其他人员全部买断,与财政完全脱钩。买断就是政府付钱给被精简的人员。按省文件的标准计算,一年补偿一个月,平均800元,20年就是1.6万元,再加上社保的追缴,也要1.5万元,加起来就是3万元一个人。现在湖北的乡镇有50多万干部,如果一半要买断,就要支付75亿元的成本。[5] 由于各乡镇要买断的人员远远超过一半,大多数乡镇的行政事业单位都拖欠干部职工的工资和集资,在分流人员时还必须还清债务,因此,各乡镇分流人员要支出的费用远远超出全省所估算的数字。如沙洋县某镇不计派出所、国土、工商、税务、司法等县直管部门的人员和教师,参加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财政在编人员(含退休人员)有201人,其中事业人员175人、公务员26人,改革后核定编制为62人,需买断139人,超过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买断安置费和偿还买断人员的欠款总共需480多万元,人均也超过3万元。即便镇将所有闲置的能够变卖的资产全部变现、省财政部门给每个分流人员补偿4000元并将2004—200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提前支付到位,仍缺少300多万元。其结果,荆门市的乡镇分流人员直到2005年春仍没得到妥善安置,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没有完全达到。
四、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的能力
当前,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少数宗族组织仍在发挥作用的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缺乏内生合作能力,需要乡政府和村委会等外生型组织来提供生产生活秩序,尤其是经济的协作。[6] 减免农业税从四个方面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1.财力大幅度下降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干部的减少,使乡村无钱办事、无人办事。2.乡村组规模的扩大,不便于干部为村民服务。3.不向农民收税和收费,使乡村干部失去了向农民服务的动力,只重视招商引资。4.不准乡村组织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削弱了乡村组织劳力和资金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威。
五、提高了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比例,有助于减少党政部门之间的推诿和磨擦,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可能不利于对权力进行监督,导致腐败
在党政两个系统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 是精简干部的重要方法。 荆门市在2002年村委会和村支部换届选举时就提倡村支书竞选村主任,村支委的其他成员竞选村委会的其他职务,有许多村是书记主任一肩挑;2004年进行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也要求:党委书记原则上兼任乡镇长,2名党委副书记, 一个担任人大主席一个兼任纪委书记,2—3名党委委员兼任副乡镇长,2—3名党委委员兼任人武部长等职务。兼职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兼职在减少人员和降低成本的同时可消除长期存在的村委会和村支部、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提高行政效率。但兼职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兼职也可能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对权力失去制约,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乡镇党委与政府的分工常常是一个主管决策、一个主管执行,党委书记与乡镇长的分工常常是一个管人、一个管钱,二者互相配合也互相制约;村两委和书记主任的关系也类似。如果决策权与执行权,特别是用人权和财政权都集中在一人手中,就很难对其监督。如沙洋县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村财务透明度普遍低于书记主任分设的村。
六、加强了县对乡、乡对村的控制,有利于中央政令畅通和法制的统一,但也可能使乡村两级组织自我活动空间减少,不利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
随着农业税率的降低直至取消,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在乡村两级组织收入中的分量将越来越重,有利于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以财政控制行政、用数目字管理国家,是以商业作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特征;[7] 中央通过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上级政府通过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维持对下级的支配权,也是现代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主制度配合,在转移支付成为乡村两级组织的可支配财力的主要来源时,乡村就会完全丧失自主权和独立性,乡村干部就会完全变成唯上而不愿为民服务的官僚,与推进村民自治和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如荆门市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各村的会计,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的工资也由乡镇政府确定,村干部基本上变成了乡镇政府在村的执行人,很少过问村内的公益事业。
七、凸显了乡村债务危机
早在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两级就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但由于当时的税收政策不规范,乡村可以通过多收费向农民转嫁危机,也可通过高息借贷对外掩盖危机,还可通过寅吃卯粮来向后转移危机。取消农业税使得以上种种方法难以施行,乡村只能依靠自己的合法收入来还债。但大多数债务严重的乡村集体经济都不发达,可支配的收入主要是上级所拨转移支付,于是乡村债务危机便无法掩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激化农村矛盾和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总之,减免农业税对乡村组织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就整体来说,积极的大于消极的,但如不消除消极影响,就有可能达不到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防范其消极影响。现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弱化农业乡镇政府的决策功能,去掉其发展经济的职能,取消其财政,使其成为县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
这里的农业乡镇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其财力(包括预算内、预算外和自筹)主要由农民负担或税改后只能靠转移支付维持运转的乡镇,将其由政权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就是不设人大、政协,实行党政兼职,由县政府直接任命和监督管理,没有独立的财政。许多人持这一主张,徐勇和贺雪峰作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其要点如下:一是历史上乡镇一级一直没设政权,现在乡镇政府也不完备,公安、国土、教育、工商、税务、司法等都由县直管;二是农业乡镇由于缺少工商业支持,农业生产的有限剩余无法满足作为一级政权的需求,其财政不可能自负盈亏;三是乡镇一级人大人数少、无常设机构,不可能对乡镇政府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乡镇直选又可能导致黑金政治。
二、提高村级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首先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维护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村民大会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应该有权做出强制性规定,对没有正当理由不执行有关出工出钱等会议决定的村民进行制裁,如可用粮食直补金抵账,乡镇机构也应协助,以便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决定。其次要增加转移支付到村的数量或者将粮食直补资金交给村组集中使用,以便村组有钱办事。目前,将粮食直补资金直接补到农户,虽能表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关心和对农业的重视,但并没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提高农民收入帮助不大。因为不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成本,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福利和长期保持农村稳定的。
三、控制乡村组的规模。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其辐射半径和覆盖人口不能过大,否则就会降低服务效率[8]
就目前来说,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应以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或人口不超过10万为宜,人口稀少的山区以面积不超过300平方公里或人口不超过2万为宜,其他地区的乡镇面积应在200平方公里以内、人口应在5万以内。村作为村民自治单位,是由原来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的,现在仍在起作用的大集体时代留下来的中型水利工程都是以村为单位修建的。因此,村的范围应以方便村民开会、生产为原则,不宜过大,最好面积不超过8平方公里、人口不超过2000人。 村民小组是由原来的生产队演变而来的,现在基本上成为一个人情娱乐单位,其规模应方便村民日常交往,以50户左右为宜。[9]
四、通过分权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将财务收支签字权交给民主选举的其他干部行使
党政一把手分设时,签字权由镇长、乡长、村主任行使,书记作为事实上的一把手,可实施有效监督,财务人员也可以向书记负责或以要接受书记检查为由制止镇长、乡长或村长的不正当收支;在党政一把手一肩挑后,仍由一把手行使签字权,则财务人员根本无法履行财务监督权,很容易顺从一把手的意志,共同作弊,因为财务人员的任免权事实上掌握在一把手手中。因此,在党政一把手一肩挑后,必须将财务收支的签字权交给与一把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行使。
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化解乡村债务
目前虽没有操作很强的办法,但温铁军提出的“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可作为一个参考原则。
当然,最重要的是县乡村三级的改革要配套,特别是要改革对乡村干部的评价任用制度,乡村干部的报酬和升降应不与经济发展指标和税收完成情况挂钩,应以群众是否满意和社会是否稳定为衡量标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乡村两级盲目招商引资以致乱占耕地和破坏环境,才能引导乡村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持农村的稳定和繁荣。
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税论文; 转移支付论文;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论文; 农业论文; 农村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税费改革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