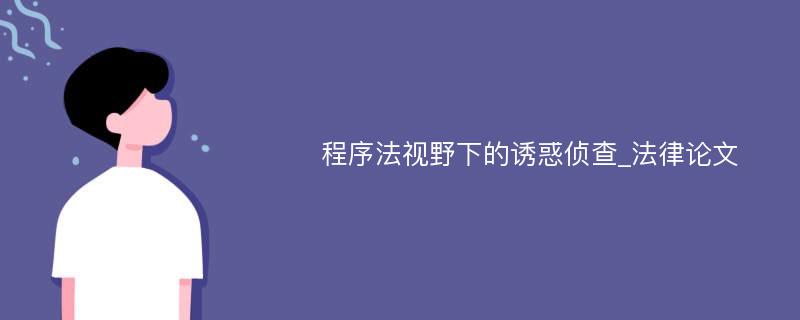
程序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日益突出,侦查机关迫于打击这类犯罪的需要,实践中已开始广泛采用诱惑侦查方法。例如据广西桂林某地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的毒品犯罪、假币犯罪这两类案件94件共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注:参见马滔:“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第69页。)然而,对实践中这种颇有争议性的诱惑侦查方法,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这无疑与诉讼的法治化要求是不相宜的。因此,从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要求出发,有必要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轨道。那么,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应该进行怎样的规范与控制?诱惑性的侦查手段一旦被滥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如何救济?在诱惑侦查过程中如何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利益平衡?本文试图在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有关诱惑侦查和警察圈套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此进行探讨。
一、诱惑侦查的含义及与警察圈套的区别
关于诱惑侦查和警察圈套的含义,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和侦查圈套(警察圈套)是同一概念,即诱惑侦查,也称诱饵侦查、侦查圈套、侦查陷阱、警察圈套,泛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雇于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励、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人的侦查手段。(注:参见吴宏耀:“论我国诱饵侦查制度的立法建构”,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第12页。)当前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与侦查圈套(警察圈套)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方面,诱惑侦查的中心词是“侦查”,而侦查圈套的中心词是“圈套”,二者的语意侧重略有不同;另一方面,虽然侦查圈套一般都是以某种诱惑为基础,但是也有些圈套是很难归入诱惑之范畴的。(注:参见何家弘、龙宗智:“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载《证据学论坛》(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第三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侦查陷阱)并非同一概念,并认为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含义。(注:参见吴丹红:“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第23页。)笔者认为,应该将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但是这种区分绝不应仅仅从字面含义上来进行,而应该从这两个概念的历史起源出发,探讨两者深层的法律意义。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新的侦查方法,最初引起法学界关注的是193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索勒斯违反禁酒法一案。在美国,所谓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是指侦查机关或其代理人为了对某人提起控诉,而采用引诱的方法,使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实施犯罪的一种非法侦查行为。(注: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six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P532.)而什么叫诱惑侦查,《布莱克法律辞典》并未作出解释,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诱惑侦查(police encouragement),是指国家侦查机关对那些已有犯罪意图的人,为获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当他真的被诱使而实施犯罪时,当场予以抓获的一种合法侦查行为。对二者的关系,美国有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诱惑侦查并不是一种非法的侦查手段,但是,当这种手段的运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即犯罪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警察的行为,他们为了提起公诉,引诱那些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去实施犯罪——这时警察的行为即构成了警察圈套。(注:See Israel·K·Lafave: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Constitution.West Publishing Co.P206.)而且,在美国还有警察圈套合法辩护(the defense of entrapment)之说,即被告人可以主张警察的诱惑性侦查行为已构成警察圈套而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但是,被告人并不能以警察采用的是诱惑性的侦查手段非法收集证据为由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由此看来,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即诱惑侦查是一种合法的侦查行为,而警察圈套是一种非法的侦查行为,当诱惑侦查这种合法的侦查方法被滥用,越过一定的界限后,即为非法,构成警察圈套。而且,世界各国之所以将诱惑侦查这种侦查手段在立法上予以认可,赋予其合法地位,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效打击犯罪,也就是说,诱惑侦查这个概念是从侦查权的运用、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提出来的。而美国之所以提出警察圈套合法辩护之说,实际上就是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角度提出来的,是对诱惑侦查这种侦查手段的一定限制,是当诱惑侦查被滥用后被告人可以行使的一种救济权利。
在明确了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的本质区别以后,有必要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一般都认为,根据被诱惑者在被诱惑之前有无犯罪倾向,诱惑侦查可以划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并认为前者只是使被诱惑者已有的犯罪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是强化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因而是合法的侦查行为,后者则是对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因而是非法的。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同时认为,对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一概持肯定态度也是与法治要求不相宜的。实际上,对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各国也都予以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包括明确规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案件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及相应的程序控制。只有符合法律规定、遵循程序要求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才是合法的。侦查机关虽然只是提供了机会,但是如果这种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适用范围,违反了程序要求以及提供的这种机会超出了正常的限度,那么就属于违法行为,构成警察圈套。
综上,笔者认为,所谓诱惑侦查,是指对重大复杂的隐蔽性犯罪案件,在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或犯罪倾向的条件下,侦查人员严格根据法律的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犯罪机会和条件,待其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这种特殊侦查手段有以下特点:其一,诱惑侦查是一种任意性的侦查手段。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侦查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根据其强制程度的不同,日本学者一般将侦查行为分为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任意侦查是相对于强制侦查而言的,前者指不用强制手段,不对相对人的生活权益强制性地造成损害,而由相对人自愿配合的侦查,后者则是指通过强制方法对相对人进行的侦查。侦查人员在实施诱惑侦查时,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只是为侦查相对人提供机会,创造条件,在整个诱惑侦查过程中,相对人有权决定是否“配合”。因此,诱惑侦查是一种任意性的侦查方法。其二,诱惑侦查是一种主动型的侦查方法。传统的侦查方法是一种被动型的侦查方法,即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才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侦查活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犯罪行为日趋多样化、隐蔽化、组织化和智能化。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侦查方法是时代的要求。(注:参见[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因此,为了适应新的犯罪形势,跟踪监视、监听通讯、诱惑侦查等主动型侦查方法便应运而生。在诱惑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为有犯罪意图和犯罪倾向的嫌疑人创造条件,提供其实现犯罪意图和犯罪倾向的机会,在嫌疑人实施犯罪时,当场予以抓获,从而迅速有效地侦破案件,减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诱惑侦查实际上是在犯罪还未发生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便提前开展的一种主动型侦查方法,这与传统的先有犯罪后有侦查的被动型侦查方法是不同的。
二、诱惑侦查的实践及立法概况
作为一种侦查方法,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就曾运用诱惑侦查来捕捉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采用这种手段进行反间谍工作。二战后,这一侦查手段又被运用于查禁卖淫、赌博、贩毒等犯罪当中,自60年代起,又扩大到侦缉恐吓案件和追查盗窃赃物,在70年代之后,再进一步扩大至侦缉行贿、受贿、犯罪组织和窃取产业情报等犯罪。
在美国,最早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是1932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SorrellsV.United States一案。此案一、二审法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却以警察圈套为由,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此,“警察圈套合法辩护”在美国司法中得到运用。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在ShermanV.U.S(1958)、United StatesV.Russell(1973)、Hampton V.United States(1976)三案中,对警察圈套合法辩护和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再次予以确认。1978年,FBI成立了秘密侦查委员会,试图通过加强内部监督来主动地规制诱惑侦查。1981年1月5日,美国司法部又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实施的许可条件、原则、程序等,最终以成文法形式来规制诱惑侦查。
日本最早确认诱惑侦查合法地位的法律是1953年《麻药管理法》。该法第53条规定:“麻药取缔官及麻药取缔员,在进行与麻药犯罪有关的侦查时,经厚生大臣许可,可不受本法规定之限,从他人处受取麻药。”1954年的《鸦片法》第45条以及1958年的《枪炮刀剑类所持等管理法》第27条也对侦破鸦片、武器交易犯罪时诱惑侦查的运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注:参见马跃:“美、日有关诱惑侦查的法理及论争之概观”,载《法学》1998年第11期,第19页)
德国立法对诱惑侦查也有相应的规定。1994年修改颁布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秘密侦查部分就规定了诱惑侦查。该法第110条a项规定:在侦查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犯罪时,允许派遣秘密侦查员侦查犯罪行为,而且这种秘密侦查员可以以“传奇身份”参与“法律关系交往”,并且“为了建立、维护传奇身份,在不可避免的时候允许制作、更改和使用相应的证书”,该法第110条b、c、d、e项还分别对实施包括诱惑侦查等在内的秘密侦查的条件、程序以及获得的证据之使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为了对付国内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法国于1992年制定了针对毒品犯罪的特殊诉讼程序,即该国刑事诉讼法“毒品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编。该编明确规定:“……经共和国检察官和预审法官的同意并授权,司法警官取得、拥有、运输、寄送或交付毒品给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人或贮存、保留毒品的,均不承担刑事责任。”该规定通过豁免司法警察为侦查目的而介入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方式,承认了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
英国非常谨慎地讨论过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英国刑法中将它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法官们认为:“为了诱捕罪犯,仅仅为实施犯罪提供机会或者诱因是合法的,这犹如加入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并将必定实施的犯罪一样。”(注:[英]J·C·史密斯、B·霍根著:《英国刑法》,马清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并且,为了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皇家警察委员会给警察当局提出了如下明智的建议:“作为一般规则,警察在侦查犯罪时不得加入犯罪,除非该犯罪的实施在通常的情况下,根据假定第三方是不可能察觉的。而得到警察局长明示的、书面的授权,对于加入犯罪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注:[英]J·C·史密斯、B·霍根著:《英国刑法》,马清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可见,英国对诱惑侦查实施的批准程序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从反面论证了英国法律对诱惑侦查手段的认可。
最早对诱惑侦查予以认可的国际性文件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二战后,毒品成为世界公害,贩毒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此背景下,1988年12月29日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的第6次全会上通过此公约。该公约第11条规定了“控制下交付”的诱惑侦查手段,即在侦查中一旦发现贩毒者手中拥有大量毒品急于寻找购买对象,侦查人员便可设计购买,在毒品“成交”过程中,查获毒品缉捕贩毒者。如今,这种“控制下交付”的诱惑侦查手段已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缉毒对策。
欧洲人权法院在1998年6月9日的“卡斯特罗诉葡萄牙”一案中,区分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诱惑侦查,认为前一种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而后一种则侵犯了这一权利。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申明:即使是为了打击贩毒犯罪,对秘密侦查员的使用也必须受到限制,并规定一些保障措施,《公约》第6条规定的公正审判的权利不得因为寻求侦查上的便利而被牺牲,公共利益不能为使用基于警察的教唆而获得的犯罪证据提供正当
根据。(注:参见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纵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刑事立法及实践,均对诱惑侦查的合法地位予以认可,并就其适用的原则、范围、对象和有关程序作出了规定。比较这些国家的立法及实践,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其一,诱惑侦查的适用原则和程序。各国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考虑到诱惑侦查的危险性,因而对诱惑侦查从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确立了运用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原则和报批程序,即警察只有在采用常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案件时,才可考虑使用,并须履行严格的批准程序。
其二,关于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对此,美国采取的是概括式的立法形式,其案件的适用范围极为广泛,几乎不受限制;实践中在卖淫、赌博、贩毒、恐吓、追查盗窃赃物、行贿、受贿、窃取产业情报等犯罪中都曾采用过诱惑侦查。不过自震惊美国法学界的ABSCAM事件(注:在ABSCAM事件(AB为Abdul的缩写,Scam意为诱惑)中,美国FBI于1980年以虚设的名为AbduI有限公司做掩护,由侦查员扮成阿拉伯商人,向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行贿,致使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在内的22名政治家涉嫌被捕,并被判有罪。)之后,学者们对贿赂这类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适用诱惑侦查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相比之下,德国则采取的是列举式的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在毒品、假币、武器交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重大职业团伙等犯罪案件中,可以采用诱惑侦查。法国的立法规定仅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值得说明的是,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与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实际上,无被害人的犯罪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65年由美国学者埃德温·舒尔提出的,这类犯罪主要包括贩毒、非法堕胎、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色情刊物、卖淫、嫖娼、赌博等。(注:参见[美]乔治·P·威尔逊:“国家干预和无被害人的犯罪”,一舟译,载《法学译丛》1987年第3期,第11页。)由此看来,有些有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也可以考虑适用诱惑侦查,而有些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则没有必要采用诱惑侦查。
其三,关于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及证明标准。由于警察圈套成立标准的主观说在美国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而受其影响,美国司法部1981年制定的《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规定,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只有“足以怀疑”或“有足够理由”相信嫌疑人有犯罪倾向时才可实施诱惑侦查。而德国对此则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即必须是有证据证明嫌疑人即将或正在参与犯罪时,才可考虑适用诱惑侦查。
其四,关于警察圈套成立后的法律意义。诱惑侦查行为一旦被滥用而构成警察圈套时,其意味着什么呢?在美国,被告人可以以警察圈套为由作无罪辩护。在英国,警察圈套不能作为被告人无罪辩护的理由,但法官在量刑时可以考虑警察圈套这一事实而减轻刑罚。(注:参见[英]克罗斯·琼斯著:《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在德国,诱惑侦查超出了其合理的范围,所收集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应予排除。(注:参见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在日本,实践中警察圈套一旦成立,应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而学界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说、免诉说、驳回公诉说等不同主张。(注:参见[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三、诱惑侦查的不当行使——警察圈套成立标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对隐蔽性很强的犯罪案件的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如果在法律上许可的范围内恰当地运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侦查手段一旦被滥用,势必对公民的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那么,如何确定警察的诱惑性侦查行为被滥用而构成警察圈套呢?也即警察圈套成立的标准是什么呢?
关于警察圈套的成立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学者的研究颇具代表,本文以此为例进行探讨。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四个典型的判例,即Sorrells V.United States(1932)、HermanV.U.S(1958)、U.S V.Russell(1973)、Hampton V.United States(1976),确立了判断警察圈套能否成立的主观标准(Subjective approach或Predisposition test)。
依主观标准来看,警察圈套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被告人在被诱惑之前是否有实施犯罪的主观倾向,而不考虑警察的引诱行为,如果警察的引诱行为针对的只是一个已有实施犯罪心理倾向或意图的人,则警察圈套不能成立。反之,如果一个根本没有犯罪心理倾向和意图的人在警方的引诱下,实施了犯罪,则成立警察圈套。在这种标准下,“警察圈套能否成立,必须在陷入圈套的轻率的清白者与轻率的犯罪者之间划一条界线。”(注:See sherman V.U.S.356U.S.369(1958).)依据主观标准,被告人若主张警察圈套成立,则必须先提供证据证明其犯罪是由于警察的引诱而实施的,然后由控方证明被告人本来就有犯意,即使警察不诱惑其实施犯罪,该犯罪也必然是会发生的。
尽管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上述四案确立了警察圈套成立与否的主观标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参与审理这四案的少数法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警察圈套能否成立,考虑的不应是被告人在被诱惑之前有无犯罪倾向,而仅仅应当考虑警察的行为”。(注:See Charles.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 and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and Concepts,the foundation press,P566.)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标准(Objective approach或Conduct of authorities test)。依据客观标准,警察圈套能否成立取决于警察的引诱行为,而与被告人是否有犯意毫无关系。如果警察的引诱行为超出了一般的诱惑范围,即引诱行为在客观上能导致一个没有犯意的人产生犯意,那么警察圈套即可成立。对警察圈套成立的证明责任(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都完全由被告人承担。
在Sorrells V.United States一案中,参与审判的法官罗伯茨(Roberts)、布兰迪斯(Brandeis)、斯通(Stone)首次提出了客观标准说,认为确立警察圈套的基础就是为了“确保警察及其侦查行为的纯洁性这一公共政策”,根据该观点,警察圈套一旦被提出,审查的仅仅是警察的引诱行为,而被告人在被诱惑之前有无犯罪倾向与警察圈套成立与否无关,并由此进一步认为,确定警察圈套是否成立,是一个审查警察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问题,而不是确定被告人有无犯罪的事实问题,因而应由法官裁决,而不应由确定犯罪事实的陪审团来裁决。(注:See Charles.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 and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and Concepts,the foundation press,P568.)
在Sherman V.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参与审判的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道格拉斯(Douglas)、哈兰(Harlan)和布伦南乔因(Brennanjoin)四名法官也认为,判断警察圈套是否成立应采用客观标准。在此案中,弗兰克福特法官认为,采用客观标准有助于树立公众对司法机关公正裁判的信心,并认为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比有三点优势:(1)它更有客观性,便于操作;(2)它更有助于规范警察的侦查行为;(3)它有助于减少对那些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的严重偏见。(注:See Charles.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 and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and Concepts,the foundation press,P569.)
在United StatesV.Russell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参与审判此案的法官斯图尔特(Stewart)和道格拉斯(Douglas)也坚持客观标准,认为主观标准缺乏逻辑理性,并且容易导致对被告人不公正的偏见,并进一步指出,政府的义务是预防犯罪,而不是引起犯罪。(注:See Charles.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 and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and Concepts,the foundation press,P570.)在Hampton V.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根据主观标准对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然而参与此案审理的鲍威尔(Powell)法官对因被告人在被诱惑之前有犯意而被定罪提出了质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无论在什么案子中,当警察只是证明了被告人有犯罪的主观倾向时,没有任何正当程序原则,没有任何司法监督权力会支持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注:See Charles.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 and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and Concepts,the foundation press,P571.)
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内少数法官关于警察圈套成立与否客观标准思潮的发展,诱惑侦查手段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从而要求将警察的诱惑侦查行为纳入合法诉讼原则的呼声日益强烈。直到1978年,联邦第三巡回法院在审判United States V.Twigg一案时,首次采纳了客观标准,并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容忍执法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及对由这一行为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注:参见马跃:“美、日有关诱惑侦查的法理及论争之概观”,载《法学》1998年第11期,第21页。)
纵观美国警察圈套成立标准的判例及学理发展,警察圈套的成立标准经历了由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的转变过程。对此笔者认为,主观标准主张对已有犯罪倾向的人,警察可以采取引诱的行为使其实施犯罪,从而尽快予以逮捕归案,以免继续危害社会,这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主观标准又进一步提出以过去的犯罪记录及平时的恶劣品质、表现等来证明被告人在被诱惑之前已存有犯意,这无疑是错误的,它会使所有刑满释放人员及道德品质低下者都面临着一个被引诱实施犯罪的考验,这等于承认了“天生犯人”这种早已遭到历史所否定的犯罪学理论。而且,即使被告人有犯罪倾向,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提供机会的引诱,他最终是否一定会犯罪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客观标准强调以警察的引诱行为是否会足以引起一个假定还没有犯罪心理倾向的正常的人去实施犯罪。如果是,则构成警察圈套,反之,则不构成警察圈套。这实际上要求对警察的诱惑侦查行为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将其诱惑侦查行为纳入合法诉讼的轨道,这无疑符合现代诉讼程序理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客观标准强调的是以一个正常的没有犯意的人是否会产生犯意为判断标准,这实际上是忽略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所有的被引诱对象都使用同一个标准。这既容易导致一些自我控制能力和抵抗诱惑能力比社会中正常人要低的本无犯意的无辜清白之人因警察的诱惑而犯罪,也容易导致诱惑侦查手段对一些具有反侦查经验的嫌疑人失效,从而放纵了一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这无疑束缚了警察的手脚而不利于打击犯罪。
同时,笔者也认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警察圈套进行的不同界定。主观标准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意,这实际上是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引诱后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来确定警察圈套是否成立。客观标准强调的是警察的引诱行为是否正当,这实际上是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根据警察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来确定警察圈套是否成立。对任何一个公民作出有罪判决,必须是被告人的行为从实体上符合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而且在追诉程序上也必须遵循正当程序的基本标准,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确定警察圈套的成立标准时,应该将实体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程序上是否正当结合起来考虑,而不应单纯地从实体或程序的角度来考虑。
综上,笔者主张,确定警察圈套是否成立,应结合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具体地说,在确定警察圈套是否成立时,应考虑以下三点:
第一,确定被告人在被警察引诱之前是否存在犯意。如果被告人的犯意是由于警察的引诱而产生的,则对被告人定罪在主观要件上就存在重大瑕疵,那么这时就完全不必考虑警察的引诱行为在客观上是否正当,就应认定警察圈套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若主张警察圈套,则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犯罪行为是由于警察的引诱而实施的,然后由控方证明被告人的犯意在警察引诱之前就已存在,警察的引诱只是使被告人的犯罪意图以行为的方式暴露出来。不过,此时控方要证明被告人的犯意,绝不能仅凭被告人的犯罪前科及平时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提供被告人有即将实施犯罪的有关证据。
第二,确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警察的引诱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如果被告人是由于警察的引诱而产生犯意并实施犯罪,这时并不需要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警察的引诱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可认定警察圈套成立。但是,如果被告人即使在被警察引诱之前就存在犯意,这时确定警察的引诱行为是否合法还必须考虑警察的引诱行为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告人在被引诱之前已有犯意,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提供机会型的引诱,被告人也不会或不可能实施犯罪,即警察的引诱行为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警察的侦查行为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看就存在重本瑕疵,这时就可认定警察圈套成立。否则,在被告人被警察引诱之前已有犯意的情况下,如果警察的提供机会型引诱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被告人即使不被警察引诱,其犯罪也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警察机关为了打击犯罪而作出的引诱行为就是正当的,这时警察圈套就不能成立。
第三,确定警察的引诱行为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的其他基本要求。尽管诱惑侦查是一种任意性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诱惑侦查这种主动型的侦查手段极易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因而世界各国一般都对诱惑侦查的使用原则、范围、对象及控制程序作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在确定诱惑侦查是否被滥用而构成警察圈套时,还必须考虑警察的侦查行为是否符合立法中关于实施诱惑侦查的有关程序规定。如果警察的诱惑侦查在程序上有重大违法行为,即使被告人在被引诱之前已存在犯意,而且即使不被警察引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也必然会发生,那么,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也应认定警察的诱惑侦查行为构成警察圈套。
四、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诱惑侦查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方式和手段日益更新,特别是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的大量涌现,这就迫切要求新的侦查手段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实际上,近几年来,侦查机关迫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压力,诱惑性的侦查手段已自发地应用于侦查实践。
在侦查实践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一文。在此通知中明确规定: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时,有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种情况是数量引诱,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可能判处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对具有此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此,笔者认为,本《通知》从保护被告人人权角度出发,对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明确规定应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这对规范诱惑侦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诱惑侦查毕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使许多犯罪案件当场人赃俱获;而另一方面,一旦被滥用,极易使无辜的公民遭受不幸。因此,仅凭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文件来规范诱惑侦查是难以满足司法实践要求的,有必要从立法上建构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这既是当前打击犯罪的紧迫要求,也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客观需要。
立足于当前我国的犯罪形势,借鉴国外关于诱惑侦查的立法及实践,笔者认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建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赋予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地位
同时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制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其规制的内容应包括实施诱惑侦查的原则、适用范围、对象、限度和批准程序等。
1.适用原则。依笔者看来,实施诱惑侦查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即侦查人员在实施诱惑侦查时,必须严格遵守关于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和对象,同时还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遵守程序的规定。二是必要性原则。如前所述,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在适用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得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只有在采用常规侦查手段不可能侦破案件时,才可考虑适用诱惑侦查,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应当尽可能地避免采用诱惑侦查,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应该采用诱惑侦查。对此,美国和德国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美国司法部1981年制定的《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就明确规定:“陷阱的设置,应尽可能地避免。”《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0a条也规定,只有在“采用其他方式侦查方式但成效渺茫或者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派遣“秘密侦查员”实施诱惑侦查。
2.适用范围。各国关于诱惑侦查允许适用的范围不尽一致,然而一般呈现出以下特点:(1)主要是无被害人的隐蔽性犯罪案件。这种案件无论是收集证据,还是抓获罪犯,都极为困难,运用一般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因而不得不采用诱惑侦查方法。(2)重大的、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的案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职业团伙等犯罪领域,可以派遣秘密侦查员使用诱惑侦查。由于诱惑侦查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极度危险性的侦查手段,因而只有在需要侦破的案件是重大的、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时,运用极具危险性的诱惑侦查手段才具有存在的合理基础。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我国的侦查实践,笔者认为,下列案件可以考虑使用诱惑侦查:第一,有关贩卖毒品、假币、淫秽物品、盗版光碟、假证及出售增值税发票等隐蔽性很强的无被害人犯罪案件;第二,对一些经常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被害对象作案的惯犯,在精心准备足以保证引诱者人身安全的条件下可以实施诱惑侦查;第三,对一些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对贿赂案件能否适用诱惑侦查?笔者认为,对贿赂案件采用诱惑侦查,对于打击贪污腐败,无疑是一把利剑,但是国际上用诱惑侦查手段打击贿赂犯罪的政治后果值得注意,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ABSCAM事件以及2001年3月印度发生的政局动荡(注:2001年3月13日,印度某电视台播放了一记者扮成商人以军火交易为诱饵向军方行贿的实况录象,从而导致印度执政党——人民党主席拉克斯曼当晚宣布辞职,随后国防部长辞职及一批高级官员被解职,致使政局动荡。)。因此,贿赂案件能否使用诱惑侦查手段,还必须进一步的权衡利弊,慎重考虑。
3.适用对象。从一定程度上讲,诱惑侦查实际上是对被诱惑者抵制犯罪诱惑能力的严峻考验,因而随意地对一个公民实施诱惑侦查是极不道德的,更不会为法律所允许,这与侦查机关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的任务也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诱惑侦查的对象也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如以上笔者在讨论警察圈套成立的标准时所述,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应当限于特定类型的案件中,且只能在侦查机关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倾向并准备实施犯罪的某一确定的公民。譬如,当犯罪嫌疑人向社会发出“要约”时,警察就可以“承诺”而实施诱惑侦查。
4.适用限度。刑法只能对人的行为定罪,而绝不能对人的思想定罪。因此,即使一个人已有犯意,在该犯意未以犯罪行为的方式暴露出来之前,对有犯意的人也不能定罪,这是主客观统一定罪原则的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在侦查机关对已有犯意的人实施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时,对侦查机关所提供的“机会”也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侦查机关给侦查相对人所提供的机会必须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没有侦查机关的提供,侦查相对人也可以找到其实现犯罪意图的机会。否则,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机会是侦查相对人自己无法找到的机会时,则侦查机关提供的机会就有制造犯罪之嫌。
5.批准程序。为了确保诱惑侦查不被滥用,除在立法上明确上述适用条件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在美国,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有争议的”侦查措施,在实施前,必须事先征求检察官的意见。在德国,采取诱惑侦查这样的秘密侦查手段,必须取得检察院同意,特殊情况下,甚至必须经法官同意。在英国,采用诱惑侦查,必须得到“警察局长明示的书面的授权”。据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同时考虑到诱惑侦查的性质,在我国是否批准允许诱惑侦查,应由侦查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必要时还应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交换意见。
(二)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作为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量刑的情节考虑
事实上,从刑法定罪量刑的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也存在重大影响,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犯罪形态的影响。实施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基本前提是即使警察不引诱,该犯罪也会必然发生。但是,在没有警察引诱的情形下,该犯罪会发展到什么形态呢?是犯罪既遂?还是犯罪预备、犯罪中止或犯罪未遂?这些无疑都是不确定的。基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将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作了严格区分。然而,在诱惑侦查过程中,由于作为引诱者的警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嫌疑人实现其犯罪意图的犯罪行为当然都能“顺利”实施,嫌疑人最终的犯罪形态当然是犯罪既遂,从而使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犯罪行为仅发展到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的可能,从而在量刑上也就失去了减轻、从轻、免除处罚的可能。因此,如果诱惑侦查被采用,而对被告人按犯罪既遂处罚,那么在量刑上就存在不公正的可能。
2.对犯罪地位的影响。我国刑法根据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并明确规定在量刑上应区别对待。在诱惑侦查案件中,都有作为诱惑者的警察参与,有的甚至起主要作用,从形式上看,作为诱惑者的警察应认定为主犯。如果作为被引诱者的被告人在犯罪中,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那么根据刑法规定,被告人就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形式上的主犯因是警察,而警察因诱惑侦查而参与“犯罪”已被赋予合法地位,该主犯不会得到追究。既然主犯不会被认定,被告人也就不可能被认定为从犯,当然也就享受不到从犯量刑的优惠待遇。
因此,基于上述考虑,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案件,法院在量刑时,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被告人本来的犯罪形态和犯罪地位,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建立完善的救济措施,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诱惑性的侦查手段一旦被警察滥用,即构成警察圈套时,被告人将享有那些权利呢?笔者认为,应根据前述警察圈套的成立标准,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寻求平衡。具体来说,有以下措施:
1.赋予被告人无罪辩护的权利。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应享有无罪辩护的权利:一是警察对没有犯罪倾向或犯罪意图的人实施诱惑侦查,从而导致被告人犯罪的;二是尽管被告人有犯罪意图,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提供机会,被告人的犯罪意图也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形下,之所以要赋予被告人无罪辩护的权利,是因为若没有警察的不当侦查行为,被告人根本就不可能实施犯罪。因此,在法庭审理时,若被告人主张无罪,而控方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本身就存在犯罪意图或犯罪倾向、或者控方不能证明警察对被告人提供的“机会”适当,则应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
2.建立相应的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警察对已有犯意的嫌疑人提供了适度的机会,但是,警察在实施这种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过程中,超越了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或违反了其他有关程序的规定,那么,这种通过违反程序规定的诱惑侦查所收集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现代刑事诉讼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模式主要有强制排除和法官自由裁量排除两种立法模式,那么我国对违反正当程序的诱惑侦查所收集的实物证据应该采取那种排除模式呢?笔者认为,鉴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还普遍存在,正当程序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若采取自由裁量的立法模式,则这种排除规则很可能难以落实。因此,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诱惑侦查所收集的实物证据,笔者建议采取强制排除的立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