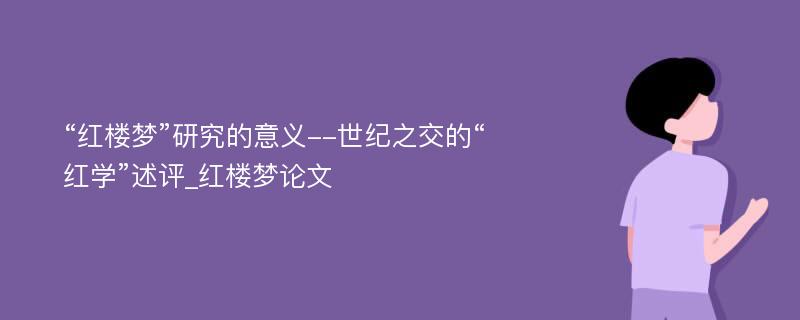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红楼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快就是下一个世纪了,尽管公元的纪年法属于基督教文明,但因为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把公元两千年作为“槛”和“限”来对待,各个学科都纷纷反思、回顾、总结、瞻望,尤其是针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和发展。鉴往知来,这是古训和通例。借着纪元的交替,把工作乘机推动一下,也是人类的智慧。
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华人文学科,红学也恰恰走完了近一百年的历程。对红学作沉思检讨,已经有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之回顾》的发表。笔者不揣谫陋,想主要从红学或《红楼梦》研究的“意义”这一层面提出一点看法。
考据:红学已有的实绩
诚如周汝昌先生所言,够得上学术的“红学”应该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算起。[1]
红学以“考证”开头。不带任何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应该承认,近一个世纪来红学最重要的实绩是在考证方面。
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之核心是“考证”和“辨”。他们从发现带有批语的《石头记》抄本的研究开始,考证出行世的《红楼梦》其实是“真假合璧”——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这一点胡适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实在的夫子自道:“我是曾经在四十年前,研究《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版本的问题。”(《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
后来居上的是周汝昌的奠基之作《〈红楼梦〉新证》,其主体“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六、七十年代另外两位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和吴恩裕,其代表著作《〈红楼梦〉探源》、《有关曹雪芹十种》,从书名标目已经可知其注意重心所在。
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多次红学讨论的热点,一时“小像”,一时“石兄”,一时“墓石”,一时辩驳脂批本的真伪,一时又争论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乃至红楼梦研究所的主要成果《红楼梦》新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和《〈红楼梦〉大辞典》以及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郭豫适和韩进廉的两部红学史著作、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等的出版,都显示出红学的兴奋点大体上仍然没有背离胡适所标榜的“考证”路标。
海外的红学研究也不例外,从赵岗到潘重规,从周策纵到唐德刚、柳存仁,其真正的贡献其实仍不脱考证的范围。
尽管仍然争论不休,但应该说,近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版本和它的作者及其家世等材料的发现、整理、辨析和考证的成绩硕果累累,有目共睹。这些考证的成绩为深入《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基础。
义理:“意义”之障蔽
但《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敞开”过。
清末民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其真实的学术价值十分有限,它仅仅是牵引来西方某种哲学思潮框套《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从“引进”角度而言,自然有其意义,但意义也就仅此而已。从“学术”质素而言,其实难以称道。笔者在《〈石头记〉探佚》中有专文论析,这里从略。
胡适与俞平伯在《红楼梦》“义理”上,所达到的该书只是写曹家“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或“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这种认知,其肤浅也显而易见。“自传说”从《红楼梦》的基本质素认定上很不错,在文本内涵“意义”的开掘上,胡、俞却都从未深入,极不深刻。胡适晚年云:“《红楼梦》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俞平伯在受到批判后,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再发表意见,而其晚年“大彻大悟”的意见却是“只是一部小说”、“高鹗有功,胡适、俞平伯有罪”云云,可见其识力本来并不透彻。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红学基本上成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从李、蓝二人的“四十年间半部书”,到洪广思的“阶级斗争形象史”,已基本上逸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成了政治的婢女。其中当然也能过滤出一些“合理因素”,但不成比例,除了某种历史认识的价值之外,裨益于后学的质素实在不太多。
这一期间有何其芳与蒋和森的红学论著曾对那一时代的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实质是何、蒋二人的著作在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多少显示了一些“人性论”的温馨感性色彩,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对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氛围那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火药味”有所缓冲,对《红楼梦》的内在价值之真正学术性的认知则有根本缺失。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们的论著之立论都不区分前八十回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高鹗续书。[2]
到八、九十年代,从数量上观照,仅从八十年代开始出刊的《〈红楼梦〉学刊》来看,涉及《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人物、审美等方面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之出版也数以十计。表面看来,引进了各种“新思潮”和“新方法”,与八十年代以前思想禁锢的时期比,可谓丰富多彩。但从一个历史的层面考察,这些出版物的大多数(不是没有,但不多)对《红楼梦》的“意义”之彰显并未有突破性的建树。这与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思想之不成熟是互相对应的。
有趣的是,号称“思想自由”的海外红学界,其对《红楼梦》“意义”之认识,则更为浅薄。仅举林语堂《平心论高鹗》和苏雪林所说“原本《红楼梦》文笔之恶劣,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即可见海外的“水平”了(当然也有个别独具慧眼的红学研究者,如李辰冬和宋琪,但他们的影响还未达到开风气、领风骚的规模)。
《红楼梦》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症结:曹、高优劣之辨
这种“意义”的障蔽其突出表现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孰优孰劣长期以来纠缠不清,反复争论而没有结果,并由此而衍生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论战”。
按说,从胡、俞以来,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区别在考证的层面已经完成,鲁迅在其小说史和杂文中已经论到了二者的“绝异”和“殊不类”。照一般的“顺理成章”,下一步就是探索二者之间的“意义”之差异了。可是从胡、俞以降,到李、蓝、何、蒋,到八、九十年代的许多红学专家,尽管在其他一些枝节问题和个人恩怨上有许多矛盾,甚至势同水火,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了惊人的“一致”和“共识”。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意义”,论述后四十回续书的“功绩”——而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老掉牙的话。一曰续书使“残稿”成为“完璧”,有助于原本的流传;二曰续书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写成悲剧,也写了抄家,有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意义;三曰后四十回续书比众多“续书的续书”高明,为大众所认可,为历史所承认。这些道理都不错。但近百年对《红楼梦》的“意义”就反反复复地嚼说这种“常识”性的话头,对曹著和高续的“绝异”那一方面则停留在一般性的“说说”那种水平上,对其中包含的极为巨大的文化问题、美学问题、民族心理问题等“意义”麻木不仁、钝觉滞感,红学界的识力之平俗、思力之贫弱、境界之难超也就不言而喻了。
周汝昌感叹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还“红学”以学》)其实又何止一个胡适?“文字笔墨”尚且无能鉴别,何况更深的“意义”问题呢?
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能在高的学术层次上展开,于是“红学界”就经常被一些“形而下”的问题所困扰,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造成一些“泡沫红学”的景观。
以最近十几年的例子说。在“小像”、“书箱”和“石兄”的锣鼓渐息之后,张家湾出来一块“墓石”,西北又“发现”几首“佚诗”,于是群情激动,众议喧哗,说“真”说“假”,轰动一时。本来类似于这种问题,无论是真是假,也只能算是红学的“边缘”,有其价值,但价值也有限,因为这与《红楼梦》的文本意义距离很远。对这些问题自然也应该研究讨论,但绝不应该成为红学的“中心”和“旋涡”。边缘成了中心,真正的中心问题自然“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这种局面的出现,社会传媒有其责任,但红学界自身的责任还是主要的。
如有一种喜欢弄轰动效应,爱发表声讨声明式的“治学”方法,对曹雪芹的伟大心灵捍格不通,对后四十回续书盲目崇拜,既批俞平伯“崇曹贬高”,又责李希凡“极左”,更攻周汝昌“误导青年”,好像左右逢源,其实连基本的艺术感受力和思考力也很欠缺,其深层思维模式的僵化、落后及受“毒害”之烈只能让人苦笑和叹息。
有三四位研究者分别著书立说,企图推倒胡适、俞平伯对脂批本《石头记》的考证结论,或说脂批本全系“伪造”,或曰脂砚斋故意作伪。本来学术无禁区,任何人都有提出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力,问题是这些“研究”缺乏学术质素,不遵守学术规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顾逞臆非想,全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服善态度,而其根源,也还是识力、思力和艺术感受力的缺失。这些“研究”连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文本差异这样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都无能分判或有意视而不见,更何谈《红楼梦》的“意义”询问?还有什么学术的高水准可言呢?
还有一种,爱红发痴,而治学基础不足,于是走入迷宫,“越钻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据其乐无穷自有天地”,由荣国府联想到故宫的台阶,进而得出林黛玉是刺杀雍正皇帝的侠女,曹雪芹是反清的义士之惊世骇俗的结论。从学术自由的原则,这种观点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进入另一个思维系统,也可能产生意想之外的启发。但作为红学的学术主流,显然不能把舆论中心完全让位给这样的“热点”。
但为什么事实上竟然是一波接一波的“边缘”和“热点”占据了中心舞台呢?无他,根本原因是红学界本身的整体学术质素就有缺陷,故而无力左右局势,把红学引向真正的学术高境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胡适、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的人大都在深邃的思想和生动的艺术感觉这种层面力有未逮,于是考据成绩一枝独秀。但其实考证也离不开思考和感觉,于是出现了以考证版本开山的祖师爷却分辨不清脂批本和程高本孰优孰劣的怪现象,乃至今日又有为脂批本的“真伪”而混战不休的奇观。
连曹著高续的真假优劣这样一个基本的、讨论了近一百年的问题都不能取得共识,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反复纠缠、自说自话式的“论争”,红学界的“水平”和基本质素确实需要认真自审。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石头记》呢?
“两个半”的贡献
我在《〈石头记〉探佚》中曾说:“真正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曹雪芹,读懂了《红楼梦》的,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两个半人:胡风和周汝昌,鲁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只读懂了一半,但鲁迅的思想实质是与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对伦理本位文化产生的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深刻绝望。”
不见有人来反驳我。但这并非就是大家都赞同我。拙著《石头记探佚》旧版新版,问世十余年,也不见众多反对探佚的专家学者有哪一位写过一篇正面文章来“回应”一下,我等着被批得“体无完肤”,可是等不到,只有那么只言片语偶尔来挠一下痒就又溜之大吉了。
这是顺笔提及,还是说“两个半”。这两个半里只有一个可以称作专业红学家,其他的两位都只能算红学的票友。但这两位中一位是思想家兼小说家,一位是文艺理论家兼诗人,而他们又都是革命家。
我以为,这就是红学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只有具有思想家、艺术家和革命家质素的人才有可能把红学或《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引向真正的学术领域。不一定要是思想家、艺术家或革命家,但一定要具备这种质素。因为《红楼梦》本身是有这些质素的。
这“两个半”,都不约而同地看出了曹著和高续的“绝异”,都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境界和文明高度的“中华大文化”的根本问题,都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但又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地并不太相同,鲁基本是从直觉生发,胡基本是从境遇激发,周则是从专业研究感发。
“两个半”的具体分析拙著已经作过,这里不再枝蔓。鲁与胡已作古,周还在,任何人都非圣贤,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缺。我这里只论学,坚决拒绝阑入任何“门户”“派别”的无聊纠纷。
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
纵观近百年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一曰“婚恋主题”,二曰“政治主题”。虽然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在说法上花样翻新,其实质大体上不出此两端。
从最初清代人读《红楼梦》为拥钗还是拥黛而争得互相“饱以老拳”,到“革命派”赞美黛玉的“叛逆”和批判宝钗的“正统”,都是围绕着宝玉、黛玉和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这一“中心思想”作文章。王蒙最近说过一句幽默的断语,他说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要拥护黛玉,作为执政党则需肯定宝钗。可说概括了近四十年来红楼梦评论的精髓。
政治主题则从胡、俞“新红学”出现之前的蔡元培等的“旧红学”主张《红楼梦》有“反清复明”、“反满”等等微言大义,到毛泽东说《红楼梦》的第四回乃全书“总纲”,《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以至有“阶级斗争形象史”等提法的滥觞。索隐派和革命派其实有着共同的交叉点。
可见,婚恋主题或政治主题,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下,强调不同的方面而已。
这说明,《红楼梦》的文本里的确既存在着“婚恋”,也存在着“政治”。但无论是“婚恋”还是“政治”,都只是小说文本里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中华大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说出婚恋或政治,并不就是研究,关键问题是如何对这种文本现象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能达到这种目标,当然需要有具备思考穿透力量的睿智者,否则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例如,数十年来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有所谓“色空观念”的“局限性”的泛谈,但究其实,却是从后四十回续书写了“宝玉出家”这一情节推衍而来,通过探佚对曹雪芹原著整体作研究所得结论恰恰相反。没有严格区分和深入解剖曹著和高续的眼力、思力和能力,就事论事,于是“宝玉出家”一方面是逃避现实的“色空”,另一方面是反抗封建的“决裂”,既是对黛玉的永恒怀恋,又是对家庭压迫的反弹,婚恋,政治,都挂上钩,似乎头头是道,其实是一锅糊涂稀粥。
这正是红学界的薄弱环节所在。如前所述,红学界缺少的正是具有思想和美学质素的大家大师。
辞章:《红楼梦》的艺术与中华文化
有一种似乎振振有词的说法:《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小说来对待,红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这部小说的艺术,也就是所谓“语言、形象、性格、结构”——这才是红学的正路,《红楼梦》研究的正宗。而且,这部小说就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应该一视同仁,不得分论,因为“历史”和“群众”已经“接受”了它。
这种说法似乎有对红学中各种“边缘”排挤了“中心”作反拨的意思,但它的根本缺点是看现象不看本质,重形式不重内容,要表面不要实际,用一句老话说就是孤立地、静止地、绝对地、片面地看问题,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思力、悟性和高层次研究质素的表现。
考据、义理、辞章——这是中华传统文学艺术批评的三个层次,或曰三个方面。考据是背景、基础,义理是思想、意义,辞章指艺术、审美。但这三者,却又都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原不是像楚河汉界一般泾渭分明的。中华文化是最懂辩证法、最讲究“整体、联系”的文化,而《红楼梦》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最精致、最高级、最伟大的宁馨儿,则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特性。
举例而言,曹学和红学互为表里,“家史”和“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象”和“假(借)象”彼此映照;草蛇灰线的伏笔影射来源于“推背图”一类历史图谶;“假语村言”与“春秋笔法”及“虚实空灵”一脉相承……这所有一切,都是《红楼梦》的“艺术”和“美学”,是曹雪芹的独家秘传,后四十回续书所没有的。所有这一切又都来源于中华文化,是按照西方文艺理论那一套“典型”“形象”的阐释系统所无法发现也无法分析定位的。
《红楼梦》的艺术和审美,是中华文化的艺术和审美,当然也有和西方的艺术和审美相通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它的中华文化的“个性”。这种艺术和文化的“鱼水关系”是如此不可分离,如此微妙精巧,如此浑然一体和大化无形,周汝昌研究红学四五十年,直到最近才初理头绪,写出了《红楼艺术》的专书。
以西方文艺理论一般小说学的路数来评析《红楼梦》艺术的著述,自然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但这种价值显然是不可与抉得中华文化之秘的研究同日而语的。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但这是一部从中华文化的精光灵气中孕育出来的小说,是流淌和跳动着中华文化的血液和脉搏的小说。所以,面对《红楼梦》,就不仅要面对“一部小说”,而且要面对中华文化。
故,红学也就不能仅仅等同于一般小说学。
契合:红学与西学
强调《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共生态,并不是要对西方文化实行“关门主义”。问题仍然在于,如何在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寻找到最恰当的契合点。
事实上,西方文化的优越正在于其思维的无比活跃,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各种方法论此起彼伏,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戒律清规,没有禁区忌讳。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的繁荣与西方各种新思潮的输入有着密切关系,正是“改革、开放”根本政策的产物。
但简单的“拿来”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消化的中介。否则生搬硬套,结果就是郢书燕说。仍然说《红楼梦》研究,红学界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现有的红学界的学术梯队和结构对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本来就缺乏实在的借鉴能力,真正能从根本上弄懂弄通西方各种先锋思潮的人才其实很少,往往是根据一些二手或三手的转述往《红楼梦》上套一套,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会十分理想。以近十几年发表过的文章论,摆弄新名词的也不少,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罗钢和陈庄合撰的《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等极少数几篇。许多文章让人觉得作者对中华文化没有搞通,对《红楼梦》没有弄懂,对西方文化更只是略知皮毛,就在那里炮制“中西合璧”。周汝昌先生在其新著《红楼艺术》中说:“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原来也想用西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方法来助讲《红楼梦》的结构,后来认为这不妥当,因为那不符合我研究的时序:我初次了解西方结构主义小说叙事学(Structurial,Narratology)具体内容是晚到1989年加拿大高辛勇教授寄赐他的佳著《形名学与叙事理论:结构主义与小说叙事法》一书时的事情了,所以应留意不要让读者认为我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才来研究《红楼》结构的,完全不是。我一向不赞成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切特点还不懂得即生搬硬套外来的模式主张等等。只应先把自己的文化文学传统弄得略为清楚时,再来借助、借鉴人家的好的方法来一起说明问题。”以周先生的年资名望,尚能如此老实坦白,不强不知以为知,则其他人应当如何呢?
怎样把各种理论和方法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红楼梦》的研究上面,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只知道西方的理论不懂《红楼梦》和中华文化不行,反之也行不通。海外的学人应该是了解各种西方理论的,但他们也并没有对《红楼梦》研究作出多么杰出的成绩,许多在海外研究《红楼梦》的学人仍然不愿严格区分曹著和高续,把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对待,并援以“接受美学”的理论支持,这说明他们不仅对《红楼梦》缺少慧眼,而且对“接受美学”也不能活学活用。王国维是第一个用西方理论评论《红楼梦》的中国学者,其实际效果却对《红楼梦》的文本意义隔靴搔痒,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详细论述见《〈石头记〉探佚》)
所以,红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需要一批后起之秀,一批有能力吸收外来理论思潮,又对“国学”确有根基和肯下功夫的青年学人,一些在思考和艺术感觉方面确有实力的新鲜血液。没有这样一批新生力量,《红楼梦》的“意义”研究仍然不可能有大的进展和突破,红学仍然要在各种“边缘”和“热点”中折腾。可喜的是,最近已经出现了新的曙光,一批红学界外的搞理论和文化的青年学人已经闯进了红学界,以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敏锐触角为红学开拓出新的视域。就我很有限的眼界所及,如李劼的论著《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陈村的文章《意淫的哀伤》、陈维昭的论文《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力作。可以断言,二十一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将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将在红学、国学与西学的契合处作出崭新的创造。他们将接受二十世纪红学的考证成果,但在精神气质和义理意义层面,他们则将直接承继鲁迅、胡风和周汝昌的血脉。
意义:《红楼梦》研究与中华民族魂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但这是一部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小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美学之光、艺术之神。
《红楼梦》研究,当然包括作为一部小说的文艺创作和鉴赏层面,也包括各种基础和背景的考辨,但绝不仅仅局限于这种层面。
《红楼梦》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
从庄周到李贽,中华民族的反抗叛逆和创造精神在历史的漫漫长夜中顽强地生长着,从屈原、史迁到阮籍、李白到《西厢记》、《牡丹亭》,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在正统意识的压抑和扭曲下倔强地灿烂开放着。但最伟大的创造者、叛逆者和艺术家是曹雪芹,最瑰丽的精神文明之花是《红楼梦》。从鲁迅到柏杨,都对中华文化中腐朽和阴暗的一面作了沉痛的批判,但早在他们之前,曹雪芹已经通过《红楼梦》的创造,对此作了形象化、艺术化的反思。同时,曹雪芹奇迹般地承载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精粹与珍异,他的精血气骨直接通向了先秦诸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一个新的凤凰涅槃,需要光大历史的精彩,同时需要扬弃历史的负担。《红楼梦》研究应该在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塑再振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此社会转型、世纪交替的历史性关头,在此华夏文化救亡与更新愈益为全民族所关注的焦点时刻,在此东西方文化空前碰撞、交流对话的大时代,红学界难道不应该慎重思考自己的责任吗?红学的前途,《红楼梦》研究的意义,难道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吗?
本文所论,提纲挈领而已,如要求“严密”,则每段之下应有“笺疏”——更细致的证例、说解……但限于发表体制,也只能如此粗具规模。希望能引发大家的思索讨论,则红学幸甚,中华文化幸甚!
注释:
[1]这样说是以“学术”的基本质素定位,并非说索隐派、评点派等就毫无贡献和合理因素。
[2]何其芳提出的“共名说”本来具有理论潜势,他的艺术感觉亦颇佳,故其论“红”多有可观之处,但由于他不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红楼梦》”,故不能鞭辟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