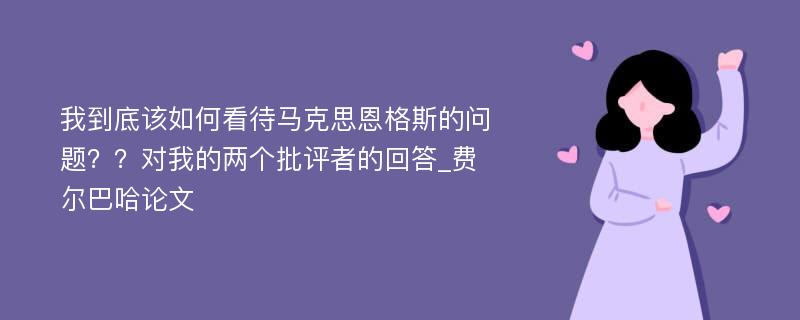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两位论文,怎样看待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楹、周世兴两教授的《追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对何中华教授反批评的批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以下简称《实质》,引用不再注明出处)(《哲学原理》2008年第12期转载)一文,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观点及其辩护进行再反驳,读后觉得有必要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讨论。鉴于《实质》涉及到某些与学术有关的问题,我仍愿意作出自己的回答,以利于澄清是非。
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这是《实质》对鄙人观点的称谓,姑且接受之)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会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相关成果的影响,但它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和条件发生作用。问题是本然地存在着的,不是杜撰或炒作的结果,更非人为制造出来的。因此,它并非像《实质》所说的那样,“是变相的西方马克思学之‘马恩对立论’或其变种,其基本手法是以‘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准把恩格斯费尔巴哈化,从而把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异质性差距’归结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和分野。”其实,我并未先验地把马恩各自的思想了解为不同的东西,先入为主地断言它们有所谓异质性。我明明说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是否存在异质性,只能是研究的结果,而不能作为研究的前提予以先验地断言”①,而且事实上我也曾先行地做过这方面的考察和讨论②。因此,我在认定马恩思想存在异质性差别时,并非从抽象原则出发得出自己判断的,而是立足于马恩著作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实际得出自己结论的。
《实质》把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说成是一个“无由无据”的问题,似难成立。对我而言,它并非无端的问题,而是切己的问题。我早年读马恩著作时遇到的一个困惑是,两位作者的思想关系并不完全像一般教科书所揭示的那样一致。只要敢于正视事实,相信每个过来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当时并不知道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我们并非“鹦鹉学舌”般跟在别人后面去独断地“宣布”马克思思想是“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思想是“旧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具有异质性距离,而是按照马恩著作本身所包含的不同取向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面目得出自己判断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之于我们,所谓的“由”就是“重读马克思”;所谓的“据”就是马恩本人的著作。毋庸讳言,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体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那里得到了诸方面印证;我们在形成自己的有关观点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它们的影响。
诚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清算的直接对象无疑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从它的标题中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我也从未说过这部著作是针对费尔巴哈的,而仅仅是说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已经同费氏哲学有着原则性的分歧。因为从原则上说,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对于鲍威尔等人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费氏哲学。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开始”的所谓“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究竟是所谓“接续”费氏的工作(像《实质》所认为的那样),还是从实质方面“告别”费尔巴哈?作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家,费氏在其立场的意义上最多能够走多远?换言之,他“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必须指出,我们不能向费氏本人提出超越他的思想局限性的苛求。因此,马克思对费氏哲学所做的扬弃,不应被视为费氏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于费氏的“超出”,不是思想上的“接续”,而是一种“革命”。
青年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好,发表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也好,都不意味着他已经确立起新哲学的原则。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青年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无疑得益于恩格斯早期著作和思想的启发(马克思对此也明确承认),但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妨碍马克思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和地位。英国学者卡弗认为,“这种方法(指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做法——引者注)就是恩格斯提前使用的先决条件这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③按照卡弗的观点,恩格斯“提前使用”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特有的方法。暂且不管这是否符合事实(恩格斯在关注经济现象方面的确领先于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哲学上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第一原则”肯定下来。在此问题上,如果说恩格斯是自发的,马克思则是自觉的。这个差别无疑被卡弗忽视了,由此造成了他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奇怪的是,在任何重要程度上,它却是一条恩格斯不曾再走的路。”④这正好可以用恩格斯的自发性来予以解释。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分工使然,但若这种方法论具有前提意义,那么无论怎样分工,都不能放弃本应作为马恩共同研究基础并为其分享的这个方法论原则。卡弗未能注意到马恩之间更具前提性的差别,即马克思从事了以实践为终极的原初范畴在哲学预设层面上自觉奠基这一卓越的和原创性的工作,而恩格斯显然并未去做这项工作。诚如卡弗所说的,“对马克思来说最有趣的是,那些活动(指恩格斯在英国的实践活动——引者注)不只是报纸杂志和工业调查,而且也包括了一种理论规划——《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它表现出了完全超过马克思当时成就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分析技能。”⑤但恩格斯领先于马克思,仅仅是在具体研究而非本体论奠基方面成立的。
《实质》认为把“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成“实践本体论”是错误的,是“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怪想”的产物。既然是“解释”,就不能不用不同于马克思的表述来展开,倘若只能重复马克思的已有说法,那么解释者就只好闭嘴,任何研究和解释都将变得多余。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用了新的说法,而仅仅在于新的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精神。
《实质》由“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推测出所谓“思辨的、理论的唯物主义者”,似乎前者是同后者对称的,不知其根据何在。事实上,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来看,他所否定的正是那种以“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为特征的把世界了解为“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因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⑦。这同《提纲》第11条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根本旨趣若不能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被肯定,就只能局限于“宣布”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的错误,而不能真正驳倒它、进而超越它。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⑧即使《实质》也承认:“实际上,认识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强调确立实践思维以观察世界,强调马克思哲学之实质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显然,这一“完全正确”的立场若不能作为自觉的哲学原则加以确立,就将无法超出个人的偏好和任意的性质。既然承认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并以实践为视角“观察世界”,那么在哲学意义上,不从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实践的终极的原初性地位,这一切又何以能够获得逻辑上的保障呢?没有一种实践的本体论承诺,所谓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所谓“确立实践思维以观察世界”、所谓“马克思哲学之实质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云云,岂不变成了空中楼阁或空头支票?它又如何有效地应对来自唯心主义的挑战,怎样有效地克服旧唯物主义的致命缺陷呢?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回到实践,更深刻的在于他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自觉地确认,从而在本体论层面上肯定了实践的终极的原初性地位。
我们甚至可以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出赞扬英国社会主义者重视实践的不少论述,但这既不能说明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不能证明恩格斯因为肯定他们,就具备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青年恩格斯说:“……就是在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像共产主义者所称呼的十足的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⑨其实,他是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各自特点时说这番话的。他一上来就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和更为实际”⑩,认为前者“判断事物的方法很好:一切问题他们都从经验和确凿可靠的事实出发”(11)。所谓“实践的无神论者”无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上帝和其他宗教概念一类的虚幻的东西根本不在话下”(12)。这显然与英国民族是一个特别强调事功和务实的民族(与其相比,法国浪漫,德国思辨)有关,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关。但恩格斯揭示这一点,既不意味着承认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有了一种类似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也不意味着恩格斯试图自觉地去建构一种基于实践的原初性而成立的哲学立场。恩格斯写道:“在一切有关实践、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大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很少了。”(13)对这段话的理解,同样可以遵循上述原则,此不赘述。恩格斯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是纯实践家……;他们的哲学是纯英国的怀疑论哲学,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理论,而在实践中遵循唯物主义,他们的整个社会纲领就以唯物主义为基础。”(14)“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是“纯实践家”,但却未能把“实践”作为一个哲学的本体论原则肯定下来。因此,他同实践唯物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不能说只要从事实践和重视实践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者。关键在于他是否在哲学意义上重视实践。正像我们不能因为人人都有一副肉体,就认为人人都是生理学家;因为人人都有思想观念,就认为人人都是唯心论者。注重实践,同那种在自觉的层面上把“实践”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确认,完全是两码事。诚然,恩格斯欣赏这种重视实践的态度,但不能因此说他就是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了。
其实,重视现实和实践,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因为它所面临的任务就是批判现状。例如,“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15)但这种做法的虚妄性在于,它误以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16)。其实,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和实践联系起来”,也不在于是否“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而仅仅在于学说本身是否包含着对实践之终极原初性的自觉确认。在马克思语境中,“共产主义者”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是盲目的和自发的实践家,而是在哲学层面上把“实践”确立为“第一原则”的自觉实践家。这种差别离开了实践作为本体范畴的哲学建构,就不可能体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7)。仅仅在一般意义上重视实践还不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若不能在哲学的终极原初性基础上确认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就无法达到马克思所追求的那种境界。
《实质》提出,“无论把马克思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首先都应当确认它是‘唯物主义’,然后才是‘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讨论旧唯物论和新唯物论之间的关系时,决不能采取这样一种做法——从它们当中挑出点儿相同的东西,然后再挑出点儿相异的东西——来了解它们彼此的关系。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论的关系问题,决不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分类学问题。拿知性思维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遮蔽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质及其革命性的变革意义。《实质》还追问道:“没有了‘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实践’所依为何所由为何?”实践作为本体范畴所固有的终极的原初性,决定了它是无法由任何一个他者来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具有不可还原性。《实质》的这种追问方式本身,就是对实践的终极原初性这一本体范畴之性质的无视和消解。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唯物主义之“物”不过是“实践”的修饰词而已,“物质”只能是从属于“实践”的而不能是相反。
《实质》认为,把“实践唯物主义”诠释为“实践本体论”,只能导致“唯实践主义”而不再是“唯物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怎么看马克思仍然沿用“唯物主义”这个称谓?他所谓的“物”究竟何所指?我曾提出,马克思所谓的“物”不再是以往的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个“物”,而仅仅是指实践本身的属性,如“物质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之类的措辞。青年马克思说过:“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18)。所谓“现实的”,是针对黑格尔关于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而言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这种观点,“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马克思所谓的“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19)。“感性活动”一定内在地具有物质属性或物质层面。马克思仅仅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称谓的,它不过是用来修饰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的。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决不是意味着在“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另外再加上对于实践地位的强调。
《实质》把我的主张叫做“‘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并认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言外之意还可以有一种非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在我看来,这种离开实践本体论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才真正面临着跌入二元论陷阱的危险。我不知道非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究竟该如何理解,《实质》似乎也未曾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若在“实践唯物主义”中保留“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像恩格斯所主张的那样),其结果必然是要么窒息作为“第一原则”的“实践”,要么解构掉这个“永久性基础”。因为两者无法在一个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彼此兼容。我认为,马克思思想虽然没有“本体论”之名,却有“本体论”之实。因为我们实在无法设想能够撇开本体论承诺而在哲学的原初基础意义上确立起“第一原则”。
《实质》认为,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实践本体论”,“仍然不过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老套的理解”。据说“无论是全部十一条《提纲》还是《形态》,都不能为所谓马克思哲学之‘本体论’从而‘实践本体论’提供任何论据上的支持”。这一论断无视30年来国内哲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之讨论的进展,而仅仅是“宣布”这样一个独断的信条,并没有给出任何“证明”。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质》作者不知何以会发生如此疏忽?问题在于,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套”理解又是什么呢?遗憾的是,《实质》并没有将其展示给我们。据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本体论式’的‘哲学’,因而从根本上说来它‘不谈本体论问题’”。这意味着除了本体论“哲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非本体论的“哲学”。我们无法设想,离开“本体论”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才算是“谈本体论问题”,是不是只有像传统本体论那样去谈论,才算是“谈本体论问题”?既然承认马克思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最伟大变革,那么以被马克思超越了的旧本体论形态为判准去考量马克思的新本体论,当然不可能“发现”马克思有自己的本体论思想。但这却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思维陷阱。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缺少的不是“本体论”,缺少的仅仅是“发现”。关键在于解读者是否具备“发现”的能力本身,若把判据滞留于本体论的古典形态,当然无法具备这种“发现”能力。
所谓本体论,就是追问并给出逻辑意义上的“第一原因”的学问,它只有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才成为可能。有无本体论,乃是区分哲学与非哲学的唯一判据。恩格斯的确说过:现代唯物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20)。但离开了本体论承诺的“世界观”,将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主观的任性,它无法达到哲学意义上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说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但事物的本真性有黑格尔意义上的,也有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还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恰当的呢?这种本真性的判准倘若脱离了特定的本体论承诺是不可能找到的。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的彻底性归根到底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恰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真谛所在。所谓“理论的彻底性”,就包括理论的本体论承诺的确立。因此,“世界观”视野之合法性的获得,无法离开特定的本体论预设。
诚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21)但必须指出,马克思是在批评施蒂纳及其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时说这番话的,这里所谓的“哲学”是有所指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特指那种思辨的哲学。所谓“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无非是指通过“把哲学搁在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卸去了意识形态包袱之后,去面对现实所采取的姿态,仅此而已。需要注意,马克思决没有因此过滤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所固有的反思的维度。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22),是“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3)。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马克思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实现这种“认识”或“理解”的努力本身罢了。其实,正如批判逻辑也必须使用逻辑一样,马克思批判思辨哲学也离不开思辨。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思辨本身所确立的原则是什么,它又是否恰当。
《实质》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给予彻底批判的正是他那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满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非所谓‘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这种说法难以成立。首先,在费氏那里,“唯心主义历史观”恰恰是他的“旧唯物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致命缺陷,怎么能够把它们机械地截然分开呢?由于费氏从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的角度看待历史,就不能理解精神的从属性,因为他无法找到比主观与客观之外在分裂更为原始的基础。他的这种脱离实践之原初性的立场,必然导致其哲学的直观性视角,从而无法解释历史中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缠绕关系。诚然,马克思说过:“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4)但若联系上下文,就不难看出,这正是对费氏“旧唯物主义”致命缺陷本身的揭露和批评。后来恩格斯也说: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25)。但问题在于,晚年恩格斯在此问题上同马克思的理解仍存有不容忽视的距离。例如恩格斯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虽然有‘基础’(指‘唯物主义的基础’——引者注),但是在这里(指人类社会及其科学——引者注)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26)恩格斯不懂得,费氏之所以在历史观领域“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归根到底乃在于他的哲学赖以立足的“基础”本身所内在地固有的缺陷。正因为如此,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才对费氏所代表的旧唯物论彻底失望。这恰好构成了马克思在《提纲》中最为自觉而集中地表达的从原初基础的层面上重建哲学的最直接的契机和动因。
《实质》写道:“费尔巴哈不是也想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但他实现超越了吗?”言外之意,似乎只要费氏试图实现“超越”而未能成功,就可以据此宣布“超越”诉求的荒谬和不可能。其实,试图超越是一回事,是否超越是另一回事,能否超越又是一回事,怎么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呢?毋庸讳言,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事实上,黑格尔试图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已经包含着这种哲学动机了。费氏专门有一篇著作,题目就叫做“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27)。赫斯在其《行动哲学》中也指出:“抽象的唯物主义和唯灵论相互影响”,“只要二元论没在一切领域,即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中被战胜,自由还不会取得胜利。”(28)但他们都没有完成这种超越。问题仅仅在于,究竟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上,这种“超越”才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于他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质》质问道:“难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形态》作者的恩格斯所讲的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就是指那个与人无关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情形究竟如何呢?在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时,恩格斯是从自然界的演化史和人的思维的物质前提这两个维度为“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作辩护的(29)。在这里,无论是人类史前意义上的自然界还是作为思维之基础的物质,都是被当作人的不在场的规定来予以设想的。因为在恩格斯的语境中,倘若不超出人的存在亦即人的感性活动的范围,他所试图捍卫的“唯物主义”就无从获得其合法性。恩格斯明确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30)。在他看来,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31)。问题在于,“物质”其实面临着与“存在”同样的尴尬。这里的要害不在于是“物质”还是“存在”,而在于恩格斯设想了“我们的视野”之“内”“外”的分别。这种分别表明恩格斯在哲学前提的意义上预设了一个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领域。如果拿这种逻辑来考量“物质”,我们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宣布“物质”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同“存在”相比,没有任何优越性和豁免权。而恩格斯所谓的“物质”又是什么呢?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这样写道:“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32)他还说:“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出来”(33)。即使我们充分注意到恩格斯强调了“感官可感知”这一角度,也无法凸显“感性对象”同“感性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及其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疏离。
《实质》提出,“难道说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不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讲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似乎在《实质》作者看来,这样讲就足以抹平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差别。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界的优先性仅仅构成实践辩证法的“前提”,但不能充当其内在“理由”,而且马克思在提及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时的总体命意恰恰是消解人的不在场这一角度(34)。恩格斯诚然也曾提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而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就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也涉及实践的重要作用但仅仅是囿于认识论范围而未曾在本体论意义上被确认一样。因此,即使像《实质》所质问的那样,马恩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抹煞的思想距离。
《实质》质问道:“‘异质性’、‘虚会’方法欲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引向何方”?首先,所谓“异质性”不是一种“方法”,而是通过研究马恩思想得出的一种结论。方法可以先验地有效,而结论不能作为研究的前提,它只能是研究的结果。因此,把“异质性”同“虚会”一并作为“方法”相提并论并不恰当。“异质性”的结论若是尊重事实的话,也根本不存在“对差异的过分强调”、“对差异的过分迷恋”问题,更谈不上“绝对否认同一性而走向相对主义”。至于《实质》提出的把马恩思想研究“引向何方”的质问,我的回答是:本人人微言轻,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方向”的作用;我在研究中也从未意识到要对什么施加影响;即使客观上产生某种影响(如引发了《实质》作者的商榷),大概也不会像《实质》所说的那样可怕。至于《实质》说“目的”“是要肢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完整性从而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差别’、‘差距’以至‘对立’”云云,倒像是一种“无由无据”的“怪想”。
《实质》还绕开争论的具体问题和特定语境,一般地讨论起什么“异质性”和“同质性”各自的片面性,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认识的真理性可能在于其(即所谓‘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引者注)合题之中,即既要看到‘异中之同’还要看到‘同中之异’,而任何夸大或者否认某个方面的企图都会导向谬误。”这种抽象的“同异之辨”,是完全撇开马恩的思想实际,作一种抽象的逻辑推演的结果。所谓“合题”云云,也不过是一种折衷罢了。离开了马恩思想的特定文本和语境,离开了他们思想及其关系的具体展现过程,去空洞地谈论异同关系,抽象地辨析“同质论”和“异质论”孰是孰非,一般化地说“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都不可或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得到的判断只能属于后天综合判断而非先天分析判断,它仅仅取决于经验事实而并非逻辑推演。
《实质》多处指责我“以‘虚会’代替‘实证’”,这一指责与事实不符。我从未讲过“可以以‘虚会’代替‘实证’”之类的话,而是明明说过:“在实证的范围内,无疑必须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语)的原则。但当证据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合乎情理的推论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之所以提出“虚会”问题,乃是针对《实质》作者在前一篇商榷文章中对“推测”的贬低和拒绝而言的。正是恩格斯说过:“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35)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那么在《实质》作者看来严格得如“科学”的思想史领域(所谓“思想史是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领域,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应该同样是如此。作为一种逻辑的“推测”能力,“理论思维”无疑具有超越经验归纳的性质。正视并承认这一点,同《实质》所谓的那种“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虚无飘缈的‘虚会’”,究竟有何关联?我未“宣称”“可以不用‘实证’”,只是在那篇文章中强调“实证”方法有自身的局限性,以便为必要的“推测”方法(所谓“虚会”)保留自己的地盘而已。《实质》说:“当所有的文献证据都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的时候,提出一种离奇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异质性差距’的观点,竟然宣称可以不用‘实证’同时又要求不接受这种观点的读者去‘证伪’它。”这段话颇值得推敲。首先,说“所有的文献证据都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这本身不过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而已,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对此究竟是怎样给出有根有据的“证明”的。其次,我只是说未曾在《实质》作者的前一篇商榷文章中见到对莱文观点的“证伪”,并未说莱文的观点不具有可证伪性。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陈述不在于它的被证伪,而仅仅在于它具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没有证伪一个观点,并不等于这个观点就不具有可证伪性,这完全是两回事。莱文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是有其思想史根据的。若想怀疑以至于否定他的观点,离开了足以证伪它的证据,就是缺乏理由的。这难道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吗?这同是否“难为读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实质》试图把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同“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剥离开来,以便将我们揭示的马恩在思想上存在的异质性差别,说成是仅仅为解读者自己所杜撰出来的,与马恩本身的思想无关。问题在于,“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同“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能否割裂开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两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关联。“‘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时产生的问题”既可以由我们本身的误读造成,也可以由“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造成。究竟是哪一种情况,不能够依靠先验的判断来解决,只能诉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的追问和清算。在这种追问之先就人为地割裂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缺乏理由的。对于《实质》来说,它可以收到一个“双刃”的效果:一方面可以轻易地把“异质性差别”观点说成是臆造和杜撰,另一方面又可以替自己的“同质说”做辩护。在《实质》看来,凡是肯定马恩在思想上具有异质性差别,就一定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而有杜撰或赋义之嫌;凡是否认这种差别的存在,就一定是“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但试图通过这种割裂来逃避挑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脱离了我们解释的纯客观的“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是朴素实在论的。在哲学解释学已经诞生的今天,这是一种过时的错误想像。
《实质》从马克思的《提纲》第1条中的一个句式来分析作者的哲学立场,恐怕也无助于证成《实质》的观点。我早已说过,在《提纲》第1条中,马克思是把唯物论和唯心论了解为正题和反题关系的。马克思说“只是(德文‘nur’/英文‘only’)从……,而不是把……”等等,不过是在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各自的片面性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决不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因为折衷主义是不能克服二元论缺陷的。所以,说旧唯物论“只是从……”,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除了保留这个方面之外,再增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在本体论前提上,唯物论同唯心论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否则也就不会有它们之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了。在此问题上,《实质》的理解倒是符合恩格斯的观点(因为恩格斯是明确主张要保留“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这个前提的),但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是试图“扬弃”对立、重建基础。这与保留对立甚至强化对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实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旧唯物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唯心论“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它们都是一种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的致命的片面性。因为二者都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36)。显然,“只是从……,而不是把……”这一句式所显示的并非一种补充关系,而是一种以扬弃的方式实现的超越关系。这可以从《提纲》第11条中相似的句式那里看得更清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7)“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分别体现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姿态,而非意味着在“解释世界”之外或之上再增加“改变世界”。
至于对马克思所作解释的“平权”问题,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出它的。我主张作为马克思的后来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恩格斯在内)在对马克思的解释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是针对我的批评者拒绝我们对于马克思的评论而言的。因为批评者暗示我们必须事先保证自己谈论的是“马克思的本真思想”才有资格解释马克思,还暗示由于我们比恩格斯蹩脚得多所以没有资格就马克思的思想及恩格斯的解释说三道四。所以,我讲“平权”问题时,是有其特定语境和附加条件的。无视这些,去抽象地讨论并反驳“平权”说,既不公道也不郑重。人们解释马克思,其能力可以有大小,水平可以有高下,但权利则是对等的。混淆权利和能力(水平仅仅取决于能力),难免引起问题的混乱,从而遮蔽问题的实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任何谈论,判断它们是否“任意的”,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新奇的观点”抑或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观点”,到底该由谁说了算?恐怕只能诉诸平等的讨论和对话,只能在建设性的讨论中逐步被澄清和凸显,而不能靠某些人的充满成见的裁决。《实质》还提到对马克思解释的“公共性”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公共性”只有在允许不同解释充分展开及相互对话中才有可能被达成。可见,公共性恰恰意味着宽容精神而非武断地拒绝和盲目地排他。因为宽容是公共性的条件而不是它的敌人。
注释:
①何中华:《是“谬见”,还是真实?——对一种责难的回应》,[广州]《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
②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济南]《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③④⑤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第47页,第50页。
⑥⑦(24)(36)(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第96-97页,第78页,第58页,第61页。
⑧(25)(26)(32)(33)(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第241页,第230页,第343页,第343页,第300页。
⑨⑩(11)(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7页,第566页,第567页,第567页,第592页,第653页。
(15)(16)(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第580页,第262页。
(17)(18)(19)(22)(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第107页,第102页,第128页,第57页。
(20)(29)(3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第374-375页,第383页,第383页。
(2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93-219页。
(28)黄枬森、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34)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本体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异质性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