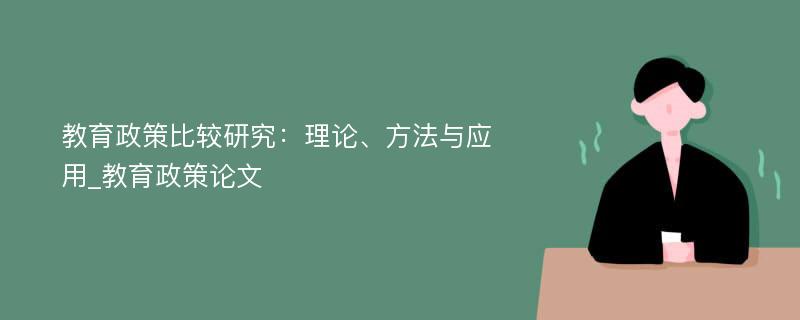
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应用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04-0033-05
政策的比较研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重要趋势。在教育领域,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也是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国际与比较教育工作者们共同关注的主题。然而,当前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却普遍存在着理论和方法缺失,重文献和思辨研究,轻实证和定量研究,缺乏规范性和跨学科视野等问题,导致此类研究的教育决策服务能力不足。[1]本文采用比较教育的视野,系统梳理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这一主题,阐述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其研究范畴和理论依据是什么?第二,怎样进行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第三,如何应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来认识和改进中国的教育政策?
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
(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内涵界定
现代政策科学之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首次提出政策研究的内涵,将其界定为:它是一种分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并通过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对特定政策问题提供解释的研究。[2]“二战”后在美国,政策研究逐渐发展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教育政策研究是政策研究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是立足于教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对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的一种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政策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3]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即采用国际视野,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具体的教育政策环境、制定、内容、实施、评价的经验和模式等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旨在发现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教育政策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问题解决效果等方面的异同。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了促进跨国间成功政策经验的交流、理解与借鉴;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弥补本土教育政策的不足,完善国家教育政策体系,服务于国家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二)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基本范畴
在研究领域方面,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各种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在发展历史方面,重视从全球化和跨文化的角度研究当前重大的、热点的、旨在解决迫切教育问题的教育政策;在研究范围方面,涵盖世界各国的和全球性的教育政策相关问题。
从我国现有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来看,多数研究以某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教育政策内容为分析对象,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财政、教育质量等政策,也包括微观层面的招生考试、课程设置、师资配置等相关政策的比较。[4]这些研究都是从探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角度,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政策进行引介或对比分析,涵盖的范畴较为广泛。但它们往往只重点关注政策的内容分析,对政策过程的研究不足;往往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主,对政策现象的深层探究和实证研究不足,使得此类研究实质上成为“对资料的简单而无序的堆积”。[5][6]
拉斯维尔曾提出政策研究具有建构主义蕴涵,即政策研究以其社会背景变迁为依托,强调政策对社会变动和革新的影响与作用。[7]换言之,那些简单停留在政策文本内容层面,未触及政策的社会变迁背景,也未探究政策对变革的贡献度的政策研究,并没有实现政策分析的深层建构主义意蕴。可见,在进行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时,其范畴应向纵深延展,应深入理解特定政策的本土背景。其实从某种意义而言,理解政策及其过程就是理解政策的背景。[8]尤其在当今全球化加剧的情境下,教育政策制定者往往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某种张力平衡。当国家A对国家B的某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要对国家B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教育背景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考察国家A相应背景的相似性、差异性和适宜度,并在应用于国家A的本土时进行必要的、甚至大幅度的调整。
(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理论探析
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政策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政策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比较研究的方法与路径。[9]要对教育政策进行比较,首先就要理解教育政策的理论根源。在此,借鉴马克·贝磊(Mark Bray)[10]书中所提出的两大政策理论:工具理性主义的政策理论(the rational perspective)和冲突理论(the conflict perspective),来探究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
工具理性主义是政策发展与分析的传统框架和模式,强调从技术层面制定和实施政策以达到某个目标。在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领域,这种决策技术理性使得政府依从成本——收益的规则来选择和执行政策,依从实证主义者的立场将政策制定视为一种价值中立的过程,将政策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权力因素简单化,甚至完全规避。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1]基于此提出了理性政策生产理论(rational policy production theory),认为政策决策过程即为依照一些系统的程序从多种对策中选取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对策的过程。这种以价值中立或价值一致为默认前提的理论衍伸出一条线性的政策分析框架与模型:(1)问题确立;(2)政策发展/形成;(3)政策采纳;(4)政策实施;(5)政策评价。[12]这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政策分析框架推崇客观、中立、科学、注重量化的实证主义分析范式,为跨国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提供了逻辑理论前提和操作范型。
然而,简单地将政策分析划分为几个步骤的论断,忽视了每一阶段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利益关系等因素,工具理性主义因而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冲突理论即为其中一种批判的声音。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是由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权利的群体构成的,政策反映的是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间的一种妥协与协商。[13]由于群体间的利益和权力冲突是时刻潜伏在社会秩序中的,而权力的合理性是人为臆断的,这就导致社会总处于冲突推动下的不断变迁之中。在这种变迁中,某一政策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模式,而只会在特定情境中和特定阶段下才产生效力。于是政策被称为权力和利益群体间动态的“游戏规则”。[14]又如史蒂芬·鲍尔(Stephen Ball)[15]所总结的那样:政策永远都不是社会群众一致意志的反映,它从来都不遵循理性的、逻辑的规则,而是利益主体间无休止争斗的结果,最终显现为当权者价值观的意志符号与象征。可见,冲突理论指导下的政策认识论强调政策分析的非实证性、反逻辑性,强调批判理性和阐释主义的价值分析。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鲍尔[16]等人发展了教育政策社会学分析范式,聚焦于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以批判的视角研究教育政策与社会控制、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解释理论、对话理论和批判理论研究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权力与控制张力。这一范式打破了实证主义范式和工具理性—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主导和垄断,弥补了实证主义缺乏对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解释张力的不足,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为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奠定了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方法与程序
(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方法
(1)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从学科本质来看,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既属于教育领域中的比较教育学科,也属于管理领域中的政策科学。由于其研究问题及理论根基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强调跨学科分析,注重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融。拉斯维尔也曾指出,政策研究基于多元学科的知识整合,在不同学科间建立起联系,合成一个聚焦于政策分析的新型的跨学科学术体系。[17]跨学科的特性使得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在比较法的基础上融入多样的方法,并解决方法融合的难题,如定量方法的操作性、定性方法的客观性以及混合方法中定量资料与定性资料的匹配等。[18]研究者们需要超越单纯的方法分类,基于探究问题和变量的需要,将定量测量和定性解释有效结合。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无疑是对上述工具理性主义和冲突理论两大理论的协商与整合,与比较法结合起来,构成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2)基于实证的量化研究方法。拉斯维尔将政策研究称为一种科学,主要是强调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数据的统计分析、模型建构和科学检验等程序的基础上,以确保政策的合理性。[19]据此,政策的比较研究也同样要遵循发展和验证理论、建构模型以及实施政策评估等步骤,以完善和推进政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转化。[20]在这些理念影响下,定量的实证研究在西方教育政策研究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21]而在比较教育领域中,虽然实证主义分析范式提高了比较教育的客观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但由于比较教育学科探究诸多不可量化的、本土依赖的和国际影响的教育因素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强调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历史的背景研究,使得追求工具理性旨趣的实证主义受到一定的局限和约束。[22]因此这种基于量化的实证分析在我国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认为,在进行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时,应尽量避免定量研究占据主导和完全忽视定量研究的两种极端;在进行跨国教育政策的共性和宏观探究时,可以基于大规模官方统计数据,以实证研究的视野寻找教育政策及其背景的共同因子,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特定教育政策的趋同,从而使庞大、复杂的政策体系的比较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为微观的、针对个案的质性洞悉奠定基础。
(3)基于阐释、批判和理解的质性研究方法。持有冲突理论的批判主义政策研究者们一致主张,政策研究的目的是剖析政策过程背后的复杂根源和影响因素,因而质性研究方法是最适宜于政策分析的方法。[23]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政策比较研究者们通过比较来建构理论,认为政策行为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强调通过对教育政策社会背景的分析来理解社会;如果在教育政策的比较中不考虑该国家的特定社会背景,那么这一政策的社会意旨与影响很可能会被误解或歪曲。[24]总之,教育政策在不同的情境下形成差异性的解读,而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即在于在比较和借鉴的过程中深入地、具有批判性地理解和阐释特定政策及其所植根的土壤。具体而言,质性研究基于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个案研究的方法,着重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教育政策及其制度背景所具有的特征,探究其价值取向,并比较不同政策模式的异同。质性研究方法挑战了主导西方政策研究界的实证主义范式霸权(paradigmatic tyranny),[25]弥补了看似精确的数字所缺乏的解释力,增强了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可信度和效度,使其在研究方法上更为多样化。
(二)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程序和步骤
西方学者对广义的公共政策研究程序与步骤提出了多样的主张,具有代表性的如乔治·麦考尔(George McCall)和乔治·韦伯(George Weber)[26]提出的分析模式二步骤:(1)政策内容分析,即对政策的目标、路径选择、意图阐述、行动计划等的分析;(2)政策过程分析,即对政策行为、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评价等的分析。又如查尔斯·沃夫尔(Charles Wolf Jr.)[27]的分析模式五步骤:(1)收集和分析政策依托的数据资料;(2)探索和建立数据变量之间的关系;(3)建构分析模型;(4)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5)检验所选择的方案模型。这些都为教育政策的跨国比较研究实践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参考。
具体到教育政策比较研究领域,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28]提出了教育政策借鉴的四步模型:(1)跨国吸引,即探究一国向目标国家借鉴学习某个教育政策的缘由、驱动力和目标等;(2)制定决策,即分析对目标国家教育政策的理解和借鉴如何转化为本国的教育决策;(3)实施/执行,即回答在决策出台后如何在本国实施以适应当地的现实需求等问题;(4)本土化,即探索借鉴和调整而来的政策对解决本国相关教育问题的影响效果。这一模型为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者提供了一套系统、详细、具有普适性的程序框架。我国学者汪利兵也从研究的选题、专题资料库的建设、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回顾、研究框架的确定、论文的撰写几个程序和步骤,给予了从事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学者们一些建议。[29]
本研究认为,要推动我国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规范化,需要依据比较研究的政策选题的特征与目的及对该政策的认知,来选取具体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继而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程序和步骤,制定框架,确定研究方法,而不必一刀切地照搬某一固定的程序。
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应用原则与规范
要发挥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所应有的改进中国教育政策的应用功能与价值,就必须在研究中遵循一些原则和规范,否则应用就会成为滥用(abuses)——实际上,这种滥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前大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的文献中。[30]
第一,理解我国教育政策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以往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最大诟病,就是光说国外,不了解国内。如果不了解本国的实际与需要,研究就缺乏相关性和现实意义。比较教育研究以往很少受到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31]我国学者应该立足于丰富的本土教育、社会和文化经验来构建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具备本土意识将有助于中国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者辨识本国的真正需要,树立有价值的现实目标和分析框架。
第二,系统分析本国和目标国教育政策的背景。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者在借鉴时应充分理解目标国教育政策生长的土壤特征,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在理解的基础上,研究者应依据本国土壤的特征,选择能够在培育条件适度调整后生存下去的种子;政策环境将决定政策移植的可行性以及移植后的生长力。总之,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者选题时应避免对政策的简单和盲目借鉴,慎重考虑本土化与国际影响力间的张力。
第三,选择国别时应避免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垄断。由于人们通常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政策借鉴垄断局面。[32]然而这种对发达国家教育体制的信赖是近乎“讽刺”的、“极其狭隘”的,[33]因为国家背景的差距使得国家间的教育不完全具有可比性。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者在实践中应祛除国别选择的盲目性,排除固有偏见,树立正确的价值立场,根据本国的政策需求寻找具有相似度和可比性的政策所在国为比较对象,为本国政策的建构和完善提供来源于国际视野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意见。此外,在同一国家内部,不断增大的地区差异性使得之前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较研究正逐步向以地区为单位的研究发展。
第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落实本土化的转型与评估。在对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时,学者们往往以本国的启示和对策作为研究的结论。但这类文献往往是基于理性思辨的自我阐释,缺乏本土化的落实与验证。有价值的政策研究应该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确保理论和实际的紧密联系。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时不能停留在学理性的层面,而应积极参与教育部门的决策咨询,与教育决策者建立合作对话关系,[34]在实践中评估和验证外来政策的本土适应性,并探测该政策对本土教育体系的推进和内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