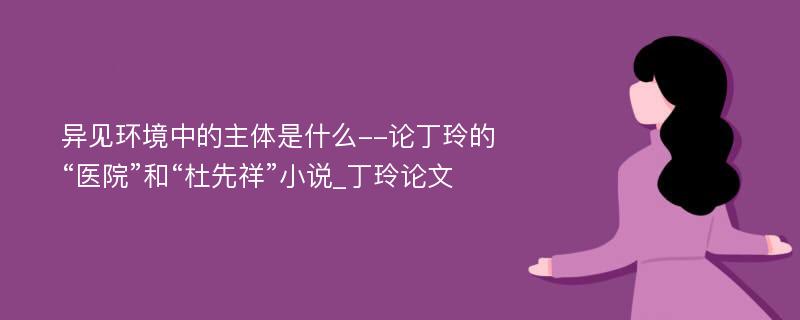
异己的环境中,主体何为——再论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杜晚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己论文,何为论文,主体论文,环境论文,医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在医院中》①陆萍最终离开医院的结局,一般被阐释为“狂人”被“治愈”、知识分子被同化。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失误:一是在文本内涵理解方面存在偏差;二是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偏颇,即把执著于启蒙事业与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两个不完全重合的问题等同起来。丁玲新时期复出后的小说《杜晚香》②,已有研究敏锐指出了其意识形态和性别立场上柔顺化的思想缺憾,但实际上这部作品还存在着以从容坚定的生活态度来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正面价值。本文通过《在医院中》和《杜晚香》的对照阅读,回应以往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丁玲创作执著探问主体内在精神的思想走向。
一、陆萍并没有被环境“治愈”
黄子平的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③和贺桂梅的论文《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④,是新世纪丁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两篇论文都对丁玲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再阐释。两位论者关注的是“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是“作品与其他话语之间的互文性”,是作品在20世纪“‘话语—权力’网络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⑤,因而这两篇论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为支点的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政治现象的深刻洞察上。黄子平的论文着重将丁玲的《在医院中》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互文对照,从而深入探究如下这一组既矛盾对立却也并非没有交互渗透的话语权力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坚持启蒙立场,以文学“疗救”社会;另一方面政治大一统话语却从“社会卫生学”出发对文学进行“疗救”。贺桂梅的论文深受黄子平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和李陀论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复杂角色》⑥的影响,而在如下问题上展示出自己的创见:一是揭示出丁玲启蒙立场与其革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认为“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二是指出了“与王实味、萧军、艾青等从文艺/政治的角度提出独立的要求不同,丁玲是唯一一位从性别角度反对妇女只有等到夺取了政权才能谈个人要求的批评者(拒绝‘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黄子平、贺桂梅论文的长处在于把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放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从而揭示出知识分子主体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篇论文在有效地推进丁玲研究的同时,却也存在这样的缺憾:对《在医院中》结尾的理解存在误读现象。误读必然会造成对文本某些思想内涵的曲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关系评价的准确性,从而导致对文本所敞开的某些重要思想视而不见。
《在医院中》的结尾处,热情敏感的女青年陆萍想改造医院中“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⑦,却陷于困局。这时,“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出现了。他肯定陆萍“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又指出“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建议她“不要急,慢慢来”,并告诫她:“谁都很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很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最终,“没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有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于是“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
这个结局往往被解释为“狂人”被环境“治愈”、知识分子被政治大一统力量同化。黄子平认为,聚焦于其论文所关注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主题,“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⑧。贺桂梅也认为:“……《在医院中》尽管是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但丁玲已经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自我说服。因此,这篇小说就可以作为丁玲心路历程的一个象征性寓言。陆萍离开医院,也可以说是丁玲从心理空间上取消了陆萍所遭遇的问题具有的合法性而予以放弃,以全新的姿态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⑨
确实,结局中,陆萍不再与环境紧张对峙,不再执著于启蒙事业,但是否就非此即彼地被“治愈”了、就“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联系1941年的延安这个作品发表的历史语境,更要追问文本内部的逻辑,还要在理论预设上充分考虑到: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启蒙事业与“狂人”被环境所“治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之外,主体还可能虽从启蒙事业中抽身而出但也并未走向反启蒙。
首先,文本中隐含作者借没有脚的人的话对陆萍所做的教诲,并不是在价值判断上否定陆萍的启蒙立场,而是在认可陆萍启蒙热忱的同时,建议她应该把保存主体力量问题放在首位。这说明隐含作者并未走向反启蒙、并未归顺《讲话》秩序。
完整地解读没有脚的人的话可以看出,他建议陆萍“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并不是批评陆萍专门盯着工农干部的缺点、看不到工农干部的可贵之处,并不是批评知识分子没有工农立场,而是担心陆萍由于只看到环境中异己的因素,便容易受到精神伤害,从而导致自我“被消磨”,而不能“支持下去”。显然,没有脚的人关怀的是陆萍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要被消解的问题。他深知作为主体的人有软弱的一面,因而把保存自我主体性问题置于改造环境问题之上。基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逻辑,他建议陆萍暂时把眼光从环境之黑暗中挪开,而从环境于己有利的因素中汲取精神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了环境具有黑暗性质、否定了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而是在肯定陆萍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同时,关怀启蒙主体的心灵健康问题,关注保存启蒙主体的实力问题。他强调医院中有“伙夫”这类赞成陆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否认院长等人是不负责任的。他说明自己之所以没有脚就是“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更是直接地现身说法批评医院工作的黑暗面、肯定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至于他说:“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并不是认为陆萍对医院现状的批评没有道理,更不是说陆萍不如她的批评对象,而是在认同陆萍立场的前提下认为从现实性上看立即解决陆萍所批评的问题有难度、要“慢慢来”。
“她为他流着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没有脚的人这种“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的状态,不同于陆萍之善感,但亦非是对没有善待自己的外部力量的屈从,而是对自己过去“只想自杀”状态的超越。联系上下文,隐含作者正是通过想象一种超越自身荣枯的人生态度来探索人在严酷环境中精神得以支持下去的路径。
总之,隐含作者借这个没有脚的人之言行探索的是知识分子在暂时无法改造的环境中如何使自己不“被消磨下去”的问题。没有脚的人,并非代表组织来“驱”陆萍心中的“邪”⑩;而是面对组织、大众之“邪”时帮助陆萍暂时把眼光移开、从而避免被这环境中的“邪”耗尽能量。之前,陆萍一直盯着环境中的“邪”,结果陷入精神困顿中。这在没有脚的人看来、在隐含作者看来,自然是一种弱点。但在没有脚的人及隐含作者的评价体系中,有一个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格局中,医院中的领导及其他庸众,是他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陆萍不懂得保存主体性,这一弱点与其理想主义品质相交融,是主体内部有待完善的、虽应该被批评但同时也应该被怜惜的品质。由此看来,作品虽然对医院中的庸众、对陆萍都有批评,但绝不是价值中立,而是如丁玲自己在整风运动中做检讨时所说的:“……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11)尽管在同一篇稿子中丁玲还说过陆萍的原型人物“并不使人喜欢”(12),但丁玲又特意强调过陆萍与原型人物之间的差异:“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13)因此,我们不能将丁玲对原型人物的评价等同于隐含作者对待陆萍的态度,应该充分领会到隐含作者对陆萍赞赏、批评、爱护、期待相交织的心情。
当然,正如黄子平所言,文本中还存在一个作为前提存在的、不必明说的、更大范围的差序格局:包括医院在内的红色根据地(以延安为代表)都是“里面”,不同于根据地之外的“外面”。这是丁玲与《讲话》的共识(14)。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医院中》显然没有认可《讲话》的这一定则:“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15)因为在丁玲此时的思想中,“……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16)。她显然认为“里面”和“外面”虽然有别,但又是相通的,因此,文艺家要用手中的笔,驱除根据地存在的、与旧社会相连结的、落后的异质因素。这正反映了此时丁玲心中“启蒙立场与其革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17)。这种以启蒙为实际内涵、以“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为对象的思想革命,自然与《讲话》之革命概念相抵牾,却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息息相通。与《在医院中》的立场相反,《讲话》要让知识分子自觉消溶到工农大众中、归顺于意识形态组织,从而把个体启蒙内涵从革命概念中清算出去,把革命“正名”为政治大一统。
其次,小说关于陆萍结局的最终设想,虽对环境之严酷性认知不够,却在价值判断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启蒙原则。
小说最后想象卫生部领导理解了陆萍,这自然是一种消解矛盾的臆想。但在这个臆想中,矛盾之所以消解,隐含作者并不是让陆萍洗心革面、改造自我去归顺院长所代表的落后秩序,而是想象卫生部领导具有理解陆萍知识分子立场的精神向度、从而使陆萍得到心灵抚慰。陆萍离开医院“并不是因为自己怯阵而退,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理想,使自己能够‘不消溶’于环境”(18)。这一结局显然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完全不同。在《狂人日记》的隐喻系统中,病愈与发狂完全对立,并不存在相互渗透的可能。狂人“赴某地候补”就意味着完全否定了自己发狂时的启蒙精神状态,而陆萍“被理解”却意味着她的启蒙立场向理解她的人渗透。这里扩张的是启蒙立场,而不是落后秩序。隐含作者与没有脚的人一样,未尝不知道“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与不称职的院长是同类,但仍然执著地希冀陆萍有一种特别的“幸运”而能“被理解”。这一方面固然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执著,即执著地以文学来启蒙革命的领导机构,殷切希望组织中有理解知识分子(至少是不否定知识分子)的力量。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执著期待也是有限度的。隐含作者只是想象卫生部领导理解了陆萍,并没有进一步奢望领导能代替陆萍去实现她未能完成的改造医院的启蒙任务。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有限度的执著期待,显然完全来自于丁玲身上留存的“五四”个性主义思想(19)。它充分说明了写作《在医院中》的隐含作者丁玲并未投入到《讲话》所代表的改造知识分子、归顺工农大众的政治秩序中。小说最后一段:“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直接点明了启蒙主体必须直面艰苦的环境、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这个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主题(20)。这种知识分子本位立场显然与《讲话》的改造知识分子立场南辕北辙。
《在医院中》包含着保存主体性、社会批判等多重主题,但如不忽视小说结局的重要性的话,应该说人在艰苦中保存主体性才是小说的第一主题。
二、主体并非一定要献身于社会启蒙事业
《在医院中》,隐含作者一方面通过想象领导具有理解知识分子的立场来顽强地实践着文学的启蒙任务,另一方面,隐含作者又充分理解陆萍仅仅沉醉在自己被理解的喜悦中而不再追问医院中的种种痼疾。这后一方面的立场就产生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知识分子与社会启蒙事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绝不可割裂的还是亦可分离的?
坚守启蒙原则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坚守启蒙原则与从事社会启蒙事业却并不完全相同。启蒙原则根据康德的定义,就是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1)。这既是呼唤个人克服自身的“懒惰和怯弱”、坚持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独立地思考“一切事情”;更是呼唤社会充分尊重个体“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那么,在严酷的异己环境中,主体应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启蒙原则落实为对启蒙主体这一方面的要求时,包含个体如何对待自我、个体如何对待社会这两个相关联的维度。以启蒙原则对待自我,就意味着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屈服于权威、不从众,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2),坚守自我的主体性;以启蒙原则对待身外的社会,则意味着主体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既抵抗不许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各种强权,也启迪大众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在启蒙主体这个问题上之所以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身份,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由于缺少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由于传统专制文化的遗毒,较容易受到新旧权威的操控、陷入从众的状态中而丧失主体性、从而呈现出“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3)的蒙昧状态。这种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在主体自觉程度上具有差别性的观点,只能视作对具体历史阶段精神现象的总体归纳,而不应该被本质化。应该始终注意把每个知识分子或大众都理解为有着各自存在境遇的具体的人。
启蒙原则中关涉自我与社会两个维度,前者是自我启蒙,是其根本性内涵;后者是启蒙他人,是前者的派生物。判断一个人是否坚守自我主体性,只有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充分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可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至于是否投身具体的社会改造事业则不应作为判断其有无主体性的根据。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抵御外部权威、社会俗见等对生命的驯化,焕发出主体的精神光彩;但由于感应到环境之黑暗,他们也很容易受到伤害而陷入心灵痛苦乃至精神变异中。鲁迅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有“韧”的战斗精神的一位,然而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等著作都深入揭示了鲁迅难以直面自我人生的精神痛苦(24);而且,“韧”本身就意味着不蛮干,就内含着在坚持战斗的同时注意保存自我实力的意思。如果把是否坚守社会启蒙岗位也当作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否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必要条件,那么则很可能由于把社会启蒙事业凌驾于启蒙者之上而使启蒙事业变成压制个体生命的力量,背离启蒙原则自身。人始终是目的性存在而不应仅仅是手段(25)。这在启蒙者与启蒙事业的关系上亦不例外。个人因自己的理性而强大,但也因仅仅凭仗自己的理性、不倚靠其他任何外来权威而脆弱。脆弱是生命的真实。任何启蒙主体都不应被要求是改造社会事业召唤下可以随时出征、永不消溶的钢铁战士。以赛亚·伯林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追问“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26)?他守护的正是人可以不受外部召唤(哪怕是正义事业的召唤)的自由限度。
启蒙主体唯有这一点是不可变易的,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必须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坚守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于社会启蒙事业,他/她从事之固然很好,但他/她亦有为了抚惜自身生命伤痛、为了保存自我力量而悬置之的权利。悬置启蒙事业,并不等同于走向反启蒙。悬置社会启蒙事业,有可能仅仅是主体在严酷的环境中退回内心世界、只是在思想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坚守启蒙立场而已。当然,这种悬置是有底线的,即必须在思想上仍然坚持“运用自己理性”的启蒙原则、在实践上不走到反对启蒙的道路上。王小波笔下“沉默的大多数”(27)即是这类悬置社会启蒙事业而自我主体性仍没有被消溶的人。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自己与小狗小趋相伴情深,“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甚至买一份饭“和小趋分吃”,但因为“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28)。这亦是人在严酷环境中合理的自我保护,并不意味着自我已经认同了大批判的荒谬逻辑、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当然,文本写出这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又产生了批判专制政治的启蒙意义。关怀启蒙主体自身的生命脆弱、重视保存启蒙主体的精神力量,与呼唤个体的人克服自身的“懒惰和怯弱”、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一样,都是启蒙的重要命题。文学作为人学,更不应忽略它。至于之所以强调个体在内心中不可放弃自己的理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可违逆启蒙原则这一底线,并非是把启蒙原则当作外部教条来规约个体生命,而是因为“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独立思考是主体免于被奴役的基本保障、是主体性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
探究启蒙原则、社会启蒙事业、启蒙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西方现代哲学中有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思想中亦有可资借鉴的丰富成果。孔子一方面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态度实践士这一阶层的社会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强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无道则隐”、“舍之则藏”,充分肯定了主体在不同流合污的前提下以放弃社会改造事业的方式来保存自我的合理权利。这正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始终珍视人的价值,在提倡士人弘道使命的同时避免使道异化为压抑人的力量。
《在医院中》,没有脚的人把陆萍从“被消磨下去”的边缘拉回。这一保存启蒙主体性的主题在结尾水到渠成,是因为作品在前面铺写陆萍与环境斗争的历程时已经充分揭示了她坚强与脆弱并存、敏锐与单纯相伴的内心世界。作品并没有把启蒙主体神圣化、抽象化,而是多侧面地刻画出陆萍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的生命丰富性。被炭气熏晕后郑鹏来看她,“陆萍觉得有朋友在身边,更感到软弱,她不住的嘤嘤的哭了起来,她只希望能见到她母亲。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指导员相信谣传而责问她,这“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在书写“陆萍不肯‘消溶’的性格和不肯‘消溶’的斗争”(29)的同时,在把陆萍身上的“‘文学气质’作为正面的、明亮的因素加以强调”(30)的同时,描述出陆萍这种脆弱与冲动兼存的弱质的小女儿心态,《在医院中》展示了抚惜启蒙者自身生命脆弱、关怀启蒙者自身生存状态的写作立场(31)。这样,作品在批判漠然、庸俗、不负责任、不尊重科学的大众习气的同时,也避免了启蒙立场的道统化以及由之所导致的对启蒙者的圣化和对启蒙者自身存在状态的遗忘。
三、《杜晚香》的复杂性
当然,确认丁玲写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根本精神上并不一致,并不意味着丁玲只有经历延安整风之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陡然归顺大一统的革命意识形态。贺桂梅、秦林芳早已指出,丁玲的创作长期存在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启蒙的倾向、坚守个性的倾向;另一种是改造知识分子、归顺革命意识形态的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丁玲创作实际情况的。贺桂梅说,经历延安整风后,对丁玲而言,“事实上旧有的话语并非外在的‘躯壳’可以完全脱去,而深植在主体结构的内部。它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压抑了。从这样的层面,可以解释为什么《讲话》之后的丁玲常常会有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呈现两种相互分裂的自我形象”(32)。秦林芳通过丁玲创作和文学理论主张的细致梳理,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事实上,自从1930年代初思想发生转型之后、在《讲话》发表之前,丁玲心中始终流淌着‘革命’的血液,‘革命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意识,始终都渗透到了其创作中”(33);同时,丁玲“对‘个性意识’仍然有所持守,当‘革命意识’成为其最自觉的显意识时,‘个性思想’这一在丁玲原有思想——创作结构中具有原发意义的思想因素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就造成了其思想——创作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34)。丁玲在不同文本和不同的创作谈中,或偏重于坚守个性立场,或偏重于归顺意识形态,或两种倾向交互并存。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其思想倾向的复杂性,避免以偏概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土改长篇小说,虽有明显贬抑知识分子干部、褒扬农民干部的反智倾向,虽然对土改运动释放人的贪欲作为革命动力这一问题缺少反思,但贺桂梅、严家炎、顾彬、秦林芳等都先后注意到了其“意识形态预设”(35)之外还存在着可贵的独立思考、人文情怀(36),从而体现出21世纪以来丁玲研究深化的特点。实际上,丁玲新时期复出之后的第一篇小说《杜晚香》也同样存在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内涵。下面我将着重探讨小说《杜晚香》中内部话语的多元性问题,并在讨论中回应本论文保存人的主体性的主题。
《杜晚香》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性别立场男权化的价值偏颇。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杜晚香对组织的仰视态度上。参加工作,“她像一个在妈妈面前学步的孩子,走一步,望一步,感到周围都在注视着她,替她使力,鼓舞着她。她不再是一个孤儿……”在大礼堂演讲时,她表态:“我只希望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按党的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种在组织面前自我孩童化、螺丝钉化的思路,彰显的是一种完全归顺意识形态组织、放弃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态度。而小说末尾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代表隐含作者表态说:“她不愧是我们的排头兵,我们一定要向她学习,和她共同前进。”这更与《在医院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完全相悖,体现了隐含作者背离启蒙文化立场的态度。《杜晚香》性别立场男权化的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倾向有时交织在一起。志愿军丈夫回到家中,“晚香知道他是‘同志’,她的心几乎跳出来了。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语言的神圣关系的人。”这里,意识形态立场的同一性成了两性精神共鸣的唯一内容,而现代人的个性、欲望则被摒弃在外。但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这唯一的精神共鸣内涵还是缺失的。“……他同她没有话说,正像她公公她婆婆一样”,可是,她“并没有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她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对此,刘慧英细致地分析杜晚香的心理:她“意识到无爱的痛苦时,她又无法全面否定这种靠传统纽带联结着的生活”,并进一步阐释说:“丁玲此时也全然无心开掘和阐发任何女性意识,因此杜晚香最终把‘怨恨’转向了自己,拼命干工作,一心扑在劳动上,最后成了劳动标兵、共产党员。”(37)秦林芳也犀利批评:“这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正是在这里,杜晚香表现出了非常传统、非常陈旧的男权观念,丁玲对这一观念显然没有进行应有的剖析和批判,倒是以赞赏的口吻表现出对人物的肯定和对这一传统观念的认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柔顺化和性别立场的男权化,表明复出的丁玲确实存在被“治愈”、被驯化的一面,尽管在同一时期的散文《牛棚小品》中又呈现出难以被“消溶”的坚守个性的立场。
但是,在这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和性别立场男权化的倾向外,《杜晚香》文本实际上还存在着多重的价值取向和多元的写作目的。
首先,与表扬意识形态排头兵这一主题并存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张扬女性无论在哪一种环境中都从容坚定的主体精神。杜晚香的人生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解放前,杜晚香的环境是异己的。这些不善的力量并非一般革命文学所设置的地主、恶霸、日本鬼子、国民党等阶级敌人、民族敌人,而是冷酷的继母和挑剔的妯娌。这种非意识形态的人物关系设置,使得小说开头部分疏离了政治主题。这一部分描述中,作品没有深入批判继母与妯娌的人性之恶,没有去探究继母与妯娌之不善的深层文化心理,而是在对之进行简单概述后着重借之表现杜晚香的坚强与从容。这种坚强与从容并非是对压制自我生命力量的对抗,但也并非是对异己力量的逢迎,而是在超越对抗—屈从模式中疏离权力、张扬主体的内在精神。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杜晚香都担负着超重的劳动,但她“也就在劳动里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她并不留意他人的不善,也无所畏惧,只是在劳动的同时“尽情地享受着寥廓的蓝天,和蓝天上飞逝的白云”,只是“安详地从容不迫地担水、烧火,刷锅做饭,喂鸡喂猪”。作品以早春盛开的红杏来象征杜晚香的精神气质,赞叹说:“呵!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以劳动能力、吃苦精神、从容安详的心态来建构女性主体性,作品思考的自然不是如何改造社会的启蒙问题,而是主体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才能“不消溶”的问题。这一精神力量,固然未曾包含启蒙知识分子的敏感气质,而主要来源于底层人的生存意识,却也没有阿Q自我奴化的精神缺憾,同样具有普适性价值。这正提示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生存论视野审视主体的精神建构问题。
对杜晚香解放后生活的描述中,作品建构了个体与组织和谐无缝的关系,从而放弃了《在医院中》那种以个体生命感受反思社会机制的启蒙视角,但是作品并没有让杜晚香的意识形态忠诚立场与自己或他人的个性意识形成交锋,没有设置杜晚香与意识形态敌人的斗争场景,因而作品也就避免了革命成长小说中常常存在的直接批判个性意识或者宣扬阶级仇恨的极“左”倾向。在意识形态忠诚话语下面,作品褒扬的是杜晚香那种无论在何处都“安详自若,从容愉快的神情”,是杜晚香热心帮助别人的“宽大的胸怀”,是杜晚香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无私情怀。这种侧重于个人气质和道德品质的叙述,固然使得杜晚香在思想上缺少了抚惜自我生命的现代个性意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缺少了圆形人物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作品所张扬的女性气质内含着主体的从容,却没有侵凌他人的盛气,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有益建构,而作品所褒扬的普适的道德内涵也消解了意识形态话语中所可能滋生的恶的力量。在知识青年与工农代表杜晚香之间,虽然把杜晚香塑造为前者的榜样,但也只是把一群知识青年塑造成普通人而已,并没有在与杜晚香的对照中贬抑知识分子。因而,作品对杜晚香解放后形象的塑造,固然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种政治态度全然有别于直接批判极“左”思潮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全然不同于为极“左”政治摇旗呐喊的“文革”主流文学。
实际上,作品在借用政治大一统话语和道德话语来确保作品的“正确”倾向时(39),也对政治大一统话语做过不成功的突围。杜晚香做先进人物报告,念别人写的稿,她感到“不安”和“空虚”,因为“讲稿的确写的很好,里面引用的有报纸社论,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有先进人物的经验,可是杜晚香总觉得那些漂亮话不是她自己讲的。而是她在讲别人的话,她好像在骗人”。根据做人“一定要老实”、“应该讲自己的真心话”的原则,她决定“用自己理解的字词,说自己的心里话”。让杜晚香的“真心话”与漂亮、正确的政治大话之间形成直接对立,这闪现出的是隐含作者丁玲一瞬间对政治大话的抵抗意识(40)。然而,在后面杜晚香演讲内容的转述中,作品并没有展示出这种感人的“真心话”有何真正超越政治大话之处。实际上,杜晚香的演讲连对自己童年生活体验的描述也完全政治化了,根本不同于小说前两节的超意识形态叙述。隐含作者在这一件事上突破政治大话的愿望和实际上重陷窠臼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杜晚香》文本价值内涵的多重性、复杂性。
总之,丁玲《杜晚香》的思想内涵是复杂多重的。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性别立场男权化,是其一重价值取向。这体现的是隐含作者对启蒙精神的背离。另一重价值取向是,褒扬女性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熟悉的环境还是陌生的环境——都从容坚强的个性气质。这体现的是隐含作者对女性主体精神的有益建构。
小结:丁玲文学气质中的另一组二元并置结构
如果把杜晚香看作是陆萍形象的发展的话,那么,一方面,对改造社会充满热忱、对组织抱着幻想的陆萍,只有再经过多次的政治风暴,才可能会被规训化成对组织和丈夫都柔顺无锋芒的杜晚香;另一方面,丁玲又何尝不希望敏感、易受伤害的陆萍也拥有杜晚香那从容坚强的心态呢?确实,《在医院中》与《杜晚香》既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又在人物精神气质的期待上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在医院中》结尾所期待的人在“新的荆棘”面前“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的品格,虽绝不是杜晚香的螺丝钉思想,但又何尝不是杜晚香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定从容的气质呢?可以说,对杜晚香安详自若气质的期待早已孕育在丁玲构思《在医院中》时期了。丁玲在谈到《在医院中》时就说过:“……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41)因此,如果把陆萍和杜晚香都看作是丁玲精神自叙传中的人物的话,那么,我们则应该充分考虑到丁玲的精神发展的非线性特点,充分认识到丁玲文学气质中陆萍与杜晚香共时并存的特点。丁玲文学精神中的陆萍维度既是坚守启蒙立场、坚守个性意识的,又是敏感、冲动、脆弱的;丁玲精神气质中的杜晚香维度既有温顺屈从、归顺政治意识形态和男权文化的一维,又有从容坚定、超越权力的压制—对抗机制的一维。这提示我们,丁玲创作除了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个性意识与意识形态服从意识的“二元并置”结构外,还在人的精神气质建构尤其是女性气质建构上也存在着敏感冲动脆弱与从容坚定共存的“二元并置”结构。丁玲既赋予敏感冲动脆弱这种心理特点以现代人的个性魅力乃至于启蒙者的先觉气质,又深切领会到其不利于主体在艰苦的环境中保存自我的弱点;丁玲既赋予从容安详这种心理特点以超越权力机制、保存自我主体性的坚强品格,又使之与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的屈从意识难解难分。这个“二元并置”结构说明,丁玲创作始终眷注于主体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保存自我这一现代人学命题。丁玲在关怀启蒙者的脆弱中显示出其“强己”(42)的人生信念,又在张扬生命坚韧力量时难免陷入精神退缩之中。丁玲的文学魅力首先在于其对主体内在精神的执著探问。
注释:
①丁玲:《在医院中》,原载《谷雨》1941年第11期,收入《丁玲短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9—589页。本文《在医院中》的原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②丁玲:《杜晚香》原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收入《丁玲短篇小说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3—648页。本文《杜晚香》的原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③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⑨(17)(32)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⑤⑧(14)(30)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154页,第159页,第167—168页,第158页。
⑥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复杂角色》,载《今天》1993年第3期。
⑦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的〈在医院中〉》,载《钟山》1981年第1期。
⑩黄子平说:“‘驱邪’仪式适时举行……仪式就是仪式,其过程、目的、功能与后来多次举行的仪式并无不同。”(《“灰阑”中的叙述》,第172页)
(11)(12)(13)(41)丁玲:《关于〈在医院中〉》,写于1942年下半年,参见王增如《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第302页,第305—306页,第302—303页。
(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3页。
(16)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8)秦林芳:《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9)秦林芳曾指出:“‘五四’个性主义传统为知识分子坚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提供了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这无疑为她敢于坚守个性、敢于与‘风雨’(社会文化环境)对峙提供了自信和勇气。”(《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20)王增如在《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中回忆说:“……1982年4月,丁玲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丁玲回答:‘就是小说中的最后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丁玲强调的是该小说保存主体性的主题,而不是社会批判主题(参见《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96—297页)。
(21)(23)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第23页。
(22)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24)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说:“人以及一般而言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不仅仅作为(nicht bloss als)这个或者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手段(Mittel)而实存,而是他的一切无论是针对自己还是针对别人的行动中,必须始终同时被视为目的。”(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26)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27)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载《东方》1996年第4期。
(28)《杨绛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29)王中忱、尚侠:《丁玲文学与生活的道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31)秦林芳曾指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赓续‘五四’个性传统,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特定文化环境的批判,坚守并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33)秦林芳:《丁玲与〈讲话〉的精神关联》,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
(34)秦林芳:《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5)钱理群:《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36)参见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秦林芳《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7)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页。
(38)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载《文教资料》2007年12月号下旬刊。
(39)丁玲丈夫陈明曾向刘慧英介绍说:“在写什么问题上她曾左思右想了很久,最后认定不论将来政局发生什么变化,《杜晚香》这样的主题精神是不会遭到非难的。”(参见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第55页)
(40)李陀将这种大一统政治话语命名为“毛文体”,并对丁玲创作与“毛文体”的复杂关系做了深入的阐释(参见《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复杂角色》)。
(42)丁玲在1942年发表的《“三八节”有感》(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中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标签:丁玲论文; 主体性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