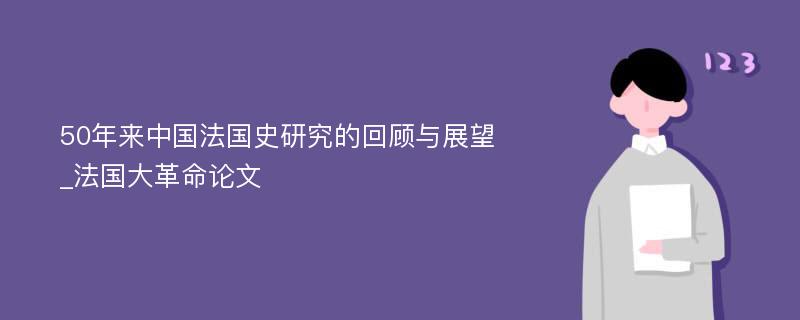
中国法国史研究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最近,我在主编《中国法国史研究信息》一书时,对此进行了详细统计。据统计,解放50年来, 我国共出版有关法国史的著、 译570种,发表论文译文约4000篇。其数量之多大约是解放前50年的30 ~40倍,可见成就之大。
一
如果将上述统计数字作动态分析,更可看出新中国50年来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它明显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入研究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49~1978)。即改革开放前30年,尽管在学术上多次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与冲击,存在着严重的照搬照抄苏联学术观点的现象,但毕竟开始了对法国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0年中总计出版著译97种,发表论文译文417篇。年均著译3种,论文14篇。而且在一些大学里开设了法国史课程,正式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二)发展阶段(1979~1988)。这10年可谓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暖了法国史的研究领域,使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开始独立思考,迈向民族创新之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1979年正式创建了全国性专门研究法国史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使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此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上规模的研究道路,并开始与国际史学接轨。10年中总计出版著译166 种,发表论文1380篇。年均出书16种,超过前30 年5 倍以上。 年均论文138篇,比前30年增长10倍。 改革开放终于带来了我国法国史研究万紫千红的春天。
(三)深入研究阶段(1989~1999)。这最近10年可谓中国法国史深入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或是科研成果的数量,都开创了空前的新局面。10年中硕果累累,共出版著译309种, 年均达30种以上。发表论文2200篇,年均220篇,均远远超过前40年的总和。 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达30多部,基本上都在这10年中出版,这些著作主要有: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郭华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孙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探新》、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侯玉兰的《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吴国庆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法国》、陈崇武的《罗伯斯比尔评传》、李兴耕的《拉法格传》、马胜利的《饶勒斯评传》、罗芃等的《法国文化史》、王家宝的《拿破仑三世》、陈峥嵘的《欧洲之父——查理曼》、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曹特金的《布朗基传》、周荣耀的《戴高乐评传》、周剑卿等的《传奇人物戴高乐》、张锡昌的《密特朗传》、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等等,尤其是一些大部头学术著作也在近10年纷纷面世,据统计50万字以上的专著共有6部, 除一部外(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60.2万字),其余5部均为近1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大出版社, 1989年,53万字;沈炼之主编、楼均信副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56.7万字;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50.4万字;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52万字;张泽乾著《法国文明史》,武大出版社,1997年,77.8万字)。在所有上述著作中,都提出了国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表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在民族创新之路上已经开花结果,正在走向成熟,而且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二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改革开放20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史家明显的研究特色。这些特色择其要者有三:
第一、研究层面大大拓宽。解放后30年,我们基本上局限在政治层面上的研究,而政治层面又根本不去研究政治体制的运作与管理,只集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范围,以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来叙述和研究法国史,一直局限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一传统史学的框架内,因而很难作出客观科学的论述。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者才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从政治层面转而研究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宗教、人口等各个层面,大大拓宽了研究范围,尤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运用政治文化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从而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多次反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反映在政治文化上。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整个社会文化中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这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在各方面,如革命的语言、标语、口号,革命的崇拜物:三色徽、自由树、小红帽,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地名、人名革命化、服装一色化、日用品政治化、私生活公开化,连跳舞也从舞厅移到广场,而且带上政治色彩,作为欢庆的表现。还有谣言,也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谣言,促使革命过程十分激烈,如89年7月14日, 有谣言说国王军队要屠杀人民了,于是激起几十万人上街革命。91年9月初, 又说:“犯人”要造反了,于是成千上万民众冲进监狱,一个晚上就屠杀了上千犯人,制造了“九月屠杀”。说粮食卖光了,于是一夜之间在粮店门口排起长队,顷刻之间出现了“抢购风”。到93年,反对派为了打倒罗伯斯比尔,谣传说罗伯斯比尔是暗藏的保王派,他打算取路易十六之女为妻,而且还在报纸上登出漫画:罗伯斯比尔一手提着人头,一手拿着酒杯,接着人头上落下的滴滴鲜血,准备喝人血,来说明他是杀人魔王、吸血鬼。于是,一个人人崇敬的伟大领袖,一夜之间遭万众唾骂,认为罗伯斯比尔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总之,研究大革命中政治文化的种种表现,不仅可以加深对大革命的理解,而且极有现实意义,值得从方法论上去认真吸取。
第二、创新观点层出不穷。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研究的灵魂,如果没有创新,学术本身就没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发挥学科的战斗作用,更不可能体现历史科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国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仅举法国大革命为例,可见一般。
1.对民主的研究。民主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都不敢也不肯去正视资产阶级的民主,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尤其是在分析《人权宣言》时,只谈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人权宣言》的虚伪性,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似乎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谈论的专利。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解放了思想,发表了诸多论文和著述,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论证了《人权宣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对近世社会的深远影响,同时为无产阶级民主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由过去的一点论到如今的两点论的分析,无疑是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
2.对法国大革命分期的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照搬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国大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即君主立宪派、吉论特派、雅各宾派统治。而且将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的终点。 以王养冲为首的我国学者,通过深层的分析,提出了六个阶段分期法即增加热月与督政府、执政府、帝国三个阶段,将大革命终结的时间延伸到1814年拿破仑帝国失败。这样的分期,不仅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反复的全过程,而且与国际史学接轨。
3.对热月政变性质的研究。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这是前苏联学者的观点,也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传统观点。刘宗绪率先发表论文(《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明确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的新见解。他认为,在当时衡量革命与反革命,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反对封建制度,是否坚持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能以雅各宾派的主张和政策为标准。雅各宾专政超越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范围,热月政变实际上结束了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和过激行为,是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历史呈现出似乎是倒退的现象,其实热月党人坚守资产阶级阵地,这恰恰是历史的正常,它使资产阶级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刘宗绪的这一新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
4.对法国大革命中反革命现象的研究。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以旺代省为中心的几个省的几十万农民参加了武装叛乱,反对革命政府。这一叛乱行为,在我国史界长期以来认定就是反革命。早在80年代,英、法的史学家已经提出异义。在我国,也有学者对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许虹在《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 引用了大量新颖的资料,对广大农民的心态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反对革命不是反革命,农民叛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为什么农民拿起武器反对革命却不是反革命呢?她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守旧保守的农民对大革命推进的政治现代化的不满、抵制和反抗。例如大革命开始后,非基督教化运动引起广大农民教徒对宗教政策的不满;乡镇行政区划的改变,引起农民心里上的不适应和生活上的不方便,对行政政策产生了不满;抽壮丁更引起农民对征兵政策的不满,极度的愤怒使几十万农民既反对贵族又不满新政府,在行为上构成了对政府的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决不是要复辟封建旧制度。所以,农民反对革命决不是反革命。不满政府反对政府,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反革命。这一有说服力的分析,改变了我国多年来公认的旺代农民反对大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简单化结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大大深化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深远的意义,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反革命现象。
5.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我们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有过一些研究,改革开放后,大大拓宽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重新评价。以法国而论,对拉法耶特、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丹东、罗兰夫人,以至拿破仑、塔列朗直到当代人物戴高乐等等,都有新的研究和评价。 其中以对罗伯斯比尔与丹东的评价最为突出。 陈崇武从1979年开始发表多篇重评罗伯斯比尔(《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的论文,对罗伯斯尔比作了独创性的论评,在指出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后期对恐怖扩大化应负的责任。楼均信、张芝联从80年代初开始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对丹东作重新评价的论文,推翻了长期压在丹东头上的“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认为丹东反对恐怖扩大化,提倡分清敌我,实行宽容与人道,是为了维护革命巩固新制度,决非反革命。丹东主张与敌国和谈,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决非通敌叛国。丹东确曾贪财受贿,但不等于出卖祖国,丹东在革命过程中确有过妥协、动摇,但基本上是一位革命家、爱国者。事实上,丹东在关键时刻的种种表现,不失为一位值得称道的革命家。例如,在1792年秋,当大敌压境,政府中的要人纷纷提出把首都迁出巴黎时丹东却力排众议,还将七旬老母从外地接到巴黎,决心全家与巴黎共存亡,并且发表著名的演说:“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号召法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与那些贪生怕死、准备逃离首都巴黎的权贵们形成显明的对照,爱国之心,昭昭天日。后来,当革命派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反对派决定逮捕丹东,有人秘报丹东,劝丹东赶快逃离法国以免一死时,丹东镇定自若,带着轻蔑和忿怒的神情激动地说:“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吗?”表示出至死也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不久,反对派果然逮捕了丹东,并将他送上断头台。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丹东虽一度长嘘短叹,垂头丧气,但当他垮上断头台的一刹那,他又显得十分坚定、沉着和自豪,他觉得自己的死是为祖国、为革命而献身,是有意义的、光荣的,于是高兴地抬起头,对剑子手大声地吼道:“把我的头拿去给人民看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丹东在关键时刻的种种表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卖国贼,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革命家,他无愧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过去我们把丹东说成是“叛徒”、“反革命”,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去生硬地服从某种政治需要,甚至将历史人物任意打扮,不惜篡改史实,这是不可取的。
第三、中法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中法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也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却很少研究。本世纪最初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我国的中法关系史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64年中法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少有人研究,只是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受到重视。据统计,近20年,总计发表论文译文166篇,出版著译约30种, 其中张芝联先后发表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与《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两文,对中法关系和两国文化交流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论述,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尤其是近10年,中法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为加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为我国的四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耿昇多年来翻译了大量著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刚起步,仍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土地,我国至今未见有专著问世,尚需国人努力。
三
以上是50年的回顾,仅选一角,足见半个世纪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进展之快,成就之大,值得我们庆贺和自豪。这完全是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来之不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在21世纪必将更加辉煌。因为第一,形势好。国际国内继续开放的大势和中法交流的加强及自由研讨的学术氛围,为研究法国史提供了根本的保证;第二,我国已有一批研究有素的法国史老专家,为今后的法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主攻的方向,可谓基础实、方向明;第三,有一支由一大批法国史博士、硕士组成的中青年研究骨干队伍,已成为中国法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中已经而且必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之,有好的环境、好的基础、好的队伍,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必将走上新的台阶。
但是,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毕竟基础差、底子薄,法国史更是如此。从国际视野看,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们基本上停留在介绍、翻译的水平上,真正上档次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还不多,比起前苏联和英、美诸国来,有明显不足。比起法国史家来,更有很大差距,存在许多空白。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戴高乐这三个领域。许多断代史,如法国古代中世纪史、复辟王朝史、维希史、第四、第五共和国史至今仍无著作出版。至于社会经济史、农村史、人口史、妇女史、宗教史等等,更少有人问津。任重道远,我们企盼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爱好者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协调下,齐心协力,不懈奋发,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使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真正进入世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