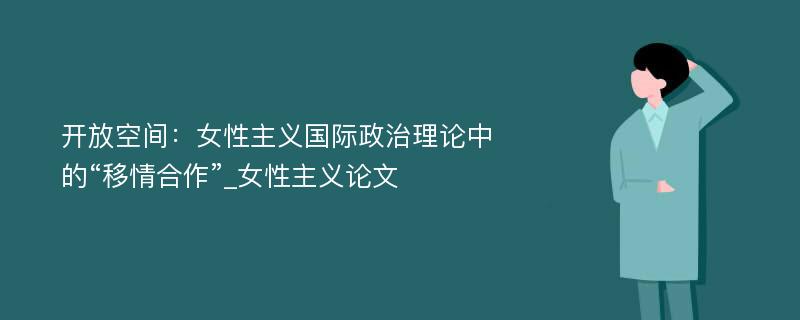
开放的空间——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共情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国际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出现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而兴起的妇女研究向国际政治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因而它的产生与发展明显地反映出后者的种种特点。不迷信男性中心社会中形成的“客观”真理的权威性,同时坚决反对以某一特定阶级、种族、地区的妇女的经历涵盖所有妇女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在批判充斥着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及其理论表现的过程中诞生,在不断反省自身的种种不足和对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中前进是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本质特征。(注:参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序”,第4页。 )它使表达全球各地区、阶级、种族妇女不同利益的各女性主义派别在相互间的争鸣中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共同推动整个妇女研究的不断深化。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其内部的各种流派在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批判该学科主流理论的社会性别(gender)内涵之同时,通过彼此的交流与互补形成用心倾听并尊重来自不同社会集团的妇女发出的多种声音,而不是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奉为神圣、以偏概全的“共情合作”(empathic cooperation)(注: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99.)——一个虽缺乏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开放的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说广泛汲取其内外各种理论派别的优势,渐次达到整体上的完善。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一方面表现为女性主义学说在国际政治学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后者中的一些学派与女性主义立场的结合。因此,它既包括在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派别,也有在国际政治学中的某些理论流派影响下出现的和平主义女性主义、世界体系学派女性主义,等等。其各自的具体认同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如“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能认同反国家的世界共同体,和平主义的女性主义可能认同任何和平运动,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可能认同对现有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的批判与抵制”。(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637页。)通过相互间的争鸣与探讨,它们共同描绘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幅色彩缤纷的图画。
由于材料和篇幅的限制,笔者将集中评介对妇女运动及妇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且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派别。
一 加入“妇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理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妇女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派别。它产生于200多年前的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 其思想脉络源自16、17世纪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 它的基本立场首先可以被表述为一种社会正义的观点,即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遇,而要取得成功则有赖于每一位妇女个人的奋斗。(注: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页。)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将排斥妇女的启蒙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扩大到她们身上,因此,它强烈地反对有关妇女在理性上较男子低劣的传统哲学理念,主张在现存体制的内部积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国际政治学中,它努力揭露妇女在国际关系领域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及寻求使之投身于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途径。莫德·巴娄(Maude Barlow )和山侬·谢林(Shannon Selin )曾披露加拿大乃至全球范围内妇女在军备控制决策方面的空缺:在加拿大,没有一位妇女担任外交部军备控制与裁军处或防务关系处的处长或副处长;迄今为止仅有一名裁军女大使被任命;进入全球约800个与核武器有关的关键性决策岗位的妇女只有5人, 还不到1%。(注: 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4,p.12.)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将上述问题的产生首先归咎于妇女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对外关系事务尤其是外交、安全、战争与和平等“高级政治”的疏离——童年时被鼓励玩枪、摆弄各种军事玩具的是男孩而不是女孩,长此以往,军控和安全便被认为是妇女既无兴趣也不擅长的“男性话题”,在外交决策中也同样如此。贝特西·汤姆(Betsy Thom)指出,联合国系统内的许多妇女不像男性那样满怀雄心壮志,因为社会上对其难以肩负决策重任的期待已被她们化做自己内在的某种信念。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社会上存在阻挠妇女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的制度性障碍,男性权威对她们公然加以歧视,拒绝提拔其担任重要职务,法律也限制了其被录用和接受培训等的机会。另外,她们还必须在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以至在专业上进步有限。为此,这一派女性主义者要求改变家庭中的性别分工,给妇女提供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外交活动的更多机遇, 以便使之广泛进入对外关系的决策领域。 (注:参见"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pp.12~14.)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理论是主张在现存社会制度和它的知识生产体系框架内部谋求男女机会均等的学说,它认同作为西方传统认识论的考察视角之一、具有等级制意义的“男/女”及与之有着内在的隐喻关系的“主体/客体”、“理性/情感”、“文化/自然”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公共/私人”、“战争/和平”、“高级政治/低级政治”、“国际/国内”等二元对立模式,(注:参见吴小英:《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载《妇女研究论丛》杂志1998年第1期,第5页。)并为使自己脱离被贬抑的“女性”范畴、提升到被认做规范与楷模的“男性”档次而竭心尽力。因此,它受到对该制度及其知识体系持否定立场的各女性主义派别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它忽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歧视与压迫妇女的总根源;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批评它只表现了社会上享有特权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希冀从事高声望职业的无病呻吟;激进女性主义则感到它无视令男尊女卑的状况遍布全球各地和各个领域的社会机制——父权制(patriarchy)的作用。(注:参见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第106页、109~111页,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第41页。)随着与其他女性主义派别互动的加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形成了在承认现代科学提供了一条认识妇女活动的可靠途径是发现、宣传、保持其对文明之贡献的有效工具的前提下要求让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加入研究队伍,将更多的社会性别课题纳入其中,以纠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被针对妇女和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男性偏见所歪曲,仅仅反映他们的经历与经验的“坏科学”,真正提高认识的客观性的认识论——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注:参见"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p.31.)在国际政治学中,它对被“价值中立”的国际关系放在首要位置上予以强调的、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国家提出了批评,认为后者充斥着将同国际政治有关的各种联系仅仅局限于外交事务中的头面人物的男性决策者;而即使在人们近距离地考察国际政治的微观领域时,后者也往往被定义为男子或所谓公众人物的政治活动而将妇女拒斥在外,很少有人对诸如德国妇女以手推婴儿车穿越柏林墙的方式促进了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及妇女儿童在战争中饱受暴力侵害等“个人”行为产生兴趣。因而女性主义者必须反复指出:“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非性别化的罗盘绘制国际政治的海图,我们可能以画出一幅仅仅充斥着男性,主要是精英男性的地形图而告终。”(注:Ibid,pp.35~36.)
但是,从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只是对以往拒妇女于科学门外的实证主义世界观的补充而非转变。在国际政治领域,它所要求的只是加入妇女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其对之所作的贡献,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固有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的存在孤立化和抽象化,看不到其生活在一个由阶级、种族、民族等各种社会关系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事实,因而它体现的只能是生活条件优裕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而绝非隶属于其他社会集团的妇女希冀改变所有人的生活现状的愿望。同时,加入“妇女”的原则也是与以排斥她们本人及其相关经验为前提的个人主义相矛盾的,这决定了它对隐含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内涵的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学说批判的程度是有限的。(注:Ibid,pp.39~40,p.42.)
二 男女有别——激进女性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理论
作为一种自我认定的系统理论,激进女性主义是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掀起的产物,其核心是对性别歧视的系统化机制——父权制的揭露。它视对妇女的奴役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认为它不仅限于政治和有酬劳动等公共领域,而且存在于以家庭为代表的个人生活之中:“个人的是政治的”,种族主义、阶级压迫等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其他各种社会机制均与此有关。(注: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第109~111页。)在这里,妇女作为一个被压迫群体与男性相对立,她们迥异于后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被当做其较男子优越的标志加以突出和颂扬。在认识论中,它主张从来自作为边缘人群和“他者”的妇女生活的观点出发观察与分析问题的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standpoint),认为她们的目光不那么片面,也较少受到歪曲,因而更加具有客观性。(注:参见"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pp.42~43.)作为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反映,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以源于妇女特殊的生活经历及价值观念的女性目光对前者中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合作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的重新考量,认为主流学派中的男性学者强调冲突,轻视合作,在他们的思想中,外交政策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维护军事安全成为国家的首选目标,这一切有必要以妇女的生活立场为出发点来进行修正。安·梯克纳(Ann Tickner )曾改写国际政治学著名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 其中权力被与女性的再生产力相联系,“国家利益”被理解为一个多层面的、依照环境而不时改变的概念。(注: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627~628页。)在激进女性主义学者从立场论的角度诠释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真诚善良、对他人的同情与爱抚、爱好和平等作为妇女永恒的天性不断受到赞颂,而被视为侵略成性、嗜权好斗、傲慢偏狭等恶习之体现者的男子则遭到猛烈的抨击。她(他)们接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将妇女更多地纳入国际政治领域的呼吁,但与前者不同的,其认为使之进入核武器和常规军备控制的决策层不是为了纠正由历史造成的妇女在该领域缺席的不公正现象,而是要将她们向往和平的观念带入其中。
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相比,激进女性主义在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批判上取得显著的突破。由其引入的父权制概念从制度化的角度揭示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性别歧视的本质。在对国际政治学主流理论的批判中,它打破了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学者定义的各类基本概念与原则“性别中立”的神话,以此引发人们对传统国际政治学说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但是,它在把妇女看成超历史的存在,无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对她们的建构和重构以及沿袭“男”、“女”之间泾渭分明的两分法等问题上与前一个流派殊途同归。(注:参见"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p.51.)其不仅因抹煞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种族、民族等差异,以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殊经验涵盖全球所有妇女的生活经历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的批判,而且它将男女之间的差异凝固化,甚至盲目地从“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中寻找依据的做法无形中又落入了自己所批判的父权制将男与女、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互割裂和对立,视妇女为情感化、消极被动、富有同情与怜悯之心,而男子为倾向于竞争、具有颇为强烈的侵犯意识、自私自利等的陷阱。(注:参见"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pp.19~20.)而其对通常被打入另册的女性及“女性”价值的赞美和弘扬与对男性及“男性化”观念的贬损也只意味着它在力图推翻旧的两性不平等机制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性别压迫机制,差别仅在于后者将长期盛行的男尊女卑颠倒过来罢了。
三 关注“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理论
在如火如荼的西方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异军突起。它一方面与父权制展开积极的较量,另一方面大力批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以优等文化自居,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国内少数民族和族裔妇女之上的“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等错误立场,以及无视妇女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将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对其所属的特定集团之外的妇女或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的傲慢态度。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是与阶级、民族、种族等其他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但社会性别又有其独立性。(注:刘伯红:《性别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6期,第6页。)这一理论的出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拉开了序幕。
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产生了以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后者的分散化和小型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注: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第123页。 )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对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等因素的关注解构社会性别、父权制等“大一统”概念,强调妇女个体间的千差万别,从根本上反对西方传统认识论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划分,提倡一种整合性的思维模式,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包括种族、民族、阶级、社会性别等)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注:参见李银河:《性别特征与本质主义》,载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第124页。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派别努力消解社会性别化(gendered)的二元论视角——“男/女”及其所象征的“公共/私人”、“安全/和平”、“国际/国内”、“高级政治/低级政治”等“男性范畴/女性范畴”之间的尊卑界限,赋予“女性化”因素与“男性化”因素同等重要的意义;摆脱将某种品质和行为片面归属于某一性别的僵化分类,超越“男/女”二者的优劣之争,建立一个多元的、兼色的色谱体系。杰·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在《女人与战争》(“Women nag War ”)中视战争为一种将社会性别固定在习以为常的角色中的描述,认为通常被用来表现分别处于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流与边缘、扮演主角(军人)和配角(平民)的男子和妇女,压制与之相悖的性别形象及战争故事的“正义战士/美好心灵”的比喻并不能消除两者合而为一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它们所代表的“公共/私人”这两种乍看毫无共同之处的行为典型在一个横断面上的重合:无论是“战士”还是“母亲”都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为未能将事情处理得更加完满而愧疚;他(她)们也同样表现出对伤病、健康、寻求保护等的关注。然而,两者却被人为地加以割裂,妇女议论战争被看做异常,男子则不应谈及“孩子”。为此,爱尔希坦认为,国际政治学应当避免对男女两性的这类“非历史的抽象、缺乏深思熟虑的赞美……道德说教和教条化的阐述”, (注:参见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pp.56~57.)倡导一种超越民族主义思想的“净化了的爱国主义(chastened patriotism)”——无论男子和妇女都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需要,并对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战争危险时刻保持警惕;反对传统上被暴力化的“公民英雄气概”(armed civic virtue),支持以非战斗形式表现勇敢和坚毅的努力。
国际政治学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说具有某种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色彩,它既关注诸如“农村的黑人母亲”(rural—black—mother)之类的妇女的多重身份及其认同的多元化和灵活性,又注意防范对“妇女”概念的任意解构造成其作为认知与行动主体的碎片化。它反对后现代主义有关“妇女”必须抛弃社会性别概念的主张,认为在尚未穷尽它的全部宝藏之前就将之弃而不用会产生这样一种可能,即在真正了解那些被边缘化的认知途径对国际关系的助益与掣肘以前就把它们白白地扔掉了,正中对女性主义学说不屑一顾的男性中心保守主义者之下怀。后现代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共情合作为自己的运作方式:参与到他人的思想与情感之中,并对后者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形成一种极富包容性的理论。它并不把自己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各个流派之间,还包括从建立在男性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主流理论派别中汲取养分。“如对囚徒困境( prisoner dilemmas)的主流描述教会我们,某些情形将比另一些更有利于共情合作的过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使我们懂得,随心所欲的对话存在着把无序当做某种做法的问题”。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把通过“共情合作”改写的国际政治理论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凯美拉(Chimera)——一个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女怪, “混血儿”意识(mestiza consciousnesses)的优势将在它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注:参见"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四 从亦步亦趋到思维方式的变革——结语
对妇女运动及妇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并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派别分别产生于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第二次浪潮和当今的后工业社会,它们分别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由完全以男性为尺度要求与后者平等的各项权利,到开始正视女性特殊的生活经历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价值观念,以及进一步从根本上转变西方经典哲学认识论中与社会性别划分存在着内在隐喻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上述流派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衍化中也明显体现出后者关注面的不断扩大,即由“以男为师”到以妇女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再在充分认识到无论男子和妇女均不具备认识论上的特殊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对传统思想方法的颠覆,促使形成包容妇女的多种声音并吸取传统理论之精华的共情合作。此间新流派的出现并未导致既有派别的销声匿迹,相反,它们在彼此间的争鸣与探索中共存,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呈现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共情合作的格局,形成了包括现象揭露(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主)、社会性别制度批判(以激进女性主义最为典型)、思维方式的革命(后现代女性主义)、创造妇女解放的良好宏观环境(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世界体系学派女性主义等)等在内的多维立体的构架,使之得以在不断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中获得无穷的生命力。
依笔者个人之见,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从对男子的亦步亦趋逐步扩展到反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共情合作”所给予的启示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任何派别,包括女性主义流派,都是从自己擅长的某个角度对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观察与研究,它们中的每一个均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注: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1999年第4期,第7页。)但绝无法涵盖真理的全部内容。因此,它们都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有作为、可能站在各国发展前列的重要国家,尤其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学会外交的技巧和国家间的各种博弈手段(与他国结盟、武力威慑、各处宣传、‘打烟幕弹’等等),更需要了解时代的进步性,敏锐洞察人类发展的前沿,及时消除自身不适合这种进步与发展需求的弊端。……我们不仅要有前一种‘小聪明’,更应具备后一类‘大智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保持二者的平等。”(注:王逸舟:《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1998年第3~4月号,第34页。)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概念引入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这不单单系指对经验层面上的妇女“问题”的探讨,更包括深入挖掘上述二者作为观察与分析事物的一个角度所指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