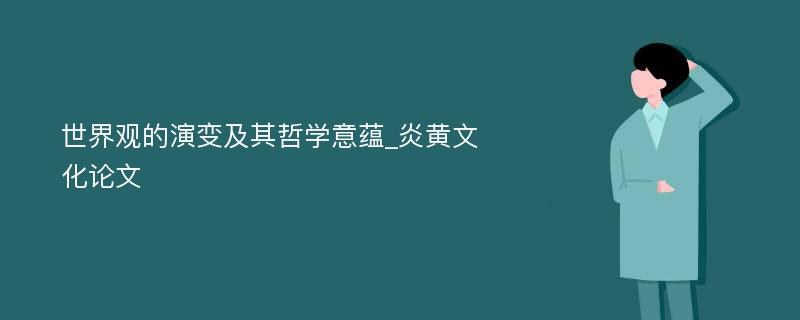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宇宙观论文,意蕴论文,哲学论文,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6-0101-07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早期发展是以华夏诸族为主而形成的部落联盟国家,其地理位置是东至东海,西至昆仑山,北至大漠,南至交趾的“天下”地理世界。这里的“天下”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和历史文化的概念。张光直在论及早期中国文明起源时,认为“‘国家’是有空间界限的政治实体,就好像一个城或一个省份一样。‘国家’的另一个意义,在较高的一层水平,指在政治这个领域之内具有若干特征的一种类型社会。在这个意义下,这个名词是一个没有时空界限的静态的、表现特征的抽象概念。”[1](P25)张光直所强调的是在中国文明的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一个多元共生的酋邦(Chiefdom)或国家,这些酋邦或国家的疆域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时间与空间。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下”是一个大多成员的网络构架,他们之间相互竞争、平行发展、彼此激荡,这是古代中国文明时期国家与国家的对立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必要条件。
1516年以来,意大利人利玛窦等带来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格致等西方文化,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撞开国门之后,中国天下一统惟我独尊的局面就开始改变。在探讨中国近代发生大变局的原因时,以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Levegson)等为代表提出“冲击—回应”模式,而哈佛大学的柯文(Paul Cohen)又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柯文在其《从中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break)并不是源自西方的冲击而是源自中国社会的内部。[2](P47)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首先有必要廓清中国人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是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3](P29),还是魏源《海国图志》中把万国当“四夷”而中国处于世界中心的天下?抑或是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说明的中国只不过是九州之外的九州,占据着四夷空间的其他民族不再是蕞尔蛮邦而是真正的“天下”?
当“天下”的概念受到了“万国”的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受到了挑战。在三千年亘古未有之变局的影响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观、道统都受到了冲击,因为传统儒家都深信,与“天下”相联系的文化和价值是不变的,而和“国家”有关的文化则可以改变。列文森指出:“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在天下之中,没有比中国文化更高的文化形态存在。”[4](P88)的确,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世界即“天下”,“天下”即“中华帝国”。
那么,中国人的“天下”到底有哪些含义?它的宇宙建构和其文化哲学语境到底是什么?它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信仰?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出现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些问题。
一、“天下之赜”的天下到“天下为公”的天下
在远古洪荒的部落时代,人神杂糅,包牺氏作琴,神农作瑟,蚩尤作兵,黄帝做旃冕,仓颉造字。《易·系辞下传》中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5](P318)
在此五次提到的“天下”,除了被当作自然之天或天地万物外的自然空间外,并没有深层的哲学意识。华夏原始社会风尚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这是一个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的时代,正如《礼记·礼运》里所说,在那个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6](P331)。人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和睦相处,俊贤在位。传说中的尧、舜、禹能宰制正义,筚路蓝缕,举贤任能。“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因此,人们有一种意识,即‘天下’不言而喻是应该统一在一起的。”[7](P8)
由此可见,华夏民族的“天下”首先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天下”,尽管不同的民族部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都能和谐相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礼”的早期形式或称卜筮之制已经呈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P318)此时的“天下”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不受外来文化大规模进入造成的破坏的干扰。并且是民主的天下,黄帝、尧、舜都无为而治,实行“垂衣裳而治天下”。《易·系辞》中还多处使用“天下”来表达自然世界中的某些特定事物的全体,如: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5](P308)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表;惟几也,故能成天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5](P318)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5](P318)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明普通人了解世界的观察活动。“天下之赜”就是指天地宇宙和社会的奥秘,“象”就是象征,并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典礼的仪式,而拥有沟通人神、天地权利的人就是早期的巫祝史宗。能够了解“天下之动”,“天下之志”,“天下之务”,“天下之疑”的才配称之为圣人,此时的“天下”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阶段,人们居野穴,与野兽同域,自然不会有人格神或天神的信仰。“天地自然在昼夜运转着、变化着、更新着,人必须采取同步的动态结构,才能达到与整个自然和宇宙相同一,这才是‘与天地参’,即人的身心、社会群体与天地自然的同一,亦即‘天人合一’。”[8](P112)实际上伏羲所作的八卦也是基本的记忆符号,但无疑存在相联系的血缘组织和原始礼仪活动。
从母系天下社会转向父系天下社会后,五服制度体现了五帝时代的平等关系,而“天下为家”体现了三王时代严格的等级对立关系。《礼记·礼运》对三代的公私关系记述最为详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人不独其亲……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大人世及以为礼……是谓小康。”[6](P331-332)
应该说,“天下为公”的社会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乌托邦构想),而是部落联盟(天下)形成时期一夫一妻制的确定,是人类早期原始文明的形式,因而受到儒家的特别推崇。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帝官天下”,“尧舜禅让”等传说理想以外,均为一姓君主,即“家天下”的小康政制。
中国最早的“天下”形式就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它反映了中国先有文明,后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规律,与一般的国家与文明同时出现不同,华夏文明的早熟应归结为中国当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生产方式,即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成早期“天下”(中国)的雏形。特殊的以农耕为主的、以自然作物交换的特殊方式,而构成了“禹稷躬稼而有天下”[9](P301)的小农经济,而其中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延续更是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社会根基。
二、“天下”的道德寓意及其空间延伸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0](P173),到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周代,“天下”的土地生产手段与生产方式都属于“国有”,财富和神的绝对权利归于王者,特别在西周厉王以后,天下王道衰微,“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表饥馑,斩伐四国”[10](P173)。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上帝神与先祖神的授命产生了“天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间有周,昭假于天。保兹天子,生仲山甫。”[10](P198)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天”不但属于贵族,而且属于“烝民”。认为,只要天下人配天受命,敬德保天,就会命如人意。此时的天下已经不是少数人的天下,正如《庄子·天下》所言,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11](P215),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上延长而敬德。同样的,在宗教观念上的天人合一是先祖配上帝的结果。“其实关于‘天人合一’的涵义,不仅仅是指人与自然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人与超自然的神灵合一。中国哲学史上的‘天’,有多重涵义,有宗教神性意义的、权威主宰的、富有人间的‘天’,有作为人与万物的创生源头的‘天’,有道德化的义理之天,有自然之‘天’,有代表偶然性的命运之‘天’等。”[12](P33)“天”由此进入人类社会的话语系统并成为人神同形同性的概念,在很多场合下它代表“天地”、“天下”和“万物”,尽管道家的“道”和佛教的dharma与其有相似性,但与英文中的“heaven”有着范畴概念的不同。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老子在《道德经》中曾51次使用“天下”这个概念,用于指“天”、“帝国”、“芸芸众生”等涵义,尽管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英文翻译可以说称得上是一流的,但对于“天”与“天下”的契合和异同还是没能充分阐释和表述。用英语“world”或“China”都不足以说明“天下”丰富的寓意。在这里限于篇幅,有关“天下”的翻译暂且悬置一旁。
如前所述,在殷商时代“天下”是由不同部落和民族组成的,在古代方十里就可号称“国”,到了夏商七十里就可以号称“大国”,故汤以七十里而起家,终至灭夏。到了殷周之际,方百里就可以号称“大国”,故文王以百里起家,终至灭商而得天下。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方数千里才称得上“大国”。激烈的战争兼并让人们看到了得天下不能靠以暴易暴,而礼、礼仪、礼义成为处理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手段。这种没有维持多久的局面在旧者将忘、新者未生的春秋末世就发生了变化,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2](P354-356)
这是一个礼崩乐坏,世道衰微,天下无道的时代。在道之“将兴”与“将废”之季,一代圣人孔夫子铁肩担道义,为恢复天下的秩序而栖栖遑遑,为确立人内在的道德自律意识而呼喊。这种道德自律是一种系统性、超越性的和批判性的反省,是一种亦道德亦宗教的内在超越。西方哲学家把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印度、中国、以色列在古代文明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突破”,称之为“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把这一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一系列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时代的智者和佛陀;巴勒斯坦则拥有了一批希伯来先知;希腊则产生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的天才。宋儒形象地说过如果苍天不生孔夫子,世界如同万古如斯的黑夜,说明了圣之时,也即是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同时也是天下无道,礼失求诸野的时代。其实,正由于天下无道,诸子百家才抨击政治社会,抗议王侯。如果不能与权势相颃颉,儒家甚至准备为天下道义而献身,这是一种近于宗教信仰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孟子手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13](P557)这是一种以道自任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实质意义上无二,但精勇进取、果敢牺牲的精神却昭然。在这样一个天下纷乱的世道,仁人志士还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P525)焦循《孟子正义》注:“古之人,得志君国,则德泽加于民人。不得志,谓贤者不遭遇也。见立也独其身,以立于世间,不失其操也。是故独善其身。达谓之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13](P525)“天下有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王道政治,而“兼善天下”则包含着为善天下百姓芸芸众生的涵义。从语言层面上讲,“天下”二字不仅有语音上的悦耳还有辞章上的排比美,更体现了一种正义感和家国情怀的道义感。且听孟夫子是怎么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3](P246)
仿佛只有一身正气凛然,有崇高伦理精神境界的人才配说出“天下”二字。这是中华民族人格理想寄托所在!是道德意志灼灼其华的闪现!是高尚人格和品格力量的源泉!是个人之浩然之气与宇宙(天下)相交融的理性主义道德自律!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3](P557),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4](P3),进而到顾亭林的“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5](P471),无不体现这一家国情怀和天下为己任的正气。
三、“道术将为天下裂”与“自我—天下”的异质同构
自周以来天下分为九畿,诸侯分为五等。“事实上有小部分的国家如鲁、晋、卫、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齐、秦、燕、楚、吴、越多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16](P254)周室东迁以后,典籍散佚四方,王官之学散为诸子之学,王室独占的天下文化思想分化为不同的思想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可避免: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11](P216)
庄子心目中的“古之人”指的一定是春秋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圣者王者能“和天下”,福泽百姓,其“天下”的理解可能是以各国诸侯邦国为中心向外延伸的地理位置。《尚书·禹贡》所谓的“禹别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反映了各自疆域和中心的空间。《尚书·禹贡》所说的各五百里的“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所说的“五服”(甸、侯、宾、要、荒),《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说的“九服”(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就是春秋前“天下”的疆域版图,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之外的边缘的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那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帝国的中心(Central Kingdom)。庄子在上述引文中用了五个“天下”,一个“中国”来描述他所悲叹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可以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积极的”(positive)和“消极的”(negative)的观点来比附说明这种局面。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天下大乱、圣贤不一、道德不一、真理崩溃、道德沦丧、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砥砺交锋的辉煌时代。柳诒徵指出:“惟历史事迹,视人之心理为衡。叹为道术分裂,则有退化之观,诩为百家竞兴则有进化之象。故事实不异,而论断可以迥殊;正不必以有春秋之始有专家之术,遂为从前毫无学术可言。”[17](P248)到底怎样评价这一时期这一局面?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见解。余英时认为,“‘破’与‘裂’自然是可以互训的,因此用西方的‘哲学突破’或‘超越的突破’之说来重释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这一历史过程,完全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其中惟一新颖之处即‘突破’蕴涵了一个比较文化史的观点,不限于古代中国一地而已。”[18](P83)。余英时认为,这种突破在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老子的《道德经》中也可以看出,“天下”是人们在春秋战国时频频使用的一个词语,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3](P12),“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3](P7),“奈何以万乘之王,而以身轻天下”[3](P15),“以天下观天下,何以知天下之然哉?”[3](P33)等等共50处之多。可以看出,当时的诸子百家有以“天下”(而不是局部的邦国)为己任的宽阔胸襟,像孟子说的那样“自任以天下重”[13](P387),这一点在具有担当意识的儒家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9](P3)
从天下——国——家——身——心——意,从宏大宇宙到心灵道德的诉求,《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心到国家社会秩序的建构模式,“把过去那种以宇宙天地空间格局为依据建立宗法伦理秩序,以宗族礼法为基础整顿国家秩序的思路,整个地改变了路向,关于国家、民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从由外向内的约束转向了由内向外的自觉,这样,关于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终极依据就从‘宇宙天地’转向了‘心灵性情’”[20](P130)。“诚”(sincerity)不仅代表着一种统一体的客体,还代表着“协同创造”模式中变化中的事件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也即是一种整合(integration)和自我实现,自我推进(诚者自诚,而道自道也)。当代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认为:“在中国的非宇宙论生成传统——儒家以及道家中——这种‘协同创造’的观念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人们熟悉的感悟方式。”[21](P88)著名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 Graham)也认为中国儒家宇宙论的特征是“天下”(宇宙)与人及其他事物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人的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的,没有那些超越的原理被用以说明它们,或者说,没有一种它们出于其中的超越的根源……。这种立场给我的印象极深,其中的新奇之处暴露了西方解释者先入之见,即以为“天”(Heaven,亦可译为“天下”,笔者按)和“道”这种概念必定有我们自己的终极原理的超越性;我们很难理解这种看法:即使是道也是与人相互依赖的。[22](P241)
这种由内向外的自觉路径包含有宗教性的超越情感,它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信仰和“极高明道中庸,即出世而入世”[23](P12)的精神。“中国人文主义要求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使天、地、人各安其位,因此能容纳天地万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国人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24](P153)儒家“道不远人”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哲学反对形上与形下的割裂与分离,而总是小心翼翼地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25](P582)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对天下、世界、宇宙、历史、人生的平实、理性的态度。
四、从“天下”到“万国”到“民族—国家”的终结
如果说三代时期的“天下”是以自然村落为主、以血缘纽带形成的邦城,春秋战国的“天下”是京畿千里、诸子纷争的邦国,秦汉大一统的“天下”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宋明时期的“天下”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国家,那么当异族用坚船利炮叩响神州赤县的大门的时候,此时的“天下”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来,自董仲舒在汉代提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26](P797)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秩序一直处于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中,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天地与阴阳相配,天尊地卑,华夏与四夷相对,尊王攘夷。古代中国是这种政治权威、宗教权威与文化权威合一的普遍王权统治之下的“天下”。董仲舒把“尊君卑臣”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社会关系方面,于是就产生了著名的《春秋繁露》《基义》篇的“三纲”之说。《韩非子》《忠孝》篇也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27](P358)
从这一点看来,儒法两家在怎样建立天下的绝对秩序方面有殊途同归之处。中国传统的政统、道统和学统在以“天下”为中心的宇宙观映衬下从来就没有遭遇过异族有力的挑战。1584年绘成的世界地图中有经纬度数,根据欧洲制图学者的绘图,中央经线将全球分为东西两半,而中国被推至一隅,利玛窦认识到如果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将是十分危险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角方圆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为了维护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势,利玛窦巧妙地作了变通,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28](P5)的思想已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群体潜意识之中。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宗主国观念,而无列国并立的主权观念。然而,正是19世纪中西的强烈碰撞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格局的理解。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中,“国”字已经与“夷”共存,而且是代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国”字。
在此之前,以“华夏中心主义”为主的中国,历来用“夷”字或同义词冠称中原天下以外的四夷部落。《春秋左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9](P15)从天下——夷——国——万国名称的使用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天下”宇宙观和时空观念。“华夷”、“海内”、“万国”、“世界”的改变不仅仅是古代中国人“天下”地理范围和地图大小的改变,而且改变的是中国人思想中的有关“天下”的定势思维:“四夷”从偏安一隅的藩国到平起平坐的国家,而中国从君临“天下”缩小到万国中的一国。“天下”的中心权威已经日落西山,而四海之内的国家正在边缘崛起,中心正在逐渐削弱、消解。
事实上,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黄宗羲对封建主义“家天下”的思想曾进行过批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到底谁为主?谁为客?黄宗羲认为在上古时代,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在封建主义专制下,这种关系被颠倒了,君主为了一人之私利可以荼毒天下,离散天下。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立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三代以下之法,只是为君主自己而立的,因此,他呼吁废除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30](P315)
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看来,“天下”不止是一个地域观念,而是一种文化认同。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爰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5](P471)
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他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意思说保卫“天下”,即整个国家民族,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事情。后来被人们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观。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时期,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岁月,顾氏在孜孜不倦地探究治国平天下之道,矢志不渝地探求救国和富国之策。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主张,是要摆脱君主一人私天下的特权,简政便民,开发资源,振兴国力。虽然顾炎武提倡的郡县守令世袭制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毫无现实性。尽管如此,顾炎武在民族危亡时期所有的“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胸襟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确实起到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用。
相比较,英文中的Nation(民族国家)一词是西方几百年来文化哲学和民族学的一个概念,它蕴涵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和语言以及独立的主权观。“非我族类”在早期含有区别血缘氏族部落的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概念指涉面已跨出了华夏天下观的大门,指中国以外的诸国。从这一点来看,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是在“四夷”的比照下逐渐显现的。从中国人不假思索地使用“天下”、“海内”、“四夷”等观念到“万国”、“国家”的使用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对中国民族的认同。至此,“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其观念已深深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既然“天下”已经变成了“民族—国家”,那么数千年来的道统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曾富有洞见地说:“儒教是中国的特有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他们(指康有为等人,笔者按)经常引用犹太人的历史来鼓舞中国,引用墨西哥人的历史来警告中国;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但他们仍能生存下来,而墨西哥人则因西班牙化和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正日益失去活力,成为其他民族的模仿品。”[4](P163)列文森在这里所关心的是儒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功能是否能继续延续,抑或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作为地理范围的“天下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但是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对传统的认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历史也只有在新旧交织中绵延、更新。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与其他民族的交流、碰撞、融合,已终于铸成了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的伟大文化体系。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3](P56)的周文化的扩散性,春秋时期南方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的逐渐融合,从佛土东来的佛教文化到近代的欧罗巴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不但不具有排他性,而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和统摄了这些文化,所有这一切像涓涓溪流汇进大海,为华夏文化的“天下”观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广博的内涵,充分显示了华夏文化体系的坚韧性、内聚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有道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又有民胞物与的家国情怀,这是值得我们正视、批判、反省所在,也是值得我们为之自豪和欣慰之处。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新的“天下”观),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融会中西文化之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收稿日期:2004-04-23
